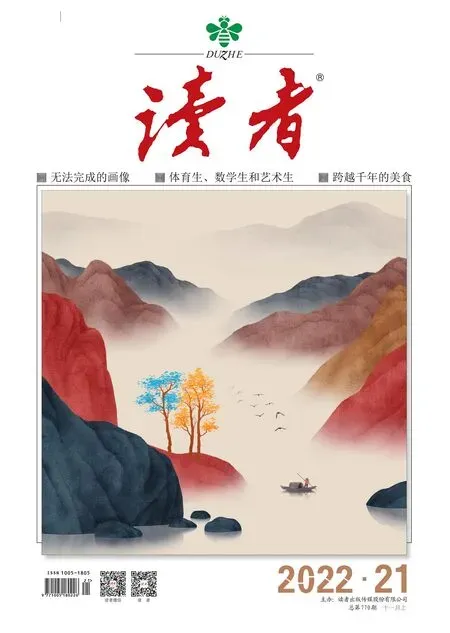母親的食物
☉趙 瑜

母親曾經在海口生活數月,不論我請她吃海南的何種食物,她都是拒絕的,本能地覺得不好吃。
這不是母親的錯,她的飲食習慣是個人生活多年所形成的一種文化的自覺。而這種自覺,是她的舒適區,是她多年人生妥協的結果。她喜歡吃的每一種食物,都有一個遠大于食物本身的故事。
母親所做的食物,大都和時間、力氣有關。母親幾乎是一個村莊的代表,我記憶中的村莊里,有數不清的平原上的炊煙,屬于母親的空間極小——院落、田野、菜地。這空間寬闊又狹窄,方圓幾里地盛放了母親的半生。
在舊年月里,一個村莊,就足以安放一個人的一生。母親在40歲之前幾乎沒有離開過我出生的村莊。所以,一說起母親,我就會想到我出生的院子、村莊,以及村莊外屬于我們家的幾塊麥田。這些勞作和生活的場景,就是母親日常生活的全部內容。
母親煮的粥,是我出生的那個村莊所有女性煮的粥的味道。母親做的饅頭,是我們村莊里所有麥子的味道。不能簡單地用“好吃”一詞來形容母親所做的食物。我18歲出門,之后的30年,吃過全國各地的面食,卻很少能吃到母親做的手搟面的味道。母親的食物,與其說好吃,不如說是母親在一碗面里,傳遞了愛。這既是哲學的,也是屬于內心的。
一個人最初的胃部記憶十分繁雜,很難準確梳理。年紀尚幼時我就知道,村子里許多孩子的母親做的食物比我母親做的食物好吃。我的母親不會做很多花樣翻新的菜肴。然而,母親做的蒸饃,對我來說,是最初的食物啟蒙。
從種麥子開始,一直到麥子收割,母親全程參與了麥子的生長過程。她珍惜每一粒麥子,面粉打出來以后,她會用一種規格極細的篩子再次對面粉進行細篩。這樣,粗的面粉被做成一種饃饃,供父母和我們兄妹吃;而細篩子篩過的白面做成的饃,是專門給爺爺吃的。
食物的匱乏,讓面粉也有了身份的差異。那時的鄉村,強調長幼有序,尊老的人才會獲得大家的認可。所以,母親的做法為她掙得了不錯的名聲。隨著年齡的增長,麥子不再緊缺,我們這些小孩子漸漸也能吃到專門給爺爺做的細面饅頭了。以后的時間里,只要吃到饅頭,我都會將母親手工做的饅頭作為參照。母親做的饅頭,成為一個地址、一個標簽。
母親的食物是眾多顏色中最清晰的白色,饅頭的白、面條的白及米粥的白。母親的食物,是眾多河流中最寬闊的那條,是一年四季中最為舒適的秋天,是秋天的樹葉落在地上后的沉醉,是我不論走多遠都洗不掉的黃河的底色。母親的食物,其實更像關于愛的碑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味蕾上,是魏碑,是漢隸,也有可能是酒醉后的一紙行草,不論我離家鄉有多遠,都能在瞬間接到食物的信息。
作為一個中年人,在外面漂泊多年,飲食習慣早已經改變。然而,母親的食物對我來說依然有效。很難解釋,人的身體記憶為何如此固執。如果說母親的食物是一種文化的鋪墊,那么,在我們的一生中,總有一天,我們所接受的食物將超出母親的食物范圍。然而,食物的記憶卻會打破身份的限制,我們對母親的接受,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包含著食物味道的捆綁。吃到母親的食物的那一瞬間,我們被時光遣返,回到多年以前,變得柔軟而單純,成為一個陳舊的自己。
母親,有多么具體,便有多么抽象。在城市生活多年,大多數時候,我已經成為一個說普通話的人。然而,一旦回到縣城,回到母親的生活圈子,我就立即又開始使用方言。那些字詞,像一道道食物,既養育了我,又溫暖了我。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可以用簡單的好與壞來進行評論,而唯有與母親相關的東西,比如母親的食物,我們無法評價。它是我成為我自己的一個起點,沒有這個起點,我將成為另外的人。
母親的食物,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比喻,它和溫飽有關,和愛相關。實際上,它大于文化,也大于審美。母親的食物是一種植物,時光越長,長勢越好。中年以后的我,自然而然地開始喜歡樸素簡單的東西。而這樣的喜歡,和母親的食物是多么一致。
原來,人生就是這樣循環守恒。疏遠和回歸,需要時間,需要距離,我們離開故鄉,是為了確認自己已經不再單一。當我們足夠豐富時,最初的、簡單的食物卻又漸次清晰。
離開才能豐富,豐富才能回歸,回歸才會簡單。人是如此,食物也是如此,故鄉呢,還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