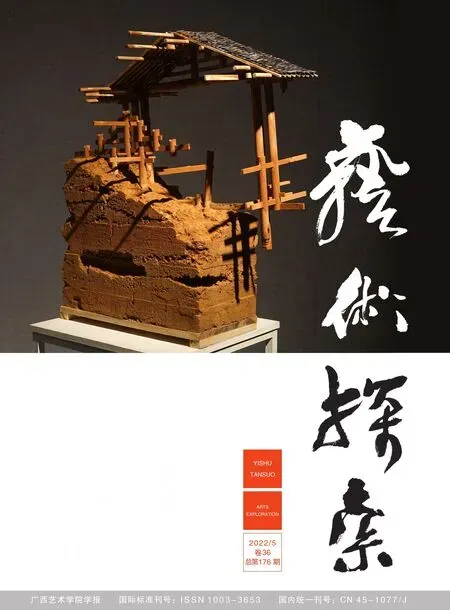異化消費語境下中國生態影視創作中的修辭實踐
牛光夏 成亞生
(1,2.山東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目前學界尚無對“生態影視”這一概念的系統梳理,更多是對“生態電影”(ecocinema)的研究。徐兆壽指出,生態電影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但始終依附于恐怖電影、科幻電影、好萊塢電影下存在,生態意識和題材沒有顯現”。直至2004年,斯科特·麥克唐納(Scott MacDonald)在《走向生態電影》中明確提出“生態電影”的概念。他認為,生態電影的根本作用是“對認知進行再訓練,為傳統媒體受眾提供一種新的認知方式(媒介)……創造了一個伊甸園,能讓人暫時擺脫現代生活——被比擬為一臺機器的現代生活中孕育的傳統消費主義。”從方法論上來說,魯曉鵬等將“生態電影”界定為“在美學上強調用長鏡頭、低電影剪接速度,內容上批判消費主義,具有生態意識,探討人類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土地、自然和動物,以非人類中心觀點看待世界,以向觀眾展示一個新自然世界為主的電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涌現出一批質量精良且具有生態意識的影視作品,有《大氣層消失》(1990 年)、《嘎達梅林》(2002 年)、《可可西里》(2004 年)、《天狗》(2006 年)、《狼圖騰》(2015 年)、《美人魚》(2016年)等生態電影;有《沙與海》(1990年)、《平衡》(2000年)、《森林之歌》(2007年)、《水問》(2008年)、《悲兮魔獸》(2015年)、《美麗中國》(2018年)、《無去來處》(2021年)等生態題材紀錄片。此外,國內還涌現了一批以生態環保為主題的電視節目,如《人與自然》《綠色空間》《綠水青山看中國》等。這些影視創作在充分展現中國歷史傳統、風土人情及地域文化的基礎之上,逐漸擺脫精英式的“自說自話”、強制性灌輸,以大眾化、溫情化等觀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方式來強化觀眾對生態保護價值觀念的認同與尊崇。由此,筆者將“生態影視”定義為:以“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為理論支撐,以批判異化消費主義和過度工業化為目的,運用視聽語言進行生態形象刻畫、生態危機預警、生態理念傳達,展現和審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包括電影、電視劇、紀錄片及電視節目在內的影視藝術形式。
本文擬從消費主義語境下環境傳播的修辭實踐入手,探討在當前消費多元化、異質化、符號化背景下,我國生態影視創作中的修辭實踐。
一、消費主義語境下的環境傳播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中宣稱人類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建立在工業文明和技術神話基礎之上、以不確定性為主要特征的風險文化已經滲透到各個社會領域,引發了諸多“潛在副作用”(latent side effects)。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科學技術不斷迭代更新,人類對地球資源過度開發,消費取向日漸異化,溫室效應,能源危機,沙漠化、海嘯、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現即是明證。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刻不容緩。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在21世紀后陸續提出“科學發展觀”“美麗中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生態理念。人類正在邁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明時代。進行環境傳播是包括生態影視在內的媒介義不容辭的責任。“環境傳播”這一術語最早由克萊·A.舍恩菲爾德(Clay A.Schoenfeld)在《環境傳播的興起》(1972年)中提出。對其進行明確定義且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是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著作《假如自然不沉默: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他指出:“環境傳播是我們理解自然,以及理解我們與自然界的關系的實用性工具和建構性工具。它是象征性媒介,我們用它建構環境問題,并用它與社會中對環境問題的不同看法進行協商”。
環境傳播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是實用性的,即通過一系列環保主題的文字、圖像和視頻來警示和說服人們致力于解決環境議題;一是建構性的,即借助特定的敘述方式和權利話語,在自然環境議題的框架內建構人們特定的生態價值觀。在具體實施上,修辭實踐成為生態影視進行環境傳播與意義縫合的重要手段,通過勸服性話語(persuasive discourse)喚起受眾被技術理性和消費主義不斷消磨與吞噬的生態意識。可以說,從內容題材的選擇和實地考察,到拍攝和剪輯過程中人物、情節的取舍,再到播放后對環境議題的引導和生態環保事業的促進,修辭實踐始終是創作者的重要工具,貫穿于生態影視從創作到傳播的全部過程。
農耕文明時代,生產力水平的落后和人類思想的未開化使當時的森林、水源、動物等自然物均被賦予某種神秘色彩。18世紀以后,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科技突飛猛進,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強。“人為自然立法”“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萬物的尺度”等帶有偏激意味的說法把自然作為一種附著于人類的僅具備資源價值和應用屬性的元素。人類一度以自然的主宰者自居,過度攫取自然資源。消費取向的物質化與消費行為的異化,是指人們對商品背后的象征意義與符號價值趨之若鶩,正如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言:“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當做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用來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作為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的參照來擺脫本團體”。
20世紀以來,人口的過度增長和資本的急速擴張導致生態危機不斷出現,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與生態問題的嚴重性,并在實踐、理論等各個層面積極尋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持續發展之道。從生態整體性來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緊密聯系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基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戲說”的生態美學。他指出:“人在天地神人‘四方’中只是平等的一員,與其他三方一樣承擔著映射它(原文如此)者并映射自身的任務,看不出有什么特殊性,而是四方統一構成‘四重整體’,須臾難離。”這一標志著“人類中心主義”向“整體生態觀”轉型的帶有啟示性的理念,與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沙鄉年鑒》中提及的“共同體”之說相呼應。利奧波德認為,整個生態系統就是一個“生物區系金字塔”,是一個由各個相互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共同體”,組成部分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等。20世紀后半葉,生態影視由于具有視聽形象逼真、內容通俗易懂、傳播覆蓋面廣等特性,日漸成為彰顯生態人文主義和生態整體觀的重要載體。生態影視通過對水源、土地、森林、動物等特定生態意象的刻畫與展示,以及對這些修辭符號背后深層意義的揭示,來向觀眾傳遞“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綠色消費”(green consumption)等生態環保理念。
二、生態意象對人類生存困境的展示
在生態影視創作中,水、土地、野生動物等能指符號原本只是自然物,而一旦與生態環境保護掛鉤,其所指意義就被賦予了一定的象征性和勸服性,繼而成為特定的修辭意象(rhetorical image),以某種具隱喻性、警示性、啟發性的修辭方式來激活公眾對生態環保理念的感知與認同。水與國家、社會的發展及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水這一議題有關的電影在中國并不少見,如涉及水污染問題的《老井》(1986年)、《現代豪俠傳》(1993年),關乎水資源匱乏的《綠水》(2010年),人們因水而被迫離開家園的《巫山云雨》(1996年)、《三峽好人》(2006年)、《秉愛》(2007年),等等。這些電影的情節敘事、人物關系等均與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從修辭功效的角度講,運用更為通俗易懂的意象來使人們認知和體驗當下情境是修辭實踐中最有意義且具說服力的做法。生態影視中的水這一意象背后所聯結的是現存的各種環境問題——污水亂排、垃圾遍布、綠藻叢生。央視于2008年播出的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系列紀錄片《水問》,從危機、飲水、生態、利用、分配、治理、節水、文明等八個方面來呈現有關水的問題。影片聚焦于缺水地區的人們,在展示他們真實生活狀況的同時,披露了令人觸目驚心的水污染調查結果,進而呼吁在人與水和諧相處中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以2007年太湖水危機為背景的電影《河長》(2011年),圍繞一場危及城市數百萬人口飲水安全的藍藻事件展開,自封為“河長”的張清水想方設法制止身為化工廠董事長的兒子張秋江的非法排污行為。影片體現了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在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抵牾中,走科學發展與生態文明之路的決心和行動,也對部分個人或集體因利益而損害自然資源的“竭澤而漁”式做法進行了深刻批判。
與“水”的修辭作用相似,被稱為“地球原住民”的野生動物也是生態影視經常使用的重要意象。這些野生動物“原本只需考慮食物水源、天敵動物等因素以不致招致死亡,但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日漸擴大和現代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由鋼筋水泥構筑的城市高樓正不斷侵占著動物的生活家園,而違法捕獵、誘殺等,使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瀕臨滅絕”。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對動物的馴化、剝削和暴政基礎之上的。山東衛視于2018年播出的節目《美麗中國》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話題,節目展示了藏羚羊、江豚、大鴇等動物遭到人類肆意捕獵時的真實影像,直擊觀眾內心,呼吁人們自覺投入環保實踐。此外,陸川導演的《可可西里》(2004年)通過藏羚羊這一西藏地區特有物種的生存境遇來表征青藏高原生態鏈的斷裂和失衡;運用紀實性手法攝制而成的我國首部以鳥類為拍攝對象的劇情影片《天賜》(2010年),通過記錄黃渤海交界處某個海島上一只黑尾鷗的艱難成長歷程來喻示生命的平等與可貴;由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掌鏡的中法合拍片《狼圖騰》(2015年)亦將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理念寄寓在狼這一意象上。以上影視作品皆通過野生動物的符碼來傳達萬物平等的觀念。
三、搭建環保話語框架,接合批判性意義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中指出,“框架”(frame)是一種“解釋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能夠幫助人們“定位、感知、識別和標記各種具體事件”,也可以借助某種兼具多義性、主觀性及建構性的話語修辭策略,來影響人們對現實事物的看法或取向。在不同框架體系中,修辭實踐的表意系統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與流動性,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促使生態影視的創作者根據所持的話語立場與認知框架來賦予影視主體以不同的含義,進而在話語修辭場域中開展合法性意義爭奪。他們所依據的生態理論和思潮,如環境正義、綠色消費主義、深層生態學、生態浪漫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全球生態主義等,雖各有側重點,但都旨在以殊途同歸的生態理念和環保意識來挑戰并批判現代社會過度工業化的正當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一個環境優美、萬物和諧公共空間的設想。
在話語修辭場域的框架搭建中,其符號能指與所指意義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漂浮的、移動的狀態,在不同文化語境、認知系統和地緣空間中,同一個符號具有不同的所指。這就需要通過“接合”(articulation)實踐來尋找并建立符號與意義之間的對應性和關聯性,將符號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按照特定的意義網絡進行配對與連接,進而創造出全新的符號意義。生態影視創作的出發點和首要職責就是在由生態整體觀構筑的環保框架中,通過批判性意義接合的修辭方式來揭示當前環境狀況及其成因,如由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所導致的工業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由人口基數龐大所導致的資源開發過度及部分地區貧困問題,由公民環保意識不足而引發的亂拋亂丟等。
由于具有真實性、客觀性、在場性等特征與關注社會現實、傳遞時代呼聲的價值訴求,被譽為“人類生存之鏡”的紀錄片在呈現生態環境狀況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直觀展示生態環境遭到人為破壞和惡化時,更能引發人們的共鳴。在榮獲2016年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IDFA)新人單元大獎的生態紀錄片《塑料王國》(2014年)中,獨立紀錄片導演王久良通過展現廢棄的英文時尚雜志、標有英文字樣的生活垃圾、電視機中播放的外國節目等修辭意象,將塑料這一“人類世”(Anthropocene)產物與目前全球化語境下中西發展差距而導致的垃圾出口現象相關聯。相較于戰爭、炮火帶來的直接傷害,境外輸入的塑料等不可降解物質是毒害幾代人生態環境的 “慢暴力”(slow violence),這是“一種隱形的慢性暴力,是一種通常不被視為暴力的消耗性暴力”。
在生態框架的意義接合實踐上,青年導演趙亮以更具實驗性、先鋒性的創作方式來隱喻人類的過度索取與生態文明的岌岌可危。以核污染為主題的《無去來處》(2021年)中,趙亮將觀照視野放至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日本廣島等世界范圍內受核污染的地區,以極具未來感的紀錄風格與景物肖像式的鏡頭語言,展現了核爆炸后貧瘠荒蕪的土地及面目全非的當地人民等令人觸目驚心的景象。片中將帶著詭異微笑的日本藝妓面具、由真人扮演但化著慘白妝容的日式人偶與核武器爆破時的駭人場景相接合,以一種戲仿的修辭手法來標示核武器的使用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危害。
由此可見,在消費主義異化的后工業時代,被人們普遍共享和認同的話語范式就是“工業主義話語”(discourse of industrialism),其基本特征是“維系一切社會關系再生產的秩序與理性都必須服從于經濟增長和物質進步這個最基本的生產邏輯”。而生態影視創作的價值就體現在借助環保框架和批判性意義來構建一種“對抗性話語”(insurgents discourse)或“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通過這樣的修辭策略來宣傳生態整體觀,挑戰工業主義極度迷戀的“技術決定論”與“物質神話論”,以調和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與日俱增的矛盾。《沙與海》(1990年)、《家在向海》(1991年)、《藏北人家》(1991年)、《最后的山神》(1992年)、《茅巖河船夫》(1993年)、《龍脊》(1994年)、《神鹿啊,我們的神鹿》(1996年)、《遠去的村莊》(1996年)、《山里的日子》(2000年)、《可可西里》(2004年)、《美人魚》(2016年)等國產生態影視作品均以一種或協商或對抗的話語實踐,來重新審視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生態文明的生存處境與前景,并嘗試對占據主導性位置的工業主義話語進行勸服、調和乃至抗議、批判。其中,由導演孫增田創作完成的《最后的山神》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皆將鏡頭聚焦于在時代洪流中日趨凋敝的少數民族文化生態問題,不論是最后一個鄂倫春族薩滿孟金福,還是不能適應城市生活的鄂溫克族女畫家柳芭,在無法改變現代工業文明入侵和沖擊的情況下,都選擇歸隱山林或回歸家鄉,堅守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園。周星馳《美人魚》中,富豪劉軒企圖利用裝置驅逐海洋生物以實施填海工程,在與美人魚姍姍的相處中,他的意識發生了轉變。該片將維護海洋生態的環保理念融于導演一貫無厘頭的喜劇影像風格之中,以通俗化的敘事方式批判了人類的過度商業開發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
結語
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等國際環保組織共同制定了《世界環境保護戰略》(),開篇即發出警世之言:“我們并不是從我們的父母那里繼承了地球,而是從我們的兒孫那里借用了地球。”當下高價消費、符號消費、炫耀性消費等消費異化行為大行其道,消費結構的失衡、消費心理的扭曲導致生態系統遭受肆意破壞,野生物種遭到大量獵捕。人類只顧眼前利益的舍本逐末式做法,勢必會帶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大眾媒介應當行使好“哨兵”和“雷達”的角色,充分發揮環境監測、社會守望和生態教育功能,通過對環境議程設置與公共風險信息傳遞來進行“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強化公眾的環保認知,使公眾形成生態風險倫理與責任意識。而作為視覺文化時代重要媒介形式之一的生態影視,主要通過對水源、森林、土地、野生動物等生態意象和修辭符號的重新定義與再現,呈現當前的生態危機與環境問題,并致力于搭建一種兼具多義性、主觀性、建構性的環保框架來接合生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意義,進而實現生態危機預警、樹立綠色生態形象和宣傳生態保護理念。同時,我國生態影視創作應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整體觀,打造兼具國際通約性與本土特色的上乘之作。這亦是中國生態影視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