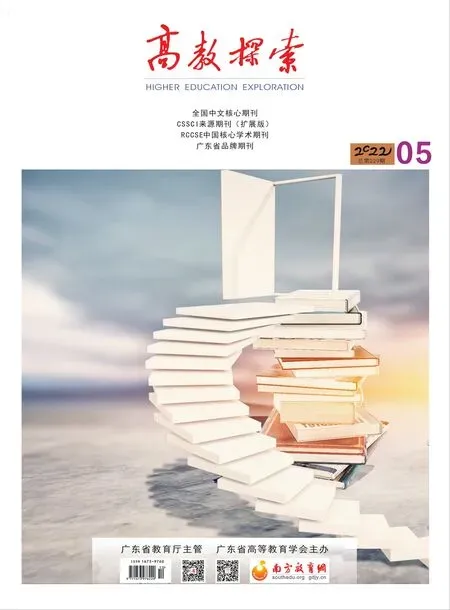職業本科教育的政策變遷與發展策略*
陳寶華
1994年,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通過“三改一補”政策獲得快速發展,并隨著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迅速擴張成為高等教育體系的“半壁江山”。2006年,教育部在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確:高等職業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2014年,提出“探索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2019年,開始“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2021年,確定“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如何辦好職業本科教育成為當前我們急需思考和探索的課題。本文對職業本科教育相關政策變遷進行梳理,重點聚焦高等職業教育是類型還是層次、誰來承辦職業本科教育、如何提升職業本科教育質量等三個發展階段,同時借鑒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展經驗,針對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作初步思考。
一、職業本科教育的政策變遷
根據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提出并建構的高等教育發展的政府、市場、大學“三角協調模式”,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屬于比較典型的偏向政府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都是在政府出臺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下積極推進,當然也包括職業本科教育。通過政策變遷的分析,能較好把握職業本科教育發展的背景和脈絡,更好地貫徹落實“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的精神,做到保持辦學方向不變、培養模式不變、特色發展不變。
1.職業本科教育的萌芽階段:類型還是層次
我國歷來重視職業技術教育,20世紀80年代開始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實踐和探索后,在政策文本中逐漸明確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體系專科層次的一部分。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技術院校”,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該《決定》首次在政策文本中提到“高等職業技術院校”和“職業技術教育體系”,認為職業技術教育是區別于普通教育、強調行業特色、自成體系(初級、中級和高級)的一種新型教育類型,而高等職業教育屬職業技術教育的高級部分。
1994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通過“三改一補”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方針。“三改”是現有的職業大學、部分高等專科學校和成人高校改革辦學模式,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一補”是少數具備條件的重點中等專業學校通過改制或舉辦高職班等方式,作為補充發展高等職業教育。1998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明確:高等職業學校屬于高等學校的一種,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1999年,教育部、國家計委印發《試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舉辦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實施意見》,提出試用新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探索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并將其限定為專科層次,具體承擔機構包括短期職業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等。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再次明確: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技術學院的畢業生經過選拔考試符合條件的可以進入本科高等學校繼續深造學習。
由于高等職業教育僅限于專科,所以其和高等專科教育一起統稱為高職高專教育,各政策文件嚴格要求:不允許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升格為本科院校。2000年,《教育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指出:“高職高專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進一步規范高等職業學校的名稱,為了體現職業教育特點,逐步統一規范為“××職業技術學院”。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嚴格規定:2010年以前,原則上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不升格為本科院校。
盡管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較晚,政策文本把其僅限為“專科層次學歷教育”,但學術界一直有聲音認為高等職業教育不應是層次教育,而是類型教育,并提出積極探索本科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例如,郭揚(2002)認為,為適應我國加入WTO后對于培養技術精英人才的要求,我國應該發展較長學制的高等職業教育——技術本科;石偉平、徐國慶(2003)從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體系發展兩個維度,充分論證我國發展技術本科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李均等人(2003)認為,高等職業教育“乃培養高級技術應用性人才之教育。作為一種高等教育類型,高職應包括專科、本科、研究生等多個層次”;雷世平等人(2005)認為,發展本科層次高等職業教育,對于不斷完善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優化職業教育結構,更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2.職業本科教育的興起階段:誰來辦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探索,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職業本科教育也逐漸興起,誰來承辦職業本科教育成為該階段探討的重點。
2006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首次明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職業本科教育因此成為一種可能,至于誰來承辦,文件并未提及,高等職業教育的重點由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建設。同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加快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決定,重點支持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2010年,教育部、財政部決定,在原來100所高職院校進行重點建設的基礎上,新增100所左右國家骨干高職院校,并要求“堅持高等職業教育的科學定位和辦學方向,2020年以前骨干高職院校不升格為本科院校”。
2011年,教育部《關于“十二五”期間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對誰來承辦職業本科教育提出意見:“對民辦普通專科層次學校,如其布局合理,辦學條件達標、辦學特色突出、無違規行為、畢業生屆數在7屆以上,符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可在原有基礎上申請組建本科學校。”同時,強調“高等職業學校原則上不升格為本科學校,不與本科學校進行合并,也不更名為高等專科學校”。因此,職業本科教育先由民辦職業技術學院升格為職業技術大學開始試點和探索。
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在已有民辦職業技術大學的基礎上,開辟本科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學校轉型的新路徑,探索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區域產業轉型升級需求,引導一批傳統普通本科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轉設為獨立設置高校的獨立學院,鼓勵其向應用技術類型高校定位和轉型,并同時強調原則上專科高等職業院校不升格為或并入本科高等學校。同年,為了更好落實上述文件,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強調現代職業教育是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促進全體勞動者可持續發展的教育類型,并就研究型院校、應用技術型院校及高職院校的分類管理制定更為具體的建設規劃方案。在已有傳統普通本科高校以及獨立學院向應用技術型院校轉型發展外,也鼓勵本科高校與示范性高職院校加強合作,協同培養高層次應用技術人才。此外,繼續強調“原則上現有專科高等職業學校不升格為或并入普通高等學校”。
2019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重申: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一種教育類型,并繼續完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積極推動傳統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院校轉型,鼓勵有條件的普通本科高校舉辦應用技術類型專業或課程,并啟動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簡稱“雙高計劃”)。隨后,197所高等職業學校成為“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件不再重申高職院校不升格或不并入的規定,轉為“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2019年12月,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2020年6月更名為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經教育部批準,升格為本科層次職業學校,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成為全國首家公辦本科層次職業院校。
2020年,教育部《關于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就獨立學院轉設工作作出要求,到2020年末,所有獨立學院均完成轉設工作方案的制定。同時,推動部分獨立學院完成轉設工作,并“鼓勵各地積極創新,可探索統籌省內高職高專教育資源合并轉設”,“學校的名稱一般為××××職業大學或職業技術大學”。該文件為多年來苦苦尋求升格機會的高等職業學校注入一針強心劑,在各地政府的積極協調下,幾十所高等職業學校與獨立學院洽談合并事宜,并進入轉設公示環節。2021年,教育部印發《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試行)》,加強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的規范和管理,引導高校科學設置專業。
至此,職業本科教育興起并進入實踐探索階段,承擔該任務的除了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是唯一一所由公辦高等職業學校直接整體升格以外,主要是由普通本科院校轉型的應用技術型學校、民辦高等職業學校升格和獨立學院(或與專科層次高等職業學校合并)轉設的職業技術大學。據教育部網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21年9月,普通高等學校2756所(其中本科1270所、專科1486所),以“職業技術大學”命名的本科學校共19所,其中12所為民辦。對于誰來辦職業本科教育的問題,學術界也一直有聲音認為應用技術院校專注度不夠、民辦院校水平不夠,還是應該通過遴選優秀專科層次職業技術院校升格為職業技術大學來承辦。例如,石偉平、徐國慶(2003)認為有的高等職業學校具有豐富的技術教育辦學經驗和雄厚的技術教育辦學條件,這些學校升格為本科探索職業本科教育,更容易辦出技術教育的特色。黃達人等人(2012)提出“專業試辦”方案,依托辦學質量高、辦學資質好的高等職業學校,進行職業本科專業人才培養的探索。邢暉、郭靜(2021)認為應用技術本科和職業本科具有非常相似之處,但不能混為一談,職業本科教育不應包含應用技術大學;民辦高等職業學校升格舉辦職業本科教育難以服眾,應公辦民辦“一視同仁”,以辦學條件為依托,同臺競爭。筆者(2017)認為,通過并不承認自己是職業教育的應用技術大學承辦職業本科教育,并不利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甚至存在阻礙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風險。
3.職業本科教育的深化階段:如何辦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探索,由應用技術型學校和民辦職業技術大學承辦職業本科教育并不被人們所認可,政策文本重點轉向在專科層次的高等職業學校優中選優,強調辦學方向、培養模式、特色發展等三不變,職業本科教育進入如何辦的深化階段。
2021年1月,教育部《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設置標準(試行)》要求,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要堅持面向市場、服務發展、促進就業的辦學方向,堅定職業教育定位、屬性和特色,辦學目標是培養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
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對職業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進一步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
2021年7月,教育部《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提出,增強高等職業教育適應性:“以優質高等職業學校為基礎,穩步發展本科層次職業學校。”穩步發展的原則是堅持高標準、高起點,并嚴把質量關。同時,通過專業設置標準、學位授予以及評價機制等,引導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堅持職業教育屬性,辦出職業教育特色。8月,《關于開展“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強調:“擬設立的本科層次職業學校,須把控節奏、優中選優。”“原則上每省(區、市)不超過2所;獨立學院轉設事項不受數量限制。”至此,教育部“十二五”“十三五”時期強調不允許公辦高等職業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的基本政策被徹底放棄。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并要求職業本科教育“三不變”,即辦學方向不變、培養模式不變、特色發展不變。同時強調,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占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以上,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和培養質量。原來要求的引導傳統普通本科高等學校轉型為應用技術類型高校培養本科層次職業人才,變化為鼓勵應用型本科學校開展職業本科教育,這顯示在政策文本上不再把應用技術型教育視為職業本科教育的一部分,應用技術型高校也不再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一部分。職業本科教育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二、麻省理工學院發展歷程與啟示
提升職業本科教育質量是當前職業技術大學自身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所賦予的使命和責任。充分借鑒國外高等學校的成功經驗,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厘清職業本科教育的內涵,探討其發展策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簡稱MIT)自19世紀60年代創校以來,一直堅持與企業的緊密合作,從講授實用工藝的多科技術學校到科學技術型學院,再發展為研究型大學,并開創創業型大學模式,成為學校與企業、技術與科學、技術與人文等深度融合,順應、推進、引領產業革命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世界高等學校典范。
19世紀是美國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時期。19世紀前半期,產業革命、西進運動等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科學教育思潮影響深化,杜威實用主義哲學觀逐步成型,社會對高等教育推行實用性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此背景下,MIT首任校長羅杰斯積極響應社會需求,強調科學為基礎的實用技術,構建與企業的緊密關系,力求創立一所完全不同于傳統古典大學的新教育機構:以教授實用工藝為主的多科技術學校。之后,世界高等教育發生深刻變化,德國洪堡以“為科學而生活”的理念主導柏林大學崛起,美國“威斯康星觀念”促使贈地學院興起。MIT歷經半個世紀的實踐與探索,一方面堅持既動手又動腦的“新式教育”,另一方面吸收柏林大學科學技術研究要素,以及贈地學院直接服務社會發展需求的要素,20世紀初發展成為具有較高社會聲譽的科學技術型學院。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高等學校普遍出現財政危機,第九任校長康普頓采取一系列舉措,進一步加強人才培養與科學技術應用研究的結合,強調創新創業教育,把與企業的關系拓展為“政府—大學—企業”的三螺旋關系,進一步豐富了“新式教育”的內涵,并成功把這所科學技術型學院轉型為研究型大學,躋身美國頂尖大學之列。20世紀80年代,第十五任校長維斯特繼續豐富“新式教育”內涵,挖掘“新式教育”特色,進一步促進大學與企業的深度融合,提升“政府—大學—企業”三螺旋關系,共同推動美國高端技術市場化取得巨大成功,開創創業型大學之先河。何謂創業型大學?美國亨利·埃茨科維茨的《麻省理工學院與創業科學的興起》以MIT為例,從兩次學術革命的視角,論述大學的職能和使命從單純教學到科學研究,再演進到服務于經濟發展。在研究型大學基礎上,創業型大學通過科研成果的轉化直接服務于產業和社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據美國波士頓銀行1997年報告,MIT師生在全球建立了四千多家企業,就業人數超過百萬,年營業額超過2000億美元。
MIT能從多科技術學校起步,逐步發展成為科學技術型學院、研究型大學,最后開創創業型大學模式,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高等教育典范,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歸納起來有三點。
第一,學校與企業深度融合。MIT自創立以來,一直致力于構建區別傳統大學的、與企業具有緊密關系的“新式教育”。與企業的緊密關系作為創校基因深深烙印在MIT每名師生的內心深處,大家以與企業關系緊密為榮;與企業的緊密關系作為學校文化根植在教學模式改革、產業技術創新、區域發展服務等學術行為中,固化、提升為滿足不同時代發展需求的“形神合一”的新教育范式,伴隨并支撐著MIT經歷“多科技術學校——科學技術型學院——研究型大學——創業型大學”的發展軌跡。
第二,技術與科學深度融合。MIT自創建以來便謀求實施“新式教育”:堅持既動手又動腦、以科學為基礎的實用技術教育。傳統科學研究以知識為邏輯起點,以發現知識為目的,這個知識是否“有用”是不確定的。技術研發與傳授則基于知識的“有用性”,以求解決實際問題。MIT通過與企業緊密聯系,敏銳獲取或推斷商業開發、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的核心知識——“有用知識”,并將其融入人才培養、科學研發及社會服務中。同時,MIT還采取不同于傳統大學的行政運行機制和學術治理模式,充分發揮自身的智力優勢,直接(參與)成立科技型企業,把學校的學術屬性與科技公司的經濟屬性有機融合在一起,并都獲得廣泛、等值的良好社會聲譽。這種通過在市場中交換學術資源以創造價值的努力,被學者稱為“學術資本主義”。
第三,技術與人文深度融合。一方面,MIT作為“新式教育”創校有別于古典學院,但同時也傳承了歐洲中世紀大學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特質。另一方面,MIT吸收了20世紀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家赫欽斯的教育思想。赫欽斯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為人的發展奠定基礎,在于發展人性,而非培養人力;通識教育是最有價值的教育;大學的宗旨在于傳播和創造知識,而不僅僅為學生以后的工作服務;職業教育以職業為導向,使受教育者只掌握從業的技術技能,卻不了解職業崗位中的基本原理,從而束縛了他們在職業崗位中的創新意愿和能力,也限制了他們未來職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MIT構建了包括科學和人文教育的健全而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人文社會科學課程賦予培養目標精神文化意義和社會價值,從而將實用技術教育提升到更高層次:提升道德品格,完善人格修養。
三、職業本科教育發展策略思考
職業本科教育作為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事物,要實現穩步發展,一方面要堅持,另一方面也要創新。堅持就是堅持職業需求導向、服務社會發展,做到職業教育辦學方向不變,職業教育屬性和特色不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標不變。創新就是進一步優化人才培養方案,促使培養目標更契合、培養模式更科學、培養質量更卓越。
1.優中擇優,穩步推進
基于目前應用技術大學以及民辦職業本科院校的現狀及發展愿景,積極探索職業本科教育,完善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主要依靠獨立升格的公辦職業本科院校。一直以來,我國高職院校(特別是公辦院校)和MIT一樣,致力于構建區別傳統普通大學的、與企業行業具有緊密關系的“新式教育”,具有良好的校企合作基因。由于歷史的原因,目前公辦專科層次職業技術院校雖然數目眾多,但質量和條件參差不齊,因此,試辦職業本科教育不宜一哄而上,而應該優中擇優,穩步推進。筆者建議,在前期國家“雙高計劃”建設的基礎上,遴選部分辦學理念先進、辦學條件較好、社會聲譽良好的公辦專科高職院校整體升格為本科層次的職業技術大學,積極開展職業本科教育的探索和實踐。同時,吸取英國多科技術學院“學術漂移”的經驗,考慮職業本科教育涉及面較廣、探索事項較為復雜,為了避免對其它專科層次高職院校的沖擊,建議試辦周期不宜太短,至少應設四年及以上。并根據試辦情況,及時評估,為后續穩步推進職業本科教育提供科學依據。
2.精準引導,高度聚焦
職業教育的最大特色和亮點是產教融合,這也是職業教育的生命線。產教深度融合無疑是職業本科院校發展的挑戰。借鑒MIT從多科技術學校到創業型大學的發展經驗,產教深度融合至少應該體現在院校具備商業開發、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的核心知識,從而順應、推進、引領產業革命和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層面如何精準引導職業本科教育積極推進產教深度融合?經濟學的觀點認為,高等教育及院校行為受出資方影響外,還受出資方的付款方式影響:“不僅僅是誰付賬誰點唱,而且付賬的方式也是怎么唱的決定因素。”“支付經費的手段對高等院校及其內部行為者的行為也有著重要影響。”為此,建議政府在加大對職業技術大學資金投入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完善資金支付方式,有效促使其更加貼近市場,更加有利于獲取商業開發、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的核心知識,突顯職業本科特色。例如,把政府專項財政資金與院校通過市場籌措的資金聯系起來,按一定比例配套,并且采取“先市場、后財政”的時間順序配置,避免出現以往傳統高等院校向政府搶項目、爭資源以及“重立項、輕結項”的現象。同時,為了更加聚焦產教深度融合這個突破點,政府政策層面應適度放權,在確保辦學方向不變、培養模式不變、特色發展不變的前提下,職業技術大學具有更多自主權進行改革創新,例如“職教高考”是否成為其招生主渠道、校外實訓基地如何科學配置、院校內部如何分配通過市場競爭獲取的資源等。
3.優化機制,加大激勵
克拉克認為創業型大學的核心要素是組織轉型,構建一個能對多樣、復雜的社會需要及時作出“創業型反應”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實踐層面,職業技術大學應充分借鑒MIT創業型大學模式,緊緊圍繞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特別是應用廣泛的產業領域,積極探索對社會需求及時主動進行“創業型反應”,運行科學高效,充分體現產教深度融合特色的院校內部運行機制。一方面,真正以社會發展和需求為導向,成立跨領域的研究院(所),有效促進各個學科的交叉和融合,提高應用技術研發能力,直接為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提供現場應用技術支援。例如,成立集成電路研究院,包括理科、工科、文科等多個門類,在中美貿易戰及我國經濟“雙循環”發展等大背景下,為各類企業解決應用技術研發及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另一方面,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優化內部二級組織資源分配方案、教師職稱評聘及考核分配制度等,允許和鼓勵教師在專利權運用制度、以研發成果為基礎創建技術型企業,以及為企業提供應用技術支持等方面大膽探索與實踐。例如,通過提高橫向課題自主分配資金比例、允許教師利用校內資源為企業開展生產性實訓項目等措施,鼓勵教師積極引進企業項目,帶領完成基礎課學習的學生,在大二大三進行真實項目的實習實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