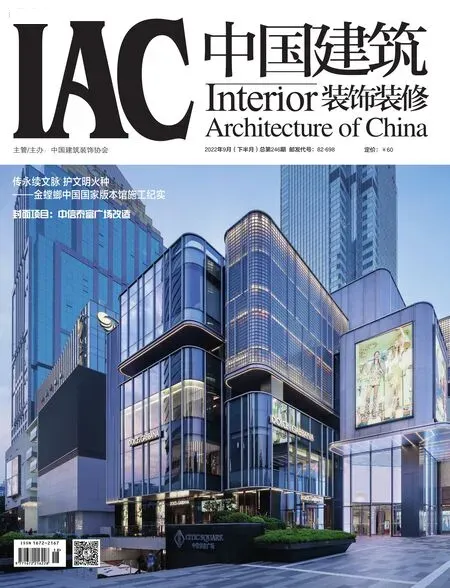陳家祠的灰塑裝飾藝術特征及文化內涵
劉 康 張金明 黃俊杰 蔡嘉倫
陳家祠屬于合族祠,又稱為“陳氏書院”,位于廣東省廣州市,是嶺南獨具特色的傳統建筑群體。1888 年,由陳氏鄉紳向廣東省72 縣的陳氏宗親籌資建造而成,并于1894 年落成;總占地面積約15 000 m2,坐北朝南,整體呈院落式布局,內含19 座不同單體建筑。
陳家祠被譽為“嶺南建筑藝術的明珠”,集嶺南建筑工藝裝飾之大成,幾乎全部堂、院、廊、廳、門、窗、欄、壁、屋脊及架梁都展示了嶺南建筑的“三雕二塑一鑄一畫”等建筑裝飾的高超技藝。其中,陳家祠灰塑總面積達2 448 m2,總體長度達2 562 m,其規模為嶺南灰塑之首[1]。
陳家祠的灰塑工藝很好地展示了嶺南地區的地方文化藝術特色,作為傳統手工藝之一,因為工藝煩瑣,一度傳承斷代。
中華傳統藝術作為我國歷史精粹不應流失殆盡,而是要傳承綻放,以灰塑藝術為代表的地方藝術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與地方發展進程的縮影,陳家祠灰塑藝術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理應得到廣大研究者的關注。
1 陳家祠灰塑的價值
灰塑又稱“灰批”,是嶺南地區的傳統建筑裝飾工藝,主要運用在山墻頂端、門額窗框、屋檐瓦脊以及亭臺牌坊等處。據史料記載,早在公元884 年,灰塑工藝就已經存在,宋代以后灰塑工藝得到了快速發展,清代時期的應用則更普遍,常裝飾于廟宇、祠堂中,以此彰顯建筑的貴氣。
1.1 信息價值
灰塑是當代精神文明與人類物質的精粹,更是一定時期內人們工藝水平及審美取向的物化體現。英國學者特倫斯·霍克斯(Terence Hawkcs)在其著作《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中指出:“在人的世界中沒有什么東西純粹是功利的,甚至連最普通的建筑也以各種方式組織空間,這樣,它們就起指示作用,發出某種關于社會優先考慮的事項,這個社會對人的本性的各種先決條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信息。”陳家祠灰塑裝飾更像是此類的符號系統,能夠將該時期的社會態勢及文化姿態完美地表達出來[2]。
對于灰塑,不僅要將其視為靜態藝術形式,而且要將其散發的人文生活氣息作為重要參考,了解當時的社會現狀,分析其制作緣由。陳家祠是民間建筑的一種,規模上深受制度約束,因此為了能夠凸顯出該宗族的強大,只能從建筑裝飾層面入手,通過刻畫陳家祠灰塑中較為細節的紋飾、內容,充分體現人們的心理需求。陳家祠灰塑就像龐大的“數據庫”,能夠為后人提供豐富的歷史、人文信息。
1.2 象征價值
受宗族文化影響,灰塑被賦予了廣泛而深遠的象征意義。為了能夠表現出較為強大的宗族文化,不僅要刻畫出宏偉的建筑,還要描繪出雍容華貴、氣勢磅礴的灰塑造型,并且它也積極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明清時期在全國范圍流行開來[3]。
陳家祠的灰塑圖案題材大多是歷史沿襲,其諧音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例如,其中桃寓意“壽”,蝙蝠寓意“福”,二者結合則寓意福壽兩全。諸如此類均是以吉祥為主題,以喜慶色彩為裝飾,體現了情感與題材上的共鳴,是灰塑藝術的特征之一。
2 陳家祠灰塑的藝術特征
2.1 設計構思特征
在陳家祠建筑裝飾中,灰塑工藝設計構思精巧細膩,別致大方。首先,在擬定題材后,要細化推敲其構圖,并以某個視覺中心為原點進行系統化組織空間的構建,再塑造諸多細節性的建筑裝飾,基于此創造別致、典雅的藝術形式。其次,設計者需注意構圖中不同元素、構件的和諧性,這樣才能創造出相得益彰的畫面,充分發揮灰塑藝術的意境美。再次,設計者主要利用對稱方式進一步突出祠堂的莊重、嚴肅感,符合中國傳統建筑的營造思想。但是過于對稱,又會使人在觀賞、使用祠堂的過程中對灰塑藝術產生死板、笨重的印象。最后,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應注意把握整體建筑較為和諧的平衡感,同時又要注重細節上的靈活設計,以賦予建筑工藝靈魂。因此,應將對稱和均衡相互融合,提升整體構圖層次感、主次突出、細密嚴謹,構建出和諧系統的意境美感。另外,灰塑構圖中常在屋脊上對吉祥人物、花草果木、幾何紋樣等進行綜合構圖,傳統美學在整體布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陳家祠的門廳及倒座房垂脊上,一對灰塑工藝獨角獅呈現對稱式構圖。獅身重心在后,朱紅色獅頭向前探出,獅眼神采奕奕,嘴角微微翹起,血盆之口大張,頭部兩側點綴金色鬢毛,活靈活現。相較于頭部的“濃墨重彩”,獅身的處理更簡單,頭身與鬢毛相互連接,主次分明。建筑上,兩只獅子雖形態、體貌并不完全一致,但總體呈現對稱式分布,整體畫面和諧統一。而且設計者在構筑灰塑獅子時,通過設計生動活潑的面部表情,刻畫出細致的動作,這些“巧思”能夠極大程度呈現灰塑獅子的靈動性,既保證了對稱構圖的工整性與和諧性,又能夠賦予更生動靈巧的意境美感,使得觀賞者在品鑒陳家祠堂灰塑藝術的過程中,能夠同步感受到莊嚴、肅穆、靈巧、生動等多樣化的韻味,獲得更復雜、高端的美感。
在門廳屋脊處,不僅利用對稱工藝,還利用了均衡工藝。例如,在側門屋脊處應用了具有吉祥元素的童子、仙人等角色。其中,童子位于建筑的最高處,腳下臥著象征幸福的瑞獸,手持象征財富的銅錢;仙子置于獅子上方,緊抱寶瓶,神態祥和;壽星則依舊使用我國古人所喜愛的老者形象,手持仙桃、腳踏仙鶴。除了重點人物,設計者還在畫面中添置了云紋、回字紋等象征吉祥的裝飾,構建和諧畫面。
2.2 禮制裝飾特征
封建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極大程度上依賴于嚴謹、完善的禮制制度,禮制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在當時的建筑、裝飾等方面亦可窺探到禮制元素。以陳家祠的灰塑藝術為例,其所具備的藝術性同樣是建立于禮制之上。
陳家祠正廳正脊上的灰塑裝飾極為豐富(圖1),所排列的動物裝飾大小不一,形態各異,數目不等。等級越高,建筑中所具有的脊獸數量規模也就越大,同時其體型、外觀也會更顯眼,而脊首的位置、體形以及色彩設計等也受相關禮制規定約束,因此不可越級。陳家祠灰塑工藝在位置處理方面,需要以整體建筑布局的形制、類型以及設計為主,并在此基礎上突出傳統的禮制規定,做到建筑與禮制、物品與人文遙相呼應、和諧統一。其中,以建筑中軸為主線,從中軸出發設計、建造的灰塑工藝品群普遍具有體形較大、等級高、突出性強的特征,在中軸左右兩側逐一降低脊獸的等級,直至建筑末端。

圖1 陳家祠正廳正脊脊獸(來源:作者自攝)
陳家祠建筑整體空間中的灰塑工藝裝飾品,穿插著有序的廊廳、偏間,層次遞進式向中間靠攏,充分凸顯出主殿的氣勢宏偉。在裝飾物的形制上,相關禮制已明確民間用房不可雕飾等級較高的麒麟、龍鳳、圣賢人物等題材,只可雕飾鳥獸、蟲魚、山川、博古等等級較低的選材。此外,祠堂禮制地位雖然遠不及寺廟、宮殿等建筑,卻仍舊是民間建筑用房中禮制等級最高的類型。陳家祠堂中所應用的灰塑工藝不僅有麒麟、仙童、日月等,而且嶺南地區的獨特香果、春色也都一一體現出來,有效消除了與平民間的距離感,展現了灰塑藝術獨特又自然的和諧之美。對于民間建筑而言,盡管禮制更傾向于約束其建筑等級的標尺,但正是因為禮制的約束與控制,才使得陳家祠在建筑設計與建造過程中,既能促使裝飾更加肅穆,又能營造出更富有趣味的民間習俗,營造出自然的空間氛圍[4]。
2.3 題材選擇特征
陳家祠建筑裝飾中,灰塑工藝在題材選擇上豐富多樣,且貼近生活,滿足人們對未來的美好祝愿。相關設計者依照給定的題材內容,在工藝、造型、色彩等方面進行系統加工整合后呈現出來。在特定場所中,這種提示性題材的選擇也是營造環境氛圍的重要方式。
建立祠堂,旨在以更好的方式祭祀祖先,是家族榮耀的象征。在莊嚴肅穆、宏大壯觀、教化功能顯著的祠堂裝飾設計中,灰塑工藝技術恰好能滿足此類需求。它豐滿且充實、色彩鮮艷且豐富,具有較好的兼容性,適用于祠堂、住宅等不同種類、功能的建筑。通過細化裝飾紋樣,并隨意搭配與重復使用不同的元素,既能將主體造型特點襯托出來,又可以在建筑物的不同部位體現其設計意圖。如祈福題材、瑞獸題材等,通過灰塑藝術祈盼吉祥富貴、四季平安、五谷豐登、人丁興旺、健康長壽,或者用植物的形式來表現求子愿望等。
陳家祠堂中應用的灰塑藝術大多以民間風俗為主題,并利用諧音、借喻等手法來闡釋教化、引導、祈福的意向。在眾多元素中,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是最常見的手法之一,能夠通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元素以及情境等構成特定的故事情節,并以相應的建筑、景色風景為背景,通過植物、動物、陳設等科學配置構建出引人入勝的畫面。例如,陳氏祠連廊上“桃園三結義”的灰塑圖案工藝,取自《三國演義》中劉備、關羽、張飛結拜為義兄弟的故事,引人深思的同時,充分體現出濃厚的教育含義。又如“竹林七賢”的刻畫,意在不可與奸佞同流合污,要注意提高自身修養。
在祥禽瑞獸的灰塑工藝中,麒麟、龍、獅子、猴子、馬及羊是動物元素的典型代表,如“麒麟吐玉書”的構圖,麒麟降至代表祥瑞降生。同時,孔雀、鳳、錦雞、喜鵲等為飛禽元素的代表,而各種花草瓜果、博古雜寶、紋樣團飾也是豐富畫面的重要點綴元素。其中,蓮子寓意“連生貴子”,而龍眼作為重要的嶺南佳果,其別名桂圓象征著“富貴與團圓”,在民間深受喜愛。
另外,陳家祠灰塑工藝的設計元素十分豐富且具有良好的教化意義,而不同的設計巧思也能夠彰顯當時設計者和匠人的獨特審美情趣、思想認知、價值觀念以及抒情方式,創造出更加鮮明的塑工工藝。然而由于觀賞者與設計者知識儲備不同且時代不同,難以系統化欣賞及解讀題材裝飾的內涵,因此它更多代表的是華麗性的裝飾和擺設,充分顯現出昔日家族的輝煌[5]。
3 陳家祠灰塑的文化內涵
陳家祠的灰塑,在遵循傳統禮制特征的基礎上,通過嚴謹均衡又不失靈活的構圖形式,再加上豐富多樣的題材選取,共同構建了多樣的灰塑形式。
陳家祠建筑主體以青灰色為主,古樸大方,通過灰塑的裝飾,使其更豐富、靈動、艷麗,但又不失沉穩。灰塑藝術中蘊藏著豐富的民俗文化元素,反映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和審美情趣,同時也深刻體現了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積淀,生動地折射出當時的民俗心理和民間信仰。通過對灰塑的解讀,可以了解其背后的民俗文化,并將其很好地傳承下去。
4 結語
灰塑構圖中,常在屋脊上對吉祥人物、花草果木以及幾何紋樣等進行綜合構圖,在此過程中,傳統美學在整體布局中,起到了較為獨特的裝飾作用。陳家祠灰塑工藝在位置設計與處理方面應以建筑布局及整體形制為主要藍本,做到裝飾與禮制、美觀性與教化性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