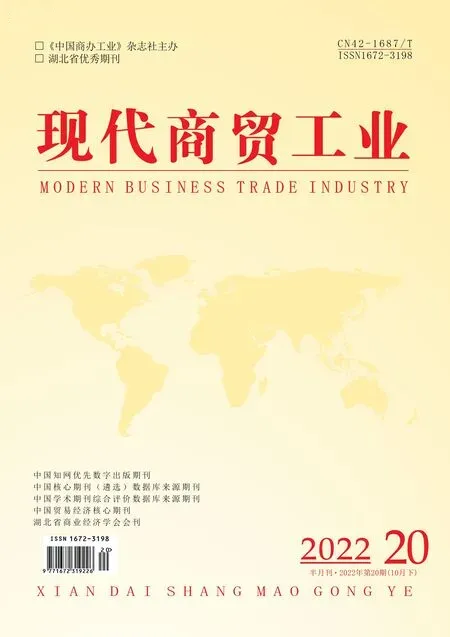基于中國地級市的電視問政與公共服務支出研究
鄒淵文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1 文獻綜述
公共服務支出可以直觀地反映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用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府績效,以及政府向群眾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它可以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何凌云,2014)、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薛鋼,2015)等,對社會生活福利與經濟增長有重要的影響(唐穎,2014)。特別是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日趨成熟,對財政支出結構向公共服務領域傾斜的需要更加迫切。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在供求雙方的作用下,按市場效益最大化的目標配置資源。因此,市場活動本質上是一種趨利性的活動,這決定了其在公共品供給等非盈利性領域的資源配置存在天然的缺陷。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要求政府強化在公共領域的服務職能。一方面,逐步退出市場;另一方面,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提供保障,從競爭性領域轉向為市場提供解決外部性的條件(李文軍,2013)。然而,從已有研究結果來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積極性不高(呂煒等,2008;石英華,2017)。并且,在我國,政府更偏好提供“硬公共品”而在醫療、教育等“軟公共品”的供給方面不足(劉成奎,2012)。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間的垂直競爭和水平競爭。居民“用腳投票”倒逼地方政府通過提高支出效率以增進社會福利,從而形成了“為增長而競爭”的壓力(Li & Zhou,2005;繆小林等,2017)。根據財政學原理,生產性(投資性)支出與民生性支出相比,能夠更迅速地發揮波狀乘數效應,帶來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短期效益。因此,政府間競爭將助推財政活動更多地作用于生產性支出(Cohn,1997)。另一方面,現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增大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左翔等,2011),使財政支出向生產性領域傾斜以追求短期經濟增長。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監督機制的缺乏也是公共服務支出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龔鋒等,2009;劉書明,2016)。從內部來看,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政績考核面臨有限能力和信息不對稱的約束(Bardhan & Mookherjee,2000),特別是當下“唯GDP”論尚未完全破除,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作為一個顯性指標,依然是地方政府官員追逐的重點,這會掩蓋經濟增長背后的民生問題。從外部來看,來自普通民眾的力量十分有限(周黎安,2007)。普通民眾沒有能力反映、沒有渠道反映,成為促進民眾充分發揮監督力量的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而電視問政作為連接政府與民眾的橋梁,搭建了一個政民互動平臺,有效地緩解了上下級政府之間、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了媒體作為“第四權力”的作用(亢廷錕,2019)。
電視問政節目是一種媒介化治理的創新。治理指的是一個有序的過程,通過它,執政者制定并執行公共政策,監督并評估執政的舉措,以提升執政的正當和有效程度(閆文婕,2020)。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存在,電視問政節目對于政務執行的直觀作用是為官民對話搭建新的平臺,為政府回應民意提供了重要的途徑,其關鍵在于其有沒有起到“治庸問責”的監督作用(胡春艷,2017)。以往的研究中也表明,媒體在監督作用的基礎上,如果能得到政府的幫助與介入,就有可能更好地發揮治理的作用(楊德明,2012)。然而,已有關于電視問政的文獻大多局限于管理學和傳播學,且大部分研究是針對某一或某幾個電視問政類節目展開的個案研究。例如有學者從管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與城市治理創新的關系,以中國最早的武漢市電視問政為例,分析電視問政對城市創新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問題,如參與性、公共性、反饋性不足,為節目運營優化提供一定借鑒(張立榮等,2016);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了電視問政作為中國式公共新聞的新探索,對電視問政展開概念界定和發展趨勢的探索,按照具體案例展開剖析(顧亞奇,2014)。相關文獻為研究電視問政與公共服務支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有利于完善電視問政在財政監督方面作用的理論。
目前,已有的探究公共服務支出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包括腐敗與經濟尋租(谷成,2016)、國家審計(鄭石橋,2018)、地方政府分權程度(陳思霞,2014)等,關于電視問政對公共服務支出的作用的研究還較少。即使擴展到政府職能領域,也多是定性分析和模式探索為主,鮮有從經濟學視角分析電視問政對該領域的影響。文章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加以創新,通過基于大樣本數據和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彌補了該領域定量研究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計
為探索電視問政對公共服務支出產生的經濟效應,文章將電視問政節目的開通視為一種“準自然實驗”,通過構造雙重差分模型(以下簡稱DID模型)考察節目開通的凈效應。將有電視問政節目開通的城市設為處理組,其余地級市設為對照組,以節目開通時點為界,就將所有地級市劃分為4個子樣本。考慮到地級市開通節目的時間并不相同,不能使用傳統的靜態DID方法,因此,文章借鑒Beck等(2010)的思路,構建多時點DID模型進行研究。模型形式設定如下:
,=+,+∑×+++,
其中,為時間固定效應,為城市個體固定效應,,為隨機誤差項,表示城市,表示年份。
2.2 變量設計
2.2.1 被解釋變量:公共服務支出()
文章將教育支出、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列為公共服務支出領域。考慮到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數據缺失嚴重,且該類支出在總支出中占比較小,故剔除該類支出,使用其它兩類支出的總和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作為公共服務支出()的代理變量。
2.2.2 解釋變量:問政節目開通()
虛擬變量實際上包含了時間項和處理項的交互項(即×)。對于2019年底之前未開通過電視問政節目的城市(對照組),取=0。對于處理組的城市來說,取=1,且在節目開通之前,取=0,節目開通之后,取=1。這樣,在四個子樣本中,只有當處理組的城市開通節目之后,虛擬變量才會取值為1,其余情況取值皆為0。文章在劉珊(2020)所統計的中國電視問政節目名單的基礎上構建電視問政數據庫。截至2019年12月,省級電視問政節目共11個,涉及10省市區;地級電視問政節目共167個,涉及139個城市。鑒于文章的研究目的,對于一個城市開通多個節目的情況,文章不作考慮,統一按照=1處理。
2.2.3 控制變量()
文章參考潘虹(2020)所研究的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的影響因素,在剔除多重共線性影響后,將控制變量選為產業結構(,當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人均gdp)、財政分權(,當地財政支出占全省財政支出的比重)。
2.2.4 數據說明
文章的基礎數據來源于2010-2019年中國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統計年鑒中相關數據。對于直轄市,將其整體看作城市。考慮到部分城市數據缺失嚴重,故進行了適當剔除,最終保留了278個城市的觀測值。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國泰安數據庫、EPS數據庫、中經網數據庫進行填補。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表1匯報了電視問政對地方公共服務支出的影響效應。此外為了考察影響是否存在滯后效應,還采用電視問政虛擬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例如_1表示當城市開通問政節目一年及以上時,電視問政虛擬變量取值為1,反之為0。參數估計結果表明,電視問政對教育醫療支出在當期的估計系數為0.0096,且在10%水平下顯著;滯后1期的系數為0.0143,且在10%水平下顯著;滯后3期的系數為0.0179,且在10%水平下顯著,說明電視問政節目的開通可以促進當地政府將更多財政資金投入到教育和醫療領域,且這種影響存在滯后效應,隨著節目的播出,這種影響將不斷增強。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3.2 平行趨勢檢驗
DID模型的使用前提是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樣本滿足平行趨勢。文章以-1期為基準組,基于基準回歸模型的繪制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如圖1。圖中黑色圓圈為估計系數,過圓圈的豎線為95%的置信區間。可知在縱向虛線左邊,可以認為黑色圓圈的數值與0相比無差異,說明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同時,縱向虛線右邊黑色圓圈的數值大于0,且呈現遞增趨勢,進一步說明了電視問政的開通對地方公共服務支出有促進作用。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3.3 穩健性檢驗
3.3.1 安慰劑檢驗

圖2 安慰劑檢驗
事實上,一個地區是否開通問政節目并非完全隨機,也就是說處理組樣本的選擇可能受到一些不可觀測因素的干擾。因此,文章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從地區角度進行反事實檢驗。從278個地級市中隨機抽取139個作為假想的節目開通城市,即處理組;其余城市作為對照組。重新進行回歸,并重復1000次。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的核密度分布圖如圖2中,縱向虛線代表了基準回歸中參數估計的真實值0.0096。可知絕大多數反事實估計的結果均位于虛線左邊,表明基準回歸中電視問政對公共服務支出的促進作用并非受到未觀測到的因素所致。
3.3.2 改變樣本期間
由于基準回歸中的樣本時間跨度是主觀設定,如果時間跨度太大,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事件從而帶來估計的偏誤。同時,政府的換屆或官員的更替也可能引起財政支出偏向的改變。因此,文章將上述因素納入考慮范圍重新進行估計。包括①改變樣本時間跨度后重新估計(如設置2010-2017年、2012-2019年為被研究的樣本期間等);②剔除政府換屆的首尾年度后重新估計(如剔除2012和2013年、2017和2018年等)。多次估計的結果顯示的系數仍顯著為正,支持基準回歸的結論(因篇幅有限,回歸結果不在正文中展示)。
3.3.3 剔除省臺的影響
目前,全國共有省級電視問政節目11個,涉及10省市區。由于文章以地級市作為樣本進行準自然實驗,故必須考慮到省級問政節目可能存在的影響。因此,為了驗證這種影響是否顯著,首先以所在省級電視臺已開通節目的10省市區為處理組,其余22個省市區(不含港澳臺地區)為控制組,進行省級樣本的DID檢驗。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1)(2)(3)列。及其滯后1期和3期的參數估計結果分別為0.0266、0.0274、0.0277,且均在95%水平下顯著,表明省級節目對公共服務支出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比地級問政節目的效果更加強烈。表(4)到(6)列展現了剔除已開通節目的10省市區所包含的101個地級市、使用剩余177個地級市進行DID分析的參數估計結果。結果表明:及其滯后1期和3期的系數分別為0.0106、0.0168、0.0195,均大于基準回歸中的系數,且其滯后1期和3期的系數在95%水平上顯著,作用效果相比基準回歸更加明顯。一方面說明了基準回歸中省臺的影響可能掩蓋了一部分市臺的影響,從而造成問政節目的作用效果被低估;另一方面,剔除省臺影響后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結論,電視問政對公共服務支出存在促進作用,且作用效果存在滯后效應。

表2 考慮省臺影響的回歸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得到的結論為:電視問政可以促進當地政府將更多財政資金投入到教育和醫療領域,且這種影響存在滯后效應,隨著節目的播出,這種影響將不斷增強。剔除省臺影響后,電視問政的作用更加明顯。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以下方面:
(1)對政府來說,要轉變發展觀念。為了提高地方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實現財政支出向民生財政轉變,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地方政府首先應改變以往的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發展目標的戰略,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當下,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要體恤百姓、體察民情,真正把握民眾所需,在教育、醫療等軟公共品方面著力,切實提高百姓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對上級政府來說,應該將公共服務水平納入政績考核范圍,充分發揮制度的激勵、約束和篩選作用。
(2)對媒體來說,要落實“第四權力”。要推進問政節目建設,提高其受眾范圍、增強傳播力。當下,問政節目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往往容易收集到較多素材。而在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環境等問題的報道中,則容易受到較大阻力。媒體應明確自身定位,切實落實責任,在節目內容上,要進一步明確問政主題、豐富節目內容,本著以民為本的原則進行選材、制作節目。同時,問政節目的初衷不僅僅在于揭露問題,更在于問題的解決。對于節目中報道的問題,要嚴格落實問責機制和反饋機制,真正做到有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
(3)對民眾來說,要充分發揮監督作用。要加強自身政治素養建設,充分意識到作為公民應當扮演的角色。要充分利用“民眾-媒體-政府”這一監督路徑,對于實際中的缺位失職、違法亂紀現象及時、如實準確地予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