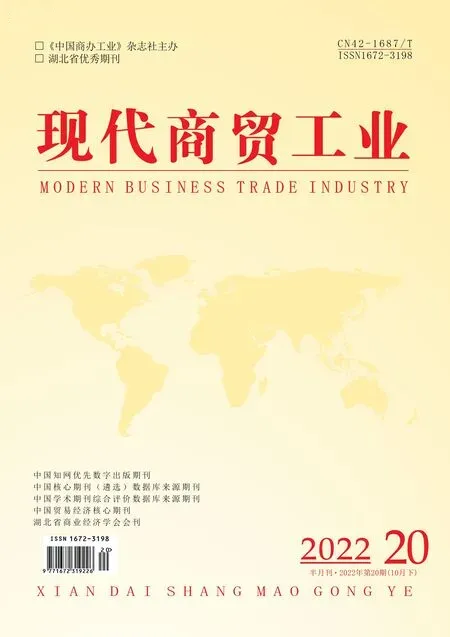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行為的不正當競爭認定路徑探究
——基于平臺經(jīng)濟視野
夏一景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0 引言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的意見》將數(shù)據(jù)認定為生產要素。大數(shù)據(jù)時代,傳統(tǒng)企業(yè)紛紛向平臺型企業(yè)轉型,開發(fā)、運營大數(shù)據(jù)產品成為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基本特征與基礎條件。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具有開放性、多邊市場以及網(wǎng)絡效應等特征,利用大數(shù)據(jù)產品提升用戶黏性的商業(yè)模式為平臺企業(yè)帶來了巨大競爭優(yōu)勢。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在激勵創(chuàng)業(yè)釋放技術創(chuàng)新紅利的同時也誘發(fā)了諸多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典型案例如利用技術手段抓取大數(shù)據(jù)產品而引發(fā)的競爭糾紛。
司法實踐中,對于涉及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不正當競爭的案件一般采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這一原則性條款解決,其理念表達出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采取財產權保護模式的傾向。“淘寶訴美景案”作為我國大數(shù)據(jù)產品不正當競爭糾紛第一案,首次確認了數(shù)據(jù)企業(yè)對其大數(shù)據(jù)產品享有財產性權益。由于當前立法對數(shù)據(jù)的權屬認定闕如、現(xiàn)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尚不能完全回應數(shù)據(jù)保護的獨特要求,以及實務中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新型競爭行為中競爭關系認定標準不一等原因,對此類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guī)制還處在探索階段。
1 大數(shù)據(jù)產品性質界定及現(xiàn)有保護路徑
1.1 大數(shù)據(jù)產品和用戶信息、原始數(shù)據(jù)的界分
大數(shù)據(jù)產品與用戶信息、原始數(shù)據(jù)在物理性質、用戶和網(wǎng)絡運營者權益等方面具有本質區(qū)別(見表1),前者是于后者基礎上形成的創(chuàng)造性產品,是區(qū)別于原始數(shù)據(jù)和用戶信息的新權利客體。網(wǎng)絡運營者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享有獨立的財產性權益:生成方式上,大數(shù)據(jù)產品主要依賴于網(wǎng)絡運營者的智力勞動投入;呈現(xiàn)內容上,大數(shù)據(jù)產品展示的是在巨量原始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基礎上通過算法深度開發(fā)整合形成的衍生數(shù)據(jù)。從市場價值角度,大數(shù)據(jù)產品可以為運營者所實際控制和使用,已具備交換價值,并為經(jīng)營者帶來一定的競爭優(yōu)勢,是平臺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表1 數(shù)據(jù)產品和用戶信息、原始數(shù)據(jù)的界分
1.2 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法律保護的競爭法路徑
司法實踐中,大數(shù)據(jù)產品并未被界定為財產權,而是作為企業(yè)的經(jīng)營條件與水平等比較優(yōu)勢的排他性利益,被歸為“競爭法意義上的財產權益”。因競爭法保護模式下的大數(shù)據(jù)產品權益是基于市場競爭者的侵害而出現(xiàn),無法獲得事前救濟,學界有觀點將此種消極賦權模式下企業(yè)就其主張的權利稱為“準財產權”。競爭法意義上的財產權益往往負荷根本性或一般性的價值,將大數(shù)據(jù)產品視為競爭法上獨立的新型財產權益予以保護,其合理性在于減輕了司法機關在知識產權法、物權法上對其進行正當性、體系化論證的壓力,在當前數(shù)據(jù)確權尚未明晰的背景下最大程度保障了網(wǎng)絡運營者的權益,回應了大數(shù)據(jù)戰(zhàn)略發(fā)展的訴求。然而,要運用競爭法規(guī)范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進行法律保護,首要問題便是如何將反不正當競爭法有限的、難以將被訴行為直接涵攝的規(guī)范適用其中。若能在現(xiàn)有規(guī)范中找到相應類型,即可對該種不正當競爭類型的描述和構成要件進行法律適用上的操作。
2 平臺經(jīng)濟對競爭關系認定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同業(yè)競爭
在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去中心化與去結構化發(fā)展影響下,市場競爭模式與行為呈現(xiàn)為多維競爭與跨界競爭下的流量爭奪與數(shù)據(jù)博弈,競爭關系也從傳統(tǒng)、狹義的同業(yè)競爭關系擴大至廣義的競爭關系。掣肘于同業(yè)競爭意義上的傳統(tǒng)競爭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范圍。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經(jīng)濟所營造的新型競爭生態(tài)重塑傳統(tǒng)競爭關系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兩點:
其一,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非同業(yè)平臺經(jīng)營者之間存在流量競爭。流量是衡量平臺價值的基礎,平臺通過對流量的吸引奪取此消彼長的競爭優(yōu)勢,并經(jīng)由特定模式將其變現(xiàn)盈利,對流量的爭奪與對競品流量的損害是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競爭區(qū)別于傳統(tǒng)競爭的主要特點之一。
其二,跨界競爭已成為平臺經(jīng)營主要競爭模式。大數(shù)據(jù)產品具有網(wǎng)絡外部性與鎖定效應,前者代表產品價值與用戶規(guī)模呈正相關,后者意為平臺用戶因網(wǎng)絡外部性的作用被鎖定,具有較強的使用慣性。處于平臺經(jīng)濟核心地位的平臺企業(yè)在商業(yè)模式上通過創(chuàng)新大數(shù)據(jù)產品提升用戶體驗,促進多邊用戶的交互作用在用戶組間產生正向網(wǎng)絡交叉效應。基于用戶體量優(yōu)勢與產品鎖定效應,平臺極易將一個市場的競爭優(yōu)勢傳遞到另一個市場,跨市場競爭使得處于不同細分網(wǎng)絡服務領域下的經(jīng)營者具有直接競爭關系。在此種覆蓋整個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的統(tǒng)合型競爭下,囿于特定或相對關系進行評價已不再適當,司法實踐業(yè)已打破和拓展傳統(tǒng)同業(yè)競爭轉向廣義的競爭關系。
3 我國司法實踐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行為不正當競爭認定現(xiàn)狀及困境
3.1 立法現(xiàn)狀: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文本設置存在局限
數(shù)據(jù)不正當競爭糾紛中,《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可適用的規(guī)范有新法所增設的第十二條“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以及一般條款,其中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的設置是對當前瞬息萬變的新型競爭行為的積極回應。根據(jù)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適用窮盡前者方能存在適用后者的空間,一般條款的保護方式是立法上的次優(yōu)選擇。具體到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的認定上,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第二款前三項的類型化規(guī)定既不周延也不互斥,難以歸入其中,而兜底條款中對“妨礙、破壞”“正常運行”的具體構成要件語焉不詳,裁量空間較大,可操作性較弱。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在實踐中的適用頻次和效果也印證了這一點,故而訴諸一般條款進行認定。
3.2 司法現(xiàn)狀:法官裁量尺度不一且易向一般條款“逃逸”
如前所述,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的構造本身并非完全封閉的列舉,兜底條款的設置實際上賦予了該條較廣的輻射力,特別是提供了轉向適用一般條款的空間,加之現(xiàn)有法律對于大數(shù)據(jù)產品的定性與具體保護路徑闕如,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通過法官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的個人理解加之法律原則、立法目的等補充進行處理。其中,法官個人的價值判斷和理論選擇都將影響案件的定性與裁量,且一般條款雖更具靈活性但其調整范圍也較為模糊,對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yè)道德等內容的判斷無法統(tǒng)一,故而依賴一般條款對大數(shù)據(jù)產品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規(guī)制,既存在濫用一般條款之嫌,也并非這一問題的最優(yōu)解。
有論者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的兜底條款針對性更強,與大數(shù)據(jù)產品不正當競爭糾紛適用契合度更高,適用該條款可以分解一般條款的適用壓力。但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自身的局限性,從既有相關案件看,法院在解釋適用互聯(lián)網(wǎng)兜底條款時仍傾向于從一般條款中尋求釋法說理路徑,出現(xiàn)“以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之名,行一般條款之實”的傾向,或者拒絕具體規(guī)則的涵攝,徑直向一般條款逃逸。并未被直接列舉規(guī)定的大數(shù)據(jù)產品糾紛同樣存在兜底條款適用模糊的問題,具體司法適用條件需在個案中予以提煉。
4 完善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類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的建議——以《解釋(征求意見稿)》為視角
4.1 優(yōu)化與彌補相關法律規(guī)范架構
4.1.1 細化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適用條件
以前揭問題為導向,應基于平臺經(jīng)濟新競爭生態(tài)特點進一步釋放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適用效能,將構成“妨礙、破壞”對產品或服務正常運行的條件進一步明晰。《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五條對此有所體現(xiàn),該條對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適用條件進行了細化,并引入了對公共利益、經(jīng)營者利益與消費者利益“三元疊加”利益的考量,反映了司法對一般條款適用利益判斷原則的有效借鑒。
然而,《解釋(征求意見稿)》將適用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要求提高至需說明五個要件的同時,適用一般條款的認定要件反而更少,這是否會倒逼審判中進一步向一般條款逃逸?筆者認為,法院在數(shù)據(jù)不正當競爭糾紛中應秉承謙抑的司法態(tài)度適用一般條款,并嚴格遵循適用窮盡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方能存在一般條款適用空間的邏輯,避免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在審判中被空置。但僅規(guī)范兩條款的適用順位尚不能完全回應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可能被架空的問題,仍需增加一定的限制。因此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適用要件不應高于一般條款,通過解釋的方式對其進行補充時應更為審慎。
4.1.2 通過立法豐富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類型化規(guī)定
司法實踐的經(jīng)驗表明,現(xiàn)行競爭法體系尚不足以回應紛繁復雜的互聯(lián)網(wǎng)新型競爭帶來的挑戰(zhàn),故在規(guī)范現(xiàn)有條款適用的基礎上,通過立法不斷更新、豐富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類型化規(guī)定的重要性毋庸諱言。這一點在《禁止網(wǎng)絡不正當競爭行為規(guī)定(公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guī)定(征求意見稿)》)根據(jù)實踐經(jīng)驗增加了對數(shù)據(jù)爬取、“二選一”等行為規(guī)定的設計中也可窺見一斑。
4.2 調整競爭關系定位,革新競爭行為正當性判定理念
在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下中競爭行為與競爭關系并不發(fā)生必然邏輯聯(lián)系的底色下,競爭關系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功能定位已呈現(xiàn)淡化趨勢,實務中已有觀點認為,競爭關系不再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起點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多元利益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而競爭行為的正當性判定是不正當競爭認定的肯綮之處,平臺經(jīng)濟顛覆和重塑下的新競爭模式也推動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guī)制路徑進階至行為正當模式。但司法實踐對于數(shù)據(jù)抓取行為的正當性認定缺陷尚存,評價競爭行為正當性的說理證明簡單、價值判斷模糊,對經(jīng)營者利益考量稍顯單薄。故而在大數(shù)據(jù)產品抓取行為的不正當競爭認定中,應堅持競爭法的價值取向,革新競爭行為正當性判定理念,同時擺脫欲判定行為正當與否首先需要判斷是否存在競爭關系的思維定式。
4.3 引入實質性替代標準
司法實踐中,實質性替代是構成不正當競爭的重要因素,是認定數(shù)據(jù)不正當競爭的損害結果標準。由于誠實信用原則與商業(yè)道德存在一定抽象性與模糊性,在規(guī)制數(shù)據(jù)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實踐中應更多綜合客觀標準予以判斷。而實質性替代標準既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yè)道德的客觀體現(xiàn),也是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兜底條款的具體化。《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六條表達了實質性替代標準的肯認,進一步限定了保護數(shù)據(jù)類型,強調經(jīng)營者不得通過非法手段抓取數(shù)據(jù),進而對其他經(jīng)營者提供的相關產品或服務產生實質性替代,《規(guī)定(征求意見稿)》亦采取了同樣的態(tài)度。
目前實質性替代的認定標準爭議尚存,亟須明晰。“實質性替代”本就是一種客觀事實,產品或者服務之間相似度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實質性替代結果發(fā)生與否,應從數(shù)據(jù)控制者相關產品用戶的視角出發(fā),充分考慮用戶是否能夠通過被訴行為達到獲取所需服務的實際效果,使用目的是否已經(jīng)實現(xiàn)。此外,具體表現(xiàn)為損害數(shù)據(jù)產品服務生態(tài)以及惡意破壞用戶黏性等對于網(wǎng)絡運營者潛在利益或平臺商業(yè)模式的侵害也正成為識別是否構成實質性替代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