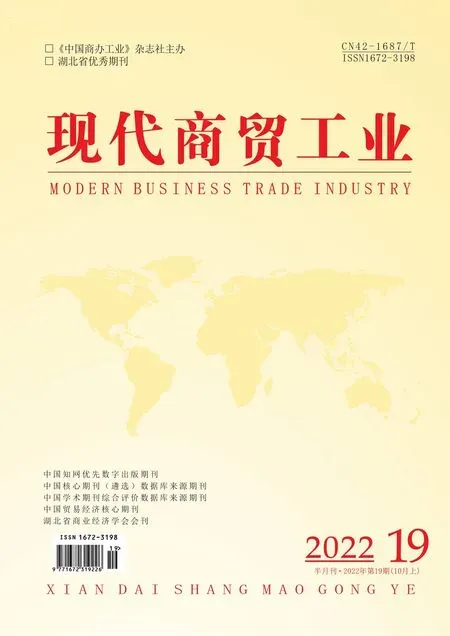數字貿易內涵、規則及其影響研究:一個文獻綜述
朱 強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浙江 杭州 310000)
1 數字貿易的內涵
數字貿易前身是電子商務,并且因為跨境電子商務的蓬勃和數字技術的創新使得數字貿易這一概念脫穎而出。由于各國數字貿易發展水平不一,且對所制定出來的數字貿易商品范圍的接受程度目前也是各執己見,國際關于數字貿易的相關協定也是在不斷協商之中。所以學術界尚未有一個對數字貿易的權威定義。
1.1 國外對數字貿易概念的定義
國外對于數字貿易的認識分為以下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只是的把數字貿易當作是純粹的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
第二種觀點,進一步把數字貿易過程中的實體產品和帶有數字化特征的實體產品包含進來。
單純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201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報告中最早將數字貿易狹義地定義為“通過互聯網傳輸而實現的產品與服務的商業活動”。從USITC對數字貿易的最初定義來看,很明顯其著重突出貿易標的物是無形的,即一切貿易活動發生的過程與商品都是數字化的,此時的定義無疑是狹隘的。但在2017年8月,USITC在《全球數字貿易1:市場機遇與外貿限制》里再次縮小了范圍:“任何產業內公司通過互聯網提交的產品及服務。通過固定線路或無線數字網絡提供產品和服務”,對2013年的定義進行了沿用。
包含了數字化特征的物理產品。2014年USITC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第二次報告中所闡述的數字貿易明顯具有更深一層次的概念:“基于互聯網和互聯網技術的國內商業和國際貿易活動。其中,互聯網和互聯網技術在組織協調、生產或者傳遞產品、服務方面扮演重要的作用。”這是被目前學術界較為認可的一種定義。2015年歐盟提出了“數字化單一市場”概念,并認為數字貿易是利用數字技術向個人和企業提供數字產品和服務。三大國際組織(OECD、WTO和IMF)一致認為,數字技術是數字貿易的支撐,實現貨物與服務線上或線下交付。
1.2 我國研究機構的定義
我國對數字貿易的研究同樣分叉成兩條路。中國信通院根據2019年的《數字貿易發展與影響白皮書》定義數字貿易為“信息通信技術發揮重要作用的貿易形式,其不僅包括基于信息通信技術開展的線上宣傳、交易、結算等促成的實物商品貿易,還包括通過信息通信網絡(語音和數據網絡等)傳輸的數字服務貿易,如數據、數字產品、數字化服務等貿易”。而中國工信院又認為:“數字貿易是以數字技術為內在驅動力,以信息通信網絡為主要交付形式,以服務和數據為主要標的跨境交易活動。”顯然工信院強調的數字貿易不包括物理商品交易。
上述可見,不僅國際上對待數字貿易具有分歧,國內研究機構對待數字貿易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成果與看法,分歧的主要觀點還是貨物是否數字化這個關鍵點上,目前國際上對這一點也還是沒有統一的明確規定。根據國內國際權威機構發布的數字貿易相關定義,以美國為首的數字強國對數字貿易的定義更具有權威性,由于我國還未在區域貿易合作中正式用以數字貿易進行談判,更多的還是以電子商務形式進行國際合作,因此本文更傾向于信通院給出的數字貿易定義與內涵。
2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
目前以美國、歐盟等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著數字貿易規則制定話語權,本文主要對具有代表性的美歐數字貿易規則進行梳理。
2.1 最具代表性的“美式模板”
數字化發展以來,美國為了實現數字貿易強國,不僅率先對數字貿易做出了定義,也是世界第一個將數字貿易規則作為一條獨立條款寫進了其主導的雙邊貿易協定里面的國家。從單個經濟體來看,美國在2019年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數字服務規模(進出口總額8450.3億美元),全球市場占比更是達到了16.7%。
從2000年美國—約旦FTA開始,到2003年美國—新加坡FTA,再到2015年美國主導的TPP協定,分別出現了第一個具有非約束力的電子商務章,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電子商務章以及整套完整的數字貿易章,美式模板越來越完善且貿易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目前關于研究數字貿易規則的熱點大致可分為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源代碼非強制本地化以及個人信息保護等幾個方面(Aaronson,2016)。Mikic(2009)提出,美國早期構建數字貿易規則主要集中在電子傳輸免關稅、貿易無紙化、透明度和數字產品非歧視性待遇等方面。2020年美國、墨西哥、加拿大達成的《美墨加協定》(USMCA)直接以《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作為基礎,并對其某些既有規則進行深化與擴展(如刪除了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例外規定等),并引入一些新的更大適用范圍條款。USMCA是體現目前美國最高水平數字貿易規則“美式模板”的代表。
2.2 特性鮮明的“歐式模板”
目前全球范圍內的服務數字內容出口領域,歐盟占了主要部分。數據表明,歐盟ICT服務出口在2011年到2018年七年間,從2095.5億美元上漲到了3068.7億美元,出口額已經占據了全球54%。并且歐盟的數字貿易規則零散地分布在電信章、知識產權章、投資章以及金融章,并未完整的成章成節,涉及數字貿易的條款也零散地分布在這些不同的章節之中(表1)。歐式模板和美式模板最大的不同在于歐式模板大部分內容僅局限于歐盟內部,少部分零星分散于區域貿易協定中,在國際上遠不如美式模板的滲透式影響。

表1 歐盟數字貿易規則分布及內容
歐式模板最主要的幾個內容包括:文化例外原則、數字市場一體化、跨境數據自由流動以及數字稅。國際上,歐盟除了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則,還特別在服務貿易章節的通則中附上視聽例外條款,但歐盟擔心在文化領域過于強硬的話語會導致自身文化發展受阻,故此“文化合作”措施又孕育而生。但這很顯然是歐盟的緩兵之計,該措施流于表面,明顯缺乏促進彼此文化交流合作的誠心。歐盟2015年開始正式發布《數字化單一市場》,宣布了支持其數字化戰略的三大支柱:提供給消費者以及企業更好的數字產品和服務;創造蓬勃發展的數字網絡和服務的環境;最大化發掘歐洲數字經濟的增長潛力。跨境數據自由流動方面,對外歐盟和美國相繼簽署了《安全港協議》《隱私盾協議》,但因無法平衡“跨境數據自由流動”與“隱私保護”,兩方協議也陸續失效。歐盟內部,2018年歐盟頒布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數據保護法”。具體是說,只要是在歐盟內部的機構,其數據的交互流動不受地域限制都受GDPR的監管;而在歐盟境內沒有設立機構,但給歐盟內的群體提供數字商品或服務時也受GDPR的監管。征收數字服務稅方面,2018年歐盟委員會提出數字服務稅方案,提議對通過用戶參與的數字服務活動征收3%的流轉稅。但該提案在歐盟內部國家分歧嚴重,未能達成統一征收標準,因此歐盟內部國家都在實行符合自己利益的數字稅方案。
2.3 美歐模板的比較
前文對數字貿易規則“美式模板”和“歐式模板”進行梳理,本節從橫向選取了數據監管、市場準入、數字平臺管理、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數字壁壘五個方面來對“美式模板”和“歐式模板”進行比較(表2)。

表2 “美式模板”與“歐式模板”的比較
兩國數字貿易規則在這五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開放程度,從表中來看,美式模板在這五方面基本都做到了自由開放和體系完整,而歐式模板則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許多限制條件以及嚴格的管控。但美歐也在數字平臺管理以及知識產權保護上意見統一,都給予了開放和保護態度。
3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演變對中國的影響
目前,我國數字貿易的規模(2019年)已經突破了1.4萬億,同比增長19.0%;出口總額7869.5億元,同比增長21.7%;總進口額5995.6億元,同比增長15.6%;貿易順差1873.9億元,同比增長46.1%。當前美歐等發達國家試圖主導全球數字貿易規則,中國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刻不容緩:
(1)美歐等發達國家企圖統一全球數據流通,掌握數據流通規則話語權。謀求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共識是美歐等發達國家共同訴求,尤其在拜登上臺之后,雙方在數據保護方面逐漸達成共識。藍慶新(2019)提出美歐日數據流通“朋友圈”的觀點,認為跨境數據互通可以幫助美歐等發達國家打造垂直型數字分工模式,以其核心技術和數據來滲透底端發展中國家。
(2)中國與美歐數字貿易訴求分歧較大,難以融入國際主流。美歐之間雖然在個人數據隱私保護程度和方式上存在分歧,但均主張開放全球市場以及反對強制技術轉讓;中國的數字貿易規則基本上可以用跨境電商規則來覆蓋,十分重視國家安全以及消費者個人隱私的保護,并且有數據本地化的要求,目前來說分歧較大,會倒逼發達國家互相靠攏,不利于中國參與全球數字貿易競爭。
(3)數據監管滯后,抵御美歐數字貿易規則沖突能力缺乏。“棱鏡門”事件發生后,各國清楚了解了美國的網絡霸權,對網絡安全越發重視,關于數字網絡安全的問題更是絞盡腦汁。對比歐盟的GDPR條例,我國數據跨境流動與個人隱私保護相關立法仍在醞釀階段,數據分類分級標準亟待完善,在與美歐數據流通之后難免會產生個數據安全問題,因此對于這方面的法律以及監管體系的構建也是中國和國際進行數字貿易談判的必要前提。
4 啟示
目前,美歐就“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及“個人隱私保護”方面一直未能達成一致訴求,中國可以在不損害我國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平衡數據的開放、監管和隱私性。同時我國應積極與“一帶一路”國家開展雙邊數字貿易規則洽談,建立相關糾紛解決機制和數字貿易合作機制,幫助沿線國家改進和完善大數據、云計算、金融支付等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最后我國應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跨境電商領域,完善構建跨境電商規則,同時完善我國的《數據安全法》,平衡數據的“開放”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