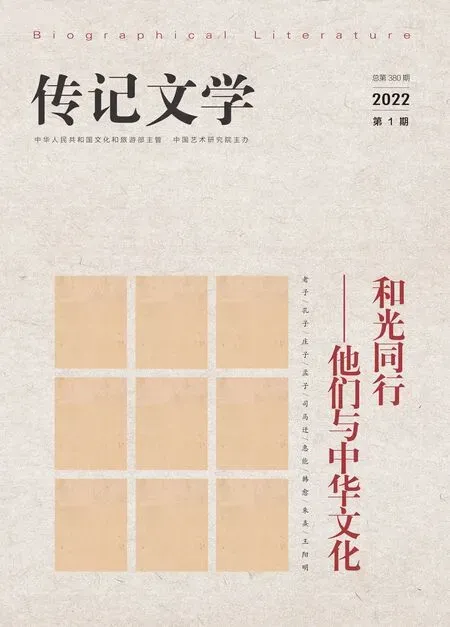《梅艷芳》:建構(gòu)傳記電影中的“情動”機制
孟 琪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生院
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不斷形塑著電影的外在形態(tài)和敘事內(nèi)核,改變著觀眾固有的視聽經(jīng)驗。傳記片的創(chuàng)作也在技術(shù)賦能后,拓展出更為豐富的表達(dá)場域,突破了原有的時空界限,且在題材、形式等方面也不斷迭代創(chuàng)新。作為一部以“時代巨星隕落”這一帶有群體性“創(chuàng)傷”記憶的事件為核心的傳記片,《梅艷芳》不失為此種轉(zhuǎn)向的例證,即由對歷史的重現(xiàn)逐漸轉(zhuǎn)為對記憶中主題、人物的重塑,以貼近當(dāng)下觀眾的視角,實現(xiàn)歷史與當(dāng)下的“回環(huán)”,進(jìn)而通過對“創(chuàng)傷事件”的重現(xiàn),為觀眾提供了一個聚焦已逝年代的微觀視角。
“香港的女兒”
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梅艷芳》在中國大陸地區(qū)票房已達(dá)到1.1億元人民幣,在中國香港地區(qū)票房也已超過5130萬港元。或許,這一數(shù)據(jù)放置于中國電影票房格局中并不算特別出色,但是,因梅艷芳的身份,對中國香港地區(qū)的票房成績予以審析,才更能透過其商業(yè)價值和對影迷發(fā)揮的詢喚作用,對影片進(jìn)行更為深入的辨析。
當(dāng)下中國香港的電影市場中,一方面,國外電影的大量涌入持續(xù)對港產(chǎn)電影作品施壓,不斷擠占市場份額;另一方面,中國香港影片的出品數(shù)量相較之前嚴(yán)重縮水。在這種語境下,5年來中國香港年度票房成績“TOP10”中,港產(chǎn)片能夠躋身其中的并不多。從2017年到2019年,未能有一部港產(chǎn)片入圍。直到2020年,受疫情影響,全球電影生產(chǎn)數(shù)量銳減,好萊塢影片頻繁在中國香港撤檔,港產(chǎn)片才有所表現(xiàn),但也僅有《乜代宗師》《幻愛》兩部作品躋身年度票房“TOP10”;2021年,全球疫情陰霾還未完全散去,港產(chǎn)片創(chuàng)作依舊維持兩部的數(shù)量進(jìn)入總票房前10名,而《梅艷芳》便位列其中,并獲得了全年港產(chǎn)片的票房冠軍。
在中國香港,“梅艷芳”這個名字有著特殊的文化含義,其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明星身份,進(jìn)而與當(dāng)?shù)氐纳鐣⑽幕c歷史等多方面相關(guān)聯(lián)。正如影片《梅艷芳》在結(jié)尾時的字幕所示,梅艷芳不僅是一代歌星與影星,更是“香港的女兒”,影片也即是通過她的這一“聯(lián)動”性身份,實現(xiàn)了一次傳記片的“情動”經(jīng)濟嘗試。
“情動”理論盛行于20世紀(jì)90年代,其“以情感為理論焦點,側(cè)重于研究情緒歷史的復(fù)雜敘述,超越了基于修辭學(xué)和符號學(xué)的研究范式”。“情動”(affect)這一概念,由荷蘭哲學(xué)家斯賓諾莎最先提出,認(rèn)為情動是一種身體與心靈協(xié)同,主動或被動地與情感、情緒等相關(guān)聯(lián)的過程,同時,他“把情感理解為身體的感觸,這些感觸使身體活動的力量增進(jìn)或減退,順暢或阻礙,而這些情感或感觸的觀念同時亦隨之增進(jìn)或減退,順暢或阻礙”。法國哲學(xué)家德勒茲對此進(jìn)一步闡釋,他認(rèn)為情動的產(chǎn)生不僅源于身體與身體的間互性,同時也源于對周圍事物的情感聯(lián)動。他指出,人不是一個被動的效應(yīng),不是一個被塑造出來的寂靜之物,而是一個情感的流變過程,是一個永恒的流變過程。從“情動”理論出發(fā)審視《梅艷芳》這部影片,便不難發(fā)現(xiàn),其從制作、宣發(fā)等各個方面均設(shè)置了“情動”切口。
首先,作為傳記片,梅艷芳無疑是影片最大的看點,但她所在的時代又與當(dāng)下距離過近,且作為跨時代的巨星,她顯然是一種無法復(fù)制或難以再現(xiàn)的想象。因此,為了增加影響力,影片在公映前半年就開始宣傳,并將物的“情動”性也囊括進(jìn)來,比如在放出的預(yù)告片中,不僅有梅艷芳一生的縮影,同時還有如荔園、妙麗中心、利舞臺等用CG技術(shù)還原的舊時香港的標(biāo)志性地景,通過對“非人的、物化的情動標(biāo)簽”的強調(diào),在觸動粉絲之余,以情懷激起普通受眾的觀影欲望。
其次,影片作為時間跨度較長的“史詩”類作品,除了梅艷芳之外,香港也成為其中的主角。片中借由梅艷芳這一視角呈現(xiàn)的,不僅是她作為歌手、影星的一生,更是香港跨世紀(jì)的流變,以一種“既是看梅艷芳,也是看身處黃金時代的香港”的“雙主角”式情感疊加吸引觀眾。
最后,懷舊主題是影片激起觀眾“情動”的又一視角。其實,在中國香港的電影中,懷舊主題并不是《梅艷芳》這部影片獨有的特色。從21世紀(jì)初期開始,在《金雞》(2002)、《歲 月神偷》(2010)等影片中,懷舊就已經(jīng)成為中國香港電影的“代名詞”,其中的情愫,也并不僅僅指向過去,而是更多給當(dāng)下人以希望。影片《梅艷芳》在此時上映,可以說正中中國香港當(dāng)下的境遇,其中對“非典”時期的呈現(xiàn)以及隨之而來的梅艷芳最后的歲月,讓影片處于一種微妙的時空節(jié)點上:它存在于過去,卻又暗含著對未來的某種期許。這種期許既是梅艷芳作為“香港的女兒”,自身的拼搏精神與拒絕移民、終身奉獻(xiàn)于香港的勇氣和堅毅,同時也是對當(dāng)下正飽受新冠病毒困擾的港人的鼓舞與提振。在這里,對病毒的“同構(gòu)”,將香港建構(gòu)成一個多重時空并置的場域。
正如斯賓諾莎和德勒茲所述,身體與身體,或者說身體與物之間“是相互的感觸,是一種內(nèi)在性的沒有縫隙的接壤,是接壤的刺激和招惹,是關(guān)聯(lián)性的一波一波的煽動,是觸碰之后的回音和共鳴”。以上三方面,無疑是影片對觀眾與文本之間關(guān)聯(lián)性的淺層接壤,構(gòu)成了《梅艷芳》票房成績背后的潛在動因,而更為深層的“情動”機制,其落腳點還在于影片的文本之中。
時空縫合、人物的成長與精神共鳴
《梅艷芳》的票房成績,絕不僅是一次關(guān)于“情動”經(jīng)濟的嘗試這么簡單,最重要的還是影片在文本層面對觀眾深層情感的調(diào)動。如前文所述,如若將“情動”經(jīng)濟作為讓觀眾走進(jìn)影院的“情動”切口,那么,影片文本所要建構(gòu)的必然是這種“情動”觸發(fā)下的情感傳遞。基于此,設(shè)置“情動”機制成為文本層面亟須完成的任務(wù)。影片通過對梅艷芳經(jīng)典歌曲的選用、人生重要節(jié)點的紀(jì)錄影像,將真實與搬演、歷史時空與當(dāng)下時空縫合在一起,在聲音參與敘事的同時,勾連起人物的成長歷程,并將孕育的香港精神滲透其中,從時空并置、人物塑造和精神傳承三方面,逐漸完成了其“情動”機制的建構(gòu)。
影片采用“畫中畫”的結(jié)構(gòu),以紅館舞臺的告別演唱會開始,回溯至梅艷芳從荔園舞臺階段開始的演藝歷程,最終結(jié)尾再次落腳于告別演唱會,完成結(jié)構(gòu)“閉環(huán)”,以“編年體”式的線性敘事展現(xiàn)了她近乎一生的歲月:從“宿命”般地進(jìn)入演藝圈,到后來一路走紅成為香港巨星,再到歌廳被“掌摑”事件的沉寂,最后到堅持重回舞臺的堅毅。在這起承轉(zhuǎn)合中,影片雖為單線敘事,但在時空架構(gòu)方面采用了紀(jì)錄影像與影片文本交叉剪輯的方式,通過梅艷芳的銀幕再現(xiàn),一方面激起了觀眾內(nèi)在情感的涌出;另一方面也在影像的轉(zhuǎn)換中,中斷了觀眾潛在的連貫性觀影情緒,打破了時空再現(xiàn)鏈條的完整性。在影片為數(shù)不多的紀(jì)錄片段中,梅艷芳的身影既是“情動”的入口,同時也是“情動”的出口。影片為此巧妙地選用梅艷芳在幾次人生重要節(jié)點中的歌曲演唱片段如《風(fēng)的季節(jié)》《心債》《夕陽之歌》等,作為文本轉(zhuǎn)換的場景,讓聲音參與進(jìn)敘事的同時也完成了梅艷芳此時內(nèi)心情感的外化表達(dá)。這種雙重時空的縫合,促成了影片背后的情感邏輯:當(dāng)梅艷芳在觀眾內(nèi)心的追憶能指被無限擴大,當(dāng)傳記片的可塑性不斷被擴寫的同時,那些存在于觀眾記憶中,被反復(fù)回味的真實影像,最終都與影片文本融為一體,拓展為對整個香港黃金年代的情愫,引起大眾的廣泛共鳴。
影片“情動”機制建構(gòu)的另一方面來自于對梅艷芳人物的塑造。因為是傳記片,影片的情節(jié)離不開真實的過往,但是,如何在真實的基礎(chǔ)上對人物性格予以突顯?《梅艷芳》對此進(jìn)行了探索。在香港社會,梅艷芳的人物成長如同一個英雄的成長。“經(jīng)典傳記片強調(diào)英雄人物挑戰(zhàn)‘困境’而以‘凱旋’告終。”影片也即是將視角落在梅艷芳的演藝事業(yè)中,并由此建構(gòu)了一個女性英雄的成長之旅。在約瑟夫·坎貝爾的論述中,英雄的塑造有一套相對固定的模式:“出生起就被賦予了非凡的力量”;“命中注定的孩子不得不面對長期的默默無聞”;結(jié)束童年的冒險、英雄性格顯露;取得第一階段的勝利;遭遇挫折和打擊;在次要人物的協(xié)助下重返戰(zhàn)場;完成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成長,同時這種成長可能也伴隨著英雄的離去。這一英雄的成長模式被完美地復(fù)刻在影片中,不僅在開片部分呈現(xiàn)了她的歌唱天賦,同時兒時的荔園舞臺、消失的父親、兄弟姐妹中僅她一人在香港出生、女身男聲等特點的強化,突顯了她被“非凡力量”賦予的人生起點——為舞臺而生。之后情節(jié)的發(fā)展也正如上述模式一般,梅艷芳經(jīng)歷了第一階段的輝煌后,失戀與“掌摑”事件讓她陷入沉寂,最終在劉培基、蘇孝良等“代父”角色的幫助下,重回舞臺,完成了英雄的成長與離去。在坎貝爾的觀念中,“充滿生命渴望的英雄能抗拒死亡并將其推遲……如果死亡帶給英雄任何恐懼,那么英雄便不是英雄了。第一個條件是與墳?zāi)惯_(dá)成和解”,“他只是睡著了……或者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于我們當(dāng)中”。梅艷芳的離世無疑是“離去的英雄”的最好注解,同時這也引出了影片第三層面的“情動”建構(gòu)——精神的共鳴。
在《梅艷芳》中,這種精神不僅僅體現(xiàn)在她自身的奮斗與拼搏,以及作為一個公眾人物身兼的社會責(zé)任、奉獻(xiàn)意識,更重要的還是整個香港演藝圈,甚至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精神傳承。正如劉培基在影片中所說的,“前輩提拔后輩是天經(jīng)地義”,從梅艷芳在眾多前輩的幫助下走紅,到她演唱會為徒弟提供機會,讓他擔(dān)任監(jiān)制,并再次重復(fù)那句“前輩提拔后輩是天經(jīng)地義”。影片無疑以傳承為核心,達(dá)成了敘事與表意的閉環(huán),也正是這一主題的表達(dá),讓影片在展現(xiàn)“今非昔比”的香港時,擁有了指向未來的期許和魅力。
身體的凝視與主體性的召喚
在“情動”理論中,身體是承載“情動”的場域;而在傳記片中,身體的顯影也成為其重要的“情動”機關(guān),由此開啟受眾在影片中主體性的代入。但矛盾的是,在傳記片中,身體往往會陷入一種悖反的困境。一方面,演員是過往真實的載體,其往往承擔(dān)著傳記人物自身的多層次含義;但另一方面,演員同時又是自己,是其自我與過往作品中所演繹的人物的合體。這種矛盾性通常會促成影片的兩種走向——多層次的“情動”體驗與受阻的主體性召喚。
對于前者來說,關(guān)錦鵬在1991年導(dǎo)演的《阮玲玉》是很好的例證,影片通過紀(jì)錄片、影像史料和張曼玉的演繹三條線索,將20世紀(jì)30年代的上海與90年代的香港并置,詮釋出作為演員的張曼玉和作為傳記人物的阮玲玉的多義性的身體,賦予了阮玲玉新的生命力。但是,在《梅艷芳》中,演員王丹妮的出演卻讓傳記片的身體呈現(xiàn)陷入吊詭。一方面,王丹妮與梅艷芳在外形,特別是側(cè)臉的剪影上的神似,讓影片在關(guān)于梅艷芳的生活紀(jì)錄影像有限的情況下,拓展了傳記片可以表達(dá)的邊界,擴大了影片的敘事空間,豐富了影片對傳記人物的可塑性;但另一方面,王丹妮作為演藝界的新人,在沒有表演經(jīng)驗以及過往作品中的形象積累的基礎(chǔ)上,又造成了觀眾想象的匱乏,削弱了影片更深層次的藝術(shù)探索。特別是在對面孔的凝視時,影片多次用特寫鏡頭,讓王丹妮的面孔充斥整塊銀幕,意圖將梅艷芳的內(nèi)心情感可視化,同時力圖打破 “第四面墻”,向銀幕前的觀眾示意召喚。但是,此刻特寫鏡頭對人物內(nèi)心情感的表露和質(zhì)詢作用,顯然是失效的。在列維納斯的觀念中,面孔是一種他者的存在,“但是他者,絕對他者——他人——并不限制同一的自由。在把這種自由喚向責(zé)任的同時,他也創(chuàng)建這種自由并為其進(jìn)行辯護(hù)”。基于此,作為他者的面孔,成為觀者對影片中有限內(nèi)容所引發(fā)的無限思想外溢的切口,并時刻提醒著觀者對他者境遇的體驗與思考。而在《梅艷芳》中,特寫的面孔不僅放大了演員刻意模仿的缺陷,甚至成為觀眾代入影片情緒的某種困擾——在連貫的敘事中,特寫的面孔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們,這是虛構(gòu)的。這其中的矛盾并不在于王丹妮與梅艷芳是否真的相似,而是在于在觀眾對演員的情緒跳脫之后,影片沒有給予觀眾更深層次思考的余地。
顯然,在這種身體凝視的失效中,影片對觀眾主體性的召喚也產(chǎn)生了阻礙。《梅艷芳》對觀眾群體的詢喚大致包含三個范疇:粉絲群體、女性受眾與普通觀眾。粉絲群體作為最可靠的受眾基礎(chǔ),影片所賦予他們的吸引力自然無需多言;而普通觀眾作為可商榷的對象,亦能從影片的情懷建構(gòu)、精神共鳴等方面竭力爭取。除了這兩者之外,影片作為女性傳記片,女性觀眾實則處于前兩者之間的交叉地帶,她們或從屬于粉絲群體,試圖在迷戀之外尋找到梅艷芳作為女性所獨具的特質(zhì)進(jìn)行主體代入;或從屬于普通觀眾,通過影片中梅艷芳所體現(xiàn)的女性自覺達(dá)成共鳴。但應(yīng)該澄清的是,影片對于梅艷芳的刻畫卻止步于一種徘徊在無性別與女性意識之間的游離狀態(tài):遺憾的戀情、對婚姻的渴望以及對父權(quán)的依戀等,無疑將梅艷芳視作一位傳統(tǒng)女性的形象予以展現(xiàn);而對女相男聲特質(zhì)的強化、女扮男裝的演出“戰(zhàn)服”以及對其英雄化的塑造和對義氣、情懷的書寫,卻都以“史詩”類影片慣有的,男性習(xí)慣的宏大敘事維度,讓梅艷芳處于一種既彰顯女性自覺,并試圖挑戰(zhàn)男權(quán)社會制度,但又自覺自愿地成為男權(quán)社會產(chǎn)物的矛盾狀態(tài)中。“女扮男裝”或女性的男性氣質(zhì)突顯固然與香港電影或時尚潮流中的“易裝”文化有關(guān),但影片試圖表達(dá)的內(nèi)容過于細(xì)碎,也難免讓其陷入一種寬宏有余卻深度不足的境地。
或許,《梅艷芳》這部影片在文本層面的確存在些許問題,因此受到眾多影迷與觀眾的詬病,但若將其視為一個與香港相關(guān)聯(lián)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來審視,實則瑕不掩瑜。影片試圖呈現(xiàn)的,不僅是傳記片與歷史、文本與受眾之間的對話與勾連,更重要的是,它在此時上映,確是為當(dāng)下提供了一個可回溯的窗口,讓觀眾在互通的情懷中,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自我療慰。基于此,影片的些許不足也變得可以原諒。
注釋:
[1]全球票房數(shù)據(jù)及大陸地區(qū)票房數(shù)據(jù)來源自貓眼專業(yè)版實時票房:https://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 ;中國香港地區(qū)票房數(shù)據(jù)截止到2021年12月5日,來源自香港國際影視展:https://event.hktdc.com/fair/hkfilmart-sc/s/11082-General_Info rmation/%E9%A6%99%E6%B8%AF%E5%9B%BD%E9%99%85%E5%BD%B1%E8%A7%86%E5%B1%95/%E6%AF%8F%E5%91%A8%E7%A5%A8%E6%88%BF.html
[2]劉芊玥:《“情動”理論的譜系》,《文藝?yán)碚撗芯俊?018年第6期。
[3][荷]斯賓諾莎著,賀麟譯: 《倫理學(xué) 知性改進(jìn)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84頁。
[4][6]汪民安:《何謂“情動”?》,《外國文學(xué)》2017年第2期。
[5]戰(zhàn)迪:《情動轉(zhuǎn)向:后批評時代電影理論建設(shè)的一種可能》,《當(dāng)代電影》2020年第3期。
[7]張英進(jìn):《傳記電影的敘事主體與客體:多層次生命寫作的選擇》,《文藝研究》2017年第2期。
[8][9][10][11][12][美]約瑟夫·坎貝爾著,黃玨蘋譯:《千面英雄》,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頁,第292頁,第285—327頁,第320頁,第321頁。
[13][法]伊曼紐爾·列維納斯著,朱剛譯:《總體與無限 論外在性》,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頁。
[14]張英進(jìn)認(rèn)為,這種帶有宏大歷史維度的敘事模式更符合傳統(tǒng)的男性視角,進(jìn)而將《阮玲玉》視為“力圖以女性視角挑戰(zhàn)男性習(xí)慣的宏大歷史敘述”,認(rèn)為許鞍華的“《黃金時代》很大程度上仍然認(rèn)同宏大歷史敘事”,因此,其導(dǎo)演主體性在《黃金時代》中的突顯遠(yuǎn)不如關(guān)錦鵬在《阮玲玉》中的堅定。(參見張英進(jìn):《傳記電影的敘事主體與客體:多層次生命寫作的選擇》,《文藝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