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先生的為人和治學(xué)(一)
趙 明
青島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
公木先生逝世已經(jīng)22年了,但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他始終沒有離去。我做過他的學(xué)術(shù)助手,師從先生十年。其后,雖云山阻隔,仍有十年的書信往來(lái)。甚至,在他逝世半個(gè)月前,我們還有聲息相通。在先生離世后,文藝界、學(xué)術(shù)界許多與他接觸過的人無(wú)不因他真誠(chéng)、寬厚情懷中的人性光輝而緬懷景仰、唏噓感嘆。我從游公木先生近20年,對(duì)于他的為人、治學(xué)都有近距離的觀察和感受。不少了解此情的朋友和學(xué)生,曾建議我把這段歷史寫成文字,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作為《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歌》詞作者顯名于世的公木先生豐富的人生經(jīng)歷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我不能拒絕這個(gè)建議,我對(duì)公木先生的緬懷,不應(yīng)默存于心里。“向前!向前!向前!”以軍歌激越百萬(wàn)將士、提振雄威的公木,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我?guī)煆墓鞠壬嗄辏鶜v、所見、所聞的諸多故事。
公木(1910—1998),原名張永年、張松甫,又名張松如,直隸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歌》詞作者,著名詩(shī)人、學(xué)者、教育家。早年就讀于輔仁大學(xué)、北平大學(xué)第一師范學(xué)院(后改為北平師范大學(xué))國(guó)文系。青年時(shí)期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業(yè),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xué)和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任教,后調(diào)入軍委直屬隊(duì)政治部文藝室任主任。1942年,他聽到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并參與討論。1946年,他赴東北,曾任東北大學(xué)教育長(zhǎng)、東北師范大學(xué)教育長(zhǎng)。“文革”結(jié)束后,歷任吉林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吉林省作協(xié)主席等職。公木先生是“業(yè)余”詩(shī)人,一生都在從事教育管理和教學(xué)研究工作。他是學(xué)識(shí)淵博的學(xué)者,是培育了幾代學(xué)人、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但最重要的是,他追求真理,正直一生,躬盡辛勞,雖屢經(jīng)坎坷而不改初心,成為無(wú)數(shù)后學(xué)心目中人倫師表的楷模。
一朝春暖
1977年,“文革”剛剛結(jié)束。從這個(gè)積雪消融的春天開始,我所在的農(nóng)村,地處長(zhǎng)春郊區(qū)的新立城,已陸陸續(xù)續(xù)有插隊(duì)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我在農(nóng)村生活歷時(shí)8年,早已牢固樹立起扎根農(nóng)村,生于斯、老于斯的念頭。不是我不想回城,而是我沒有任何人脈關(guān)系,沒有什么驕人“資本”去尋找可接收我的單位。我的青年時(shí)代和而立之后長(zhǎng)達(dá)十年的中年期都已結(jié)束。我蹉跎半世,與其返回城里,還不如過著遠(yuǎn)離喧囂、較少人際紛擾的村居生活。在農(nóng)村的日子,也讓我有了另一種收獲:從春雨、夏風(fēng)、冬雪、朝霞、夕暉,到一年四季時(shí)序流轉(zhuǎn)、草木榮枯、萬(wàn)象更變,我從不適應(yīng)到適應(yīng)。在這里遠(yuǎn)比在城市更能親和自然,能夠接受她的撫觸和慰藉。比起城市,農(nóng)村生活確實(shí)很艱苦,我住著兩間草房,夏漏雨、冬透風(fēng),每年都要修葺;住在坡上,沒有水井,一切生活用水,都要到坡下的一口井去汲,回來(lái)便要擔(dān)著兩桶水一路爬坡。這是當(dāng)時(shí)我們基本的生活情況。但比起剛下鄉(xiāng)時(shí)與插隊(duì)知青同住的情況,已是大有改善。自我在農(nóng)村和知青共住兩年之后,在一塊坡地上,我終于建起了一個(gè)屬于自己的“家園”。而我周邊的幾戶村民,也都樸實(shí)、善良,在我們遇到困難時(shí)(如草屋修葺等事),也都會(huì)熱心幫忙。就在1977年的春天,我從幾十里之外的山區(qū)買來(lái)一車柳樹枝,把我這兩間草屋、三分宅基圍成了綠色庭院。我是真的準(zhǔn)備后半生像陶淵明那樣過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生活了。但是,當(dāng)我筑起的“家園”的綠墻又經(jīng)歷了一個(gè)春秋的風(fēng)雨櫛沐,柳條圍墻已成一道綠陰風(fēng)景的時(shí)候,我才如夢(mèng)初醒:眼前的田園生活和所謂“詩(shī)意般地棲居”,能為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兒子長(zhǎng)期接受嗎?做醫(yī)生的妻子想返回長(zhǎng)春工作,并且已經(jīng)收到商調(diào)函;在農(nóng)村長(zhǎng)大,剛剛上小學(xué)的兒子也需要良好的學(xué)習(xí)和成長(zhǎng)環(huán)境。我的“陶潛夢(mèng)”,到了應(yīng)該清醒和立即決斷何去何從的時(shí)刻了。我明白,這一切的關(guān)鍵,在于能不能找到一個(gè)愿意接收我、同時(shí)我也愿意去的工作單位。
我把妻子接到單位商調(diào)函的信息和我求職的想法告訴了在吉林大學(xué)工作的兄嫂,他們分別在哲學(xué)系和中文系任教。嫂嫂李扶乾1961級(jí)吉大畢業(yè)后留校,對(duì)中文系的情況比較了解。這時(shí)已到了1978年的夏秋,1977級(jí)的學(xué)生即將升入大二,1978級(jí)同學(xué)又剛剛?cè)雽W(xué),1979級(jí)的課程安排和師資配備也進(jìn)入了議程,兄嫂所在的系都已引進(jìn)了不少教師。我的想法是哲學(xué)系或者中文系都可以,能進(jìn)入吉大就好。嫂嫂建議我到中文系,并熱心地承擔(dān)了推薦和溝通的工作,但我心里還是很不踏實(shí):荒廢了學(xué)術(shù)青春,繼之又僻居鄉(xiāng)村多年,已屆“不惑”之年而實(shí)“多惑”的我,到底能再做什么?事到臨頭,面對(duì)“大考”,我才發(fā)覺這確實(shí)是個(gè)躲不過的坎。
從程序上來(lái)說(shuō),要調(diào)入系里任教,首先要經(jīng)由教研室做專業(yè)考核,再由系務(wù)會(huì)議討論通過,然后上報(bào)人事處,等待學(xué)校批準(zhǔn)。完成這個(gè)程序要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其中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受阻,我的“戲”就結(jié)束了。我的理想是進(jìn)古典文學(xué)教研室。我的弱點(diǎn)是年齡偏大,而且還缺少考核需要的成果,也沒有和年齡相配的學(xué)術(shù)職稱。這些弱點(diǎn),自然會(huì)在古典文學(xué)教研室的引進(jìn)工作中觸及并討論。這時(shí),擔(dān)任系領(lǐng)導(dǎo)的程書記向我透露一個(gè)重要信息:已屆古稀之年的公木先生時(shí)任吉大副校長(zhǎng)兼中文系名譽(yù)主任,此外還兼任多項(xiàng)重要社會(huì)職務(wù),亟須配備一名學(xué)術(shù)助手,目前尚未定人選。如我愿意,他即電話聯(lián)系公木先生。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對(duì)他表示感謝。程書記當(dāng)場(chǎng)打了電話之后,隨手就在桌上撕下便箋,上面寫著:
公木,東中華路33號(hào)201。上午,9點(diǎn)30。
東中華路33號(hào)的公木先生
長(zhǎng)春市東中華路是條整潔而靜謐的短街,它的東出口通向吉林大學(xué)鳴放宮,西出口則通向開闊的地質(zhì)廣場(chǎng)。這條不足千米的短街,竟然泰斗云集,大家薈萃,先后居住過眾多大師級(jí)的學(xué)者,其中數(shù)理化學(xué)科的就有朱光亞、唐敖慶、余瑞璜、吳式樞、王湘浩、高鼎三等人;而文史哲方面則有古文字學(xué)家于省吾,歷史學(xué)家金景芳,詩(shī)人、學(xué)者、教育家公木,作家廢名和哲學(xué)家高清海等。
那是9月中旬一個(gè)風(fēng)和日麗的上午,公木先生約我到他家見面。他住在東中華路33號(hào)被人們習(xí)慣稱作“十八家”的一幢小樓里。這幢建于20世紀(jì)50年代,灰瓦、黃墻、紅院套的3層小樓,因?yàn)榫幼∵^不少名人,我在年輕時(shí)就有耳聞,心向往之,路過時(shí)也曾多次仰望,但惜乎難得一見大師們的儀容趨止。在趕赴東中華路“十八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漸趨緊張,不停地猜想:即將出現(xiàn)在面前的公木先生是延安時(shí)期的老干部,《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歌》、電影《英雄兒女》主題曲的歌詞作者,該有一副怎樣肅肅威嚴(yán)的儀容呢?他的歌詞,連同他的筆名“公木”二字,都讓我聯(lián)想到“革命”“戰(zhàn)斗”“堅(jiān)強(qiáng)”……
想著,想著,我已走進(jìn)了“十八家”的院內(nèi):兩側(cè)幾株喬木在陽(yáng)光下,“涂金”的葉片閃閃發(fā)光;樹邊的田垅里,還剩幾行枯黃了的玉米秸依然挺直;幾個(gè)橘紅色的碩大南瓜橫臥地表,曬著和煦的秋陽(yáng)。看到院內(nèi)這種農(nóng)家景象,一瞬間,我的心情平緩下來(lái),心理上的距離似乎縮短了。我穿過一條小徑直抵一樓門洞,快步走上二樓,在201室門前稍停,看表上時(shí)針到了9:30,正好是約定時(shí)間,我輕觸了門鈴。一位父輩年紀(jì)的長(zhǎng)者從室內(nèi)迎出,我趨前問候,報(bào)上名字,老人直接把我引入臥室里間的房?jī)?nèi)。這是我第一次走進(jìn)一位學(xué)者的書房。除了靠窗的南向,整個(gè)房間排滿了書架,每個(gè)書架上又?jǐn)D滿了書。還有一些書和報(bào)刊,因?yàn)闊o(wú)處容身,暫時(shí)堆放在房間的角落里。南向窗前,有一張黑赭色的寫字臺(tái)和一把竹椅。面對(duì)寫字臺(tái)的方向,擺放著供單人坐的兩只布沙發(fā),也和桌椅一樣,是老家具。我知道面前的人就是公木先生。他見我有些拘謹(jǐn),便先示意我在沙發(fā)上坐下,回身又倒了一杯水給我,然后坐回到他的竹椅上與我相對(duì)。此刻,我的心情已放松下來(lái),并迅速完成了對(duì)公木先生的“掃描”:我面前的長(zhǎng)者中等身材,一身淺灰的便裝,配著黑色的布鞋。說(shuō)不上魁偉,卻足夠挺拔結(jié)實(shí)。方頭寬額,鬢發(fā)雖已花白,眉宇間卻仍透出一縷英氣,端莊的儀容,半顯堅(jiān)毅,半露慈祥;而一雙很有神采的眼睛,也會(huì)讓人感受到非凡的睿智。這次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可謂是重大機(jī)遇性的見面,并不像我事前想象得那么正規(guī)、嚴(yán)肅,而儼然如我和一位長(zhǎng)者之間進(jìn)行的一次親切交談。公木先生從詢問我的個(gè)人經(jīng)歷和家庭情況開始,很自然地把話題引入到讀書和志趣,然后便傾聽我的讀書心得,進(jìn)而對(duì)我作出評(píng)價(jià):他認(rèn)為我對(duì)所讀的書擁有個(gè)人的視角,特別是我對(duì)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學(xué)者王夫之撰寫的《船山遺書》的通讀,使我能夠跟隨王夫之的引領(lǐng),理清從先秦以迄宋明這段時(shí)期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luò)和梗概,這不僅開闊了我的文、史、哲視域,同時(shí)也使我經(jīng)歷了一次很好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王夫之不僅為“六經(jīng)”“別開生面”,而且對(duì)以《論語(yǔ)》《孟子》《老子》《莊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著作和魏晉玄學(xué)、隋唐佛學(xué)、宋明理學(xué)的評(píng)述,也都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在史學(xué)和文學(xué)領(lǐng)域也多有開新之論,如《讀通鑒論》《宋論》《楚辭通釋》及所著《詩(shī)話》的詩(shī)論等,也多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令人服膺。通讀中的專注和思考,于我而言,收獲是遠(yuǎn)大于聽課和讀教科書的。《船山遺書》是我二十幾歲時(shí)下過功夫認(rèn)真讀過,并做了大量文獻(xiàn)卡片和分類評(píng)語(yǔ)的一部大書。我之所以用時(shí)兩年閱讀此書,緣起于1961年年初,吉大哲學(xué)系講授中國(guó)哲學(xué)史的吳錦東老師邀我合作撰寫一部有關(guān)王夫之的專著。他要求我先行通讀全書,做好資料準(zhǔn)備工作,然后再找他商量提綱擬定和分工撰寫等事宜。我好不容易啃下了這個(gè)“大部頭”,待到去找吳老師請(qǐng)領(lǐng)下一步工作任務(wù)時(shí),卻發(fā)現(xiàn)門鎖高掛。到哲學(xué)系問詢吳老師去向,有知情人告知他早已離職回印度尼西亞結(jié)婚(吳老師是華僑),后又到香港經(jīng)商去了。我摘寫的大量資料卡片和幾本閱讀筆記,就這樣成了一堆廢紙,但我并沒有把它們?nèi)拥簦茄b進(jìn)一個(gè)大紙箱中,作為紀(jì)念品保存了下來(lái)。同公木先生的見面,給我提供了一個(gè)自由選題、自由發(fā)揮、展示所長(zhǎng)的機(jī)會(huì),讓我把多年用心做足的功課,集中在一個(gè)多小時(shí)的時(shí)間內(nèi)進(jìn)行了概略陳述。因此,初次面見學(xué)識(shí)淵博的公木先生,我就得到了賞識(shí)。當(dāng)然,這些都不是公木先生直接對(duì)我說(shuō)的,而是事后中文系的領(lǐng)導(dǎo)私下告知我的。我在當(dāng)時(shí)只是感覺公木先生在認(rèn)真而耐心地聽,間有幾次插話提問,并無(wú)任何詰難。最后,當(dāng)我辭別公木先生時(shí),他起身后只簡(jiǎn)短對(duì)我說(shuō)了一句話:“你回去等待吧。”我退出書房,如釋重負(fù),心情完全輕松下來(lái)。返家的路上騎著自行車,50多里的距離,不到兩個(gè)小時(shí)就到了。妻子在家坐臥不寧,一直惦記著今天面試的結(jié)果,當(dāng)我把最后那句話告知她時(shí),我們這才相信8年的農(nóng)村生活即將結(jié)束。晚上,躺在多年睡習(xí)慣了的土炕上,我總是睡不著,想著白天的事:東中華路33號(hào),坐擁“書城”的公木先生,還有他那深邃而慈祥的目光、他傾聽時(shí)的沉思……身旁的妻兒都已入睡。睡炕前的窗欞,浮動(dòng)著徘徊蕩漾的月光,透進(jìn)草屋,有幾縷映射到貼滿舊報(bào)紙的土墻壁上。這一夜,我身如夢(mèng),又似夢(mèng)非夢(mèng)。時(shí)光的流逝、命運(yùn)的起落、偶然的機(jī)緣,有時(shí)真讓人辨不清真與幻、夢(mèng)與覺的界限。
撰《老子校讀》的公木先生
1978年10月初,國(guó)慶節(jié)剛過,我和妻兒告別鄉(xiāng)居,舉家返回長(zhǎng)春。“文革”結(jié)束后,高校住房本已極緊缺,新調(diào)入的人員很少有得到學(xué)校安置住房的。好在,我臨時(shí)在校外借到了一間小房,全家人總算有了落腳之處。芳華雖逝,但我的學(xué)術(shù)青春卻由此展開。
在吉大中文系,公木先生主要從事古典文學(xué)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研究生教學(xué)工作。作為他的助手,我的工作其實(shí)就是在學(xué)習(xí)中協(xié)助,在協(xié)助中學(xué)習(xí)。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準(zhǔn)時(shí)來(lái)到公木先生家中,準(zhǔn)備聽取他的工作交待。

公木先生和他的學(xué)生們,后排居中者為本文作者
但是,當(dāng)我走進(jìn)書房,向正在伏案寫作的公木先生請(qǐng)領(lǐng)工作時(shí),他先是抬頭看了看因?yàn)榘徇w而有些憔悴的我,然后又示意我坐下。我有些不解,公木先生認(rèn)真地問起了我回城后生活如何安排等問題。他顯然清楚,從鄉(xiāng)下回城,住房肯定是一大困難。說(shuō)心里話,工作伊始,能夠聽到公木先生這樣的大學(xué)者問起自己生活中的冷暖困苦,已經(jīng)很令人感動(dòng)了;更意想不到的是,前一天傍晚,公木先生還利用飯后的時(shí)間,穿過東中華路東口,又過了條南北通向的大路,步行到鳴放宮所在的那個(gè)空曠的大院子里(現(xiàn)稱“牡丹苑”),去看他和妻子吳翔老師曾經(jīng)住過的兩間倉(cāng)庫(kù)房。“文革”結(jié)束,這兩間倉(cāng)庫(kù)房在他們搬出之后,便空置起來(lái),被校后勤部門用來(lái)堆放雜物。公木先生看到倉(cāng)庫(kù)房未被他人使用,決定待我到來(lái)后即抓緊時(shí)間去看一看,如果愿意入住,他就找后勤部門疏通一下,以便我盡早把家安頓下來(lái)。我聽后感謝之情難以言表,頓出哽咽之聲,但為極力控制情感,不讓眼淚流出,我沒有迅即回應(yīng)先生。他大概以為我在條件上有所考慮,不愿去住。于是又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這只是暫時(shí)的,眼下學(xué)校實(shí)在困難。我都能住,你有什么不能的!”
就是這句話,讓我思索并回味了幾十年:這里有公木先生的艱辛經(jīng)歷,有他無(wú)懼困苦的堅(jiān)韌意志,但更多的是他對(duì)我現(xiàn)實(shí)困境感同身受的關(guān)懷。是的,長(zhǎng)我近30歲的公木先生能住,我又有什么不能住呢?這個(gè)約有兩間大小的倉(cāng)庫(kù)門房,并不比我在農(nóng)村那兩間草屋差,至少不用我每天爬坡挑水。對(duì)于短暫棲身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是夠“檔次”了。只是因?yàn)榇饲拔乙言谂笥涯抢锝璧搅艘婚g居室,三口之家也還住得開,我不想讓公務(wù)繁忙的先生再為我的家事操心費(fèi)力。但這件事讓我感受到的溫暖,卻永駐于心,終生難忘。半年后,在吉大工作的兄嫂調(diào)入北京工作,而公木先生也出面向?qū)W校總務(wù)部門提出了一個(gè)“合情、合理、合法”的入住理由,我因此搬入他們的兩居室。自此,進(jìn)入了“安居樂業(yè)”的狀態(tài)。
我的助手工作,最早就是從公木先生的老莊研究介入的。在我到來(lái)之前,公木先生傾注了多年心力撰寫的《老子校讀》初稿已近尾聲。我來(lái)后,先生把已竣稿的上編《道經(jīng)》部分4本手稿交給我,讓我先校閱一遍,校閱中有什么想法、建議可記錄下來(lái),隨時(shí)向他提出。在此后的一段時(shí)間里,我的主要注意力也因此投注到研讀《老子》和《莊子》上。
公木先生對(duì)老子的興趣和關(guān)注由來(lái)已久。他晚年撰著《老子校讀》以及脫胎于此書的《老子說(shuō)解》,曾令很多關(guān)心或熟悉他的同事、朋友和學(xué)生們不解:“紅色詩(shī)人”公木,《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歌》《東方紅》《英雄兒女》主題曲這些廣泛傳唱、深有影響的曲目的歌詞作者公木,怎么會(huì)同撰著《老子校讀》的張松如聯(lián)系在一起呢?在別人看來(lái),兩者之間不僅橫著一道難以相融的巨大情感障壁,而且它們文化色彩的反差亦甚鮮明。如果只是把公木看作以詩(shī)歌為戰(zhàn)斗號(hào)角的“詩(shī)人”,我們就難以理解學(xué)者公木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甚至我們也無(wú)從理解革命歲月、戰(zhàn)士經(jīng)歷和歷盡坎坷之旅的公木是怎樣成就了“戰(zhàn)場(chǎng)奏軍歌,人倫樹師表”的人生。
首先,在到延安之前,青年時(shí)期的公木已涉獵了大量的原典、古籍,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孔孟、老莊對(duì)他的精神建構(gòu)必然有所影響;其次,公木的中年和老年時(shí)期,老莊哲學(xué)對(duì)他不無(wú)紓困作用,提供一種精神力量和豁達(dá)情懷。而他晚年撰著《老子校讀》,更因緣于兩件事:第一件事是,1973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長(zhǎng)沙馬王堆發(fā)掘出西漢初期長(zhǎng)沙王丞相利蒼及其家屬的墓葬,其中的大量精美絲織品和包括帛畫、帛書在內(nèi)的珍貴文物得以面世。其中帛書有《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與后世諸多通行本有異。這一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啟發(fā)了公木先生以帛書本《老子》檢驗(yàn)校正后代諸通行本誤讀錯(cuò)簡(jiǎn)的念頭。第二件事是,1973年以后,大學(xué)的文科教學(xué)還缺乏規(guī)劃。公木先生感到迷惘,“因想到老氏之旨,以清虛謙弱自持,或可醫(yī)治我無(wú)補(bǔ)于時(shí)無(wú)濟(jì)于世的忿戾偏激”(《老子校讀》“后記”)。這時(shí),公木先生開始了專注《老子》的著述之路。整整一段時(shí)間,他閉門索居,讀帛書、校《老子》,沒有誰(shuí)知道他在搞什么,只有住在隔壁的古文字學(xué)大家于省吾先生與他相互過往,引為同調(diào),時(shí)有摩研切磋,抑或公木先生于篆籀古文的釋讀有所請(qǐng)教。此外的知音人,就是逾世之交、同在長(zhǎng)春而在東北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工作的楊公驥先生。公木先生與楊公驥先生二人相識(shí)于延安,又于50年代初期合作從事文史研究。待到1976年后,二者學(xué)術(shù)上的聯(lián)系漸多,公木先生把《老子校讀》竣稿的部分不時(shí)寄給楊公驥先生,二人亦借書札往來(lái),論《莊》說(shuō)《老》,析辨奧義。時(shí)間到了1978年春,公木先生擔(dān)任了由校到省,直到國(guó)家的各種職務(wù),會(huì)議接連不斷,借用他自己的話來(lái)說(shuō),“實(shí)在是生活在忙亂中,暈頭轉(zhuǎn)腦,顧此失彼,不加強(qiáng)壓力,自然便停擺了也”(《老子校讀》“后記”)。是年4月26日,公木先生接到同樣也是賓客盈門、文債如山的公驥先生的贈(zèng)詩(shī):
寒霜?dú)v盡又逢春,
枯木重華稀世珍。
座上不虛談笑客,
案頭未了應(yīng)酬文。
懸口滔滔浮白日,
垂發(fā)皤皤挽黃昏。
欲追王弼窮奧旨,
怎奈無(wú)暇學(xué)老君。
詩(shī)中提及的王弼,是曹魏人,著名玄學(xué)家,以《老子注》聞名天下。1978年秋冬之際,《老子校讀》的撰寫已近尾聲,而公木先生卻諸事紛繁、多任在身的時(shí)刻,我來(lái)到了他的身邊。我能協(xié)助先生的,多是抄抄寫寫、校對(duì)文字一類的事,而在這種協(xié)助的過程中,我倒是有機(jī)會(huì)認(rèn)真踏實(shí)地習(xí)讀《老子》諸多傳世本,也算是穿越歷史,在“老子學(xué)”中走了一遍,這對(duì)于我后來(lái)撰寫《道家思想與中國(guó)文化》以及有關(guān)道家與中國(guó)文學(xué)的系列論文奠定了基礎(chǔ)。1979年冬,為周圍同事、左右?guī)熡殃P(guān)注和期盼了6年之久的《老子校讀》終于面世。但沒有想到的是,對(duì)于我為此書所做的那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公木先生竟給予了熱情洋溢的鼓勵(lì)和不吝筆墨的肯定。他在“后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直到去年冬趙明同志調(diào)來(lái)我校,助我一臂,才把勁兒上足,時(shí)鐘再度發(fā)出滴答聲,今年春天赴京參加詩(shī)歌座談會(huì)歸來(lái),一鼓作氣,命筆急就,又把《德經(jīng)》四十四章趕了出來(lái),全部殺青,是在五月。于此期間,還綜合八十一章說(shuō)解大意,寫了一篇《論老子》,這篇東西,便更加是與趙明同志共同探討,并得他協(xié)助才寫成的。可以這樣說(shuō),如果沒有趙明同志,此書或?qū)⒐μ澮缓垼鞘谴笥锌赡艿摹!闭?0年過去了,今天看到先生的這段深情獎(jiǎng)掖的文字,我只深感有負(fù)先生,愧對(duì)先生的獎(jiǎng)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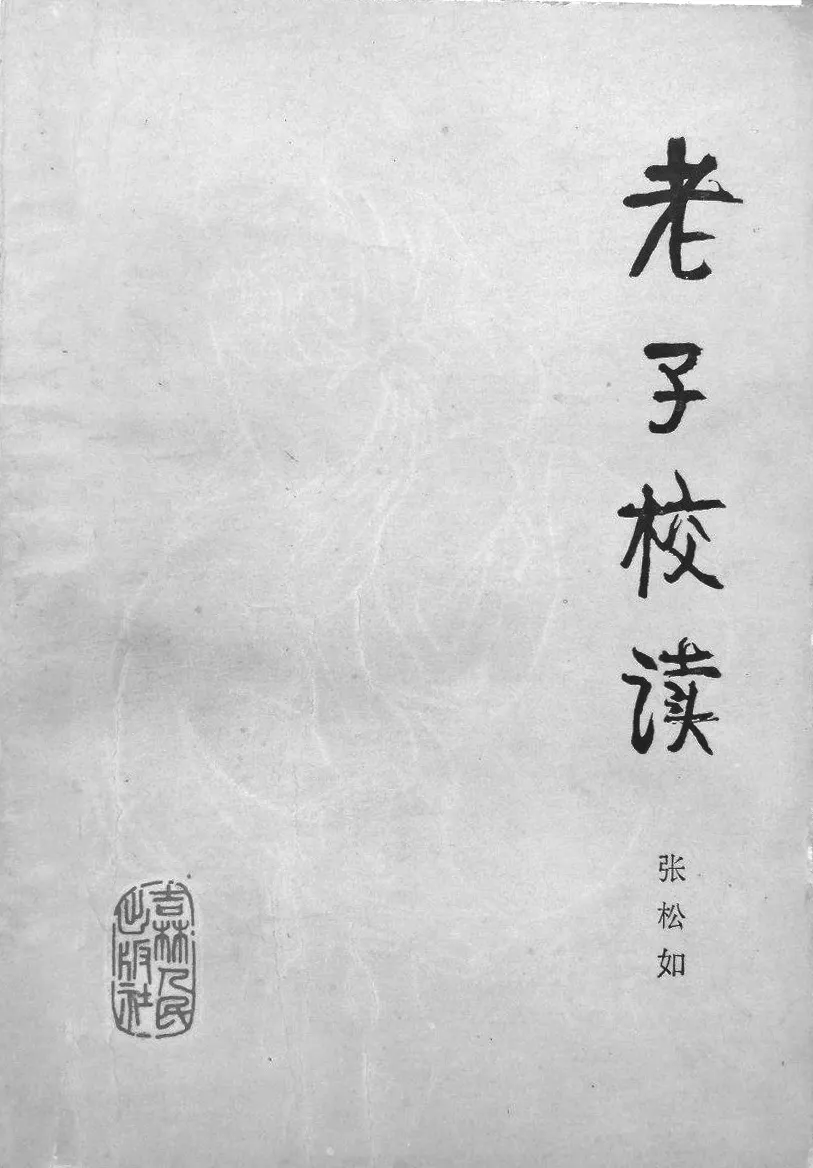
張松如(公木):《老子校讀》
公木先生的莊子情懷
對(duì)于撰著《老子校讀》,公木先生曾戲稱自己是“初學(xué)”,說(shuō)自己“是一個(gè)富有興趣,敢湊熱鬧的人”。事實(shí)上,以詩(shī)為人所知的公木先生于經(jīng)史、于古文字,都有很深的學(xué)術(shù)造詣。公木先生在青年時(shí)代曾為高級(jí)中學(xué)講授國(guó)文和文字學(xué)課程,他編著的《中國(guó)文字學(xué)概論》,由他的老師、中國(guó)語(yǔ)言學(xué)界的泰斗黎錦熙審訂后出版。扎實(shí)的文字學(xué)和經(jīng)史功底,在他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所顯示。他在晚年撰著《老子校讀》,實(shí)亦淵源有自而非偶然。《老子校讀》是在1993年湖北省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jiǎn)《老子》之前,較早利用長(zhǎng)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用以檢校后世諸通行本《老子》的著作。這部專著不僅做到了“悉取古今諸本,檢別疑謬,審義所安,擇善而從”,寫定“經(jīng)文”并附以“校釋”,而且全書81章每章都綴以“譯語(yǔ)”和“說(shuō)解”。《老子》是近于詩(shī)體的古文,公木先生又是學(xué)者兼詩(shī)人,所以每章的“譯語(yǔ)”,都以生動(dòng)、活潑的現(xiàn)代語(yǔ)言,讓讀者享受到奧義玄思中的深邃詩(shī)意或恍惚朦朧的老子詩(shī)美。這一點(diǎn),只要將它和諸家譯語(yǔ)略作對(duì)比,特色立判。最后的“說(shuō)解”部分,既針對(duì)每章主旨作“原汁原味”的解讀,又聯(lián)系全書按老子思想的邏輯線索作引申和發(fā)揮,使讀者讀每章都得窺《老子》全貌。這樣一部既完備又有特色的《老子》讀解本,它的問世,必然會(huì)引起海內(nèi)外學(xué)人的關(guān)注。果然,不久中國(guó)臺(tái)灣旅美著名學(xué)者、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客座教授,以研究老莊哲學(xué)蜚聲海內(nèi)外的陳鼓應(yīng)先生,在其所著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老子今注今譯》中,即“嚶鳴友聲”,不僅對(duì)公木先生的《老子校讀》作出了公開的學(xué)術(shù)回應(yīng),而且他本人也不避遠(yuǎn)途,專程來(lái)吉大拜訪公木先生以達(dá)仰慕敬重之意,遂由“相忘于道術(shù)”的默會(huì)而有了后來(lái)合著的《老莊論集》(1987年由齊魯書社出版)的面世。大約也是在此前后,又有日本東京大學(xué)文學(xué)部池田知久教授一行3人專程來(lái)訪公木先生,就日本的《老子》研究和有關(guān)老子的諸多感悟與之交流討論。池田知久教授等人為了更詳盡地了解公木先生最新的老子研究,特意在吉大招待所駐留了3天。其間除有一次面見公木先生外,其余具體交流工作便由我代勞。池田知久教授回國(guó)不久,即在日本《海外東方學(xué)》雜志上著文介紹了公木先生其人和他的《老子校讀》。此后,還有多位日本漢學(xué)家,以拜訪或書信的形式,繼續(xù)了有關(guān)《老子》的文化交流。公木先生在完成有關(guān)老子的著述后,曾有過接下來(lái)再寫一部關(guān)于《莊子》的書的想法,他多次在與我的交談中流露:他對(duì)兼具深邃哲思與悲憫詩(shī)情的《莊子》由衷喜愛和激賞,在情感和審美層面上,甚至超過了對(duì)《老子》的興趣。我長(zhǎng)期受公木先生情懷熏陶,對(duì)此亦深知之。實(shí)際上,具有濃郁詩(shī)人氣質(zhì),想象力超拔瑰奇,行文漫無(wú)涯際的莊子,才是公木先生的神交和心儀對(duì)象,是他晚年祈望的一個(gè)能與前哲共舞遙契的心靈之約。很遺憾,他急于做和必須做的事情太多,不能推辭的會(huì)議也太多。他能放棄自己的熱愛,卻不能冷卻詩(shī)人的熱腸和對(duì)社會(huì)的責(zé)任。他對(duì)剛剛崛起的一代詩(shī)壇新人和初綻蓓蕾、尚待滋溉的文學(xué)青年,都擔(dān)負(fù)著園丁般的責(zé)任。他抽出很多時(shí)間看詩(shī)壇新人寄來(lái)的詩(shī)刊或信件,給他們寫評(píng)論,引導(dǎo)并呵護(hù)他們的成長(zhǎng),其中就包括舒婷、北島和徐敬亞等“朦朧派”詩(shī)人。他還擔(dān)任著副校長(zhǎng)、校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主任等職,主管全校文科科研、職稱評(píng)定等事務(wù)。叩門找他主持“公道”和向他傾訴的教師,有時(shí)一天中就要接待幾個(gè)。這都因?yàn)樗珶嵝模揭捉耍鞒终x。一向健康,很少患病的公木先生,在這樣多頭緒、多“戰(zhàn)線”、高強(qiáng)度的工作狀態(tài)下,終于支撐不住,病倒了。

1979年10月,公木(右二)參加全國(guó)第四次文代會(huì)留影
1981年春,持續(xù)的心絞痛引發(fā)了心梗,公木先生住進(jìn)了醫(yī)院。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有限的精力還必須落在詩(shī)和詩(shī)學(xué)的領(lǐng)域,這是由他的“詩(shī)人”身份注定的,也是為了完成教育部列出的學(xué)科規(guī)劃的任務(wù)要求:公木先生主編了由先秦至近現(xiàn)代九卷本的《中國(guó)詩(shī)歌史論》,跨度之長(zhǎng)、體系之大,前所未有。這一浩大學(xué)術(shù)工程,使進(jìn)入晚年的公木先生在完成對(duì)《老子》的解讀后,未能得償注《莊子》的夙愿,這是他的一大遺憾。有幸的是,在和他多次的談老論莊中,我斷斷續(xù)續(xù)地記錄了他對(duì)莊子覃思卓見的雨絲風(fēng)片,其中每個(gè)論點(diǎn),都足以延展發(fā)揮為一篇精彩的文章。比如:“詩(shī)騷”是中國(guó)詩(shī)歌的雙源,“莊騷”則是中國(guó)文學(xué)璀璨的雙珠。這一線索,貫穿了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演進(jìn)和發(fā)展之路;莊子是“哲之詩(shī)”,屈原是“詩(shī)之哲”,共同達(dá)到了“悲憫”高度,此后再無(wú)詩(shī)人可企;莊子文學(xué)性的特點(diǎn)是浪漫主義的浮想聯(lián)翩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犀利觀察,是“冷眼熱腸”;莊子借助大量寓言來(lái)表達(dá)深?yuàn)W的哲理,在《莊子》一書的理論線索上,綴滿了燦爛多彩的形象花結(jié);莊子是最深情的“詩(shī)人”,他的情感極為豐富。他所謂的“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tài)”,莫不屬于情感的范疇。莊子談人生,一則曰:“不亦悲乎?”再則曰:“可不哀邪!”這種哲思中的悲憫情懷,內(nèi)含遠(yuǎn)比詩(shī)人更為豐富、更為深沉的人生體驗(yàn)和情感;莊子總是在“道”上渲染著濃厚的情感色彩和鮮明的審美意緒。著名的“庖丁解牛”,是一個(gè)“技”(藝)進(jìn)乎“道”的過程,是一種高超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庖丁解牛之后的“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表現(xiàn)出傳神的審美愉悅情態(tài),這些都需要極高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和哲學(xué)睿智;讀《莊子》可知:思與詩(shī),哲學(xué)與藝術(shù),必在最高的靈境或玄妙處有以相會(huì),這需要進(jìn)行更廣泛而深入的對(duì)詩(shī)或藝術(shù)以及直覺、語(yǔ)言符號(hào)等的探索(公木先生晚年所著的《第三自然界概說(shuō)》深入探討了這些問題)。如此等等,不必更多羅列即可看出,若非對(duì)《莊子》有深刻的解讀,怎能有如此不同凡響的立論?莊子是廣義的詩(shī)人,或曰藝術(shù)家,但他的“詩(shī)”或“藝術(shù)”是什么?在何處?多年來(lái),我看過不少學(xué)人論莊的文章或著作,但最終還是不知所云,更不得探知九淵蛟龍之“驪珠”究在何處。公木先生既是詩(shī)人又是哲人,學(xué)識(shí)淵博,人生閱歷豐富。讀他的論莊之言,讓我恍惚有窺“驪”見“珠”之感、得情感共鳴之愉。我寫過幾篇有關(guān)《莊子》的文章,也曾被《新華文摘》及《報(bào)刊文摘》轉(zhuǎn)載,但終因?qū)W識(shí)、閱歷、情懷、才能以及諸多因素宥限,未能得發(fā)先生論莊意蘊(yùn)于萬(wàn)一。先生之治學(xué)、為人,誠(chéng)然令人欽敬追慕,激勵(lì)后學(xué)精進(jìn),然如我之庸平碌碌,終難望其項(xiàng)背。

1980年,公木(右)與蕭軍在一起
也許中國(guó)詩(shī)人或作家的職業(yè)關(guān)注、情感認(rèn)知、審美取向以及經(jīng)歷閱歷等,都與老莊情結(jié)有著文化基因的血脈關(guān)聯(lián),隨際遇變化而以或隱或顯的方式得以表露。無(wú)獨(dú)有偶,在公木先生著《老子說(shuō)解》20年后,著名作家王蒙又以閱覽感悟的方式,將自己的老莊情結(jié)連續(xù)在《老子的幫助》《莊子的享受》兩部書中盡情釋出,極“淋漓盡致”之興。這兩部以老、莊為話題的書,并非學(xué)術(shù)性著作,而全然是王蒙以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和歷練說(shuō)老解莊。王蒙要面對(duì)的并非學(xué)術(shù)界,而是文壇和中國(guó)的讀書界。在青島,我應(yīng)邀參加了一次既有學(xué)術(shù)界也有文藝界朋友出席的討論會(huì),提交了文章并在大會(huì)宣讀,文中充分肯定了王蒙解莊的特點(diǎn)和價(jià)值。其中核心的論點(diǎn)就是:作家王蒙是怎樣把“正解”留給專家,而自己卻把“謬解”變?yōu)椤懊罱狻薄J堑模趺傻雌鸱⒇S富多彩的人生經(jīng)歷,確實(shí)可為不少“妙解”提供絕佳的注腳。而作為詩(shī)人與學(xué)者的公木先生,走的是以學(xué)術(shù)規(guī)范注“老”解“莊”的路子。在這條路上,他的經(jīng)歷、閱歷、感性思維乃至悲歡激賞,都自覺受馭于理性、理智和思維,他的詩(shī)懷和激情,也都需要內(nèi)斂、沉潛,直至“自我”退出,無(wú)蹤可辨,無(wú)跡可求。這是公木完全不同于王蒙的。
(未完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