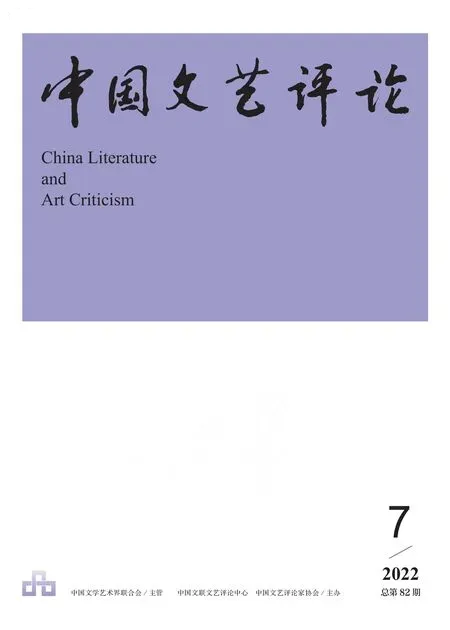清代詩(shī)學(xué)的“清空”理論范式
■ 程景牧
“清空”雖是古代詩(shī)學(xué)的一個(gè)審美范疇,而清空理論范式則在宋代詞學(xué)場(chǎng)域中形成,并在明代詩(shī)學(xué)中得到了實(shí)踐運(yùn)用。在清代道問(wèn)學(xué)與尊德性合一的實(shí)學(xué)場(chǎng)域中,原先的清空理論范式已不再適應(yīng)清代詩(shī)歌與詩(shī)學(xué)的發(fā)展,清空理論遂發(fā)生了范式轉(zhuǎn)換,審美傾向由宋明時(shí)期的尚虛轉(zhuǎn)變?yōu)榍宕纳袑?shí),由先前偏重神理、輕視學(xué)問(wèn)轉(zhuǎn)變?yōu)樾聲r(shí)期的兼重學(xué)問(wèn)與神理;內(nèi)在理路也一改以往的由虛而虛而轉(zhuǎn)變?yōu)樾聲r(shí)期的由實(shí)而虛,這種范式轉(zhuǎn)換是革命性和突破性的。學(xué)界目前對(duì)清空范疇與理論雖有一定的重視,但系統(tǒng)地論述清空理論在古代詩(shī)學(xué)場(chǎng)域中演變發(fā)展的理論成果尚屬罕見,至于清空理論范式在清代詩(shī)學(xué)中的轉(zhuǎn)換與實(shí)踐更是無(wú)人問(wèn)津。鑒于此,筆者嘗試探討清空理論范式在清代詩(shī)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轉(zhuǎn)換革新及其在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中的實(shí)踐運(yùn)用,以此揭示清空理論的詩(shī)學(xué)價(jià)值與美學(xué)蘊(yùn)涵。
一、“清空”概念的生成及其在清前詩(shī)學(xué)中的運(yùn)用
“清空”是一個(gè)古代詩(shī)學(xué)概念與審美范疇,指的是一種清雅空靈的詩(shī)歌審美風(fēng)格與境界。“清空”作為審美范疇,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出入于儒釋道三家,涵育于中古時(shí)期,具有典型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之特質(zhì)。
“清”作為一個(gè)審美概念雖最早見諸《詩(shī)經(jīng)》《老子》等先秦元典,但作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審美范疇出場(chǎng)則是始于魏晉。因?yàn)槭艿匠缟星逄摰男W(xué)思潮的影響,魏晉南朝文論即體現(xiàn)出尚清的審美意識(shí),如《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文賦》:“箴頓挫而清壯”,《文心雕龍·才略》:“張華短章,奕奕清暢”。“空”字雖在《詩(shī)經(jīng)》中業(yè)已出現(xiàn),但被賦予美學(xué)意蘊(yùn),并與“清”相結(jié)合,則是佛學(xué)思想促成的,如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里的“空”即是清靜虛空之義。雖然《心經(jīng)》中的“空”是佛教術(shù)語(yǔ),但卻凝聚著深厚的思想文化蘊(yùn)涵,“空”因?yàn)榫哂星逄撝馓N(yùn),故而能夠進(jìn)入詩(shī)學(xué)領(lǐng)域,與“清”結(jié)合,構(gòu)成“清空”這一美學(xué)概念和審美范疇。“清空”這一概念雖在唐代尚未正式出現(xiàn),但其審美意蘊(yùn)在唐人詩(shī)論中業(yè)已具備,如李白評(píng)謝朓詩(shī)所用的“清發(fā)”,杜甫評(píng)庾信詩(shī)所用的“清新”,皆含有“清空”之義。司空?qǐng)D《二十四詩(shī)品》中的沖淡、清奇、含蓄、高古、形容等范疇皆蘊(yùn)含著一種清新淡雅、空靈幽遠(yuǎn)的清空之美。
由南宋至于明代,清空這個(gè)審美范疇出入于詩(shī)學(xué)與詞學(xué)之間,先出于詩(shī)學(xué)領(lǐng)域,然后由張炎引入詞學(xué)領(lǐng)域,并進(jìn)行理論建構(gòu),清空理論范式即在詞學(xué)場(chǎng)域中正式生成。明代詩(shī)學(xué)繼承了張炎建構(gòu)的清空理論范式,胡應(yīng)麟、許學(xué)夷等人在詩(shī)學(xué)理論批評(píng)中援引清空概念,以清空概括唐代律詩(shī)的風(fēng)格。但是明代詩(shī)學(xué)的清空理論還是沿襲宋代的范式框架,雖略有新意,但大同小異,沒(méi)有質(zhì)的變化。究其原因在于宋明兩代均處于宋學(xué)的文化場(chǎng)域之中,由宋至明,儒學(xué)以理學(xué)為主導(dǎo),因此在宋學(xué)場(chǎng)域中,清空理論范式得以發(fā)展定型并基本保持不變。宋明詩(shī)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清空理論范式偏重詩(shī)歌本身美學(xué)特質(zhì)的闡釋與建構(gòu),偏重內(nèi)在義理蘊(yùn)涵的開掘,彰顯出一種由虛而虛的思維理路與尚虛黜實(shí)的審美精神。宋明學(xué)者對(duì)清空理論范式的建構(gòu),固然推動(dòng)了詩(shī)學(xué)的進(jìn)步,解決了一些問(wèn)題,但同時(shí)也產(chǎn)生了留待后世學(xué)者解決的諸多問(wèn)題,比如清空能否與質(zhì)實(shí)協(xié)調(diào)起來(lái),而不是一直相互對(duì)立,這是宋明學(xué)者未涉及的。明清易代,政治社會(huì)、文化思潮均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先前學(xué)者所建構(gòu)的清空理論范式已然不再適應(yīng)詩(shī)學(xué)的變革與時(shí)代的變化,因此在新的學(xué)術(shù)文化前提下,清代詩(shī)學(xué)共同體對(duì)清空理論范式進(jìn)行了革新,結(jié)合時(shí)代學(xué)術(shù)文化重新闡釋清空,建構(gòu)出一種新的清空理論范式,并將革新后的清空理論范式運(yùn)用于詩(shī)歌批評(píng)之中。因此在清代詩(shī)學(xué)中,清空理論即發(fā)生了范式轉(zhuǎn)換,新的清空理論范式在詩(shī)學(xué)理論闡釋與詩(shī)歌批評(píng)中得到了踐行與完善。
二、清代詩(shī)學(xué)中的清空理論范式轉(zhuǎn)換
清代以前的清空理論范式均是由虛而虛,偏重神理,輕視學(xué)問(wèn)根柢,是尚虛黜實(shí)的。清代詩(shī)學(xué)的清空理論范式則是由實(shí)而虛,在學(xué)問(wèn)根柢的基礎(chǔ)上追求神理、文理,主張?zhí)搶?shí)結(jié)合,是尚實(shí)的,因此清代詩(shī)學(xué)共同體通過(guò)這種內(nèi)在理路實(shí)現(xiàn)了清空理論的范式轉(zhuǎn)換。清代詩(shī)學(xué)的清空理論范式是在舊的理論傳統(tǒng)中孕育出來(lái)的,因此是對(duì)前代革命性的紹承,不但注重從虛處著眼,從藝術(shù)精神層面發(fā)掘清空的美學(xué)蘊(yùn)涵,更注重從實(shí)的層面,從學(xué)問(wèn)素養(yǎng)與神理義理結(jié)合的角度來(lái)觀照清空理論內(nèi)涵的文化底蘊(yùn)。
清代詩(shī)學(xué)共同體對(duì)清空理論的范式轉(zhuǎn)換賦予清空范疇以全新的美學(xué)蘊(yùn)涵,使清空理論變得空前深邃。這種理論范式轉(zhuǎn)換固然是詩(shī)學(xué)共同體的自主選擇,但是這種自主選擇的背后有著極其深厚的學(xué)術(shù)文化在驅(qū)動(dòng),學(xué)術(shù)文化作為外緣因素對(duì)清空詩(shī)學(xué)理論的范式轉(zhuǎn)換起到了推動(dòng)作用,同時(shí)也促進(jìn)了詩(shī)學(xué)內(nèi)在理路的改變。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大體分為漢學(xué)與宋學(xué)兩大體系,漢學(xué)以道問(wèn)學(xué)為標(biāo)志,偏重學(xué)問(wèn)根柢;宋學(xué)以尊德性為依歸,偏重義理思辨。清代學(xué)術(shù)表現(xiàn)出明顯的漢宋兼采,尊德性與道問(wèn)學(xué)合一、學(xué)問(wèn)與義理合一之特色。清代樸學(xué)一改明代學(xué)術(shù)的空疏而以實(shí)學(xué)為尚,是對(duì)明末清初以道問(wèn)學(xué)為傳統(tǒng)的實(shí)學(xué)的延續(xù)與發(fā)展。清儒在道問(wèn)學(xué)的同時(shí),也重視尊德性,只是將尊德性的學(xué)理傳統(tǒng)轉(zhuǎn)移到對(duì)道問(wèn)學(xué)的追求上來(lái),即通過(guò)道問(wèn)學(xué)以尊德性,以學(xué)問(wèn)為基礎(chǔ)來(lái)探求義理,而不是一味地空談。顧炎武即主張“經(jīng)學(xué)即理學(xué)”,惠棟主張“六經(jīng)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阮元主張“義理從古訓(xùn)中來(lái)”。戴震則提出學(xué)有“三難”(淹博難、識(shí)斷難、精審難)的觀點(diǎn),淹博與精審屬于學(xué)問(wèn)素養(yǎng)層面,而識(shí)斷則是對(duì)義理的探求了。因此,清代樸學(xué)的實(shí)質(zhì)即是以實(shí)學(xué)為基礎(chǔ),進(jìn)行義理的探求,兼采漢宋二學(xué),兼融道問(wèn)學(xué)與尊德性。
三、清空理論范式在清代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中的運(yùn)用
清空理論范式在清代詩(shī)學(xué)中轉(zhuǎn)換革新并成功運(yùn)用于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之中。范式的存在決定了要解決什么樣的問(wèn)題,清空理論范式被清代詩(shī)學(xué)共同體用來(lái)開展詩(shī)歌批評(píng),理論范式既是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的重要前提,也決定了批評(píng)對(duì)象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清空理論范式被清代詩(shī)學(xué)共同體所接納,那么在此范式引導(dǎo)下選擇的批評(píng)對(duì)象即具有清空的審美蘊(yùn)涵或彰顯出清空的詩(shī)學(xué)意義。總體說(shuō)來(lái),清代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清空理論范式的運(yùn)用,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是將清空作為點(diǎn)評(píng)詩(shī)句的術(shù)語(yǔ),表現(xiàn)出點(diǎn)到為止、言近旨遠(yuǎn)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將清空置于詩(shī)人整體風(fēng)格的評(píng)價(jià)之中,將清空的理論蘊(yùn)涵融于批評(píng)闡釋之中。這兩方面均折射出學(xué)問(wèn)與文理合一的尚實(shí)的清空理論范式之特色。
清空理論范式在清代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中得到了實(shí)踐運(yùn)用,這一方面為理論范式提供了實(shí)例支撐,另一方面使得理論范式的學(xué)理蘊(yùn)涵得到進(jìn)一步的拓展。清代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中的清空范疇與理論彰顯出學(xué)問(wèn)與文理的合一,既體現(xiàn)出清代詩(shī)學(xué)的精神蘊(yùn)涵,也體現(xiàn)出清代學(xué)術(shù)的特質(zhì)。雖然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大多依據(jù)的是批評(píng)者的直覺(jué)經(jīng)驗(yàn),但究其本質(zhì)卻是理論范式在背后起著指導(dǎo)作用,因?yàn)槔碚摲妒皆谝唤?jīng)確立之后即成為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的前提。詩(shī)學(xué)共同體是理論范式的踐行者,將理論范式寓于批評(píng)之中,在具體的批評(píng)實(shí)踐中固化了理論范式的權(quán)威性與合法性,因而詩(shī)學(xué)批評(píng)是理論范式在確立以及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余論
值得注意的是,漢魏詩(shī)歌因?yàn)橐孕郧闀r(shí)事為主,而被清人目為質(zhì)實(shí),其實(shí)詩(shī)風(fēng)的質(zhì)實(shí)即是在漢學(xué)的學(xué)風(fēng)影響下形成的,以性情時(shí)事為主即展現(xiàn)出詩(shī)歌情感的真實(shí),而不是像宋人那樣堆砌典故、密集意象而缺乏真情實(shí)感的質(zhì)實(shí),所以漢魏詩(shī)歌之質(zhì)實(shí)就是清空的質(zhì)實(shí),是融學(xué)問(wèn)與神理、義理合一的質(zhì)實(shí)。是故,從清代詩(shī)學(xué)的質(zhì)實(shí)理論范式可以看出,清空理論范式即是在質(zhì)實(shí)理論基礎(chǔ)上的推進(jìn),是指在學(xué)問(wèn)根柢深厚質(zhì)實(shí)的基礎(chǔ)上,衍生出神理義理、抒發(fā)出真情實(shí)感的一個(gè)理論結(jié)構(gòu)。在清代詩(shī)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清空理論范式中,質(zhì)實(shí)與清空對(duì)立統(tǒng)一,清空以質(zhì)實(shí)為基礎(chǔ),又超越質(zhì)實(shí)。而在宋代詩(shī)學(xué)、詞學(xué)場(chǎng)域中,清空與質(zhì)實(shí)相互悖立,并不統(tǒng)一。
總之,宋代詩(shī)學(xué)的清空理論范式是由虛而虛,是尚虛的,而清代則是由實(shí)而虛,是尚實(shí)的;宋代理論范式更偏重藝術(shù)神理層面,而清代則偏重學(xué)問(wèn)根柢與神理義理的調(diào)和;宋代理論范式將清空與質(zhì)實(shí)對(duì)立起來(lái),而清代則將二者統(tǒng)一起來(lái);宋代理論范式是在理學(xué)場(chǎng)域中生成發(fā)展的,而清代理論范式則是在實(shí)學(xué)的場(chǎng)域中轉(zhuǎn)換革新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