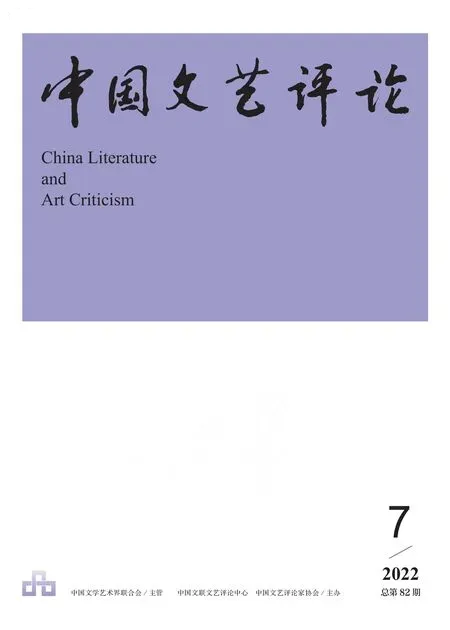新主流電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與審美更新
■ 黃鐘軍
引言
近些年,我國電影產業持續發展升級,盡管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響,國產電影精品佳作仍不斷涌現,尤其是以《戰狼Ⅱ》(吳京,2017)、《紅海行動》(林超賢,2018)、《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等,2019)、《長津湖》(陳凱歌、徐克、林超賢,2021)等為代表的“新主流電影”陸續實現票房口碑雙贏,不斷催生“現象級”效應,集中體現了中國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的昂然雄姿。新主流電影選取最能代表中國變革和中國精神的題材,將主流思想、商業創作和藝術審美融于一體,符合新時代要求和人民群眾對于文化藝術的新需求、新期待,努力達到思想性、藝術性的有機統一,聚合發揚“人民性”。新主流電影是對毛澤東“人民性”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系列重要論述的貫徹和執行。
一、“人民性”與社會主義文藝理論
(一)“人民性”文藝理論溯源及發展
(二)“人民性”和社會主義電影事業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的不斷推進升級,“主旋律電影”變得更加多元,逐漸轉向“新主流電影”。“新主流電影”一詞最早見于1999年,是在“主旋律電影”的基礎上,對其表現內容與思想內涵的一次繼承與拓展。21世紀前十年,《緊急迫降》(張建亞,1999)、《云水謠》(尹力,2006)、《集結號》(馮小剛,2007)、《十月圍城》(陳德森,2009)等影片在實現意識形態功能的同時,不斷滿足觀眾的情感期望與人文訴求。而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里,《建國大業》(韓三平、黃建新,2009)、《建黨偉業》(韓三平、黃建新,2011)、《建軍大業》(劉偉強,2017)展演黨和國家的偉大歷史。《智取威虎山》(徐克,2014)作為經典再現獲得口碑、票房雙贏。《湄公河行動》(林超賢,2016)、《戰狼Ⅱ》、《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李仁港,2019)、《中國機長》(劉偉強,2019)等影片不僅刷新了國產電影票房紀錄,也在新的社會語境下獲得了廣泛的價值認同,產生了凝聚人心的力量。以2021年的《長津湖》為例,無論是觀眾口碑還是票房紀錄,都表明了“新主流電影”的公共號召力,也深刻體現了新時代中國電影創作踐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的集體意識。當前,“新主流電影”已成為建構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媒介,而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力量自然成為它著力表現的對象。社會主義電影的表現對象一定是人民群眾,無論是電影的題材選擇,還是故事類型,甚至是美學風格,都要深耕于人民群眾。社會主義電影唯有更積極主動地反映、團結人民群眾,才能更好地把握歷史發展方向、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而對于“人民性”的強調恰恰聯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七十多年來最核心的宗旨和目標,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二、“新主流電影”創作的“人民性”
對于結合“主旋律電影”與新時代發展的“新主流電影”來說,“誰作為表現對象”是藝術創作“人民性”在內容層面的首要顯現。不同于“主旋律電影”以革命歷史、英烈模范和國家工程等歷史大事記作為表現對象,“新主流電影”更多是以“散點透視”的歷史視野,將人民群眾的普遍實踐奮斗作為表現對象。這其中既有在堅定愛國主義的基礎上英雄化書寫革命歷史中的平凡人物,也有在“英雄性”與“人民性”的辯證統一中描摹人民模范的感人事跡,亦有在新時代精神背景中聚焦普羅大眾的人性閃耀。
(一)革命歷史的人民英雄
從20世紀的《開國大典》《開天辟地》到21世紀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重大革命歷史事件一直都是“主旋律電影”刻畫的重點,在其中“改造世界”的歷史偉人一直是電影創作者著重展現的對象。近年的“新主流電影”延續了這一傳統:《紅船》(沈東、王德慶,2021)在建黨百年之際再度回望“紅船精神”,塑造革命先鋒群像,重溫建黨艱辛歷程;《1921》(黃建新、鄭大圣,2021)則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放在共產國際運動的大脈絡中,跨時空勾連起彼時風起云涌的中國實踐與此刻風起潮涌的全球律動;《革命者》(徐展雄,2021)讓我們再次瞻仰夢想著“未來的環球”和“赤旗的世界”的革命先烈李大釗……這些通過還原歷史現場以表征重大革命事件的“新主流電影”,一方面,“主流”一詞說明其秉承了“主旋律電影”通過呈現歷史原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傳統;另一方面,“新”的定位在于其“人民性”表達的具體細致,由此革命歷史不僅構成了民族集體記憶的寶貴資源,而且成就了個人歷史的參與在場。
“新主流電影”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在書寫歷史巨擘的同時,塑造出無數平凡甚至無名的人民英雄。重述抗美援朝戰爭一役的《狙擊手》(張藝謀、張末,2022)將鏡頭對準中國人民志愿軍某狙擊小分隊。這些在大歷史中只留下寥寥數筆的年輕戰士,在電影藝術的渲染下有了更加豐滿、更加生動的肖像,讓我們知道,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下其實是平凡人的生活與戰斗。另一部表現抗美援朝戰爭的影片《長津湖》也是深化視點,通過伍氏兄弟和七連的微觀視點與個體敘事,為觀眾提供了管窺歷史的不同側面,也成為以微觀—宏觀同心圓模式還原歷史真相的模板。本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真理,“新主流電影”對于革命歷史英雄人物的深挖不再拘泥于“大人物”,而是持續關注“小人物”,無疑是對革命歷史外延的“人民性”內涵的再發展。
(二)各行各業的人民楷模
源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不僅記載著歷史的探索前行,也見證著當下的悄然嬗變。近年來,“新主流電影”也將目光投向平凡崗位上腳踏實地踐行崇高理想的工作者們。如果說“新主流電影”所“銘記”的革命歷史及人民英雄,賡續了延安時期確立的人民本位傳統、家國情懷傳統,那么鏡頭下各行各業人民楷模的塑造,則是“革命性”與“人民性”辯證統一的題中之義。中國香港導演林超賢執導的“行動三部曲”以極高的完成度媒合了香港電影的商業特質與“新主流電影”的意識形態表達,而系統成熟的特效制作也輔助了作品內容方面的拓展。
在這樣的基礎上,《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緊急救援》(林超賢,2020)將創作視點轉向電影題材中能見度較低的緝毒警察、軍事特工和救撈隊員,通過刻畫他們在營救中國公民行動中表現出的堅定與專業、奉獻與犧牲,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歲月靜好”背后職業人員的“負重前行”。
《烈火英雄》《中國機長》《中國醫生》等影片的落腳點是日常生活中比較容易接觸到的職業人群,而《奪冠》(陳可辛,2020)、《攀登者》和《守島人》(陳力,2021)等影片則捕捉到帶有一些“神秘感”的社會實踐脈搏。《奪冠》以中國女排事業的發展為主線,張揚了堅韌超越的女排精神;《攀登者》寫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登山隊員挑戰極限、為國獻身的英雄主義情結;與前兩部影片塑造群像不同,《守島人》將個人歷史娓娓道來——王繼才、王仕花夫妻32年以島為家,在嚴苛的自然環境下證明自己“守島就是守國”的崇高信念。由此可以看出,“新主流電影”中不僅有波瀾壯闊的大歷史,也有激蕩人心的“微相學”。“新主流電影”時刻準備著讓各行各業工作者的生活世界在銀幕之上交相輝映,參與著民族文化記憶的締造。透過這些生活中、工作中的英雄,“人民性”與“英雄性”實現了高度的辯證統一。
(三)千家萬戶的時代篇章
三、“新主流電影”的“人民性”引領
不斷推陳出新的“新主流電影”,在美學上代表了新時代的中國形象、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也在道德上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未來的“新主流電影”也應該堅持“人民性”原則,在電影制片、發行、放映等各個環節采取相應策略,繼續創造“叫好又叫座”的文藝精品。
(一)大眾化策略:類型強化、明星意識、市場提振
從審美接受的角度來看,“新主流電影”是面向大眾、邀請大眾、期待通過大眾檢驗的文化產品。“新主流電影”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動遵循著貼近觀眾、擁抱觀眾的大眾化原則。
首先,“新主流電影”通過類型化,加強現實生活的可感性。近年來,“新主流電影”的類型化程度不斷加深,鑄造出一批以軍事戰爭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類型大片。對比《戰狼》(吳京,2015)的邊境沖突主題,2017年上映的《戰狼Ⅱ》經由一次在遙遠非洲采取的撤僑行動,滿足了觀眾的安全需求和家國期待;2018年的《紅海行動》又將敘事空間擴展至索馬里海域,讓觀眾一覽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棲作戰實力;在電影《長津湖》中,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對手不是反叛組織、雇傭軍和海盜,而是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實力懸殊的殘酷戰爭既是世界和平的贊歌,也是居安思危的警示。
其次,“新主流電影”借助明星效應給現實主義帶來契機與挑戰。《建國大業》開創了一個新的傳統:眾多華語明星紛紛進入主流電影生產體系,為彼此帶來建設性的符號資本。明星效應在電影“神話”書寫中的功能不容小覷,但我們也要認識到,一部好影片的感召力,絕不只是靠一張張明星臉就能實現。經過“新主流電影”審慎選擇的演員可以創造外形上、精神上的雙重現實,讓觀眾在感嘆“形似”的同時,領悟精神層面的“神似”。成功的“新主流電影”創作者會充分考量知名演員對于觀眾的表演價值,超越“數星星”,引導觀眾提升欣賞水平和媒介素養,將“追星”心理投射到更深刻的情感價值認同中去。
最后,“新主流電影”努力開拓市場空間,利好相關產業服務于民。中國電影在市場化的摸索過程中,越來越注重電影的檔期屬性,形成了賀歲檔、暑期檔、國慶檔“三足鼎立”的態勢。近年來上映的“新主流電影”也多集中在三大檔期,而且交上了令人滿意的“答卷”。《戰狼Ⅱ》于2017年暑期刷新國產電影票房紀錄,之后幾年,該檔期相繼涌現《我不是藥神》、《八佰》(管虎,2020)、《烈火英雄》等票房、口碑雙豐收的優質電影。2021年國慶檔期間,《長津湖》再次刷新紀錄,并同2022年賀歲檔接力上映的《長津湖之水門橋》(徐克,2022)聯手創造近百億票房、超兩億人次觀影規模。“新主流電影”在各大檔期打下的漂亮仗既構成了中國電影市場的中流砥柱,也通過相關產業在國內外的連鎖式發展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因此我們要在積極培育中國電影市場的同時,加大力度孵化、整合、提振相關領域業態在國內外的發展。
(二)審美性內涵:以雋永的電影語言書寫中國精神底色
如果說曾經的“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三元區分代表的是相對分立的審美屬性和相對穩定的受眾群體,那么“新主流電影”則希望打破、重整市場的疆界、審美的疆界。說到“新主流電影”,無論是敘事上的類型強化,還是表演上的明星意識,其邏輯前提都是從最廣大觀眾的視角出發,融合上述三類電影,實現深耕意識形態、拓展市場空間、提升審美體驗的目的。
基于這個目的,“新主流電影”采用最強大的創作團隊、最精良的視聽技術以及最有效的發行放映,通過感官上的震撼和情感上的沉浸,達到綜合性的審美經驗,潛移默化地激發觀眾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人民認同,將新時代中國精神的書寫、中國學派的建構推向高峰。
其一,真實事件是“新主流電影”現實主義美學的木本水源。對于公眾來說,歷史上曾經發生、新近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真實事件,不斷載入人們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心理。記憶兼具敘事性、創造性特征。“新主流電影”只有把“想象的共同體”的記憶經驗以各種方式講述出來,才可以獲得不竭的創作動力。以戰爭類型為例,無論是血性方剛的《戰狼》系列,還是動人心魄的“行動三部曲”(《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緊急救援》),抑或熱忱追憶的《長津湖》系列,都是由真實事件改編而來。戰爭電影與大眾的戰爭記憶,與他們保家衛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緊密相連,在先進視聽技術的支持下,讓戰爭的殘酷、世界的動蕩以及人類的愿景深入觀眾心中,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反映性和建構性。
其二,真實人物使得“新主流電影”浪漫主義以微知著。把人寫好是好電影、也是“新主流電影”的重要標準。觀眾看電影,最關心的還是人的故事,他們通過注視電影人物的言語、行為、思想,尋找生命的參考,回望自己的本心。《中國機長》《中國醫生》所創造的高票房、高熱度,固然有強烈視聽效果的助力,但對于具體處境下人的凝視才是好電影的終極標準。在這些凝視真實人物的作品中,既有對于個體形象的獨特渲染(如《我不是藥神》),也有對于時代群像的影像致敬(如《攀登者》《奇跡·笨小孩》)。“新主流電影”在商業片視聽奇觀的轟炸和藝術片喃喃自語的留駐之間,見證“源于真實、高于真實”的真實事件與人物。由此可見,“新主流電影”正是對“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的真誠踐行。
“新主流電影”對于現實、對于人類的關注不僅包括日常生活的高度提煉,還有對于浩瀚宇宙的無限遐想。以《流浪地球》(郭帆,2019)為代表的“硬科幻”類型,體現出“新主流電影”表現我國太空探索事業的勇氣、實力以及滲透其中的世界主義視野、宇宙主義視野。影片在太陽毀滅的假定性下構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代表著全球社會的真人演員在數字技術搭建的末世景象中,提出了應對地球危機的中國思考、中國方案。由此可見,“新主流電影”是面向未來的、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它借助電影工業層面的類型拓展,在更大的認識論、方法論層面揮寫出偉大的中國精神底色。
(三)“觀眾”即“人民”:“新主流電影”的社會效益優先原則
電影的發展離不開市場,市場也因電影的發展而繁榮,但是“新主流電影”強調:一定要平衡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在制片、發行、放映的全過程中,“新主流電影”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要始終沿著“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方向,使電影的社會效益最大化、最優化。比如抗疫題材影片《穿越寒冬擁抱你》(薛曉路,2021)為疫情期間包括護士、廚師、快遞員、鋼琴教師、婦產科醫生等在內的武漢人民群眾留影,人物與事件“平凡中見不平凡”,讓觀眾看到“新冠”可能激發的正向精神(堅韌、執著、樂觀、向上),也讓人們看到在疫情中守望相助的大寫的愛。該片在審美上認可了觀眾的情感,在價值上引導了人民的實踐,開啟了電影社會效益的諸多可能性。
類型強化、明星意識、市場提振等大眾化策略的確為“新主流電影”贏得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歸根結底要把社會效益做好,表達人民訴求,指導群眾實踐,彰顯社會風貌,分享時代成就。這必然會讓“新主流電影”貢獻更多的“文藝高峰”,促進社會效益、經濟效益良性互動。
結語
從“主旋律”到“新主流”,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性”作為一條創作“金線”始終貫穿在電影藝術的發展中,從未改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文藝為了誰”“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的質詢仍在回響,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以人民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將迎來新的輝煌。
“新主流電影”在最近幾年的創作實踐中,始終以表現人民現實生活、滿足群眾審美需求為依歸,“人民性”意識更加充分、完善。它既繼承了謳歌革命事業、凸顯歷史成就的“主旋律”創作原則,又創作出一系列“以小見大”的優秀作品。它所講述的故事中,既有革命歷史的人民英雄,也有各行各業的人民楷模,還有千家萬戶的時代篇章。“新主流電影”借助類型強化、明星意識、市場提振等大眾化策略,實現了電影與時代、與世界的關聯互動和同頻共振,不僅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用事實說明了電影的社會效益。在此過程中,中國電影產業強勢崛起,順利踏上由“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新征程,讓中國價值、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在影像與聲音的交響中傳遍世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電影的“人民性”將在表述上、審美上繼續延伸、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