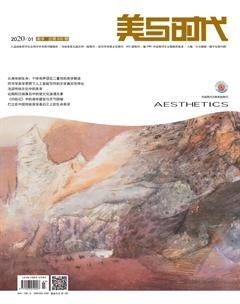從精神分析視角對《沉默的羔羊》中比爾潛意識的解讀
摘 ?要:《沉默的羔羊》中的比爾認為他自己有變性癖,然而他的變性癖只是一種粉飾,他的暴力殺人行為隱含著他的貪欲,這種貪欲其實是一種俄狄浦斯情結中的戀母情結,而這種戀母是很隱蔽的,甚至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認的。從精神分析視角解讀比爾的變性癖及暴力殺人行為背后所隱藏的復雜的潛意識狀態,并考察這種潛伏于意識表層之下的潛意識的活動方式顯得尤為重要,它有助于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真實心理狀況,從而從心理學的角度給與其積極治療,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解決美國當代社會恐怖的途徑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潛意識是混亂無章又復雜多變的,精神病患者的潛意識更是錯綜復雜,因此,很難將其單獨分類進行分述,只是為了便于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將其大體分類,加以詳述。
關鍵詞:精神分析;沉默的羔羊;比爾;潛意識
弗洛伊德認為,幼年生活的凝縮物是組成人類潛意識的基本成分。因此,對幼年生活經歷進行有目的地再現,將有助于了解一個人潛意識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過程。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大多都是由于其幼年成長過程中遭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創傷,這種心理創傷可能是由于他人施暴,也可能是源于某些事件對其產生了極大的心理沖擊。《沉默的羔羊》中的比爾屬于前者。本文結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三重人格結構”“力比多理論”與變異的“俄狄浦斯情結”“心理防御機制”這四種理論,試圖解讀水牛比爾的變性癖及暴力殺人行為背后所隱藏的復雜的潛意識狀態,考察這種潛伏于意識表層之下的潛意識的活動方式,找到其為尋求滿足而采取的方式及途徑,以此探索人物的心理疾患,探尋造成美國當代社會恐怖的根源。
一、比爾的“三重人格結構 ”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與伊底》中提出了“三重人格學說”。“三重人格”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位于無意識結構中,它由先天的、原始的基本欲望構成,按照“快樂原則”活動,它是可以為人提供活力和動力的能量之所;“自我”,位于意識結構中,它是較為理性的,按照“現實原則”行事,“自我”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間,它一方面對“本我”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它又受到“超我”的制約;“超我”,按照倫理道德、社會規范等要求的“至善原則”行事,它是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位于人格中的最高層,常常壓抑本能沖動。“在人格動力系統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人格的整體。它們各自代表了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代表了理性和心理社會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當三者處于協調時,人格表現出一種健康狀態,當三者不協調時,就會產生心理疾病。”[1]
在人格結構中,“本我”是無意識的,它遵循“快樂原則”,迫使人設法滿足內心深處原始遺傳的本能和欲望。比爾的“本我”也表現出上述特征,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原始本能,即他對于女性肉體的貪戀與占有。影片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暗室內放著音樂,比爾穿上了由眾多受害女性身上剝下的人皮制成的“女士大衣”,他在音樂中來回扭動,顯得很快樂。這種快樂是“本我”按照“快樂至上”原則行事的,它并不以社會道德作為評判的標準。另一方面是比爾“本我”對于寵物狗的愛憐,這種愛憐是一種善意的愛憐,然而又與“超我”中的善意不同,因為它不是由于道德規范形成的。在自己的暗室內,他不必偽裝自己來迎合社會道德對人的規范束縛,因此這種善意是自發的,是出于本能的。正是上述這種不以道德規范為標準來評判好壞的“本我”,為比爾提供了心理能量,使得他在受到童年創傷時未選擇自殺,而是能夠找到存活于世的快樂,盡管從社會道德價值的視角來看,這種心理能量未必全然具有積極意義。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總是試圖調節外部世界、“本我”、“超我”三者間的平衡,然而這三者間卻常常互不相容,這就導致“自我”經常不能完成任務。比爾的“自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在他按照“現實原則”行事。當史達琳找到他時,他穿起服裝,與她保持較為禮貌的談話。盡管當屋內的電鈴響起時,他就已經意識到史達琳是警方的人,他的偽裝在此刻根本沒有必要,但是從小接觸到的社會環境,還是讓他按照社會現實原則行事,穿好衣服,進行禮貌交流。另一方面表現在他的“本我”內部原始本能與善意本能的沖突、“本我”中的原始本能與超我的沖突。當凱瑟琳對他乞求道,“求求你,我想回家”“我想見我媽媽,求求你放過我吧”時,比爾的面部明顯表現出了一種難以掩飾的痛苦,也就是說他并非完全冷酷無情。在凱瑟琳乞求他的時候,他的內心深處是有情感波動的。“本我”內部只追求快樂的一面與原始存在的一部分善意的沖突、“本我”中的原始本能與處于社會中不自覺地受到社會道德準則制約的“超我”間的沖突,這兩種沖突互相交織、共同作用,形成了比爾內心復雜波動的狀態。比爾作為一個反社會的精神病患者,相比較正常人,受到的社會道德規則的束縛相對較少,但并不等于完全沒有。人是社會人,既然處在社會中,就不可能完全不受社會影響,起碼在凱瑟琳求救的那刻,那一丁點兒的道德準則也使得他的內心有過片刻的掙扎。
“弗洛伊德認為,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處于協調平衡的狀態時,才能保證人格的正常發展;如果過分地擴張一方或者過分地壓抑另一方,導致人格動力狀態中的能量場分布不均衡時,關系失調乃至遭到破壞,就會導致精神病和人格異常。”[2]比爾復雜多變的非正常人格結構則屬于后一種情況。
二、比爾的“力比多”
及其變異的“俄狄浦斯情結 ”
弗洛伊德認為,每一個人生來就有一種能夠使人追求快樂、尤其是性快樂的本能,這種本能就是“力比多”。“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弗洛伊德所謂的性沖動中的性,與生理學和解剖學意義上的性不同,也不是指以生殖為目的的狹義的性生活,而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性,是一種更廣泛的肉體能力,首先以快感為目標,其次才為生殖服務。”[3]比爾的變性癖和暴力殺人深受這種“力比多”的影響。他對繼母本能的性欲方面的占有沖動,使得他貪戀女性肉體,他的變性癖實際上是一種變異的性欲釋放,這種變性癖是他釋放童年創傷的一種出口。變性癖與暴力殺人是毫無關聯的,之所以這兩種變態行為能夠統一到一個人身上,那是因為這兩種行為皆源于童年創傷。比爾并非從小就作案,也就是說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間,他對于女性肉體的貪戀還處于一種隱秘的潛意識狀態,是由于某一個契機才觸發了他隱藏于意識下的那段童年創傷記憶。影片中史達琳發現了第一個受害者的首飾盒內側藏著的幾張女性半裸照片,由此推測比爾與受害者可能是親密關系。正是這種朝夕相處、與女性的親密接觸觸發了他童年的記憶,他對于繼母的這種充斥著既憤恨又隱秘的愛意,使得比爾對第一個受害者也產生了相同的情感。這種又愛又恨的情感交織著,終于有一天促使他將其殺害,達到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占有。這次的殺人行為未必是事先預謀的,但是這次作案,卻引發了他本能中的惡欲與貪念,他感到了別樣的快感,這種快感遠超過了性欲所帶來的快樂,正是如此才引發了其后的一系列作案行為。他找到了一種可以讓生理和心理都產生快感的方式:一方面是殺人的刺激與貪念的滿足帶來的快樂;另一方面,他發覺,可以將受害者的皮剝下,為自己做一件人皮女裝,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變性,滿足了他想要通過變性來改變身份的愿望。弗洛伊德認為,力比多理論還包括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的本能表現在饑餓、渴、性、維持生命的創造性力量。童年的虐待造就的“本我”與“超我”的沖突、變異的“俄狄浦斯情結”等皆屬于生的本能,盡管這讓比爾受到折磨,但這種痛苦也是維系他生存下去的變異動力。
弗洛伊德認為,“俄狄浦斯的故事反映了每個孩子自己的無意識愿望:‘弒父娶母或者是‘弒母嫁父,即每個孩子都對異性的父親或者母親懷有一種特殊的柔情,并對同性的母親或者父親有敵意,希望自己能取代他們的位置成為父親或者母親的妻子或丈夫”[4]。通常對于男性而言,顯示出的“俄狄浦斯情結”是一種戀母仇父的心理。戀母,其實就是受力比多中的性欲影響。仇父,是指通常情況下同性之間互相排斥的心理。而比爾在童年時期被繼母虐待的經歷,使他產生了一種變異的“俄狄浦斯情結”。這體現在他將對父親的仇視與對母親的依戀這兩者都統一到對其繼母的情感上。影片中資深的心理學家漢尼拔分析,比爾殺人是為了滿足他的本性,而他的本性并非他所表現出來的變性癖或殘暴殺人,而是貪圖。他貪圖什么?貪圖的是女性的身體。再深一層分析,他的貪圖,其實一方面是嫉妒他想要擁有的女性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對于女性的依戀,也就是說他雖然對于繼母對他的虐待心存憤恨,但也隱秘地對繼母有一種占有的甚至是將自己也變為女性的想法。影片中有一個特別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飛蛾。飛蛾象征著蛻變,說明比爾也想要蛻變。他想變成女人,因為從小被虐待,他討厭自己的身份,他的內心深處認為男性是受虐方,是被壓迫的一方。這可以解釋他的變性癖行為,因為變性癖顯示出的也是被動的、懦弱的特征。而他的繼母是施虐方,是強勢的一方,因此如若變性,他則不再是軟弱的一方。這可以解釋他的暴力殺人行為,因為暴力殺人是主動出擊的一方,因此他的這個暴力行為本身也許就是戀母情結的另一種表現。
三、比爾的“心理防御機制”
“心理防御機制”最初的提出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他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對此進行進一步的系統研究后逐漸成熟起來。“所謂心理防御機制是自我用來與本我和超我壓力對抗的手段。當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的威脅而引起強烈的焦慮和罪惡感時,焦慮將無意識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機制,以某種歪曲現實的方式來保護自我,以緩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5]52每個人都會利用“心理防御機制”來調整心理狀態,適度的使用可以緩解心理上的焦慮與壓力,然而如若過度使用則可能使“心理防御機制”失去其積極效用,甚至導致產生變異效用,給個體帶來相應的生理及心理疾病。比爾屬于后者,他也試圖通過“心理防御機制”來達到心理平衡,只是這種使用超出了適度的范圍,以致產生了變異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防御機制”有如下特征:(一)防御機制并非有意識的,它們是無意識的,或者說至少部分是無意識的。(二)“防御機制有自我欺騙的性質,即通過掩飾或偽裝我們真正的動機,或否認可能引起焦慮的沖動、動作或記憶的存在而起作用。”[5]52(三)防御機制本身并非病理的,相反,它們對于維持健康心理狀態有著積極作用,但需適度使用[5]52。(四)防御機制可能是單一機制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多種機制共同作用。
比爾的內心復雜多變,正是如下幾種“心理防御機制”在起著作用,這些機制大多都產生了非積極意義的效用。(一)仿同(Identification)。所謂仿同,是指個體在潛意識中,不經意地效仿自己所仰慕的名人,學習對方的語言、態度、舉止、表情、作風等。比爾的身上所體現出的則是與仿同截然相反的反感性仿同:繼母長期對他的虐待,卻使得他不但沒有對向他進行施暴的繼母感到痛恨,反而不斷向其靠近,甚而也從受虐方變為施虐方。(二)“投射(Projection),把個人主觀的思想、本性、感情等特性,強制套在別人身上,忽視自身的錯誤行為,把焦點集中在別人身上,是一種攻擊性的機制。”[6]49比爾的投射對象不是人類,而是他的寵物狗,相比較正常情況下所顯示的攻擊性而言,比爾將自身心理投射到寵物狗身上則顯示出一種柔情。比爾在小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樣是弱勢群體、是可以被隨意欺凌的對象,因此對小狗充滿愛憐。(三)“歪曲(Distortion),將本來的事實以錯誤的方式去解讀,不理會客觀現實和曲解原意,改變成個人內心能夠所接納的看法,屬于精神性質。”[6]48比爾不能接受自己是男性的客觀事實,他以錯誤的方式將男性與被施暴者、弱者相等同,因此強烈地想要改變自己的性別,他認為性別的轉變可以使他變為強者。這種歪曲過于極端就會出現幻聽、幻想等癥狀。(四)幻想(Fantasy)。“當社會現實中出現困境時,而人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難題,會嘗試透過幻想體驗的經歷,沉醉于幻象世界中,以彌補自己在現實中的失敗,令內心恢復平穩狀況。”[6]50比爾屬于過度幻想者,他因為無法通過正常的變性手術使其達到身份轉變,便逐漸厭惡現實社會,因多次被多家醫院拒絕而逃回自己所編織的幻境中。在那間隱藏于小閣樓的房間內,比爾穿著人皮大衣,幻想自己已經變性成功,沉醉于這種自我編造的幻想中。(五)轉移(Displacement)。“在特定的條件下,把當時的內心某一種情感轉移到另一時刻釋放出來,這種情感往往是不良的,對個人來說是沉痛和難受。”[6]49當年的童年創傷帶給比爾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痛苦,他沒有選擇當時對繼母發泄自己的這種不滿,而是將其深埋在心里,最終在多年后爆發出來的就是極其反人類的變性癖與殺人行為。(六)轉化(Conversion)。“某人經歷過特定的事情,從而產生相應的情緒問題,將個人心理上的問題,如焦慮、抑郁、強逼等代替軀體上的病癥,故此釋出內心的痛苦一面。”[6]50由于童年創傷,長大后的比爾一旦與女性朝夕相處,生理和心理上都會產生一種當年面對繼母時的變態占有欲及恨意。(七)“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基于自身不易接受的情緒,在潛意識當中運用一些亳無根據的道理試圖辯解。”[6]49這是一種文飾作用,“指無意識地用似乎有理但實際上站不住腳的理由來為其難以接受的情感、行為或動機辯護以使其可以接受。”[5]52這個理論有兩個著名的案例:酸葡萄心理和甜檸檬心理。前者是丑化失敗的動機,后者是美化被滿足的動機。比爾則屬于后者,此方法指企圖說服自己及他人,自己所擁有的或是所做的是最佳的選擇。比如,比爾認為他自己是變性癖,然而他的變性癖只是一種粉飾,他的暴力殺人行為潛伏著他的貪欲,這種貪欲其實是一種俄狄浦斯情結中的戀母情結,而這種戀母是很隱蔽的,甚至是他不愿意承認的。
正是由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不協調,“力比多”及變異的“俄底浦斯情結”“心理防御機制”這幾個方面造成了比爾的心理疾患,導致其產生變性癖及暴力殺人行為,而這一切都是因為童年創傷對其的影響。窺一斑而知全豹,比爾的潛意識折射出美國當代社會恐怖的根源之一,即童年創傷。由上述分析可知,比爾的所有反社會行為其根源皆是童年創傷的投射,由此可以看出童年創傷對于一個人的精神是極具破壞力的,也正是由于童年創傷的作用,才導致一批與比爾一樣的人患上精神疾病,甚而產生反社會行為。因此,從精神分析視角解讀比爾的變性癖及暴力殺人行為背后所隱藏的復雜的潛意識狀態,并考察這種潛伏于意識表層之下的潛意識的活動方式顯得尤為重要,它有助于了解到精神病患者的真實心理狀況,從而從心理學的角度給與其積極治療,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解決美國當代社會恐怖的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1]彭畘齡.普通心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43.
[2]汪柳花.解讀《荊棘鳥》中的瑪麗·卡森:以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為視角[J].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5):59-63.
[3]趙云龍,趙建新.論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論[J].社會心理科學,2013(1):24-26.
[4]李麗丹.俄狄浦斯情結研究及其批判——兼評俄狄浦斯神話與文學批評的關系[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17-20.
[5]畢金儀.淺談心理防御機制理論[J].中國社區醫師,2006(14).
[6]顏剛威.試論心理防御機制理論[J].黑河學刊,2017(6).
作者簡介:溫竹梅,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