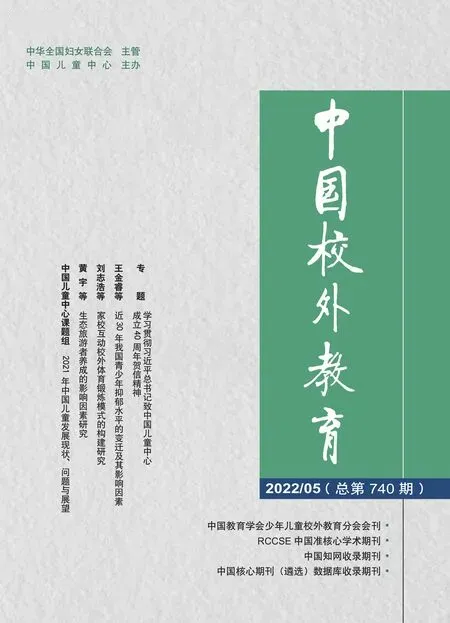近3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王金睿 周姿言 邱凡碩 彭海云 劉匯濤 辛素飛
一、引言
抑郁(depression)作為一種常見的心理衛生問題,在青少年群體中尤為常見。有研究表明,抑郁是青少年自殺、吸煙、酗酒、學習能力下降、攻擊等問題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1]。因此,青少年抑郁問題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然而,當前關于青少年抑郁狀況的研究結果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者認為中學生抑郁情況不容樂觀[2];也有研究表明,中學生抑郁狀況總體處于較低水平[3]。梳理對比發現,研究結果相悖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測查中學生抑郁狀況的工具及評價標準不同。例如,《流調中心抑郁量表》和《抑郁自評量表》采用基于時間頻度的4級評分法,而《中學生抑郁量表》采用基于嚴重程度的5級評分法。第二,研究對象多樣性,包括不同階段(初中生、高中生)[4]、不同類型(普通中學生、職業中學生)[5]以及來自不同生源地(城市、農村)[6]的中學生。第三,導致研究結果不同的最重要且最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現有研究對青少年抑郁的調查多處于特定時間段,而忽視了近30年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代變遷而變化的問題。另外,現有研究多從個體特征或學校及家庭環境等中介變量討論青少年抑郁狀況的影響因素[4-6],很少有研究關注經濟狀況等方面的社會宏觀因素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布朗芬布倫納和莫里斯將個體心理的各種社會影響因素歸納為一個由微觀、中觀、外觀、宏觀系統和時間系統構成的生態系統,為社會轉型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分析框架[7]。我們認為,社會轉型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依賴生態系統的傳導,其中相關的中介變量隸屬不同的生態系統,它們單獨或共同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目前關于青少年抑郁的研究多針對單一系統,缺少宏觀的系統間的探討。為此,本文借助橫斷歷史的元分析方法的優勢,探究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代的變化趨勢。同時,結合相關社會指標,探究導致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變化的宏觀因素,從更宏觀、更系統的角度,進一步擴展青少年抑郁的影響因素框架,進而為改善青少年抑郁狀況提供更系統、更全面的理論思路。
(一)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遷
近30年來,社會急劇轉型給人們的生活節奏和思維方式帶來巨大改變,同時也對個體的情緒造成一些消極影響[8]。例如,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生活節奏變快可能使得個體的負性情緒增加[9];社會轉型使得社會風氣更加開放、多元,可能導致離婚率持續上升,進而造成個體對家庭的信任感降低,感到精神痛苦、情緒低落,增加抑郁情緒產生的可能性[10]。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社會現象給青少年帶來巨大影響[11]。隨著網絡等現代化技術的發展,社會大環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逐漸增大。已有橫斷歷史研究發現,社會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使得青少年情緒的穩定性下降[12];此外,社會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增大等宏觀環境的變遷引起家庭經濟壓力增大及家庭沖突增多等近端環境的變遷,不和諧的家庭環境導致青少年滋生更多社會適應問題以及更多消極自我評價[4][9]。情緒的穩定性下降與持續性的自我否定是抑郁的核心特征[13]。因此,本研究推論我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也呈逐年上升趨勢,并著重從更系統的宏觀視角針對青少年抑郁的內在影響機制進行深入探討。
(二)影響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社會因素
通過整理青少年抑郁的影響因素發現,早期研究多從人口統計學變量(如年級和性別等)進行討論[14],后來從個體其他的心理特征角度(如應對方式、心理素質等)探討[2][5]。隨著社會劇烈變遷對抑郁的影響逐漸凸顯,研究者發現社會環境(如生活事件、社交體育活動等)因素對個體抑郁的影響已不容忽視。[3]因此,對青少年抑郁變化趨勢的探究需要進行宏觀思考。結合以往研究,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比較增多,導致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經濟地位下降,進而使人際適應力下降,引發一系列情緒問題[15]。盡管隨著經濟發展,一定的地區差距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但如果地區經濟差距過大且長期得不到解決,很可能影響社會安定,導致總體威脅增加[16],進而可能導致青少年產生一系列情緒適應問題,抑郁水平上升。再加上快速的人口轉變與劇烈的社會變遷導致社會聯結程度降低,進而導致家庭社會發生一系列變化,如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17]。而青少年在核心家庭中處于重要節點地位,家庭環境變遷對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具有重要影響[18]。綜上所述,本研究從經濟條件、社會聯結和總體威脅三方面入手,探討宏觀社會環境變化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無法分離的[7]。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目前處于下降趨勢,而抑郁是心理健康的核心消極指標之一[19]。我國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上升使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但同時也帶來生存成本過高、家庭經濟負擔上升等問題。家庭經濟負擔過重可能導致青少年在學校中感到自卑,進而可能使其遭受同伴排斥[15],最終引發青少年一系列負性情緒(如焦慮和抑郁等)。與此同時,隨著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不斷擴大,社會負面情緒的累積使其主觀感知到更多孤獨感,這可能會提高其抑郁發生的可能性[20]。此外,近3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21],說明我國居民貧富分化逐漸加大。有研究發現,青少年面對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時,可能會產生無力感及一系列行為退縮(如學習和社交等),繼而引發其低自尊、孤僻、自卑等負性情緒[4][15],這可能導致其抑郁程度進一步增加。因此,本研究選取居民消費水平和基尼系數作為經濟條件方面影響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變化的社會指標。
其次,隨著經濟環境改變,家庭同樣發生了劇烈變遷。這一劇烈變遷導致家庭聯結減弱,進而引發的近端環境因素改變與抑郁存在明顯關聯[18]。逐年提高的城鎮化水平使整體人際環境不斷陌生化,個體和群體間的人際信任程度有所下降[22],整體焦慮水平呈上升趨勢[23]。而社會環境中的信任危機和焦慮情緒可通過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進而影響其抑郁程度[7]。與此同時,城鎮化水平提升帶來家族成員的流動和分離,致使現代社會的家庭規模呈現小型化趨勢,這一變化造成核心家庭生存的經濟成本、關系成本上升[9][17]。父母需花費大量時間工作,進而導致家庭沖突增多,陪伴孩子的時間、與孩子溝通的次數減少。這導致青少年獲得的社會支持資源不足,面臨挫折時可能更容易受傷,從而產生抑郁等消極情緒[9]。同時,逐年上升的離婚率降低了家庭功能的完整性[18]。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父母卷入程度下降,進而可能對其抑郁狀況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離婚率、家庭規模數和城鎮化水平作為社會聯結方面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變化的宏觀社會指標。
最后,社會轉型引發的社會威脅可能會對青少年成長環境產生重要影響。近年來,我國犯罪率不斷上升[21],社會負性事件頻發,以致青少年感知到的環境不確定性增強。這些變化可能降低青少年的安全感,進而影響其抑郁水平[24]。此外,教育狀況的變化也是中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變差的一個重要原因[11]。在我國當前教育環境下,片面追求升學率會加重中學生的學業壓力,進而加劇學生的抑郁狀況[6]。隨著國家各級各類學校逐步擴招,我國的初中升學率和高中升學率逐年提高,各種選拔考試具有強烈的競爭性,導致以超前教育、課外補習和升學競爭為主要形式的教育競爭與威脅增多,對中學生抑郁狀況產生負面影響[21]。因此,本研究選取犯罪率、初中升學率和高中升學率作為社會總體威脅方面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變化的社會指標。
綜上,目前對青少年抑郁影響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青少年個體特征及家庭環境影響等微觀或中觀層面,而本研究結合已有文獻,利用橫斷歷史研究方法的優勢,從宏觀社會層面探究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縱向變化趨勢,以及相關社會因素對青少年群體抑郁狀況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近年來,關于測量青少年抑郁的研究工具有20多種,包括《流調中心抑郁量表》《貝克抑郁量表》《抑郁自評量表》等。在眾多測量工具中,《流調中心抑郁量表》由于測量內容全面,且符合抑郁的通用定義,得到了廣泛關注。更重要的是,經過文獻檢索發現,截至目前,《流調中心抑郁量表》使用頻次最高。而且,相較其他測試抑郁水平的量表而言,該量表更適用于調查一般人群,而非病人,現已被廣泛應用于測量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相關研究[14][25]。因此,本研究選擇該量表作為研究工具。該量表共有20個條目,要求被試根據最近1周內出現相應癥狀的頻度進行4級評分,得分越高代表其抑郁水平越高。
(二)文獻搜集的標準與結果
本研究的文獻搜集標準如下:(1)文獻都使用《流調中心抑郁量表》;(2)文獻中有明確的統計指標(N、M和SD);(3)研究對象是年齡在11~18歲的中國內地青少年群體,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4)同一作者使用同一批樣本數據發表的多篇文章,只保留發表時間最早的一篇;(5)文獻發表時間截至2020年12月底。
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和Elsevier、Wiley等中外文數據庫中,分別以“青少年”“中學生”“抑郁”“心理健康”“adolescents”“middle school students”“depression” “mental health”等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篩選流程見圖1),共得到符合標準的129篇文獻(包含16篇英文文獻,所有文獻的發表時間均在1993—2020年),由于有2篇文獻的數據分別從兩個不同質的被試群體獲得,只能分別錄入,因此最終獲得131組數據(詳見表1)。基于已有研究的做法,除明確標注數據收集年份的文獻外,其他文獻的數據收集年份均用“發表年份-2”的方式計算[11]。因此,本研究的數據收集年份跨度為28年(1991—2018年),共包括203160名中學生(詳見表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
(三)文獻編碼及數據整理
本研究將最終篩選出的131組數據在SPSS 22.0軟件中進行編碼及數據錄入。首先,將每篇文獻的發表年份、數據收集年份、樣本量以及抑郁的均值、標準差錄入數據庫中;然后,對文獻的其他信息(包括期刊類型、地區、學段和性別比例等)進行編碼(詳見表1)。

表1 納入分析的原始研究基本信息和變量編碼賦值表① 為減少篇幅,表中只列出第一作者;性別比例為女生人數/總體人數;期刊類型一列:1=核心期刊(指“SCI”“SSCI”“CSCD”“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收錄的期刊),2=一般期刊(除“核心期刊”外的期刊),3=學位論文或論文集;地區一列:1=東部地區,2=中部地區,3=西部地區,4=包含兩類及以上地區;學段一列:1=初中生,2=高中生,3=中學生;NA表示文獻沒有提供相應數據信息。

續表1

續表1

續表1

續表1
(四)社會指標的數據來源
本研究從經濟條件、社會聯結和總體威脅三方面選取8個社會指標(即與中學生抑郁水平直接相關的指標),并考察這些社會指標對中學生抑郁的“預測”作用。所有社會指標的數據來自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法律年鑒》。
三、研究結果
(一)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份的整體變化趨勢
為描述中學生抑郁水平隨年份的變化趨勢,本研究以數據收集年份為橫坐標、抑郁均值為縱坐標,繪制散點圖。如圖2所示,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份的變化呈上升趨勢。

圖2 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化(1991—2018年)
同時,我們以抑郁均值為因變量,以數據收集年份為自變量進行加權線性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在加權樣本量后,年份可顯著正向預測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β=0.36, p<0.001),年份的解釋率達12.6%。同時,為控制額外變量(如期刊類型、性別比例、地區、學段等因素)對結果的影響,本研究還以抑郁均值為因變量,以數據收集年份、期刊類型、性別比例、地區和學段為自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加權樣本量的同時,納入其余4個變量后,青少年抑郁的年份效應仍然顯著(β=0.35, p<0.001),年份可以解釋抑郁12%的變異。由此可知,1991至2018年間,我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
此外,為探究28年來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上升幅度,我們根據以往研究[26]的做法,首先在加權樣本量的同時,以抑郁均值為因變量,數據收集年份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方程(y=Bx+C)。然后將年份1991和2018代入方程中,得到這兩年的抑郁均值。最后計算M1991和M2018的差值,再除以28年間的平均標準差(MSD),即為d值。結果發現,從1991年到2018年,青少年抑郁均值上升了5.92分,即上升了0.62個標準差(d=0.62)。根據Cohen[27]的效果量評定標準可知,青少年抑郁均值的上升幅度介于中等效果量與大效果量之間。
(二)青少年抑郁與宏觀社會指標的關系
由上可知,近3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份呈線性上升趨勢。那么,其上升趨勢與宏觀社會變遷有怎樣的關聯呢?如前所述,青少年抑郁與上述8項宏觀社會指標間的相關或許可以解釋。結果顯示,加權樣本量后,除基尼系數外,當年的其他社會指標均對青少年抑郁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見表2)。而且,為更加詳細地說明社會變遷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按照以往相關研究的做法[11],采用滯后相關分析的方法將歷年的抑郁均值分別與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宏觀社會指標進行匹配。結果顯示,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社會指標能顯著預測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化。因此,經濟條件、社會聯結和總體威脅方面的變化可能是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

表2 社會指標與青少年抑郁的關系① *p<0.05, **p<0.01, ***p<0.001。
四、討論
本研究采用橫斷歷史研究方法考察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化趨勢,結果發現,近3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呈上升趨勢,這與很多學者提出的“中學生抑郁狀況不容樂觀”這一觀點基本一致[2],也與我國青少年焦慮等消極情緒呈上升趨勢吻合[23]。但與以往考察青少年抑郁狀況的橫斷面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創新之處是:基于研究結果,以更為宏觀的視角探究青少年抑郁的影響因素。我們在考察青少年抑郁水平時納入時代變遷這一動態維度,系統地刻畫青少年抑郁的總體變化趨勢,縱向拉伸以往研究的理論意義。此外,以往多選用青少年群體中的個體作為研究對象,缺乏對個體與宏觀環境關系的關注。事實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網絡普及化,個體的社會關系不僅包括個體間的交往,也包括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的聯系[28],故在討論影響青少年抑郁的各類因素時,更應關注“青少年群體”這一抽象概念。基于此,本研究利用橫斷歷史的元分析這一方法的優勢,以近30年發表的有關青少年抑郁的129篇文獻為研究對象,從“群體”視角考察青少年抑郁的整體狀況,使青少年群體抑郁的理解廣度得以橫向拓寬。而且結合生態系統理論,宏觀因素(如宏觀經濟條件)不僅直接影響個體或群體的心理發展,還通過中觀因素(如家庭環境)等中介變量對微觀心理發展產生影響,即宏觀社會的變遷可通過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影響青少年抑郁的變化趨勢[7]。總體來看,青少年抑郁的發展離不開個體與群體、近端與遠端環境和社會變遷因素。但由于宏觀因素難以調控,改善青少年的抑郁狀況需同時關注與之相關的中觀、微觀因素。因此,本研究對宏觀因素(如經濟條件、社會聯結及總體威脅)與青少年抑郁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與整合,并從宏觀、中觀、微觀系統間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探討我國青少年抑郁的潛在影響機制。
(一)我國青少年抑郁的潛在影響機制
首先,本研究發現,當年、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兩項社會指標(居民消費水平和基尼系數)均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抑郁水平。這說明,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家庭經濟壓力增大是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雖然我國家庭收入不斷增長,但醫療、教育等家庭消費支出卻不斷上漲[22],加之近年我國社會弱勢心態呈泛化趨勢[29],家庭經濟壓力增大與社會弱勢心態泛化的疊加效應,既削減了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降低了青少年的安全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導致其抑郁水平上升[30]。此外,有研究發現,社會貧富差距增大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產生負面影響[20]。由于青少年認知容量和社會意識的迅速發展,其對貧富差距越來越敏感[30],而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又為青少年提供大量上行社會比較的機會,這可能使其更直觀地感受到貧富差距,致使心理健康水平下降[20],進而引起抑郁水平上升。
其次,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也可能與社會聯結的弱化有關。本研究發現,與社會聯結這一因素相關的三項社會指標(離婚率、家庭規模數和城鎮化水平)的增加顯著預測青少年抑郁水平的上升,可能原因如下:第一,自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大家庭逐漸被核心家庭取代,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及其聯結功能減弱[8],青少年通過家庭獲得的支持和社會資本有所減少,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對自己形成否定性評價[31],進而增加其抑郁發生的概率。同時,逐年升高的離婚率使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等特殊家庭的比例升高,以致父母的教養方式產生了過分保護和嚴厲懲罰等消極變化。而不合理的教養方式正是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原因[32],因而隨著父母教養方式的消極變化增多,青少年抑郁的強度隨之上升。第二,城鎮化水平提高引起社會群體的遷移規模不斷擴大,這使得人際環境的流動性增強[33],而人際問題也變得多樣化和復雜化。復雜多變的人際環境不僅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變差[23],也會使教師、父母等群體的焦慮和不安全感等消極情緒體驗增多[34]。同時,從微觀系統看,城鎮化需較高私人成本(租房安家費用、子女教育費用),這一現象導致家庭生存壓力變大,父母不得不外出工作以平衡收支關系,甚至可能面臨付出大量時間卻沒有獲得預期收益(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高質量的教育)的狀況,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父母的心理落差感,引發群體的消極情緒。以往研究發現,群體的消極情緒在人際互動中具有一定的彌漫性[35]。這一心理落差極有可能影響子女的情緒,進而導致抑郁等非適應性問題增多[36]。
最后,中學生抑郁水平上升還可能和與其相關的總體威脅增加有關。本研究發現,總體威脅相關的三項社會指標(犯罪率、初中升學率和高中升學率)均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抑郁水平。近年來,我國犯罪率的波動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增多以及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37]。而且,現代媒體傳播的全時性、全域性和全渠道性使青少年接觸的暴力游戲和圖片增多。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觀點,長時間接觸暴力刺激會使青少年習得攻擊行為以解決問題,同時對社會的不信任感增強。此外,隨著社會變遷,社會對教育結果的期望和要求大幅增加,家長和學校將此“期望壓力”以“分數”“升學率”等形式轉移到學生身上,給青少年帶來巨大的課業負擔,造成學業競爭加劇[6],不可避免陷入“內卷”,進而影響其抑郁水平。
(二)本研究的局限及未來展望
盡管得到上述有意義的結論,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除《流調中心抑郁量表》外,還有《抑郁自評量表》《兒童抑郁問卷》《中學生抑郁量表》等測量青少年抑郁水平的量表,可待未來文獻數量充足時采用其他量表與本研究結果進行對比驗證;其二,本研究探討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隨年份的變遷趨勢,并對社會宏觀遠端環境影響近端因素的作用機制進行解釋,但沒有對具體影響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未來可針對青少年抑郁的具體影響機制展開追蹤研究,從而更準確地揭示青少年抑郁水平的變遷趨勢。
五、結論
1.近3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水平逐年上升;
2.經濟條件、社會聯結及總體威脅可能是預測青少年抑郁水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