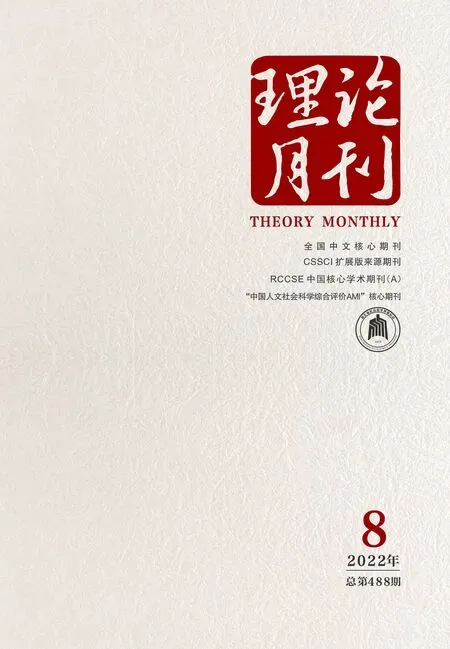從自律到參與
——藝術“介入性”的理論演變
□孫煒煒
(湖北美術學院 影視動畫學院,湖北 武漢 100083)
一、引言
20世紀,在西方的兩個前衛藝術浪潮——歷史前衛主義(1917—1968)和新前衛主義(1968—1989)——過去之后,以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和 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為代表的西方藝術批評家們都斷言:“現代藝術已經終結。”如丹托在《藝術的終結》中所述:“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數百種運動:立體主義、野獸派、建構主義、至上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宣言。這一切都過去了。藝術史不再受某種內在必要性的驅動。沒有人感覺到敘述的方向。”但是,就算對藝術史的書寫停止了,藝術家們也不會接受藝術已死的結論,他們仍受內在必要性的驅動,繼續探索著藝術可以為社會做些什么。尤其是2020年以來,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人類的危機,世界各地都涌現出了各種各樣的用藝術影響社會的項目——有進行心理療愈的、有團結志愿者的、有幫助經濟困難人群的、有反思人類生存方式的……它們都在不斷證明,藝術會隨著外部環境變化而演變出新的類型和策略,從而保持自身對社會的深刻影響。
在西方,以“社會介入”為第一要務的藝術創作在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運動中就有了雛形,并在兩個前衛藝術時期中逐漸成熟,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井噴期。西方理論界也開始給這類藝術正名,并建立了“社會介入性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等專門分類。而到了21世紀,此類藝術已成為國際上最前沿的藝術創作和研究課題之一。在近年來的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展覽上,這類作品逐漸占據主要席位,并屢獲大獎。這種藝術類型外延寬廣,不囿于傳統的美術、戲劇、電影等藝術分類,具有與生俱來的跨媒介、跨學科的特點。其基本特征是:藝術家針對特定的社會現象進行創作,強調公眾的參與性,通過藝術家與公眾的合作而完成作品,并力求以藝術的方式改造社會。這體現出當今的藝術家已經不滿足于反映社會,而更希望介入社會。簡而言之,此類作品是資本主義體系中“藝術商品”的對立面,代表著當今世界藝術發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那么,研究社會介入性藝術的首要問題是什么?以下這個典型的藝術案例常常引發人們的質疑:2016年,藝術家塔尼亞·布魯格拉(Tania Bruguera)在網絡上發布了一個視頻,聲稱自己要參加2018年總統大選,并邀請網友在線上討論——如果他們當選總統,將如何創造更美好的國家。而這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她的藝術作品,她想以此來引發公眾的討論,喚醒公眾的愛國意識。但是,這個作品的藝術性備受質疑,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藝術?”由此,我們可窺見社會介入性藝術的前衛性——其作品可以表現為任何形式,包括藝術家所創造的某種社會現實,而不必是某種物件。
進一步說,“這是不是藝術?”可以被轉化為“藝術的定義取決于美學本身,還是社會意義”這個問題,也可引申出“藝術該不該介入社會”“該怎樣介入才能保持自身的獨特性”等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背后體現的是西方藝術理論家自19世紀以來就持續進行的關于藝術自律和藝術他律的討論。只有理清這兩個觀點在西方藝術史中的糾纏和演化,我們才能理解藝術是如何一步步介入社會的。
二、“介入”的終極問題:藝術自律或藝術他律
(一)藝術的哲學評判標準
在哲學領域,藝術自律是人們用以描述藝術區別于其他社會活動的特殊性的美學概念。它肯定了藝術與社會之間的距離,與藝術他律這個概念相對。在19世紀末以來的美學論著中,它通常被用來強調藝術品沒有任何實際功能和功利價值。而在當代藝術批評中,藝術自律常常指以藝術作品自身的美學意義作為評價標準,而藝術他律則是以其他領域(如政治、宗教、道德和科技)的價值作為對某個藝術作品的評價標準。
最先在哲學上系統闡述藝術自律的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他將藝術區別于其他學科,指出“審美判斷”具有不同于感覺和理智的特殊的意義。這使審美和藝術自律性成為可能。“沒有關于美的科學,只有關于美的評判;也沒有美的科學,只有美的藝術。”人類社會中獨立的審美領域由此被構建起來,自律性審美成了獨立的美學學科的重要前提。
在康德的自律論的基礎上,黑格爾建立了獨具一格的法哲學體系,使自律和他律得以統一。黑格爾的藝術觀也跟他對自律和他律的判斷密切相關。他提出了一個具有歷史創新意義的觀點——藝術終結論,直接影響丹托、貝爾廷等人。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黑格爾,還是后來的這些藝術批評家,都不是要給藝術判死刑:“其實我們只要認真研究黑格爾有關藝術終結的敘述就會發現,他宣布即將終結的是那種承擔著真理言說之偉大職責的藝術。同樣,丹托等人宣布將要終結的,也并非藝術本身,而只是近代以來審美現代性所推崇的‘自律性’的藝術。”
在黑格爾看來,世間的種種存在都是以理念的運動為基礎的,包括藝術在內的一切存在,都是絕對運動的外在表現形式。隨著社會的變革,藝術也會通過其內部要素的競爭而實現新的轉變。這種競爭會逐漸使藝術突破其原有的形式,走向解體。換言之,在黑格爾看來,藝術一旦無法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那么它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便會逐漸被其他事物(如哲學)所取代。因社會變革而拓展疆域的藝術,不正是社會介入性藝術嗎?這樣的藝術能否突破黑格爾當時的想象界限,實現自律和他律的統一?20世紀下半葉,西方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導致工具理性盛行、主客分離等情況,逐漸腐蝕著生活和社會。借助現代資本主義的傳播和生產方式,西方的文化產業為消費者提供了虛假的滿足感,催生出“景觀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藝術怎樣在介入社會的同時又保持自律,成了學者們關注的熱門話題。
(二)藝術介入社會的美學基礎
西奧多·W.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在1962年發表了《關于介入》一文,是最早關注“藝術介入”這一話題的批評家之一。阿多諾認為,藝術以審美方式表達了對異化社會的反抗,因此,他主張藝術應該自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律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是指藝術具有與生俱來的社會批判性。他以波德萊爾的作品為例,說明真正的藝術只有在無視藝術市場的情況下,才會具有批判的光環。雖然阿多諾是左派思想家,但他特別反對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主張的直接說教或宣傳,認為這種直接的政治介入并不會“產生一種方法、一種合法的方式或一種實際的活動”。藝術應該以其自身的否定性、批判性和模仿性的特征介入社會。由于現當代藝術的外延難以界定,形式便成為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唯一中介。簡而言之,阿多諾的介入理論是一種認識論。他所論述的藝術自律切斷了與社會的關系,但每一件作品都能自給自足,都是社會現實的影子。從這個角度來看,形式更完善的藝術能夠對社會進行更為實質的介入。總的來說,雖然阿多諾的介入美學強調社會批判,但卻是與政治行動無關的非實踐性理論,還不足以成為社會介入性藝術的直接理論支撐。
關于藝術介入的重要理論轉折點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阿諾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在1991年出版了《藝術與參與》一書,提出了“審美參與”理論,并指出欣賞當代藝術的關鍵方法之一是“參與性介入”:“參與不僅被認為是許多創新的藝術和教育中的一個明確因素;它也成為了理解審美體驗的各個方面的關鍵因素。”他提出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挑戰康德“審美無利害”的理念。他提倡摒棄審美二元論,強調主客體的積極融合,或者說藝術自律與他律的統一。“對于作為藝術創造者和欣賞者的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作出的貢獻——這種貢獻是積極的和構成性的。這就是為什么我稱之為介入性美學,參與式美學。”從康德開始,經歷了以上對藝術自律和他律的討論,伯林特終于使藝術名正言順地走入了社會,并讓觀眾走入了藝術。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基礎上,“介入”和“參與”將自律和他律統一起來,這兩者不再非此即彼、相互對抗,這就為當代美學理論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經驗方法和解釋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之后所有關于藝術介入性的探討都延續了被黑格爾“終結”的藝術理論。
三、“介入性美學”的兩條路徑:關系美學與岐感美學
無論是阿多諾還是伯林特,都是在純美學的框架下談論介入/參與,并沒有深入到當代藝術批評領域。如前所述,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學界才開始對“社會介入性藝術”進行分類和理論梳理。21世紀,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催生出兩大批評話語體系——“關系美學”和“岐感美學”。這兩者構成了許多從事社會介入性藝術研究的評論家,如格蘭特·凱斯特(Grant Kester)和克萊爾·畢曉普(Claire Bishop)的核心理論基礎。
(一)關系美學
關系美學最早是由學者和策展人尼古拉斯·博瑞奧德(Nicholas Bourriaud)在1998年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被用來描述和解釋以交流和交換機制為前提的藝術作品。博瑞奧德發現,由偶發藝術(Happenings)和激浪派(Fluxus)培養的“觀眾參與”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后藝術實踐的常態。博瑞奧德從中歸納出新的美學——關系美學。關系美學尋求主體間的相遇,強調藝術家不再只是創作作品,而是要在特定情境下建立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感知機制。運用這種美學的“關系藝術”,通過藝術家與觀眾的共創使自律和他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實現了伯林特的美學追求。“當代藝術作品的形式正在從它的物質形式向外擴展:它是一個鏈接元素,一個動態凝聚的原則。”由于觀眾參與的關鍵作用,藝術家放棄了在作品中的主導地位,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或社會活動的發起人、推動者,讓藝術在大眾和社會的影響下自然生成。由此,博瑞奧德重新定義了藝術家的角色,以及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關系,并梳理了當今的參與式藝術最常見的范式和策略。
關系藝術是基于關系和溝通的藝術。因此,要評價這些藝術作品就必須考慮這種關系是如何建立的。通過分析博瑞奧德列舉的藝術案例,我們可以感知到,他認可的“關系”的基本標準是“協商”和“共存”。而另一位此領域的重要學者克萊爾·畢曉普在她2001年的文章《對抗與關系美學》中全面批判了這種標準。如果說關系藝術的核心只是讓觀眾簡單地參與到藝術作品中來,與藝術家一起創作,那么這種和諧場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她借助博瑞奧德介紹的一個具體藝術案例——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的作品《明天是另一天》展開分析。這個作品的全部內容就是提拉瓦尼在一個展覽上邀請觀眾一起做飯、分享美食。難道藝術家和觀眾的共同烹飪就構成了“協商”和“共存”嗎?在這篇文章中,畢曉普也介紹了另一位南美藝術家圣地亞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在2001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作品《給雇傭的133人染金發》。這133人是西耶拉邀請的威尼斯街頭的非法小販——大多數是來自意大利南部、塞內加爾、東亞和孟加拉國的黑發移民。于是,路人在雙年展期間看到了一個奇怪的場景,街上的眾多小販的頭發突然都變成了和歐洲白人一樣的金發。畢曉普認為,在這幅看似輕松幽默的作品背后,藝術家有效地揭示了民族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顯然,與提拉瓦尼作品中和諧舒適的“協商”與“共存”相比,西耶拉作品所反映的關系揭示了潛在的問題或沖突,測試了社會與藝術的界限。
綜上所述,雖然博瑞奧德提出的“關系藝術”和“社會介入性藝術”在很多語境里幾乎等同,但比起“關系”,“介入”強調的是對社會現實的直接干預,以及其明確、主動的政治態度。畢曉普提倡的“關系”較之博瑞奧德的,更接近于筆者所要討論的“介入”。除畢曉普外,其他西方評論家也指出,雖然關系美學誕生于前衛的語境中,但過分強調藝術創作應包含人際交往、會面、協商、合作等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這就使藝術失去了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判作用,陷入政治保守主義。
(二)岐感美學
自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發表《美學的政治:可感性的分布》以來,以畢曉普為代表的左派藝術評論家獲得了一種實用的方法論,從而對關系美學中的保守政治傾向進行猛烈批判。與在藝術理論領域深耕的博瑞奧德不同,朗西埃是一位哲學家,并建立了獨特的政治哲學體系。朗西埃從他的政治美學理論出發,認為無論是媒介特異性還是藝術政治二元論(或者說藝術自律與他律二元論),都不能幫助人們真正理解藝術的介入性,正確途徑是先理解現代藝術與現代政治的關系。“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就是政治美學與藝術美學的關系。”他認為美學與政治是同源同構的,都始于法國大革命時期,以追求民主為基礎。因此,他認為美學和政治是一體的,而非阿多諾所主張的二元分離。他把藝術中的美學稱為“元政治”,即美學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需要追問的是,在審美活動重構知覺體驗時,不同知覺之間、知覺與材料之間有著怎樣的核心關系?20世紀的當代美學構建了怎樣的新關系?朗西埃的回答是“岐感”(Dissensus),它指的是不同感性認知之間的“沖突關系”,而不是古典美學中的“再現體系”。在古典藝術中,藝術以模仿現實為基本訴求,遵循統一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但是,在浪漫主義之后,藝術實踐便不再服從于社會等級秩序,藝術家們并不滿足于畫匠或樂師的身份。任何主題和形象都可以成為藝術,人人都可以欣賞和創作藝術,美學體系也得到了相應的更新。在古典藝術體系中,認知之間的關系是和諧一致的;在當代藝術體系中,認知之間的關系則可能是相互沖突的。朗西埃將藝術的審美制度劃分為三個層次——“圖像的倫理制度”“藝術的代表制度”和“藝術的審美制度”。在三種審美機制中,前兩種都體現為“藝術家創作—觀眾接受”的一維的感性傳遞,在“藝術的審美制度”中,藝術家不再停留于制造藝術品,而是因其跟生活的沖突性的“岐感”而產生意義。朗西埃由此看到了美學與政治的一元關系——當代的藝術最終演變為對社會現實的實際干預。
以畢曉普為代表的新一代藝術學者在當代藝術批評中引入政治哲學,使藝術批評在哲學和美學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社會學來探討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回應了當代藝術創作中日益增長的介入性需求。在關系美學和岐感美學的助推下,當代藝術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社會實踐,藝術自律和藝術他律之爭似乎已失去意義。那么,如何建立一個關于此種藝術的有效的藝術批評體系?
四、社會介入性藝術批評的關鍵理論
(一)社會介入性藝術的研究現狀
在哲學、美學和政治哲學理論的基石上,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藝術批評領域對社會介入性藝術的研究接踵而至。時至今日,此類藝術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研究主題。在這些研究中,有一些反復出現的高頻,如公共、行動、情境、對話、協作、參與、社區、特定場景、劇場和表演等,能夠被看作此類藝術批評體系的坐標點。
1995年,此領域的先驅藝術家和理論家蘇珊娜·萊西(Suzanne Lacy)創造了“新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一詞。作為一名雕塑家,她明確主張當代藝術家不應僅僅將戶外雕塑作為公共藝術,而應以藝術介入社會現實,創造一種新型的公共藝術。“現代主義模式在多元文化和全球互聯的世界中不再可行,正如理論家蘇西·蓋伯利克(Suzi Gablik)所建議的那樣,視覺藝術家們正在努力尋找更適合我們時代的新角色。”同年,批評家尼娜·費爾申(Nina Felshin)編輯了一本討論介入性藝術的論文集《但它是藝術嗎?》,介紹和分析了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激進的社區藝術,強調了憑借藝術而“行動”的必要性。盡管萊西和費爾申的論述引起了學界對社會介入性藝術的關注,但她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案例研究上,還缺乏美學、哲學、社會學方面的理論依據,沒有深入地分析這種新藝術類型帶來了怎樣的自律與他律。
2000年以后,社會介入性藝術的研究才走入正軌,出現了一些解釋藝術新范式的概念。2004年,由克萊爾·多爾蒂(Claire Doherty)編輯的《當代藝術:從工作室到情境》將從事此類藝術的藝術家稱為“新情境主義者”,以呼應居伊·德波(Guy Debord)“建構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的理念——20世紀50年代末期,德波和“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用這個理念倡導藝術家在現實中構建情境來推動社會進步。多爾蒂認為,當代的藝術家正在加速實現這一構想——他們在社會現實中不斷構建特定的時間、空間和事件,從而改變世界。同樣在2004年,格蘭特·H.凱斯特(Grant H.Kester)發表了著作《對話片段:現代藝術中的社區與交流》,在其中討論了許多當代藝術家基于對話的社會介入性藝術,并創造了“對話性藝術”和“協作藝術”的概念。他的“對話美學”將藝術介入的意義生成原理融入人與人的對話關系中進行考察。2006年,畢曉普的論文《社會轉向:參與及其不足》使“社會轉向”成為藝術界的流行語,明確指出當今最前衛的藝術正在向社會進發。2012年,她將多年來對此課題的研究匯編成《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一書,因這本書對“參與”概念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歷史梳理,很快便被西方學界視為社會介入性藝術研究的里程碑。迄今為止,凱斯特的“對話”“協作”概念與畢曉普的“參與”概念是西方社會介入性藝術理論的主要批評角度。
(二)社會介入性藝術的兩個主要批評角度
凱斯特的“對話”概念強調,藝術家為實際社會空間中的特定社群創造交流機會,并帶有明顯的制度批判的傾向。它不是指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交流,也不是指觀眾與作品之間的交流,而是指不同社群之間的溝通——這是藝術家創作此類作品的主要目的。那么,對話性藝術與一般藝術實踐之間的具體區別是什么呢?凱斯特認為,前者可以超越畫廊和美術館系統的限制,這意味著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于展覽空間之外。雖然不同作品發起的對話涉及不同的內容和目的,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旨在為對話和交流提供創造性的空間”,而且“對話即是作品本身的一部分,它被藝術家構造為一個積極的生發過程”。
基于“對話”概念,凱斯特在2011年又提出了“協作”這個關鍵詞。在他看來,“協作”比“對話”更為廣泛:藝術中的協作元素不是對話的前提,但一旦有了對話,協作就已經發生了。盡管凱斯特和畢曉普一樣都使用了“參與式藝術”一詞,但凱斯特并沒有將其與“協作”區分開來。在筆者看來,凱斯特對“協作”的偏愛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場:他對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個性,尤其是藝術家在創作中的絕對主體性保持質疑態度,而“協作”無疑更能凸顯作品中隱含的集體主義傾向。如果“參與”還留下了藝術家主導作品的優勢,那么“協作”將徹底消除它。總之,凱斯特所謂的“對話”重在“說”,而“協作”重在“做”,兩者都自覺地疏離了傳統的理論話語。
可以說,凱斯特的批評話語是對“關系美學”的進一步擴充。除了強調“社群”這個特定范圍之外,他的“對話性藝術”和“協作藝術”看起來與博瑞奧德的“關系藝術”相差無幾。那么,在他的理論框架內,如何賦予這些“對話”和“協作”的活動以藝術的自律性?或者說,這種藝術的審美產生機制是什么?凱斯特沒有從當代美學或哲學中尋求理論資源,而是回到康德那里。在康德的論述中,“共通感”是建立審美判斷的基石。凱斯特認為,對話和協作的藝術可以在三個層面上產生“共通感”:一是藝術家與合作者之間的和諧對話,二是合作者之間的團結,三是能夠引發觀者共鳴的藝術成果。既然找到了這樣的創作能生發“共通感”的確鑿證據,凱斯特由此推斷出對話藝術中存在著審美判斷,并將這種“共情”概念改造為“移情”概念。不同的是,康德的審美判斷是基于主體在審視外在對象時所產生的獨特情感,而對話藝術的審美則是基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交流所產生的共情。
同凱斯特的理論相比,畢曉普的“參與性藝術”理論找到了一條更獨特和激進的道路。在她看來,“參與”是建立“關系”“對話”和“協作”的最基本步驟和根本方法。“藝術家與其說是不相關的物體的個體生產者,不如說是情境的合作者和生產者;藝術作品作為一種有限的、可攜帶的、可商品化的產品,被重新構造為一個開始和結束不明確的持續或長期項目;而觀眾,以前被視為‘觀眾’或‘旁觀者’,現在被重新定位為共同制作者或參與者。”這樣的論述聽起來跟“關系藝術”“對話性藝術”“協作藝術”類似,但是畢曉普卻跟創造這些說辭的學者持不同意見。如前所述,畢曉普曾批評關系美學的“關系”不夠政治化、缺少批判性。在2006年討論“社會轉向”的文章中,她重點批判了當代藝術評價標準的“倫理轉向”,指出凱斯特一類的批評家僅關注藝術家是否在作品中放棄了個人地位,是否充分尊重參與者的言論自由,而忽略了藝術作品的審美角度。關于凱斯特的“對話性藝術”,她批評道:“他挑戰我們的認知,提倡將溝通視為一種美學形式,但最終,他未能捍衛這一點,并且似乎簡單地認定:只要一個合作性的藝術項目在社會干預層面上發揮作用,它就注定是成功的,即使它在藝術水平上不盡如人意。”也就是說,畢曉普認為這樣的藝術批評角度僅以藝術他律作為美學評判的唯一標準,而沒有意識到社會介入性藝術實際上可以實現他律與自律的統一。
問題在于,如何證明這種統一呢?朗西埃的理論為畢曉普提供了完美的解決方案。在《人造地獄:參與性藝術和觀看者政治》中,她遵循朗西埃的“岐感美學”,通過三個合乎邏輯的步驟,成功地詮釋了參與性、介入性作品的審美機制。首先,她縮小了岐感美學的對象,將整體審美體系中的“岐感”聚焦到參與性藝術中的“岐感”。其次,她將“岐感”解釋為“思考矛盾的能力”,這個定義更清晰、更具體地闡述了“岐感”在藝術中的運行機制——藝術家制造矛盾,藝術品表現矛盾,觀眾感知矛盾。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藝術家通過藝術作品不斷激發觀眾思考矛盾的能力。具體來說,矛盾是指參與性藝術作品中的對抗性元素,如《給雇傭的133人染金發》中外國非法商販與當地居民的身份差異,以及他們的商業活動與威尼斯雙年展制度的沖突。最后,畢曉普認為藝術的自律性在“參與性藝術”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我采用了朗西埃的藝術觀念,將藝術視為一種自主的經驗領域,其中沒有特權媒介。”藝術家不需要通過否定美學來強調作品的社會或政治性質,因為美學自身就已經包含社會或政治基因。在她看來,藝術家也不必放棄創作者的身份,讓參與者主導作品,因為藝術已經天然包含生活的材料。
綜上所述,凱斯特的觀點因訴諸18世紀初的康德美學而顯得較為保守、缺乏新意,沒有找到藝術自律與他律之間的平衡。畢曉普巧妙地借用了21世紀的政治哲學,用跨學科的新視角來審視新的藝術形式,其觀點頗具前瞻性。她在著作中強調了政治哲學對當代藝術批評的重要性:“由于參與性藝術不僅是一種社會活動,而更是一種象征性的活動——既嵌入世界又遠離世界,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在這方面最終會不如政治哲學的抽象反映有用……參與式藝術的出現要求我們找到新的分析藝術的方法,盡管形式仍然是傳達意義的重要工具,這些方法已不再僅僅囿于視覺研究的范疇。”
五、結語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了解到過去兩個世紀中,西方理論界對于藝術“介入性”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介入性藝術的審美評判體系的建構。“這是不是藝術?”是此類藝術面臨的基本和終極問題,面對這一棘手問題,西方學者必須厘清藝術自律與藝術他律間的關系。于是,他們走過了從美學到哲學再到藝術批評的漫長道路,最終建立了一個松散的藝術批評體系。
其中,關系美學強調藝術家、觀眾、藝術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狀況之間的“協商”與“共存”,在此條件下,介入性的藝術可以創造緩解社會矛盾的“社會間隙”和“異托邦”。朗西埃則讓美學與政治哲學聯姻,提出了藝術與政治的一元論。也就是說,政治是藝術內部所固有的元素,藝術是對社會的政治干預。近二十年來,在博瑞奧德和朗西埃的理論基礎上,凱斯特和畢曉普在藝術批評領域內找到了研究社會介入性藝術的兩條不同道路:前者將對話與協作看作檢驗藝術水平的最高標準,而后者則拒絕此類藝術批評中一邊倒的倫理轉向,將美學的藝術自律與社會及政治意義看得同等重要。
不管畢曉普、凱斯特和博瑞奧德之間有多少理論沖突,他們都在以各自的努力來證明這些“不像藝術的藝術”的合法性,在“藝術的終結”之后不斷創立新的批評話語。批評家們將政治哲學和其他學科的理論引入當代藝術領域,反映了當今藝術發展的新需要。西方的學者和藝術家已經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當下的社會介入性藝術是對兩個前衛藝術時期的當代回應,而且在介入性上走得更遠。藝術和政治不再各自為政,藝術家和政治家正在共同努力建立朝著人道、平等和民主的方向發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