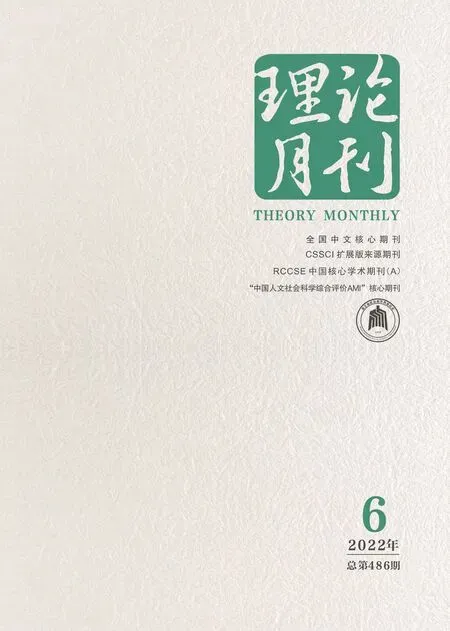區域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的發展進程與演進邏輯
——從“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到“西南特色民族文化產業帶”
□胡洪斌,江 宇
(文化和旅游部云南大學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云南 昆明 650091)
“區域發展”與“特色發展”是我國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兩大戰略。早在“十一五”時期,國家在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就提出要積極發展“西南地區具有鮮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產業群”戰略部署。到了“十三五”時期,國家先后頒布了《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總體規劃》《關于推動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建立和完善特色文化產業區域合作機制,促進區域特色文化產業協同發展。進入“十四五”時期,為了回應區域文化產業協調發展戰略,國家圍繞“支持西部地區發揮資源優勢,突出區域特色,不斷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以及“聚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持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兩條主線,進一步提出了“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的空間發展布局。從本質上講,就是要“突出西南少數民族文化活態化、多樣化特征,推動歷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風情等特色文化資源活態化展示、利用和融合發展,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主線的民族特色文化產業集群”。
一般來說,民族是在歷史演變的遷移和流動中,由于血緣、地域、共同心理素質集聚而成的“強社會關系”共同體。與此同時,民族的遷移和流動導致個體在民族之間、地域之間的社會網中發生脫嵌與鑲嵌的行為,進而形成民族之間的“弱社會關系”。民族內部的強社會關系往往是構成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關鍵,是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邏輯起點。民族之間的弱社會關系是區域內部文化多樣性引致的差異性需求在空間上得以聚合的紐帶,是區域民族文化產業帶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
由此,“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要實現區域文化產業協調發展,一方面需要依托民族內部強社會關系凝聚的文化獨特性來推動特色文化產業的在地性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之間、民族之間、地域之間的弱社會關系來實現特色文化消費在空間上的差異化集聚。在這個意義層面上,基于社會網理論的“社會關系—民族文化—經濟行為”分析框架可以成為從藏羌彝走廊到西南民族文化產業帶及其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雙向互動演進邏輯。
一、區域民族文化產業帶形成與發展的研究邏輯
民族的形成是一個不同類型的強社會關系建立并集聚的過程。通過《甲骨文字典》、金文、《說文解字》的記載,“族”字在氏族部落的社會階段,主要是指代以家族氏族為本位的軍事組織。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組織取代了氏族部落,軍事組織也就成為統治階級的“武器”。“族”字在淡化“矢鋒”含義的同時則保留和突出了“標眾”的意思。不難看出“族”強調以血緣關系作為分類人群的重要因素,并且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是一種至親的強關系。20 世紀初,梁啟超先生將德國學者布倫奇利(J.K.Bluntschli)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國,“族”字所包含的集聚意義被民族所吸收,但隨著社會發展民族體現出更多的政治性。民族與“族”代表的氏族、部落等群體最本質的區別在于,前者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后者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因而,民族除了包含“族”的人群集聚意義外,還包含國之大家的含義。血緣關系將不再作為唯一的民族特征,還包含地域關系與文化特征,這就形成了一種特定地域范圍內與共同認知下的強社會關系。因而,民族的形成是多因素導致群體集聚的結果,并且此群體中的社會關系是血緣的、地域的、共識的。這種群體集聚會產生向心力,使得群體更具有凝聚力。他們共同進行勞作與生活,建立自己的族群體制,創造語言與文化,表現出不同的群體特征,進而形成差異性的民族文化。這種差異性使得民族之間有了邊界,同時也增強了民族內部的心理認同。
民族的形成是由多種因素而導致的強社會關系的集聚,其內部具有高度的心理認同以及內部凝聚力。而民族之間由于遷移與流動使得在某一區域范圍內有了社會性或經濟性的來往,構建起一種相較于民族內部的弱社會關系。這樣,從整體性來看待多民族區域時,它的社會網趨向于立體網狀結構,民族內部的強社會關系是一個單獨的結點,結點之間又被弱社會關系鏈接。在社會網中,個人的脫嵌與鑲嵌是導致社會關系發生變化的主要行為。由于人自身是某種文化的載體,在社會活動中不時地接受著一種文化,同時又擯棄另外一種文化。因而,人從一個民族的強社會關系中脫嵌,并不是單純的社會關系的結束,還包含共同心理素質的分離,這使得他重新鑲嵌到新的社會網中時,會將之前的民族文化帶到新的群體中。因此,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伴隨著個體在社會網中的脫嵌與鑲嵌而發生的。
基于社會關系與文化特征之間的聯系,社會網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窺探到民族經濟與多民族區域之間的關系。處于我國西部的“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就是多民族地區,在它的發展歷程中包含復雜的社會網變動與經濟行為。目前,“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時,將面臨特色文化產業發展會持續強化“在地性”與區域發展訴求“共同性”的困境。社會網作為一個中觀理論,它有著不同于低度社會化(經濟學)與高度社會化(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社會關系與經濟行為之間的相互嵌入。因此,對于“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發展進程的研究,是可以從社會關系與民族文化之間、社會關系與經濟行為之間、民族文化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出發,作為從社會網視角研究區域協調發展的邏輯起點。
二、“藏羌彝走廊”發展進程中的社會關系與文化關聯
中國幅員遼闊且歷史悠久,是一個多民族國家。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就開展了民族身份識別的工作。費孝通先生對于民族識別問題,提出其核心在于對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同屬于一個人們共同體的這種心理。共同心理素質所表現出的語言與文化為民族識別工作提供了線索。
費孝通先生在對川、滇、藏和交接的川、滇西部及藏東這個區域進行民族考察時,發現在歷史上存在著頻繁的民族遷移和流動現象。這種頻繁的遷移與流動會伴隨著社會網的脫嵌與鑲嵌,使得文化在社會關系的變遷中流動。這種文化流動最容易且最明顯的表現方式就是語言。這片處于中國西部的多民族區域,主要包含兩個語支,藏語支和彝語支。屬于藏語支的有藏族、門巴族等,屬于彝語支的則有彝族、哈尼族、納西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基諾族等。語支伴隨著社會網的脫嵌與鑲嵌而產生,同時體現出藏族與彝族對于周邊民族帶來的文化影響。因而,在兼顧區域位置與人文互動下,20世紀70—8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中的“藏彝”二字理解為藏、彝兩個語支系統的民族。“走廊”一詞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含義,指該區域在地理上呈“走廊”形態,是一個“地理通道”;其二是“人文”即“歷史—民族”的含義,反映該區域是一條“歷史—民族走廊”。“歷史—民族區域”體現了空間交疊、社會關系、民族文化的歷史復雜性,但是,“藏彝走廊”僅考慮了藏族與彝族的影響,忽略了同樣是該走廊中的主要語支之一并對周邊民族有著重要影響的羌族。如果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不討論羌人對其的影響,則該民族的歷史是不完整的。1983 年,孫宏開提出了羌語、普米語、嘉戎語等十多種語言皆應屬于羌語支語言的觀點。這表明羌族也應該是“藏彝走廊”中社會網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羌人的遷徙路線大致存在三條,一是向西遷徙,二是向東遷徙,三是向南遷徙。羌人的第三條遷徙路線,也是西南地區民族格局形成的歷史原因之一。羌人的一支由岷山沿大渡河、大涼山南遷,后來定居于滇西,與當地土著民族融合,形成了哈尼、傈僳、普米、拉祜、怒、基諾、景頗、阿昌、獨龍、苦聰、拉基等族。羌族與十余個民族有著同源異流、異源同流或同源同流。“歷史—民族區域”的形成,也基于羌族與他族在社會關系上的互動。在“藏羌彝走廊”概念下的民族文化研究,實質都在揭示走廊中社會關系與文化關聯性和獨特性的聯系。一些學者通過對走廊中的神話傳說、民間信仰、文學、歌舞等進行科學的考據,從而揭示了走廊中族群遷移帶來的文化影響。這樣,民族文化特征就在復雜社會網中逐漸凸顯出來。
民族內部的強社會關系凝聚而產生的文化獨特性為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民族之間弱社會關系變遷而產生的文化關聯性則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基礎。因此,“藏羌彝走廊”中社會關系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關聯,是進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
三、“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建設中經濟行為嵌入社會關系
社會網可以在結構與行動之間搭起“橋”。多民族區域的社會網結構中包含多種類型的社會關系,進而導致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得經濟行為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在“藏羌彝走廊”中,社會關系所形成的民族的文化關聯性與獨特性,使得特色文化產業成為多民族區域轉變生計方式的一個重要產業選擇。民族內強社會關系是特色文化產業中經濟行為發生的重要基礎。由于特色文化產業的在地性傾向,弱社會關系所能帶來的社會或經濟的資源和機會都會被吸附在特定地域的特色文化產業中,并與強社會關系共同促進了特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
2014年3月,從國家層面第一次制定和頒布了區域性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規劃——《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總體規劃》。同年8月,在《關于推動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中,進一步對“走廊”建設提出了“加強對地緣相近、文脈相承區域的統籌協調,鼓勵發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特色文化產業帶”的要求。這樣看來,“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的發展可以呈現出基于社會關系、民族文化、經濟行為的關聯,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首先,多民族區域大多存在著民族文化資源富集與經濟基礎薄弱的相悖性,使得文化產業相較于工業經濟具有更強的發展適用性;其次,民族之間、地域之間以弱社會關系為主的社會網具備了文化產業實現區域發展的可能性;最后,強社會關系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能夠實現文化資源的在地性開發利用。
“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中的七省(區)依托自身的民族、地域和發展情況開發了一系列的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其一,民族村寨,這是由以強社會關系集聚而形成的民族原生態生活區域,它們往往都有著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例如貴州比較著名的有西江千戶苗寨、開陽布依族水頭寨等;四川有以康巴、納西、白馬、嘉絨、彝、羌為代表的民族文化,打造了阿惹妞民俗村寨和中國古羌城等民族村寨;云南有西雙版納傣族村寨、興蒙蒙古族鄉下村、耈街彝族苗族鄉土皮太村等。其二,在多民族區域中,受到民族文化的影響使得在當地的社會網中發生的集體活動或手工生產,表現為節慶活動和民間藝術生產。這些活動與生產是民族文化反過來影響社會網的重要手段,民族認同在個人或群體行為中得到體現。民族文化獨特性在這些活動與生產中得到展現,成為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前提。例如西藏以藏族民族文化為特色的節日,如日喀則珠峰文化旅游節、林芝桃花節等;青海省黃南州熱貢藝術,以藏族、土族等民族文化為基礎,以“六月會”“於菟”等節慶日為文化載體,進行民間刺繡、民族服飾、民族手工等藝術品的創作與生產,形成了地方性、民族性、藝術性為特征的文化產業集聚地;云南打造了一批民族文化精品工程項目,如壯族歌舞詩畫《坡芽歌書——壯鄉天籟》、傣族歌舞劇《頂家女兒》、苗族舞劇《幸福花山》等。其三,從產業園區的角度,對民族集聚地進行系統性的開發。此方式是基于民族集聚地的文化資源的產業開發,是經濟行為對于民族文化的直接介入,同時也是對以民族為主體的社會網的直接介入。這種介入重構了園區中產業群體間、民族群體間的社會關系,同時民族文化被應用在園區的特色化建設中。因此,文化產業園區成為“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設中的重要模式。例如,甘肅投資建造了文縣氐羌和白馬藏族文化旅游園、肅南縣玉水苑等特色文化產業園區;陜西有以羌族文化和青木川傳奇文化為特色的青木川民族民俗風情街;貴州建設了黔西南民族文化產業園、畢節大方古彝文化產業園、中國(凱里)民族文化產業園、貴州民族民間工藝品交易基地等。
這三種發生在“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中的主要經濟行為,表現出在微觀層面的“社會關系—民族文化—經濟行為”的雙向互動。這種互動對社會網進行了重構,產業群體間、民族群體間弱社會關系在政府的引導下被構建,并以產業發展、經濟交易為主要特征。在民族村寨、民族活動、民族文化藝術生產的經濟行為中,政府鏈接著產業群體與民族群體,引導經濟行為發生,使得文化資源有效轉換為經濟收益。由此可以看出處于互動中心位置的民族文化,被進行以實現產業化為目的的“應用”。民族文化成為社會關系與經濟行為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這讓本來以民族為主體的社會網被產業群體介入,以實現文化在地性的開發。此時的社會關系相較于“藏羌彝走廊”中以血緣、地域、共同心理素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網就有了不同,經濟鏈接密度和強度在弱社會關系中不斷提升。弱社會關系成為經濟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但是經濟行為以效益作為前提,在對民族文化的“應用”中會存在選擇性,更具有產業價值部分的民族文化能實現更高的經濟效益,同樣,能夠提供更高經濟效益的弱社會關系也更容易被建立和維持。值得注意的是,弱社會關系帶來的社會或經濟的資源和機會往往會被吸附在特定地域特色文化產業發展中,逐步形成區域內的文化產業集聚。因此,經濟行為被嵌入社會關系之中。
在宏觀層面上,對于區域特色文化產業而言,它是以文化資源的開發作為出發點,需要以社會關系和民族文化為基礎。但是,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會不斷地強化“在地性”,而產生地域間、產業間的“阻隔”,這是不利于區域性發展的。相反,要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就會對區域內部多個“在地性”發展的點,按照滿足差異性需求的分工方式,在空間上實現聚合提出要求。區域協調發展表現出經濟行為對于社會關系與民族文化的影響。“社會關系—民族文化—經濟行為”的邏輯就在從區域特色發展走向區域協調發展中實現了雙向互動。
四、區域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協調發展的內在邏輯
“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中社會網的動態變化與特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實現了產業的輻射帶動效應。例如貴州西江千戶苗寨帶來的輻射效應,帶動了貴州凱里的民族特色文化產業發展;云南哈尼村落以濃郁的民族文化和原始鄉土氣息,帶動了紅河州的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弱社會關系的擴大帶動了社會或經濟的資源和機會的流入,從而增加了不同經濟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使得特色文化產業的市場主體更加多元化,進而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更具活力。
多元市場主體的進入提升了經濟鏈接的密度與強度,使得原本服務于特色文化產業的弱社會關系鏈接起了產業群體與民族群體,讓資源與機會在不同地域之間發生流動,區域性的產業發展將更加趨向于協調性。協調發展使得弱社會關系的功能得到了擴展,從而實現經濟行為的協調性。社會關系的協調性功能包括以下三點:首先是和諧功能。除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外,在協調發展中主要是強調人與人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不斷建立和維持有效社會關系的基礎,同時也是發生經濟行為的基礎。因而,和諧的環境是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共識前提。其次是協作功能。弱社會關系鏈接起不同地方的政府、產業群體、民族群體,進而消解多民族地區的經濟行為的“在地性”阻隔,以此實現文化產業的多元化、多樣化和融合化的發展。最后是調節功能。這是基于弱社會關系達成協作之后,維持協作關系所需要進行的行為,其實質是保證弱社會關系的有效性。調節包含對于矛盾、糾紛或沖突(如資源分配、市場份額等)等問題的解決,在多民族地區主要是在于資源和市場的競爭以及關聯性經濟行為的銜接上。綜上,“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中的弱社會關系發揮出和諧、協作、調節的功能,使得在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的基礎上實現協調發展成為可能。
國家“十四五”規劃以“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的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實踐為基礎提出了“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推動文化資源活態化展示、利用和融合發展,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主線的民族特色文化產業集群,促進西南民族地區的協調發展。“十四五”規劃把握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大方向,并給予了此區域中弱社會關系的政策性保障,為政府間、產業群體間、民族群體間的弱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影響預留了發展空間。社會網中社會關系與經濟行為的相互影響在“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中凸顯,弱社會關系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影響要素。
此時的“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中的社會網具有了協調性、區域性、文化性、產業性的特征。在協調發展中,政府間弱社會關系可以將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門鏈接起來,使得政府間形成協作,共同引導區域協調發展。但是,在微觀實踐中,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持續強化“在地性”,這往往會引起區域協調發展存在地域間、產業間的“阻隔”。目前,我國其他區域發展戰略,例如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往往是通過以產業鏈為主線的供給側分工來實現區域內部的協調發展。對于“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而言,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在地性,而使得供給側的產業分工協作邏輯難以實施。這樣,僅僅依托政府間弱社會關系是難以直接消除區域協調發展中地域間、產業間的“阻隔”的。只有政府間、產業群體間、民族群體間的弱社會關系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引導資源與機會進行有效流動,并形成特色文化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因此,不同類型的弱社會關系力量是可以成為推動“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協調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結論
從民族研究的“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再從區域性特色化發展的“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到區域協調發展的“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呈現了區域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實現協調發展的演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復雜的遷移與流動形成了區域性的社會網。這種社會網中包含民族內部的強社會關系與民族間、地域間的弱社會關系。強社會關系促使民族文化獨特性的產生,弱社會關系促使民族之間文化關聯性的產生。在國家“區域發展”與“特色發展”的戰略引導下,民族之間的文化關聯性為區域性發展提供了基礎,而民族的文化獨特性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為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特色文化產業遵循了文化在地性,能夠將民族文化資源高效地轉換為經濟利益。這樣的產業發展使得產業群體介入到以民族為主體的社會網中并形成了新的社會網。社會網中有著政府間、產業群體間、民族群體間的弱社會關系。弱社會關系就成為“西南民族特色文化產業帶”實現協調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強調民族間的弱社會關系,也是在推動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這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富裕。因此,重視和強化弱社會關系有利于實現“共同性”和“協調性”發展。弱社會關系帶來的鏈接性,可以使得以滿足差異化需求的特色文化產業分工得以在空間上實現具有規模效應的集聚。同時,強社會關系也會為特色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持,避免在協調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同質化陷阱。所以,多民族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同時發揮強、弱社會關系的力量,實現文化資源的資本轉換,進而使得經濟行為在具有區域性特色化的同時兼備協調性。這或許可以為多民族區域實現協調發展提供一個有益的分析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