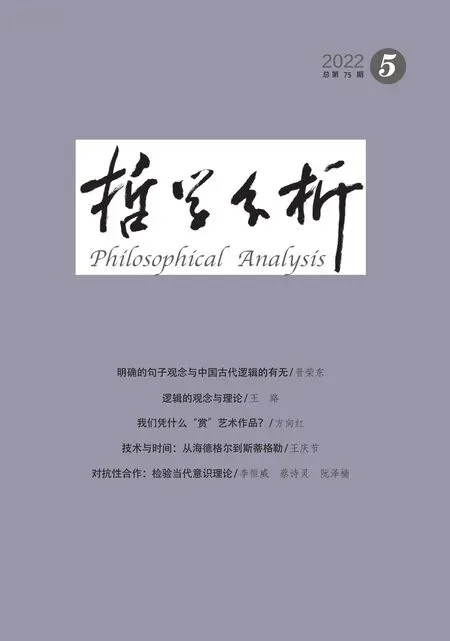董仲舒:“先經而后權,貴陽而賤陰”
——公羊家經權哲學如何完成天道化改造
唐 艷
經權學說是公羊家政治哲學一大核心內容,因為它關涉道德律令執行過程中如何處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張力問題。《春秋》之大義,需要“經”的規范統領,也離不開“權”的變通智慧。《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陳立《義疏》曰:“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公羊傳》首次以“反經”釋“權”,強調權雖悖逆于經,但并不背離倫理道德要求,是一種因事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之善舉。《論語·子罕》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認為,相比人之學習、求道和人格塑建,權是最難以被人認識、把握和實踐的。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的生動案例來解釋權,主張權是個體遇到緊急情況時自發做出的本能性、情景性、瞬時性的行為反應。荀子重視“宗原應變,曲得其宜”,萬變不離其宗,行權必須抓住經不放。從孔、孟到荀子,經權觀念傾向于定性描述,而缺乏論證氣息。借助《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文本可知,董仲舒作為公羊學大家,嚴判公羊學“反經”之說,吸收陰陽家、黃老道家的思想精華,運用陰陽、五行理論來對經權法則進行嚴密地論證和演繹,將經權問題上升至天道高度予以考量,突破了孔孟研究經權的說教方式,完成了對公羊家經權觀念的天道化改造。
一、經權的天道機理:“相與一力而并功”
董仲舒基于至上的、絕對的、崇高的天道法則為公羊學經權問題尋求理論依據,天如何運作,經、權關系就該如何呈現。其通過陰陽、四時、五行元素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宇宙圖式,徐復觀稱其為“天的哲學大系統”。《春秋繁露·陰陽位》曰:“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天地之氣不是任何理性原則和知性分析所能詮釋的概念,陰陽、四時、五行的關系圖式顯然是一種現象描述,“是把宇宙發生的、原先并不可言說的本體事件硬拖進語言世界里予以介紹”。因而,要理解董仲舒的天道運作機制,就不得不依托于這些元素之間的組合排列與意義交織。《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從董仲舒開始,談天不離陰陽,陰陽之氣的損益變化與流動運轉為天道增添了不少亮點與動感。董仲舒以陰、陽為根本,搭建了一個渾圓、系統、活潑、動態的宇宙架構,充分施展了陰、陽之氣運行的方式、途徑和路線,使其成為一種根本性、普遍性的天道法則而貫穿于萬事萬物當中。
在傳世文獻《春秋繁露》中,陰、陽各自有其特定的位次順序與運轉方式。《陰陽位》篇曰:“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陰陽之氣運行的方式、軌跡、出入各不相同。陽氣起始于東北,至南方極盛而為酷暑,至北方而藏休。陰氣始于東南,至北方極盛而為大寒,至南方而屏伏。陰陽二氣“遠近同度而不同意”(《基義》),一明一暗,一剛一柔,一主一輔,一消一長,盛衰有節,往來有序,相伴相隨。陰陽二氣的運作模式既有感性和諧的動態意象,又不失縝密有序的推演邏輯,正是在這種感性與理性、現實與精神、具體與抽象之間相互交融、平衡和映襯的過程中,使得陰、陽在天道運行圖式中頗具美感與動感,韻意無窮。陰、陽不僅在時空點上不并行、不俱出、不互斥,且各自在天道四時的變化中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陰陽終始》篇曰:“冬至之后,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二氣,你來我往,此出彼入,各得其理而不相混雜,各行其道而相資為用,互濟互補,和洽有度。陰陽二氣出入、損益無須外力推助,乃天道自然造化之勢,多而無溢,少而無絕,消長隨行,強弱相生,以促成歲月四時的循環更替。
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根本上是陰陽二氣消長運作的不同表現。《官制象天》篇曰:“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少陽、少陰、太陽、太陰不是量化的概念術語或直觀的感性判斷,而是代表著陰、陽二氣在不同時間、空間中的狀態和性質。陰陽流轉不息,天地四時永續,動而不亂,變而有節,呈現出圓潤、和諧、充實的宇宙動態圖。余治平說:“董仲舒的宇宙發生是從陰陽二氣開始的,這里的移、來、遇、合、別、適、上、下、還、出、入、均、平、損、益、始、成、藏、終,每一個概念都具有強烈的動感特征。陰陽變化,四時‘更替’,因而董仲舒的宇宙圖式轉動了起來,先秦儒家宇宙觀到漢初被注入了強勁的動能,也一改過往呆板、凝固、僵死的局面。”董仲舒成功吸收和改造了漢初的陰陽學說,形成動態化、系統化的宇宙觀念。不同于儒家以往抽象、靜態地處理經權觀念的作風,自董仲舒開始,以天道釋經權,以經權顯天意,為公羊學研究注入了鮮活的血液與動能。
董仲舒還將五行與陰陽、四時、方位有序搭配、融合起來,進一步精細、全面地論證天道的運作機制。《天辨在人》篇曰:“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少陽為東,配木、配春,主萬物生長;太陽為南,配火、配夏,主萬物養成;少陰為西,配金、配秋,主萬物生成;太陰為北,配水、配冬,主萬物休藏。陰陽、四時、五行運作井然有序,協同默契,誰不干涉誰,誰也離不開誰。“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董天工《箋》曰:“共同成就功業。”陰陽變化、五行生勝、四時更替同時發生,齊心協力,相互推動,共聚能量,彰顯天道之功。陰、陽、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其中任何一個元素都是凝聚各方能量的結合體,而主宰這種錯綜交雜、協同并作的力量源頭便是天。董仲舒把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人看作天的“十端”(《官制象天》),十大元素共同構成了天道的運作機理,這種完美自足、生生不息的天道系統,可為經權問題的論證提供可靠的理論基礎與堅實的信念力量。
二、陰陽經權的特征:親陽疏陰,任德遠刑
在董仲舒所構建的宇宙體系中,陰、陽恰恰對應權與經,天道始終以陽為主導、核心,以陰為輔助、叢屬。因而,以天之意,經、權必定有主次、輕重、先后之分,而不可能相提并論。天有喜怒哀樂之情,善善惡惡之性,“與人相副,以類合之”(《陰陽義》),其對于陰、陽的態度,偏其所好,寵其所愛。揣測天道陰陽之義,便可理解經、權的內在關系。
其一,陽生陰殺,陽尊陰卑。《陰陽義》篇曰:“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一歲四季,天道愿意以春、夏、秋三個季節主萬物之生長、成熟,而只用一個冬季主物之凋零、死亡,說明生重于喪、養重于殺、陽重于陰。“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天辨在人》),昆蟲隨陽而活動、蟄伏,草木從陽而生長、凋謝,帝王據陽而改正朔,禮法以陽定尊卑,天下萬物無不崇陽、尊陽、貴陽。《周易·系辭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韓康伯注曰:“施生而不為,故能常生。”天地生生不息的根本動力也是陽,離開陽,誰也無法生存。因而,上天有好生之德,“右陽而不右陰”“貴陽而賤陰”(《陽尊陰卑》)、“任陽不任陰”(《陰陽位》),始終以陽為重、以陰為輕。
其二,陰虛善移,陽實常居。《陰陽位》篇曰:“是故夏出長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于下,冬出守虛位于上者,陰也。”陽氣始于東北,向南而行,至北而入,夏長主養則出,冬藏主化則入;陰氣始于東南,向北而行,至南而入,冬出、夏入皆守于空虛之位。“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董天工《箋》曰:“此敘陰陽之位,陽出入俱實,陰出入俱空。”(第167頁)在天道四時運作過程中,陽氣始終被彰顯、呈現,處于實在之位,而陰氣一直被回避、隱藏,處于空虛之位,足見天道“任陽不任陰”的意志。《天辨在人》篇曰:“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陰氣運行,春季處于東方,秋季處于西方,夏季陽氣盛,陰氣處右之空位,冬季陽氣衰,陰氣處左之空位,冬、夏陰氣分別處于上下之空虛位;陽氣運行,春季居上,冬季居下,始終有其常居之處。可見,陰氣一歲四移,飄忽不定,守于空位。而陽氣常居其位,施展其功,雷打不動。陽實陰虛,陽常陰變,天道“親陽而疏陰”之意明矣。
其三,以陽為德,以陰為刑。陰、陽為天道范疇,德、刑為人倫規定,董仲舒把天道人倫化、人倫天道化,進一步解釋了陰、陽之地位與功用。《漢書·董仲舒傳》曰:“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虛空不用之處。”天之刑、德表現在陰、陽,陽主生,陰主殺,天道大顯物之生,而排斥物之死,意在貴德而賤刑。《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劉文典解曰:“德,始生也”“刑,始殺也。”冬至陰極陽生,有生發之象,故以德養之;夏至陽極陰生,有肅殺之象,故以刑正之。董仲舒還將陰陽、德刑、四時融入人之情感進行深入分析。《王道通三》篇曰:“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于秋,陽始于春。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藏秋,大人之志也。”陰陽分別對應德氣與刑氣,春季陽氣萌發,代表萬物始生、欣欣向榮之貌。《漢書·律歷志上》曰:“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白虎通·五行篇》又曰:“春之為言偆,偆動也。”“偆”同“蠢”,意指萬物蠢蠢欲動、朝氣蓬勃之象。秋季陰氣始出,萬物衰落,凄凄慘慘,有悲愁之象。《禮記·鄉飲酒義》曰:“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鄭玄注曰:“愁讀為揫,斂也。”秋季陰氣來襲,萬物由盛入衰,陽氣漸息,宛若人之愁容。相比于秋之憂愁、冬之悲涼,人們更愿意從春之喜悅、夏之愉快。故“先愛而后嚴,樂生而哀終”(《王道通三》)是人之本性所趨,亦是天道所旨。《王道通三》篇曰:“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天意多喜春、夏、秋之生物、成功、養生,而慎用冬之喪終。“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王者發天意而治天下,當重德性、行教化,謹用刑罰。
其四,少取陰以助陽,陰陽從不相離。相比于天對陽的親任與喜愛,其對陰的態度十分嚴肅、謹慎,原則是少取陰以佐陽,盡可能少用、節用,但并非不用。一方面,陰氣當慎用。《天辨在人》篇曰:“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天始終把陰放在次要、輔助的位置,稍稍取用來推動陽氣的運行,好比刑罰只能成為德教的輔助手段,只有萬不得已時才會啟用陰、動用刑。陰氣雖少用,但在天道運作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陰陽義》篇曰:“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余以歸之冬。圣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余以歸之喪。”天不會濫用陰氣,少取之以成物之秋熟,剩余皆歸之于冬,藏休不用。圣人少取陰氣以立威嚴,其余皆當用于喪亡之事,而不可過度用陰而亂殺無辜。陰氣主喪死,死之“百物枯落”、喪之“陰氣悲哀”(《陰陽義》)絕不可能成為天道主流,而只能成為陽氣之輔助、陪襯。另一方面,陰氣不得不用。天雖不親陰,但絕不棄陰;陽雖不從陰,但離不開陰。《順命》篇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后生。”董天工《箋》曰:“參,參合。”(第200頁)陰陽參天地而生,二者不可或缺,交合互濟,以化育天地萬物。《穀梁傳·莊公二年》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后生。”陰以空虛守其本,從不奪占陽之功德,出入有時,休藏有節,一心一意輔佐陽氣完成歲之大業,若沒有陰氣的肅殺之功,陽氣就無法有序運行,萬物亦不可能盛衰有度,更不存在四時的往復更替了。《周易·系辭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高亨解曰:“陰成為陰,陽成為陽,是其本性。”陽盛陰入,陽衰陰出,各有其理,各自成性,陰不凌陽之主,陽不斥陰之輔,二者誰也無法超越或替代對方。
董仲舒對天道陰陽關系的詮釋十分深刻明晰、生動具體,陰陽能用于德、刑,亦能用于經、權。陰陽交合互濟以成歲時,經權相輔相成以盡人事;獨陰、獨陽物不能生,有經無權、有權無經人不為仁;天近陽而疏陰,人執經以行權;天好生而惡死、尊陽而卑陰,人守經之大本,慎權變之用。陽實守位,陰虛四移,經主綱常,權主變化;陰陽交合有序,經常共存有道,等等。在董仲舒看來,天道陰陽的運作法則便是經權關系發生的理論根源,從中可以催生出諸多有趣的觀點和命題。
三、關系推演:“以陰為權,以陽為經”
陰為權,陽為經,陰陽有先后、主輔、貴賤、尊卑之序,經權有輕重、主次、本末之分。《陽尊陰卑》篇曰:“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是故陽行于順,陰行于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對應陽、德,權對應陰、刑,陽氣“前而任事”,陰氣“后而守空”(《基義》),二者一實一虛、一任一空、一盛一衰、一顯一隱、一先一后,順逆各異,陰看似反于陽,卻終能以少陰之功助成陽之盛德。刑看似背反于德,其目的仍是教人向善,進而與德保持一致。凌曙注曰:“猶權之反于經,然后有善也。”權沒有破壞、背叛或逃離經,就像陰從來不會脫離陽一樣,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善。蘇輿認為“雖曰權,皆在權成”疑當作“雖曰權,皆以經成”,權之目的是經,而不是為了其自身,其使命是實現、成就經。陽與陰、德與刑、經與權之間并非是矛盾關系。陽借助陰成就生養之德,經配以權成就人道訴求,陰以陽為主導,權以經為方向。《陽尊陰卑》篇曰:“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后刑也。”經比作陽而用于盛,權比作陰用于末,陽尊于陰,經重于權,故天道以陽彰顯其大經、大德,而以陰藏匿其刑、權之意。經是人倫禮法之正道,權只是在特殊情境下臨時適用的一種偏道而已,是對經的補充和推動。《玉英》篇曰:“明乎經、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董天工《箋》曰:“適權,應變權衡。”(第46頁)唯有掌握了經權之間的內在聯系與變化規律,分清主次、輕重、利弊,靈活處理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情景和事物,時刻保持豁達明朗的心境,不被外在復雜的困境所迷惑,才能在恰當的時機、情境中做到“適權”。
經、權的先后順序與陰陽之道相同,凡事以經為主、為先,以權為輔、為后,只有當執經無法解決問題時,方可考慮行權。《陽尊陰卑》篇曰:“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于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氣始終處于卑賤、空虛、次等之位,根本就沒有資格去操控四時生養之事,始終要給陽讓位,陽需要陰時,陰輔助之;陽無需陰時,陰藏匿、靜閉之。權恰恰應該具有陰的處事品格,靜守其位,藏伏其志,等待必要時刻再發揮功用。《陽尊陰卑》篇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于盛,陰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后權,貴陽而賤陰也。”陽主“暖”“予”“仁”“寬”“愛”“生”,陰主“寒”“奪”“戾”“急”“惡”“殺”,前者象征溫和、美好、積極、善良、生機之象,而后者代表寒冷、陰暗、消沉、邪惡之義,無論是天還是人,皆愿近陽而遠陰。同樣,執經讓人安心、愉悅,而行權讓人擔驚受怕、冒險恐慌,人們往往也更愿意選擇經而避免權,或者先守經,若經走不通再選擇行權。《玉英》篇曰:“《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經禮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只要按規矩辦事,一般不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或批駁,使人安放其心、無憂無慮,“因人們只有按規律或規則辦事,才能使行為付出的代價與成本最低,才能使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得到普遍認同”。而變禮無法可依,容易使人忐忑不安、顧慮重重,甚至可能蒙受違逆道義的嫌疑。董仲舒強調“先經而后權”,即在沒有特殊情況時,經是做人的首要選擇和第一原則,任何人都該安分守己,毫不猶豫要去維護綱常倫理。只有萬不得已時,才考慮行權,而且行權想要成功,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非常人所能為之。
經盛權末,經先后權,從來都不是要否定或消解權的價值與意義,甚至權在某些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是經無法達到的。《陰陽終始》篇曰:“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于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于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于東而止空處,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董天工《箋》將“秋出于東方”改為“秋出于西方”(第169頁),少陽靠近木,太陽靠近火,陽氣各得其正位,而秋天少陰卻不能隨從金,否則會傷害火之功用,故少陰根據形勢而附身居其所適之位,以便推助年歲之功。陰陽之進退、出入、順逆之道并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要根據具體情況而靈活應變的,最終仍然是為了維系陽實陰虛、陽主陰輔之天道法則的正常運行,故曰“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經、權也是在不同境遇中彰顯其價值的,當使用經行不通或者有更大損失時,就必須考慮權變。朱熹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行權是在某些情境中不得已而做出的最佳選擇。《淮南子·汜論訓》曰:“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在情形緊迫的關鍵時刻,權是應急措施,而絕不可替代經而被普遍化。經、權雖是兩種不同的處世方式,但二者的內在精神具有統一性和可通約性,終極目的都是為仁行義、走向善道。
陽不可替代陰,經無法消解權,經、權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宋明時期,理學家們逐漸模糊了經、權之間的界限,甚至以經解權、以經同權。程頤曰:“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指權衡、權量,行權是指通過判斷是非而做出符合義的行為決策,故權本身并無“反經”之意,而是可以與經等同的。朱熹曰:“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權雖與經殊名,但其本身離不開經,甚至與經同體,從來都沒有從經當中分化出去。趙清文認為,朱熹是將“經”和“權”作為兩個實踐性的范疇來理解的。在道德實踐中,“經”側重的是行為選擇所達到的應當、合宜的狀態,而“權”則側重于行為選擇的過程。而漢儒對權的解釋多源自《春秋》公羊學,主張“反經有善”“反經合道”,強調經有經道、權有權道,二者有區別,也有共性,只有深刻領會經權之間的內在關系,才能在具體道德實踐中操控自如,可謂“沒有離開權的經,也沒有離開經的權,而是權中有經,經中有權”。楊海文說:“一旦夸大其詞,漢儒的‘反經合道為權’就成了經權互悖之論,宋儒的‘常則守經,變則行權’就成了經權互隔之說。既然朱熹并未一棍子打死‘反經合道為權’之說,董仲舒也認可‘常則守經,變則行權’的合理性,雙方的沖突就有可能得到調和。”宋儒的經權觀念并非完全排斥漢儒的“反經合道”之說,“漢、宋兩家積淀并構筑了傳統經權觀,其實質則是經權互隔之說:經是經,權是權”,如何處理原則性與靈活性、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是研究經、權問題繞不開的難題,行權始終比執經要困難、復雜得多。
四、邊際控制:“必在可以然之域”
在董仲舒所設計的宇宙圖式中,陰陽各居其位、協同運行,似乎完美無缺,而天道法則一旦被置于具體的經、權道德實踐中接受效核、檢驗時,極易發生偏離或扭曲。若權被過分強調、夸大,則會造成對經的反叛、抗拒、否棄,即所謂的離經叛道,進而導致禮崩樂壞、綱常混亂。董仲舒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因而對行權之底線、原則和限度做了道德要求與倫理規 定。
行權必須要控制在一定的可行范圍之內進行,以確保經的嚴肅性與絕對性。《玉英》篇曰:“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若將“反”理解為返歸、歸來之意,則執經和行權是殊途而同歸,根本原則都是不違背儒家的道。蘇輿解曰:“在可以然之域,即為合道”(第76頁),合于道即符合人之為人的本分,在儒家看來,行權必須符合仁義之道。吳震認為,“可以然”之說法,意近“道”,符合公羊學“行權有道”之立場。《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曰:“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權雖違背了經的基本要求,但終極指向是善,道、善一體不二。《禮記·大學》曰:“止于至善。”朱熹注曰:“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善最終指向事物本身的道與理,“可以然之域”是做人的倫理限度與道德要求。行權有界限,做事才能有底線,從而不背離反經之實。“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玉英》),蘇輿《義證》曰:“目夷之立,以救宋君。衛晉之立,以得眾心,余祭夷昧之立,以讓季子。”(第77頁)僖公二十一年,面對楚軍“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的威脅,公子目夷為了打消楚軍殺宋襄公的念頭,只好假裝自己已是宋國的新君,“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目夷準確抓住了楚軍的作戰動機,在篡君位與保君命之間衡量輕重、利弊,以權變之策成功救了宋襄公的性命;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春秋》冠以國氏貶其“當國”之罪,州吁為弒君之賊而被國人所殺,之后衛宣公即位雖不正,但最起碼能暫時安定民心、保衛社稷;余祭、夷昧雖即位為君,但一心想讓位于有賢德的季扎。據《春秋》即位之禮,公子目夷、衛宣公、余祭、夷昧四者皆不正,但均有保國利民之功,故在“可以然之域”。
相反,如果“不在可以然之域”,說明已經破壞了經的要求與規范,則無論如何都不可稱之為行權。《玉英》篇曰:“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對于“不在可以然之域”的事情,即便是犧牲個人性命也不能做。公子目夷行權即位救國君,始終堅守“國為君守之”的臣子之道,從沒想過要篡奪君位、以下犯上,而是將宋襄公接回國請其繼續擔任國君,至此才算真正完成了行權,在救君命的關鍵時刻選擇行權即位,保證行權在“可以然之域”;同時,又能守住君臣大義的底線,而不碰觸“不在可以然之域”的邊際。公子目夷行權成功有兩個重要前提:其一,行權之前先進諫,以行臣子之道。據《公羊傳》記載,公子目夷勸宋襄公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軍以兵車之會往。”宋襄公為了信守僖公二十一年春季的“鹿上”盟約,不從其言,一意孤行,以乘車之會與蠻楚相會,最終被楚人逮捕,自食惡果。其二,行權是不得已而為之。面對宋襄公生死受到威脅的緊急關頭,目夷迫不得已自稱宋君,而且為了讓自己的話更可信,只好在國君面前強言“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何休以為目的是“堅宋公意,絕強楚之望”,公子目夷本無篡權之心,但為了權謀之計,必須以淡定、堅決、從容的姿態面對絕望的宋襄公與毫無道義的楚軍,頂著篡位之死罪的壓力,成功保住了國君的命,如此超凡之智慧與心境,非普通人所能及。故《王道》篇曰:“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其義焉。”公子目夷之所以有魄力行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抵抗對象為楚國,他深知對待蠻夷之邦必須劃清界限、靈活應變,堅決“不與楚國”,時刻把宋國利益放在首位,即便剛開始從道義上有不臣、不義之嫌,但結果卻能存國保君,可謂“前枉而后義”(《竹林》),功莫大焉,故《公羊傳》美其有權變之賢。對于“鄫取乎莒,以之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鄫”的事件,則“不在可以然之域”(《玉英》)。襄公六年,《春秋經》曰:“莒人滅鄫。”何休《解詁》曰:“以異姓為后,莒人當坐滅也。”周公所創的“嫡長子繼承制”,總會遇到特殊情況而難以實施,故需要采取權變對策,如各諸侯國立不宜立之君,考慮到各國情況殊異,且“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春秋》雖貶其非正,但仍待之以君、視其為國。而鄫侯從莒國尋找外姓繼承人來掌政權、主祭祀,無視血統根基,打破國別界限,顯然已經超過了行權的邊際要求,即便鄫國還在,也是自取滅亡、危在旦夕,故《春秋》夸大其為“滅”,以絕其國,《穀梁傳》直接稱其有“滅亡之道”。《春秋》之所以記錄這件事,意在警告后世在王權交接時必須重視血緣關系,不可違背禮制。
董仲舒也把“在可以然之域”與“不在可以然之域”的問題放在“大德”“小德”的語境中來審視和詮釋。“可以然之域”與“不在可以然之域”可通過大德、小德來解釋。《玉英》篇曰:“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指核心、重要、關鍵的原則和規定,有絕對、嚴格、清晰的倫理邊界與道德規范,人人皆須奉行。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大德即不越法,堅守人之為人之正道,謂之“正經”。小德,不像大德那么嚴肅,在特殊情況下有迂回的空間和余地,對事件的影響相對溫和,可以從其他方面得到補救,故雖反于經,但無礙于經之大本。邢昺《疏》曰:“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小德雖暫時性違背禮法,但最終仍然能夠回歸到經常規定上來,因而可以選擇行權。《論語·子張》中,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熹注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大德、小德對個體的道德要求不同,如果一個人能在大節上很好地把控自己、明辨是非、堅守底線,那么對于小節之事自然能夠靈活應對,行權就容易成功。《荀子·王制篇》曰:“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余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余雖曲當,猶將無益也。”王先謙解曰:“曲當,謂委曲皆當。”愛民、隆禮、尚賢乃人君之大節,任何時候都不能被破壞,當遇到緊急情況時,應該毫不猶豫以大節為重,這才是為君之正道。若違逆大節而求小節,即便付出再多也無事于補,舍本逐末,徒勞無功。因而,行權絕不能為所欲為,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分清主次、輕重,對于那些挑戰大德、大節之事,根本就不用考慮能不能行權的問題,即便自我犧牲也不能冒險去做。在能夠把握大德的基礎上,對于“可以然之域”的小德、小節之事,則可在必要時刻施展權變智慧。
實際上,權從未脫離經,權為經而權,無經則不權。《玉英》篇曰:“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譎,《廣雅·釋詁》曰:“欺也”,《說文·言部》解為“權詐也”,段玉裁注曰:“欺天下曰譎”,即欺騙、詐騙、詭詐之意,權雖帶有騙詐意味,但最終是尊崇、回歸于經的,而不是無底線、無原則地踐踏禮法、喪德害人。“鉅經”即大經,超越一般之常經,蘇輿解釋曰:“雖權譎,仍以正歸之,取其不失大經耳。”(第77頁)權不符合經的規范,但并不背離正道,“權是經歷了一番思想搏斗、矛盾抵觸、道德權衡之后的更高級的經,其是處于常經之上而超越常經的一種具有靈活性、挑戰性、創新性的經”,權超越于經又高于經,為了避免更大的傷害和損失,其在經所能承受、接納、容忍的域限之中通過另辟蹊徑的迂回策略又回歸到經,其終極歸宿是“大經”“鉅經”,比經本身的地位還要崇高、可貴。陳柱曰:“權與詐,至相異而至相似者也也‘差以毫厘,謬以千里’。善用之則為君子之權,不善用之則為小人之詐。”權與詐雖都有“反經”的性質,但前者向善守義,后者離善棄義,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君子之權”與“小人之詐”的差別極其細微,只有真正做到“變而反道”(《觀德》)、“前枉而后義”才算得上是“中權”(《竹林》),其行為結果合于道、歸于義,否則純粹便是詐。
權一旦掙脫了經的限制,無拘無束,背信棄義,實質也已經不再是權了。桓公十一年,《春秋經》曰:“宋人執鄭祭仲。”宋莊公威脅祭仲“出忽立突”,祭仲為了保君救國,暫且委從其言,等到時機成熟時再逐出公子突、復立公子忽,但自身必將背負逐君之罪,祭仲舍小我救大我,行權救鄭國。何休《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可見,祭仲的權變之計并非一時沖動、感情用事,而是深謀遠慮、從長計議,充分考慮到宋、鄭兩國所處的政治局勢而做出的睿智決策。祭仲冒著患逐君之罪的危險,最終有“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的功德,故《公羊傳》美其有權賢。而成公二年,面對齊頃公被晉師圍困的緊急關頭,大夫逄丑父與齊頃公調換服飾,并以取水為借口助力齊頃公成功逃走,逄丑父雖然也保住了齊頃公的性命,但“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竹林》),其忽略了君子的榮辱大義,使其君王茍活而蒙受恥辱,故不能稱之為行權。《淮南子·汜論訓》曰:“權者,圣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后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后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丑也。”劉文典解曰:“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當形勢,能令丑反善,合于宜適,故圣人獨見之也。”圣人通曉行權之本,能夠揆情度理,游刃有余,準確拿捏經、權之間的關系和尺度,因而可以體達權變智慧之最高境界。
五、結語
董仲舒承續孔、孟的經權觀念,以天立論,以陰陽配經權,完成了經權的天道化改造,第一次對公羊家經權觀念進行了清楚明晰的邏輯論證,使得經、權關系第一次獲得了可靠的理論來源與終極根據。董仲舒對陰陽運作法則與經權的對應關系、如何區分“在可以然之域”與“不在可以然之域”、守經與行權的邊際界限等問題展開了細致地分析和闡述,都具有獨特的創新和發明。董仲舒以天道運行的客觀法則為基點,揭示了經、權是天、人世界同有的規律,從而為權的正當性、合法性作出了極為有效的演繹和建構。董仲舒的天道系統并非是凌駕于人之上的絕對存在者,而是融入人世生活和人道精神的客觀對象,可以與人相互動,因而能夠折射出豐富多彩、情理交融、生動鮮活的人性本能與倫常要求,進一步彰顯出漢代哲學“天人相與之際”觀念的魅力與境界,彌補了先秦儒家經權哲學本體論的缺憾,開辟了公羊學經權觀念研究的宇宙論面向和視野。但董仲舒傳世文獻對道德主體當下的行為選擇的困境、如何克服理性法則與感性本能之間的對沖并未給予明確的理論交代,所以只能靠個體的生活智慧與德性工夫去靈活把握。“《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精華》),經與權、常與變在道德執行過程中不免產生各種復雜的道德問題和倫理矛盾,更多地還是要依賴于行權者自身的德性能力、意志決斷水平,還得靠敏銳的眼光、清醒的理性精神、仁義的自覺、禮法的堅守去做出正確抉擇。其實,這又恰好說明了行權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權者,圣人之大用”,只有圣人才有能力和資格行權,而對于普通人而言,行權就是一次道德挑戰,難度之大,實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