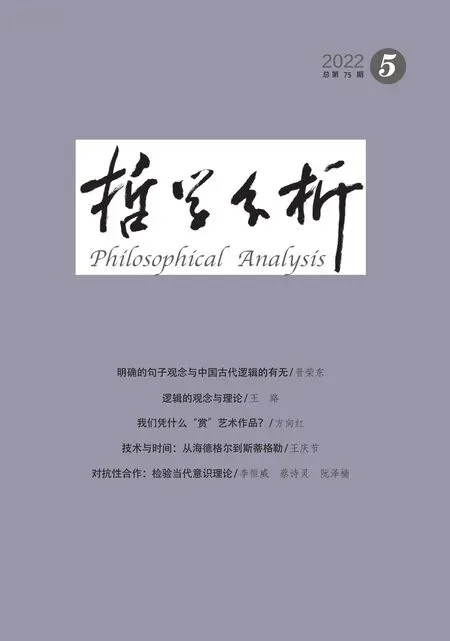樸素實在論與因果—幻覺論證
陳仕偉
樸素實在論(Na?ve Realism)是近年來重獲廣泛關注的一種知覺理論,它認為知覺經驗必然是由有意識的感官覺知構成,這種覺知直接勾連感知者與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樸素實在論者通常將這種構成性關系屬性稱為知覺經驗的樸素實在論屬性(以下簡稱NR屬性),并主張這一屬性是知覺經驗的基礎形而上學屬性,它最好地解釋了知覺經驗的現象特征。這一理論立論成功能實質推進知覺研究中的諸多問題,但其自身也遭受諸多質疑。本文即致力于為該理論提供某種辯護與發展,通過合理引入行動哲學中的資源提出一種新樸素實在論方案。
具體而言,第一節概述樸素實在論與知覺研究中兩種常見論題之間存在的張力。第二節進一步將這種張力具化為兩個反駁樸素實在論的論證,即因果—幻覺論證與解釋冗余論證,并分別加以討論。第三節給出對兩個論證的診斷及相應的回應策略,主張通過對經驗的自然主義作合理的修正,以及運用意向性行動概念重解知覺概念,我們可以在保留樸素實在論核心主張的同時對幻覺作出積極解釋。第四節討論如何實踐上述策略,即如何構建一種基于意向性行動的新樸素實在論。第五節總結與反思,說明本文核心主張與當前認知科學領域的“行動轉向”以及知識論領域的“德性轉向”之間的內在聯系。
一、樸素實在論與兩種常見論題
樸素實在論主張知覺經驗的本質是關系,這里的關系特指NR屬性,這意味著作為關系項之一的外部世界中的被感知對象必須存在,否則這一關系就不成立,相應的知覺經驗也無法達成。樸素實在論支持直接實在論的主張,即認為我們的知覺經驗直接與外部世界中的對象產生關聯,并不借助某種依賴于心靈的中介物。
然而,樸素實在論的上述主張卻可能與知覺研究中的兩種常見論題存在張力。其一是經驗的自然主義(Experiential Naturalism),主張我們的感官經驗與其他處于自然界中的事件或狀態一樣,受制于因果關系,例如神經生理學因果關系。經驗的自然主義被普遍接受源于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進步帶來的顯著影響,對知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這種自然科學理解之下的因果關系圖景。
其二是共同類假設(Common Kind Assumption),主張真實知覺和幻覺本質上歸屬于同一基本類,即無論何種在真實知覺中出現的心理事件,都能夠在幻覺中出現。共同類假設被普遍接受原因有二:一是就現象感受而言,感知者在真實知覺與幻覺中的現象感受主觀不可分辨(subjective indistinguishable);二是就因果鏈條而言,真實知覺與幻覺客觀上可以是因果匹配的(causally match),即兩者的近端原因相同。
在馬丁(M. G. F. Martin)看來,樸素實在論與這兩個常見論題存在沖突。根據樸素實在論,真實知覺中外部世界中的被感知對象必須存在,而幻覺中沒有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因此真實知覺和幻覺不屬于同一基本類。而根據經驗的自然主義與共同類假設,因為真實知覺和幻覺擁有相同的近端神經原因,兩者近端因果匹配,因此兩者屬于同一基本類。同時,馬丁認為經驗的自然主義是不可反駁的,那么如果要保留樸素實在論,我們就必須摒棄共同類假設。他提出一種關于幻覺的消極認知解釋(Epistemic Account of Hallucination,以下簡稱EAH),即我們對幻覺唯一能給出的解釋只能是它在主觀上與真實知覺不可分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屬性能夠解釋幻覺的現象特征。我將在下文表明,馬丁的方案不能真正解決困難,只有在摒棄共同類假設的同時修正經驗的自然主義,我們才能有效捍衛樸素實在論。
上述樸素實在論與兩種常見論題之間的張力可以具化為反對樸素實在論的因果—幻覺論證和解釋冗余論證,兩者相互勾連,共同構成對樸素實在論的嚴峻挑戰。
二、因果—幻覺論證與解釋冗余論證
羅賓遜(Howard Robinson)提出因果—幻覺論證以反對樸素實在論,他的論證如下:
C1.理論上我們可以通過刺激某個大腦神經過程而讓感知者產生與真實知覺主觀不可分辨的幻覺;
C2.當幻覺和真實知覺擁有相同的近端原因(proximate cause),亦即相同的神經原因(neural cause)時,作為直接結果(immediate effect)的幻覺和真實知覺必然相同,因此必然地我們應當給予它們相同的解釋;
C3.幻覺包含某種主觀圖像(subjective image)或感覺予料(sense-datum);因此,
C4.真實知覺包含主觀圖像或感覺予料。
這個結論無疑與樸素實在論不相容,樸素實在論主張真實知覺是對外部世界對象和屬性的直接感知,因而不會包含感覺予料等心靈中介。從C3到C4,是試圖從幻覺擁有何種屬性或構件進而推出真實知覺具有何種屬性或構件,這種推理的根據則在C1和C2。
C1告訴我們這里討論的幻覺不是現實意義上的幻覺現象,而是特指哲學討論中構造的幻覺,其兩大特征是:主觀上與真實知覺的現象感受無法分辨,以及客觀上其近端原因與真實知覺相匹配(相同的神經刺激)。值得注意的是,羅賓遜特別強調C1的非任意性(non-arbitrariness),或非特設性(non-ad-hocness),即當我們承認可以通過刺激大腦神經來創造符合上述特征的幻覺時,我們不是創造了一種僅在幻覺情形中出現的特殊神經狀態;相反,它與真實知覺中的神經狀態完全相同,具有相同的功能特征和直接結果。在筆者看來,羅賓遜對非任意性的強調其實是強調幻覺與真實知覺近端因果匹配的嚴格性。這杜絕了一種顯然誤解了因果—幻覺論證的輕巧回應,該回應認為羅賓遜沒有將完整的因果鏈條納入考量,如果將遠端原因(distal cause)納入考量,則我們很容易看出真實知覺與幻覺的不同。這種回應的不足在于未能意識到,C1所揭示的嚴格的近端因果匹配意味著近端神經原因淹沒了因果鏈條中遠端原因的因果效力。
C2包括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因果原則,即相同的近端原因有相同的直接結果。這里的要點在于在C2中將近端原因等同于神經原因,這體現了該論證對經驗的自然主義的遵循,即知覺是受制于自然科學研究所揭示的因果規律的現象。這在某種意義上表明,該論證也得到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背書”,厘清這一點可以使我們對C2乃至整個因果—幻覺論證的核心有更深的把握。C1和C2蘊涵了共同類假設,同時建基于經驗的自然主義,從而使得整個論證具有了反樸素實在論的效力。
傳統樸素實在論者的回應主要集中于否認C2。這種否認不是否認一般意義的因果原則,而是說當我們在給出對真實知覺或幻覺的解釋時,不能僅僅考慮因果要素,也要考慮非因果的構成性要素。在樸素實在論者看來,真實知覺中感知者對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的直接感知構成了其知覺經驗的一部分,這種構成性關系屬性提供了對知覺經驗的非因果解釋;而幻覺中,因為不存在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所以沒有相應的構成性要素,因此我們對真實知覺和幻覺的解釋顯然是不一樣的。這里涉及一般的因果與解釋的關系問題,通常有兩大類觀點:一是認為解釋依賴于因果,給出對某事件或狀態的解釋即意味著對相關被解釋項的因果關系加以說明,這種觀點往往認為解釋即等同于因果解釋;二是認為解釋相對獨立于因果,給出對某事件或狀態的解釋是純粹的知識論層面的活動,取決于我們對相關事實的認知,因此解釋并不完全等同于因果解釋。拋開兩種觀點的對錯判斷,樸素實在論者的回應顯然是采用了第二類對因果和解釋關系的理解,NR屬性被作為非因果因素納入到對知覺經驗的解釋中,并起到核心解釋作用。
這種回應可以回避因果—幻覺論證帶來的問題,但問題在于非因果因素是否真的能夠在對知覺經驗的解釋中起到核心作用。馬丁的解釋冗余論證無疑對此提出了質疑。
馬丁本人的論證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羅賓遜的因果—幻覺論證的弱化重構,馬丁接受了樸素實在論的上述回應,承認真實知覺擁有非因果的構成性要素,而幻覺沒有;第二部分是進一步討論這種弱化了的論證是否能夠與樸素實在論相容,其結論是:樸素實在論者如果堅持真實知覺與幻覺不同,可能會使NR屬性變得解釋冗余。筆者這里將兩個步驟整合重構為解釋冗余論證以方便討論,并略去了第一部分與羅賓遜原論證重合的部分。
E1.真實知覺不同于幻覺,因為真實知覺有非因果的構成性要素(NR屬性),而幻覺沒有(樸素實在論的回應);
E2.因為幻覺沒有非因果的構成性要素(NR屬性),因此,幻覺中的近端原因都可以存在于對應的真實知覺中;換言之,原則上真實知覺可以擁有所有幻覺的屬性;
E3.如果近端原因能夠解釋知覺經驗的所有現象特征,那么對每一個真實知覺而言,其NR屬性的解釋力都將被相應的幻覺所具有的屬性所屏蔽(屏蔽原則);
因 此,E4.樸素實在論雖然仍然可以主張真實知覺不同于幻覺,但是這種不同并不對如何解釋兩者的現象特征產生影響。換言之,NR屬性不具有解釋力,是解釋層面冗余的。
E1是樸素實在論者對因果—幻覺論證的回應,馬丁沒有否認這一點,但這也同時導向了E2,即除了這些非因果的構成性因素之外,幻覺擁有的所有具有因果解釋力的屬性都能在相應的真實知覺中得到復制。值得注意的是,E1和E2共同反映了馬丁所理解的幻覺與真實知覺的非對稱性,即真實知覺可以擁有所有幻覺的屬性,但幻覺并不擁有所有真實知覺的屬性。這種非對稱性一方面與樸素實在論對因果—幻覺論證的回應相容,另一方面卻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即如果幻覺所擁有的屬性解釋了所有知覺經驗的現象特征,那么真實知覺所特有的NR屬性就會在解釋層面顯得冗余(即E3)。這無疑會對樸素實在論的立論動機產生威脅——如果它所主張的知覺經驗的本質屬性其實并不具有解釋力或是冗余的,那么我們自然沒有好的理由接受這一理論(即E4)。在筆者看來,解釋冗余論證是對因果—幻覺論證的進一步深化。因果—幻覺論證告訴我們在因果解釋的框架內應當給予真實知覺與幻覺相同的解釋,這迫使樸素實在論者求助于非因果性因素,而解釋冗余論證進一步論證,我們即使承認真實知覺中存在非因果性因素,對其解釋效力也要存疑 。
馬丁認為,樸素實在論者為了回應解釋冗余論證,只能接受一種關于幻覺的消極認知解釋EAH,即我們對幻覺唯一能給出的解釋只是它在主觀上與真實知覺不可分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屬性能夠解釋幻覺的現象特征。這種解釋是純認知的,并不包括也不能包括任何形上學層面對幻覺的屬性刻畫(因而是消極的解釋),因為一旦存在這種屬性刻畫,那么根據E3,它就會屏蔽掉相應的真實知覺NR屬性的解釋力。
但在筆者看來,EAH難以令人信服,因為根據上述兩個論證中一脈相承的幻覺概念,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知識論意義上的預設,而是切實通過刺激相應的腦部神經而產生的,是和真實知覺近端因果匹配的神經狀態(回顧羅賓遜對于C1的非任意性的強調)。因此論證中的幻覺顯然具有某些積極的屬性,比如是通過刺激大腦神經所引起的。馬丁的EAH至多只能回應基于幻覺與真實知覺現象感受主觀不可分辨的幻覺論證,它保留了真實知覺和幻覺主觀不可分辨的直覺,同時又避免了NR屬性的解釋力被幻覺的積極屬性所屏蔽。但整個因果—幻覺論證乃至解釋冗余論證都是建立在幻覺與真實知覺的近端因果匹配上,而回顧對C1和C2的探討,這樣的建構其基礎是經驗的自然主義。因此,給出一個只具有認知屬性的幻覺概念并不是回應因果—幻覺論證,而是回避該論證,同時還可能陷入反對經驗的自然主義的指責。
至此,因果—幻覺論證連同解釋冗余論證將樸素實在論者帶入困境,而馬丁的EAH解釋并不能夠解決問題。回到第一節所述樸素實在論與兩個常見論題之間的張力,兩個論證說明了張力的核心在于樸素實在論者如何在不違背經驗的自然主義的同時摒棄共同類假設,亦即樸素實在論者如何在一個普遍的因果地運行的世界里為非因果性因素(NR屬性)安排一個核心的解釋角色。我將在第三節給出對兩個論證帶來的張力的診斷及相應的回應策略,繼而在第四節具體給出緩解這種張力的 方案。
三、診斷及回應策略
在筆者看來,之所以上述兩個論證能夠成功使得樸素實在論者陷入困境,是因為論證背后隱藏的兩個條件以及傳統樸素實在論者對因果—幻覺論證的回應失當,總結如下:
(1) 因果—幻覺論證和解釋冗余論證都將解釋力的來源限定在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之內。
(2) 因果—幻覺論證和解釋冗余論證對因果關系的理解都建立在經驗的自然主義之上,亦即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都存在于亞人格(sub-personal)層面。
(3) 樸素實在論者在回應因果—幻覺論證時放棄了NR屬性可能存在的因果效力,而將其作為一種非因果因素納入解釋體系中。
這三條綜合起來導致了樸素實在論者的失敗。(1)可以通過C2和E3得到確證:因果—幻覺論證把解釋力的來源完全限定在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之內;解釋冗余論證雖然可以接受知覺經驗擁有非因果因素,但認為因果因素可以進行完備的解釋,非因果因素是解釋冗余的,所以實質上和因果—幻覺論證一樣將解釋力的來源限定在了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之內。(2)可以由兩個論證中對幻覺的設定得到確證:兩個論證的基礎設定都是真實知覺與幻覺的近端因果匹配,這里的近端因果匹配被理解為相同的腦神經刺激,而真實知覺和幻覺則是相同的腦神經狀態。借用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區分,這里的腦神經刺激、腦神經狀態都是亞人格層面的存在;換言之,這里的因果性因素都是在純粹的經驗科學研究的語境下討論的,并不涉及人格(personal)層面的心理因素等。(1)和(2)共同將樸素實在論者引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要么完全否認真實知覺和幻覺擁有相同的近端原因,但這會被指責與經驗科學研究不相符;要么承認近端原因的匹配,擴大對解釋的理解,引入新的非因果性解釋因素[即上述(3)],但是解釋冗余論證隨后指出這面臨解釋冗余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可能會爭辯說樸素實在論者與其反對者享有不同的關于因果和解釋關系的理解。在樸素實在論者的理解中,NR屬性提供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近端原因的解釋,兩者并不存在競爭關系。這種爭辯初看有理,細究則發現很難實現。樸素實在論者如果堅持NR屬性作為非因果構成性因素起到了核心解釋作用,那么首先需要說明它能夠提供解釋的根據是什么,否則會使這種解釋陷入一種無根據的神秘狀態;其次需要說明NR屬性提供的解釋何以優于同時存在的因果因素提供的解釋,這無疑增加了樸素實在論的論證負擔,且仍然面臨回避經驗科學研究的指責。因此,(3)并不是好的回應。
在作出上述診斷后,在筆者看來,樸素實在論者并未意識到存在第三條道路的可能,即一方面修正經驗的自然主義,擴大具有因果效力因素的范疇;另一方面采用某種方式將NR屬性合理地納入因果因素的范疇,從而直接回應兩種論證的詰難。具體而言在于針對性地做到以下幾點:
(1) 承認具有解釋力的因素同時應當具有因果效力。
(2) 合理地修正經驗的自然主義,將人格層面因素納入因果解釋框架。
(3) 合理引入行動哲學資源,通過意向性行動重構對知覺的理解,基于新理解,NR屬性既是知覺經驗的構成性關系屬性,又是因果性關系屬性。
(1)避免了樸素實在論的解釋陷入一種無根據的神秘狀態,同時也規避了一種對于樸素實在論與經驗科學研究不相容的指責。(2)擴大了選取因果因素的范疇,修正了傳統的純粹物理主義式的自然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修正并不違背原先的經驗的自然主義主張,因為亞人格層面因素的因果效力被予以保留,它只要求我們在考慮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時將視角擴展到人格層面,這符合我們對知覺經驗的一般理解。(1)和(2)共同達到的效果是:一方面,承認我們需要在因果解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拓寬了我們對因果解釋的理解,這為樸素實在論回應兩個論證的詰難提供了空間。在此基礎上,樸素實在論者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將NR屬性納入因果解釋的框架內,即需要說明NR屬性不再僅是知覺經驗的構成性關系屬性,同時也是其因果性關系屬性,在達成真實知覺的過程中具有因果效力[上述(3)]。這種合理的方式在我看來即是通過意向性行動重構對知覺的理解,為此,我主張一種基于意向性行動的新樸素實在論方案。
四、基于意向性行動的新樸素實在論方案
構建基于意向性行動的新樸素實在論,核心在于合理引入行動哲學資源,運用意向性行動概念重構對于知覺的理解,即主張知覺本質上是一種具身的意向性行動,真實知覺是我們成功的意向性行動(intentional action),而幻覺則只是發生于我們之上的事件(a mere happening)。
這里的意向性行動是指一種體現了行動者意圖(intention)的具身(embodied)行動。它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具身性,即行動是發生于世界之中的行動者與外部世界的交互,既包括行動者所做的事,也包括世界在相應情形下的配合;二是意向性,即行動體現了行動者的意圖,且由這種意圖所推動,換言之,行動是在行動者的引導(guidance)之下進行的,是其能動性(agency)的體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意圖并不是一種完全私人的內在的心靈圖像;相反,正如安斯康姆(G. E. Anscombe)所強調的,意圖展現于行動者的行動之中,某種意義上是外顯的。相應地,基于這種意向性行動概念重構的知覺概念,即是一種體現了感知者認知意圖的具身的認知活動,知覺不再是單純存在于大腦之中的隱秘的心靈活動或腦神經狀態,而是切實地發生于世界之中的感知者與世界的交互活動,且感知者的認知意圖展現于其行動當中并因果地推動了行動的實現。
對于在行動哲學中區分行動與單純發生的事件,普遍的觀點是:行動體現了能動性,而單純發生的事件沒有。更通俗地說,行動是受到行動者控制的行為,而單純發生的事件則是不受控制的。相應地,真實知覺之所以能夠區別于幻覺,是因為前者是一個成功的意向性行動,感知者具有探尋外部世界的主觀意圖,整個認知行動是在感知者的引導之下進行的;而幻覺只是一件發生于感知者之上的事件,感知者并不具有任何主觀意圖,沒有人會主動地希望幻覺發生,感知者亦無法控制幻覺的發生。值得注意的是,幻覺是可以有意識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展現了感知者的認知意圖,更不意味著幻覺是在感知者的控制之下的活動。因此,感知者可以在幻覺和真實知覺中擁有相同的主觀現象感受,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認知意圖和認知能動性(epistemic agency)的角度對兩者作出區分。
上述概念重構豐富了知覺概念,使得我們有更多的資源來回應知覺相關的形上學與知識論問題。但這種重構不是任意進行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必要性。我將分別討論其一般意義上的必要性與特殊意義上(針對樸素實在論)的必要性,并進而說明如何重新理解知覺經驗的NR屬性。
這種重構的一般意義上的必要性體現在對知覺活動能動性要素的重新發現。長久以來,我們認為真實知覺與幻覺的唯一區別在于對應的外部世界情形不同。然而這種想法忽略了真實知覺與幻覺可能存在的另一個差異,即從行動者視角而言,真實知覺作為我們成功的意向性行動,是我們主動去做的事,體現了我們的認知意圖;而幻覺只是被動地發生于我們之上的事件,并不展現任何行動者的認知意圖。這種主體性視角的差異被長久的忽略,原因在于自笛卡爾以降,我們一直都以一種被動的模型來理解知覺,從而掩蓋了只有將知覺視為一種意向性行動才能看到的差異。依據這種被動的模型,知覺只是對外部世界刺激的接受和信息處理,知覺活動中只有一個被動的受動者(patient),而沒有一個真正的能動者(agent),因此真實知覺與幻覺的區別自然只剩下外部世界情形的差異。這種能動者缺失的知覺是一個相當貧瘠的概念,它很容易被視為一系列因果鏈條終端的結果,從而自然地導向了因果—幻覺論證想要的結論,即作為相同近端原因的結果,真實知覺和幻覺歸屬于同一類(共同類假設)。甚至可以說,這是所有幻覺論證能夠帶來問題的根源,外部世界的刺激在哲學論證中可以通過各種思想實驗(或者如本文的論證披上腦神經科學的外衣)被輕巧地設定為一致。此時若缺失了主體維度的辨識,真實知覺和幻覺作為一個最終的結果自然是難以分辨的,進而帶來一系列關于知覺的形上學和知識論問題。因此,重新發現知覺活動的主體性要素,從而認識到真實知覺與幻覺的認知意圖和認知能動性差異,正是運用意向性行動概念重構知覺概念的必要性所在。
這種重構對樸素實在論而言尤為必要,因為它拓寬了樸素實在論對NR屬性進行詮釋的空間,使我們獲得一種更為積極的新NR屬性。傳統樸素實在論將NR屬性解釋為構成性關系屬性,我們對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的直接感官覺知構成了我們知覺經驗的一部分,但是受限于被動模型下的知覺概念,知覺被簡化為一種扁平的知覺狀態,這種直接感官覺知僅被當作來自外部世界的某種給予(the given),而無法進一步作為知覺活動的能動性因素因果地參與知覺經驗的建構。因而傳統樸素實在論者只意識到NR屬性的構成性角色,而忽視了其因果性角色。但概念重構后,我們有了更多的空間來詮釋NR屬性的因果性角色。在新的理解中,知覺本質上是一個具身的意向性行動,感知者對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的直接感知不是一種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探索與交互(新NR屬性)。新樸素實在論方案中的知覺概念,其具身性特征保證了世界之中的對象和屬性必然參與了知覺活動,作為關系項之一構成了我們知覺經驗的一部分(新NR屬性的構成性角色);其意向性特征保證了在真實知覺中,感知者在人格層面對外部世界中的對象和屬性的有意識的感官覺知,既是其相信外部世界存在某對象的理由(reason),又是其知覺行動的原因(cause),即新NR屬性既在解釋相關知覺知識時扮演了辯護角色,又在解釋相關知覺活動時扮演了因果角色。
更具體而言,新NR屬性能夠扮演因果角色的原因在于,當知覺概念基于意向性行動概念得到重構后,其相應的因果關系刻畫也隨之改變。作為一個完整的認知行動,其發生的原因既包括亞人格層面的原因,也包括人格層面的原因。在亞人格層面,腦神經刺激激發相應的肌肉群的運動,從而完成相應的認知行動。在人格層面,感知者(亦是行動者)的認知意圖構成了其相應認知行動的原因,這里的認知意圖是由實時的感知者與外部世界對象和屬性的交互所確定的。感知者完成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需要相應的認知行動,而這種行動并非漫無目的,而是受到感知者的引導,這種引導的依據就是感知者與外部世界的實時動態交互。在這種因果圖景中,一方面,感知者接收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感官刺激,另一方面,這種感官刺激又實時地、因果地形塑著感知者的認知意圖,并進而影響其認知行動。整個因果圖景不再是從外部世界到感知者內部狀態的單線因果鏈條,而是感知者與外部世界之間動態的交互的因果網絡。在人格層面,感知者作為認知主體因果地主導著整個認知行動。這意味著,新NR屬性并不僅僅是說我們的知覺經驗由對外部世界對象和屬性的直接感知構成,它還引導和推動了知覺活動。換言之,如若沒有新NR屬性,知覺經驗不僅從構成性視角無法達成(缺少作為關系項之一的外部世界的對象),而且從因果性視角也無法達成(缺少相應知覺活動的人格層面的原因)。
如若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新NR屬性在我們對知覺經驗的解釋中不僅扮演著構成性解釋角色,還扮演著因果性解釋角色,第三節中應對策略的第(3)條得以實現。而基于新NR屬性,新樸素實在論方案可以直接反對因果—幻覺論證中的C2和解釋冗余論證中的E1、E3。
因果幻覺論證的C2主張相同的原因有相同的結果,進而需要給出相同的解釋。問題在于新樸素實在論方案告訴我們真實知覺和幻覺并非完全的因果匹配,或許兩者可以在亞人格層面因果匹配,但是在人格層面兩者是不匹配的,真實知覺擁有新NR屬性作為其特有的人格層面的因果因素。而在第三節,我已經表明我們應當合理地修正經驗的自然主義,將人格層面的因果因素納入對知覺經驗的因果解釋框架中,因此C2不成立。
解釋冗余論證的E1是傳統樸素實在論者對因果幻覺論證的回應,它主動放棄了NR屬性的因果解釋力,而新樸素實在論的回應顯然不同。新NR屬性不再是作為非因果因素被引入對知覺經驗的解釋中,而是作為具有因果效力的因素被引入,因此E1不成立。解釋冗余論證的E3認為當幻覺同樣擁有的亞人格層面的因果屬性能夠解釋所有的現象學與知識論特征時,真實知覺特有的NR屬性所具有的解釋力就會被屏蔽。但在新樸素實在論的框架中,對一個真實知覺的因果解釋,不僅要考慮亞人格層面的神經刺激等因素,還要考慮人格層面的認知意圖等因素,這兩者是有機地統合在一起的,亞人格層面的因果因素并不能夠屏蔽人格層面因果因素的解釋力,因此E3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新樸素實在論方案因為保留了亞人格層面的因果因素,從而為給幻覺提供積極的解釋留出了足夠的空間,這一點優于馬丁的方案。
綜上,基于新的知覺概念和新NR屬性,新樸素實在論可以有效回應兩種反駁論證。
五、結論與反思
本文通過梳理分析樸素實在論面臨的兩種反駁論證,即因果—幻覺論證和解釋冗余論證,指出樸素實在論無法基于傳統的知覺概念對兩個反駁論證作出有效的回應。筆者繼而嘗試在適當修正經驗的自然主義后,基于意向性行動概念重構知覺概念,構建新樸素實在論。依據新方案,知覺本質上是一種具身的意向性行動,知覺經驗的NR屬性被解釋為感知者對外部世界對象和屬性的主動探索與交互,它既是知覺經驗的構成性關系屬性,又是其因果性關系屬性。基于這種新方案,我們可以有效地回應兩種反駁論證的詰難。
值得說明的是,筆者的上述方案并非空穴來風,認知科學領域與傳統知識論領域的兩種轉向早已預示了從行動視角重新審視知覺的必要。
在認知科學領域,運用行動作為范式來理解知覺早已不是新鮮話題,甚至引起了所謂的“行動轉向”,諾伊(Alva No?)的知覺生成主義(Enactivism)即是其中代表。諾伊曾寫道:“知覺是行動的一種方式。知覺不是發生于我們之上的事件,而是我們做的事……我們知覺到什么取決于我們做了什么(或者我們知道如何去做)……我們生成了(enact)我們的知覺經驗;我們把它做出來。”這一系列表述都表明知覺生成主義是在試圖用行動作為范式來理解知覺。值得注意的是,認知科學領域對于行動—知覺關系的研究,很多都基于大量的腦神經科學、心理學研究案例,因此可以說運用行動作為范式來理解知覺具有一定的經驗科學研究的基礎。本文的概念重構與認知科學領域的“行動轉向”有觀點一致之處,即都認為知覺活動如同行動一樣具有具身性,是感知者(行動者)與周遭環境的實時交互;但也有不同之處,即本文還強調知覺活動具有意向性,即在人格層面感知者(行動者)作為認知能動者因果地主導了認知行動,知覺生成主義的行動概念并不強調,甚至忽略了這一點。
在傳統知識論領域,德性知識論的興起引導了所謂的“德性轉向”,其核心論題之一便在于強調對知識本質的理解轉變,索薩(Ernest Sosa)的德性可靠論(Virtue Reliablism)即是其中的代表。傳統知識論通常將知識定義為得到辯護的真信念,而德性可靠論則強調對知識的理解需要考察相應的認知表現(epistemic performance)。索薩的3A模型更是詳細地刻畫了這種認知表現的規范性,拋開理論細節,其核心是從對單純的信念進行考察轉向對更復雜的認知活動的考察。本文的概念重構與索薩的觀點基本相容,但索薩側重的是對知識的理解,而本文強調的則是對知覺本身的形上學概念重構。
無論是認知科學領域的行動轉向,還是知識論領域的德性轉向,都是對傳統的知覺和知覺知識概念的批判性反思,都體現了越來越多的對于認知活動中主體性因素的重新發現,這支持了我在本文進行的概念重構。
反思整場爭論,如果我們囿于傳統的關于知覺的被動模型進行相應的形上學與知識論討論,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幻覺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只有從根本上革新我們對知覺本質的理解,我們才能有效回應諸多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