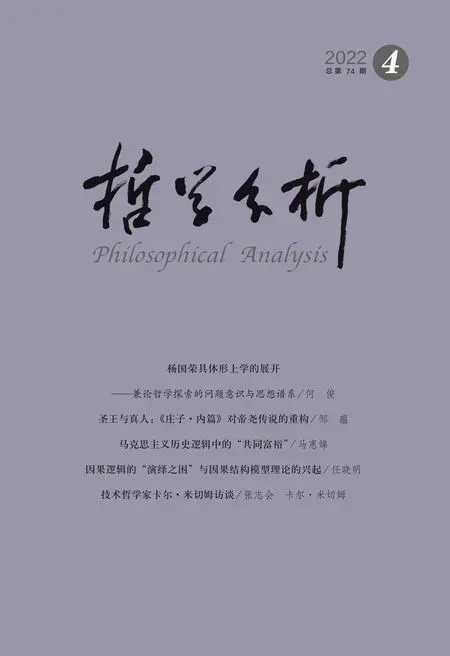圣王與真人:《莊子·內篇》對帝堯傳說的重構
鄒 蘊
通常來講,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譜系中,堯舜時代被視作一個至高的圣王時代。作為儒家重要思想來源的《尚書》,其首篇《堯典》以堯的德行和事跡作為后世君王學習的范本。孔子則把堯比作天,以“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贊頌堯的德行高遠和功績卓著。《中庸》稱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見孔子將堯舜視為圣王理想的源頭。孟子更是感慨“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他借助堯舜死后世道的崩壞來反襯堯舜時代的昌明……這些過往的儒者或是基于上古的神話和歷史,或是經過重新詮釋,都不約而同地把堯舜的時代描繪成一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至德之 世。
不過,莊子筆下的堯舜就沒有如此光輝燦爛,反倒多了幾絲彷徨不寧的氣息,尤以內篇中的堯為甚。在《莊子》中,雖然堯舜常常并列出現,但作者對堯的描述和鋪展則更多一點。《莊子·內篇》中有五則難以解釋的政治寓言都與堯有關,并且堯都是其中的關鍵人物:第一則是《逍遙游》篇著名的“堯讓天下于許由”的故事;第二則同是《逍遙游》篇的“堯見四子”的故事;第三則是《齊物論》篇的“十日并出”章,堯因征伐小國而不釋然;第四則是《人間世》篇借助堯、禹攻伐小國的事例來探討圣人與名、實的關系;第五則是《大宗師》篇“意而子見許由”章中許由對堯的批判。這五則故事的文本語境看似不相關,但實際上都通過“堯”這一人物折射出莊子對圣王理想的深刻認 識。
遺憾的是,莊學界關于《莊子》中堯的形象的解釋難有圓滿之論。經過筆者整理,相關解釋約略分為三種:其一,部分研究打破了《莊子》內外雜篇的分界,無視堯在內篇與外雜篇系統中形象的巨大差異,進而將堯在《莊子》書中出現的篇章和段落同等對待;其二,絕大部分致力于《莊子·內篇》中堯的相關研究都只是以五則寓言中的一兩則(尤其是“堯讓天下于許由”章和“十日并出”章)作為論述的中心,而鮮少全面剖析上述五則寓言并深入挖掘五則寓言之間的內在聯系;其三,當前的解釋方向主要局限于兩種,即要么認為莊子否定堯,要么認為莊子推崇堯,二者均未立足于莊子哲學的整體基調,最終沒有跳出“譽堯而非桀”的是非論 辯。
鑒于當前研究的這些缺憾,筆者以《莊子》書的思想基礎——《莊子·內篇》當中堯的形象——為研究中心,并將與堯相關的五則寓言視作一個相互闡發的整體,在莊子哲學的總體基調中去理解堯在《莊子·內篇》中的深層寓意。此外,《莊子》全書“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這五則故事都是基于上古歷史和神話傳說改編而成。如果將堯作為線索,并厘清這五則寓言和堯舜傳說之間的異同,這將就有助于我們理解莊子改編神話傳說的用意。如此一來,我們不再拘泥于一兩則寓言,而是把五則寓言融通地理解,那么堯在《莊子·內篇》中支離破碎的形象也可能趨向完 整。
通過分析這五則寓言,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則和第二則寓言同出于《逍遙游》,且都關乎對天下的治理,適合放在一起討論。第三則和第四則寓言都牽涉堯的武力攻伐相關問題,也可以對勘。第五則寓言借助許由對堯的批評引出了“天人關系”這個更根本的問題,對這個根本問題的解讀關乎莊子對堯的整體態度,因此我們在前四則寓言相互發明的基礎上,用第五則寓言來統攝全篇,最后揭示出堯在《莊子》中的整體哲學寓 意。
一、“讓天下”——心系天下的治理者
我們先看《逍遙游》中的兩則故 事: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
堯禪讓帝位于舜是堯舜傳說中最為核心的情節,也是堯最重要的政治功績之一。這兩則寓言既是對“讓天下”傳說的改造和深化,也是對儒墨共同稱頌的“禪讓說”的回應。儒墨兩家作為戰國諸子中的“顯學”,對堯舜禪讓之說推崇備至。《墨子》有云:“昔者舜耕于歷山,陶于河瀕,漁于雷澤,灰于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唐虞之道》更是竭力頌揚:“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莊子及其后學則對甚囂塵上的“禪讓說”頗為警惕,從第一則寓言中的許由到《讓王》篇的子州支父、善卷、石戶之農等,《莊子》塑造了一批不受天下之讓的“逃王高士”,這個“逃王”群體拒受天下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保身求道,可見《莊子》“剽剝儒墨”的力 度。
先看第一則寓言,莊子把堯禪位的對象由同為圣王的舜換成了隱逸的高士——許由。堯形容許由的德行如日月的普照和雨水的澆灌一般廣大,相形之下,自己不過是微小的火把和水流,哪還有資格占據著天子之位?堯于是要把天下讓與許由。許由認為天下已經被堯治理好了,堯為治天下之“實”,自己如果接受天子之位,則只配有治天下之“名”。“名者,實之賓也”,許由不會為了求名而失去“鷦鷯巢于深林”的逍遙自在。此處很可能是借助許由暗諷堯好禪讓之名,來隱晦地批評與莊子同時的魏惠王,他當時禪讓惠子不過是為了竊堯舜之名,卻無堯舜之功德。接著,許由道出了更深層次的拒受天下的原因:“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同于堯所代表的方內之圣王,許由在此處代表了方外之隱士,他們之間就如同庖廚和巫祝一樣涇渭分明,正所謂《大宗師》所言“外內不相及”。因此,許由走的是方外之路,對治理天下沒有任何興趣,即使堯把天下拱手讓與他也沒什么意 義。
再看第二則寓言的第一句:宋人到遙遠的越國去兜售殷商時期流行的發冠,到了越國才發現河網縱橫,越人斷發文身,根本不需要戴什么發冠。宋人和堯類似,以為其他人都會稀罕自己最珍貴的東西(“章甫”和“天下”),結果卻發現對方(越人和許由)根本不需要(“無所用之”),也不感興趣(“予無所用天下 為”)。
我們再回到第一則寓言的對話情境,不難看出,堯在禪讓天下之前并不理解許由的立場,只是一廂情愿地以為天下人都會像他一般鐘情于天下的治理,殊不知,天下之外還有另一個世界。同理可推,宋人也以為天下人都像他們一樣需要束發戴冠,直到進入一個與中原地區截然不同的江湖世界,才意識到還存在另一種生活方 式。
在第一則寓言中,堯雖然謙遜大度,幾乎要把自己最重要的天下讓位于許由,但歸根結蒂堯還是以治天下為意,他仍然關心天下能否在德行最好的人那里得到治理。如果說第一則寓言的許由還讓堯心系天下,未能實現逍遙,那到了第二則寓言的第二句,堯所見的人物變成了由四岳轉換而來的四子,這些方外神人卻讓堯忘記了原本重要的“天下之民”和“海內之政”,以至于恍惚間喪其天下。從第一則的“讓天下”到第二則的“喪天下”,為何出現了層次上的跨越?我們不妨作出推測:許由和四子雖同為方外之人,卻是有境界的高下之分。如果仔細推敲兩則寓言,可以發現:四子是沉默的,他們很可能就是第二則寓言前文中“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逍遙游》)的神人。通常情況下,《莊子》中的“至德之人是默不作聲的”。許由卻一直在為自己“一枝及滿腹”式的自足辯解,可見其執著于獨善其身,未能忘己。并且,《莊子》中擁有至高權力的君主通常在遇到至德之人以后方才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更何況姑射神人的“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逍遙游》)。因此,姑射神山的四子在境界上要高于許由,只有見到四子這樣道行高深的神人,才有可能讓堯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那對于堯這樣在人倫的秩序中已經達到頂峰并且功德圓滿的圣王來說,還有什么局限性可言呢?筆者按下不表,我們需要繼續釋讀第三、四則寓言才有可能給出答 案。
二 、“除四罪”——好名求實的攻伐者
第三則寓言出自《齊物論》篇的“十日并出”章,第四則出自《人間世》篇的第一個問對,在這組故事中,堯都以攻伐小國的形象出場,討論的問題也都關乎“名實之辯”,對勘有助于解釋兩則寓言中含混不清之 處:
故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圣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關于第三則寓言舜勸說堯的含義,歷來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方向:一種是以郭象(“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愿而伐使從己,于至道豈弘哉!”)為代表的主流觀點,認為堯的德性遍照萬物,又豈能容不下蓬艾小國的存在,故而以舜勸阻堯放棄攻伐來使堯釋然;另一種是以朱文熊(“宗膾、胥、敖即共工、歡兜、三苗之轉音。堯不釋然,故未之除,舜之誅放,亦行所無事也。”)為代表的解釋方向,認為舜是從正面論證堯攻伐三國的合理性,讓堯心安理得地攻伐三 國。
筆者認為,要廓清第三則寓言的解釋方向,不能孤立地看待這幾句話,而應當將其放在《莊子·內篇》論及“堯”的整體語境中,尤其要結合第四則寓言中堯的形象來 看。
在第四則寓言中,堯和禹這些人間世的圣王以“攻叢、枝、胥敖、有扈”這類蓬艾小國的形象出場,并且在“用并不止,求實不已”的過程中導致“國為虛厲,身為刑戮”的慘況。莊子稱這些圣王為“皆求名實者”,也就是既好名,也求實之人。“名”和“實”是《人間世》開篇第一個問對中出現的一組概念,“名”可理解為價值理想,“實”即是對這套理想的實現。孔子正是在教育顏回放棄出使衛國的過程中,插入了關于“好名”者和“求實”者的論述。莊子借孔子之口以比干、關龍逢的悲慘遭遇警示顏回,勸他不要再做“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的好名者,這是以自身的賢德反襯出君主的惡劣,最后反倒招致君主的猜忌和殺害。孔子以“好名者”的故事影射執意要去勸說衛君的顏回,“好名”,指的是顏回不顧身份的卑微和處境的艱險執著地要向暴君進諫的決心(“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如果說比干、關龍逢乃至顏回代表的是徒有理想卻沒有能力“求實”的有德無位者,那么堯、禹這些圣君代表的就是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的有德有位者,所以他們是“皆求名實者”。通常情況下,君主總是先有“名”(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再去“求實”。既然第四則寓言講的是堯的“求實不已”,那么第三則寓言就可被順理成章地解釋成堯的“好 名”。
我們回到第三則寓言,就能用前文所總結的第二種方向來解釋,舜用“十日并出”的譬喻一針見血地戳中了堯靈魂深處的“好名”之心:既然堯的德性比十個太陽的光芒還要廣大無邊,那處于蓬艾之間的卑弱小國又豈能一直處在蒙昧落后的狀態,堯有什么理由不去教化它們呢?因此,在舜的點醒下,堯由攻伐三國產生的不釋然之心就轉化為匡扶天下的決 心。
如此解釋,舜的勸說不僅給堯的武力攻伐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從而和第四則寓言中堯“求實不已”的堅定形象貫通起來,而且也符合《莊子》中舜比堯“更傾向于武力征伐”的形 象。
通過第三則和第四則寓言的互證,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名、實者,圣人之所不能勝也”這番人間世的普遍境況:忠厚賢良如關龍逢、比干亦不能逃離“名”所設下的陷阱,他們舍生忘死追求“名”所代表的政治秩序,最終為“名”所害;堯和禹這樣千古一遇的圣王也是在“名”的驅使下,無休無止地征服天下,讓天下蒼生“國為虛厲、身為刑戮”,終究無法避免生靈涂炭、不得安寧的悲劇。因此,莊子不無嚴厲地反復強調:“名”是人間世的兇器,它讓人的欲望不停激蕩、人的德性不斷貶損,以至于讓人“行名失己……亡身不真……役人之役,適人之適”(《大宗師》)。所以,“名”不是根本的可取之道(“非所以盡行 也”)。
然而,“名”和“實”卻是構成政治生活的必要因素。政治秩序的實現總是先由掌權者的政治熱情開啟,再依憑一系列的名目、禮法、制度來完成,這個過程就是由好名之心的攖動逐漸被強化為對現實的不停追逐,也就是有心朝著“名”這個目標不斷進于“實”的過 程。
即使是堯這樣象征治世典范的圣王也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整套步驟完成了由“名”進于“實”的人倫秩序的建構。堯的政治德行以及他“‘由個人至天下’的實踐步驟構成了后世儒家實踐論的標準程序”,可見累世之圣賢都是以“皆求名實者”為終極目 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古歷史和神話傳說中,堯總體上都被敘述為人文秩序的締造者,卻較少以武力攻伐的形象出場,而莊子在第三、四則寓言中卻塑造了堯暴力刑戮的形象,這種形象源頭何在?如果我們放眼典籍中堯舜之于周邊少數族裔的舉措,就會發現存在一個“除四罪”(共工、歡兜、三苗、鯀)的情節單 元: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書·舜典》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孟子·萬章上》
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勛……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大戴禮記·五帝德》
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記·五帝本紀》
這四段引文或是將“除四罪”歸于舜(《尚書》 《孟子》),或是將其歸于堯的行為(《大戴禮記》),或是歸于堯舜共同的行為(《荀子》 《史記》), 主體的含糊不清是神話傳說在流傳過程中很常見的一個特征,但不論其歸屬者是誰,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堯舜傳說中很早就存在“除四罪”這樣一個母題,而歷代典籍對于“除四罪”不同版本的敘事可被看作一個母題的異型。《莊子》也不例外,作者通過敘述堯之攻伐三國把堯舜“除四罪”這個神話母題改造成了堯之除三罪:《齊物論》篇中堯“伐宗即放驩兜,伐膾者,流共工也,伐胥敖者,投三苗也”,《人間世》篇中堯攻“叢、枝、胥敖即宗、膾、胥敖也”,這種把“鯀”排除出去的堯之除三罪模式一直延續到《在宥》篇中所說的“堯于是放歡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
綜上分析,《莊子》使用“藉外論之”的寓言把堯改造成不斷征服天下的攻伐主體,“求名實者”的圣王特征在堯的身上得以凝結。堯形象的重構讓我們明白:“即便人間政治達到最高的可能,依舊固有其本身的限度”,這也正回應了第一和第二則寓言中堯的局限性在何處——盡管讓天下于許由這個行為表明,堯不再以“治天下”之名自居,但他還是關心天下的治理,仍舊執著于理想的政治秩序(名)能否借一個更高明的治理者(許由)來實現(實),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堯還是好名求實的。只不過,堯作為方內的治世典范,他需要通過方外的神人(四子)才有可能意識到其政治的局限性(窅然喪其天 下)。
三、“單均刑法”——施行禮法的教化者
如果說,前四則寓言是圍繞“名”和“實”勾勒出了堯治理天下的整體圖景,那么第五則寓言則是以“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提煉出堯之治理的具體方式。和第一則寓言類似的是,在第五則寓言中,堯和許由也是以立場相互沖突的一對人物而出現,不過堯這次是間接地出場,借由意而子和許由來轉述他的教化方 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愿游于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大宗 師》)
堯在此則寓言中被許由形容成一位“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的治世君王,由“黥”(墨刑)和“劓”(割鼻子)我們自然會聯想到堯舜時期的“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堯和刑罰的聯系古來有之:春秋時期以“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來概括堯的功績主要在刑罰領域;根據《尚書·堯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的相關記載,可以看出,堯舜時期的刑罰體系已經相當完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大法官皋陶正是從堯時期開始掌握斷獄和司法大權,并且神話傳說記載他有一只能夠公正裁斷人事糾紛的神獸——獬豸。以上這些記述都說明很早就存在堯、舜、皋陶立法執法這樣一種敘述母題,后世的作者依據自己的理解對這個母題進行了各式改造,莊子則運用堯和刑罰之間的種種聯系把堯塑造成用禮法度數治理子民(“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的君 主。
理清堯的象征意味就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則寓言,即:意而子拜訪許由,希望許由能教授自己一些本領,但很快就遭到了許由的嫌棄,理由是堯已經用“仁義”和“是非”這些人為的標準把意而子自然樸素的面貌改造(黥、劓)得面目全非,意而子已經遠離大道、往而不返了。換言之,許由把意而子當前的面貌看作一種已完成的、不可逆轉的狀態。面對許由的質疑,意而子的回答是“吾愿游于其藩”,“藩”的意思是“邊界”。這句話說的是,意而子不以“方之內”或“方之外”的范圍限制住自己,雖然“躬服仁義”是對自然面貌的消解,但堯所傳授的人文教化卻也不是終極的狀態,沒有必要因此停滯不 前。
接下來,意而子舉無莊、據梁、黃帝的事例勸服許由,同時勉勵自己:我們依然可以通過“爐錘之間”的工夫去掉教化所帶來的負面損害(“失其美”“失其力”“亡其知”),也就是通過進一步的修煉回返到天機自然的境界(“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不同于許由的質疑(“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所暗含的“自然—教化”的單向進程,意而子的回復則展現了一種“自然—教化—自然”的循環進程。這種回環往復的觀念貫穿于《莊子》全書:《逍遙游》中的“鯤化鵬”故事展現了“一個從‘道’之整全到‘道’之分離再回歸于‘道’的環形過程”;《大宗師》中的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顯示出生死相續的循環流動;《寓言》篇在解釋卮言時提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可見萬物流變的循環;《至樂》篇則描述了一個“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的物物相生的鏈條……所以《莊子》認為,從“道”的運動到生命的鏈條都呈現出一種回環往復、旋轉不息的結構,意而子的立場正與這種循環論相符合,且超越了許由所代表的單向靜態結 構。
《應帝王》篇最后一個“渾沌”的故事,可以和這則寓言形成互證。在《應帝王》的結尾,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為了報答中央之帝渾沌的恩情,將其日鑿一竅,七天之后,渾沌被鑿七竅而死。渾沌的神話原型很可能出自《山海經》中的神鳥帝江,此怪獸面目模糊,沒有七竅。在莊子的改寫下,倏忽二帝自作主張地把帝江質樸渾成的面貌破壞得支離破碎,這種破壞(“鑿”)與堯對意而子的損傷(“黥、劓”)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人為地改造渾然天成的自然狀態。盡管《應帝王》篇乃至《莊子》內七篇以“渾沌之死”作結尾,但結合《莊子》的循環論,死亡并不是終點,只不過是 “永恒生命”中的一個節點。“七是循環數字之極,七日渾沌死,但七日也來復”,渾沌經歷了死亡,也會迎來新生。渾沌之死、堯對意而子的改造、意而子有修復教化之傷的可能,這些情節都暗示著在“道”循環往復的運動中,死亡(除舊)和新生都是必不可少的環 節。
面對意而子與時俱化的態度和工夫修煉的決心,許由原本嗤之以鼻的語氣也緩和了許多——從先前認為意而子完全不可能學道,轉換到一種開放的態度(“未可知也”);從開始拒收意而子入門(“而奚來為軹”),到最后愿意為意而子講述大道的核心精神(“我為汝言其大略”)。通觀這則寓言的整體基調,意而子盡管承認了堯對自然的破壞(“雖然”),卻不認為堯的教化是對自己修道的阻礙;意而子雖然不認同許由所主張的線性時間觀,但虛心向許由求教。意而子對堯和許由雙方觀念的超越,再次證明了在此則寓言中,他才是莊子的代言人(“兩忘而化 其 道”)。
借由意而子的言行,我們看到,莊子并沒有否定堯和許由的任何一方——堯所代表的“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的教化之路和許由所推崇的“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的自然之路都在“道”的循環流轉中得以保證。如果說許由之路代表的是“天”(方外),堯之路代表的是“人”(方內),那么意而子在“天”與“人”之間婉轉流變的態度則指向了《大宗師》開篇所闡發的宗旨——“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何謂“真人”?下一節將作具體的闡 述。
四、圣王·神人·真人
在《莊子》書中,“真人”一詞首次且集中地出現于《大宗師》篇(但真人的形象在《大宗師》之前出場過)。《大宗師》著名的“真人四解”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古之真人游走于方內和方外之際的自由圖景:“真人一解”(“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講述的是真人安之若命、不為外物所動的境界;“真人二解”(“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則通過真人的作息、飲食、呼吸等身體狀態的刻畫揭示了一種“本真的生活方式”;“真人三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展現了真人道通為一、隨任大化周流的自適面貌;“真人四解”(“其狀義而不朋……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以真人的體相和形貌特征為中心來揭示真人處理天人關系的智慧。通過這“四解”,我們可以看到,真人既進入了高妙超然的齊物境界,又不與人間塵世相脫離,這正合于意而子的志向——“吾愿游于其 藩”。
回顧第一節的論述可知,除了“真人”這種人格范式,莊子還討論過“神人”。和真人類似的是,《逍遙游》中所描述的神人也是得道之人(“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只不過神人向來居于方外(“游乎四海之外”),不與方內世界打交道(“孰肯以物為事”)。這也難怪《莊子》中的神人不直接出場,而是出現在接輿、連叔、南伯子綦等人的傳奇敘述中。這些神人或是居于遠離人間、纖塵未染的姑射山上,或是化身為荒郊野外、可結駟千乘的不材之木——“神人以此不材”(《人間世》),或是與習俗觀念所認定的不祥之物——“牛之白顙……豚之亢鼻……人有痔病”(《人間世》)——享有共同的價值。神人的事例和“堯見四子”的寓言一樣,都開啟了一個與人倫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外世界,同時開啟的是與方內價值(有用、天下、材、祥)相對立的方外價值(無用、喪天下、不材、不祥)。換言之,神人崇尚的價值在世俗世界一文不值,而人倫社會所唾棄的無用之物在方外世界反倒被奉為至寶。結合前三節的分析,我們已經清楚,堯作為有德有位的圣王可謂是方內價值的集大成者,而神人則是方外價值的典范,可見圣王與神人是涇渭分明的兩種人格范式。與此同時,在莊子的筆下,堯一生汲汲于天下秩序的建構而不知停歇,直到遇見以四子為代表的神人,竟舍棄自己畢生追求的價值理想。這說明神人在得道的程度上高于圣王,讓圣王意識到自己在德性上的虧損,并向往另一個全生全德的方外世 界。
方內與方外、有用與無用的對立在圣王和神人兩種人格的呈現中表露無遺,直到真人的出場才消解了二者的沖突。盡管同是得道中人,但真人不同于神人的地方在于,真人并不純然棲息在方外之地,而是與世俗世界存在自然的聯系。例如:《德充符》篇的哀駘它不受死生、存亡、窮達、貧富的影響,是一個臻于至德之境的人,同時他還能隨遇而安、與物為春,甚至讓身邊的男女長幼都被他感化;《大宗師》篇的孟孫才也是真人人格的具體顯現,他雖已齊同生死,但并不貶低喪禮,他為母親居喪期間依然“人哭亦哭”、隨緣自適;在緊隨其后的“意而子見許由”寓言中,意而子也秉持著同樣的處世觀,他雖然向往許由所師法的神人之道,卻并不對堯的禮法教化持以鄙薄的態度,而是平和地面對神人(“天”)和圣王(“人”)的差異。真人之所以能等量對待方內與方外,在于他以“道通為一”的視角看待宇宙萬物,即方內世界和方外世界在“道”的觀照下,并沒有什么高低之別。相較之下,神人的眼光卻充斥著對方內世界居高臨下的評判,“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逍遙游》),這分明是一種不屑一顧的孤傲,正如神人的代言人許由對圣王的教育嗤之以鼻一樣,這些不都是莊子竭力批評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齊物論》)嗎?顯然,神人還未抵達“莫若以明”的境界,可見其修道的境地尚不如真人圓滿。《天下》篇對莊子思想的概括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這正是對真人不即不離風貌的寫照,所以真人才是莊子最崇尚的理想 人 格。
理解了莊子的真人觀之后,我們就可以更冷靜地看待兩類理解《莊子》思想的傳統觀點:一類是以郭象為代表的“游外冥內”說,也就是在方內適性而為才能實現充分的自由,隱逸于方外反而不能“實現性分所具的社會性潛能……難以真正實現自身的適性逍遙”,在這種觀點的統領下,就會得出:堯這樣充分實現社會性潛能之圣王正是逍遙游的典范,因為他以無為而治的方式保證了自己和天下秩序的自由;另一類是以荀子、司馬遷等人為代表的虛無避世說,持這類說法者大體都認為莊子學說“蔽于天而不知人”,即倡導人們過一種遠離塵世的隱逸生活,甚至由此延伸出莊子“壞法亂倫……欲天下而不理……欲絕圣賢,使天下各止其知”的“廢莊說”,換言之,這種立場包含著一種認識,即堯作為仁義禮樂觀念的代表被莊子所棄絕。前一種觀點認為莊子主張方內才能實現自由,這樣就導向對堯形象的推崇;后一種則認為莊子要歸于方外的虛無之境,從而引出對堯作為方內圣王的否 定。
顯然,上述兩類觀點都不符合《莊子》的真人觀,真人既達到了玄同萬物的廖天一之境,又不與世俗社會相脫離,故而能在方內和方外“兩行”其道,而不是二者擇其一。這樣一來,莊子對堯的整體態度也漸趨明朗——雖然莊子借助堯的圣王形象揭示了人倫世界的不完滿,但這樣揭示的目的并不是將方內生活予以否棄,而是導向對整全之道的求索,同時,這個道與世俗生活不相分 離。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運用莊子的循環論和真人觀來回應開篇提出的問題:不同于先秦儒家對堯的稱頌,莊子誠然沒有建構起一個光輝燦爛的堯形象,而是運用諸多神話傳說重構了堯的圣王形象。值得強調的是,莊子重構圣王的目的不在于解構人倫生活的價值,而是讓我們認清方內世界的局限,從而牽引出更為博大的“道”的本體論。換言之,莊子在批評堯的同時,并不純然否定堯,而是正視堯在道的流轉中的合理性。真人盡管是比圣王和神人更為理想的人格范式,然而真人在方內與方外游走的形態也印證了,莊子之意并非取消圣王和神人,而是要接納和銜接兩個世 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