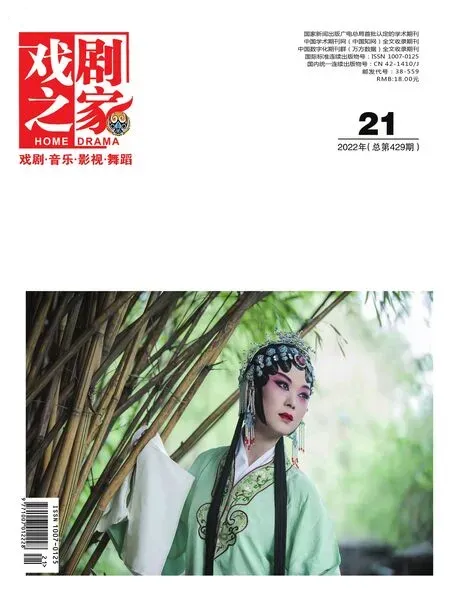從符號學視角看音樂伴隨文本在音樂教學中的作用
黃寶順
(東華理工大學 藝術學院,江西 撫州 344000)
一、“文本”的基本概念
文學上的文本是指書面語言的表現形式,是具有完整、系統含義的一個句子或多個句子的組合。在符號學中,“文本”一詞的意義界限較為廣泛。最窄的意義,與中文的“文本”相近,指的是文字文本。比較寬的定義,是指任何符號表意組合,印刷的、寫作的、編輯出來的文化產品,從手稿檔案,到唱片、繪畫、樂譜、電影、化學公式等(趙毅衡,2010)。現今包含音樂作品信息的符號集合也不限于文字文本,因此本文中的中小學音樂課程中攜帶了所要教授作品相關信息的多種符號所形成的組合都是這里所討論的“文本”及“伴隨文本”,即是從比較寬泛的定義來分析文本。
音樂課堂中存在大量的音樂的伴隨文本,且有出現的先后順序,當然不同的伴隨文本也會同時出現,這些文本也有自身的特點,且這些文本將是學生所學知識的信息保留載體。正確認識和分析小學音樂課堂中的音樂文本及其伴隨文本的特點和作用對音樂教師來說具有一定意義。
二、音樂文本的展開與跨越
鐘啟泉先生將課程實施過程中產生的文本分為四類(現成文本、教案文本、課堂文本、教后文本),其中教學設計文本即教案正好與之對應,這是教師憑借自身經驗擴展單一教學材料的關鍵文本。教師在進行教學前需要分析所教學齡的學生心理特點、與此同時對音樂課本上作品的音響特點、作品結構、情緒特點等進行初步分析形成教案文本。而在進行教學設計時不僅僅是教案文本的書寫,為了順利實施教學設計和豐富課堂還需要準備多種材料。而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通過分析音樂作品的顯性伴隨文本來對教學材料進行擴充。
(一)通過副文本展開原文本框架
教學設計內容如何取決于教師對教材解讀的程度,音樂教材所給的內容是有限的,作品蘊藏的其他信息需要教師自己加以擴充和豐富。對原教材框架內的一些內容的擴充可以通過顯性文本第一類文本——副文本來實現。音樂作品的創作者、標題、作品類型都屬于副文本。副文本因素影響著文本信息的接收,特別是對于小學生來說,音樂的非具象性使得他們在對音樂作品接收并做出解釋時產生困難。因此對教材上作品文本的副文本進行分析和提取,然后加以利用會使得教材內容更加充實,學生對教材內容的認識深度也會有所增加。
以人音版三年級下冊(2015.01 版本)音樂教材為列,對“第一課愛祖國”中的作品《紅旗頌(片段)》的其中一個副本內容進行簡單分析,來感受副文本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看到“愛祖國”是這一課的總標題,這一課的幾個作品《我們走進十月的陽光》《紅旗頌(片段)》《盧溝謠》《只怕不抵抗》都包含了個人對“祖國”的一種積極的態度和情感。五星紅旗是中國的國旗,在多個場合下紅旗就代表著中國,比如掛在聯合國總部前面的紅旗就是象征著中國。作品《紅旗頌》的標題屬于副文本,同第1 課大標題“愛祖國”一起,攜帶著作品表現的內容和情感的信息。在標題下面寫有“管弦樂”,這對該作品演奏樂器做出了明確的標識,說明作曲家在創作該作品的時候選擇了最適合表現作品旋律的樂器種類是管弦樂器。通過對以上兩個副文本攜帶的信息簡單分析,教師便可以在教學設計時根據副文本攜帶的信息進行相應地設計,比如根據標題副文本引入愛國故事,紅旗圖片等等,根據“管弦樂”引入樂器知識等等。副文本只是文本的框架因素,通過副文本擴充教學材料并沒有采用新的作品文本,因此我們還需要通過下面的型文本進行跨框架操作。
(二)通過型文本跨越原文本框架
美國的中小學音樂教材種類眾多,但是很多州的音樂課程并沒有采用固定的已出版的音樂教材,中小學音樂教師依據課程標準,自行設計教材選用作品從而形成具有特色的音樂教學內容。音樂課程作品不應該僅限于教材,音樂教師會根據課程標準和學生來選取其他材料來進行教學作品之外的材料的擴充,且被用于擴充的材料與本身要進行教學的作品要具備一定聯系才能被采用。
型文本是顯性伴隨文本的第二類文本,它指明文本所從屬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規定的文本“歸類”方式(趙毅衡,2010)。而對應在音樂課堂的引入的“文本”材料上,具體包括要教學作品的創作者的其他作品、具備同種民族文化的作品、同一題材的作品、同一體裁的作品、不同樂器演奏的同一作品、具備同種價值觀的作品等等。例如教授歌曲《苗家兒童慶豐收》時,這個作品具有明顯民族文化標識,教師應當對作品的文化性產生敏感的反應。我們可以引入苗族的蘆笙樂曲曲譜及相關的音響,把曲譜文本引入教案之中,準備曲譜產生的音響效果文本和音樂所存在的情景視頻(苗族人民逢年過節,他們都要舉行各式各樣、豐富多彩的蘆笙會,吹起蘆笙跳起舞,慶祝自己的民族節日);歌曲《苗家兒童慶豐收》的型文本共同具備明顯的苗族文化特征,通過多種不同的苗族音樂擴充了學生的文化視野,使得教師有更好的材料支撐。型文本的應用是在教材文本的內容之外,從邏輯順序上來看,型文本的應用必須依據副文本的解讀和分析。
顯性伴隨文本是在文本生成之前便已經存在,本文所談論的教學設計文本不等同于教案,教學設計“文本”是在進行正式課堂教學之前教師對教材解讀而形成的一個攜帶教材相關信息的符號組合體,包括圖片、曲譜、音響、視頻等多種形態的文本。在小學課程的縱向結構上,顯性伴隨文本提供了一種課內資源與課外資源的聯結關系。為課堂教學的實施提供了材料保證,有了縱向的材料才會形成橫向的課程發展。
三、音樂文本的解釋與創新
解釋性伴隨文本出現在文本生成之后,并且在解釋文本時起到作用。因此這類伴隨文本發生在教師接收文本信息并解釋文本(解讀作品信息時)和學生接受并對文本信息進行解釋時。
(一)經驗與想象
鏈文本是接受者解釋某文本時,主動或被動地與某些文本“鏈接”起來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比如,我們在看見某明星代言的廣告時,可能會同時想起一些該明星代言的其他廣告和一些他參與過的作品等。鏈文本不等同于型文本。型文本是在生產或解讀時意識到的文本集群類型,而鏈文本是在文本被接收同時接收的文本,某個符號文本的接收變成一批文本的集團接收(趙毅衡,2010)。因此鏈文本范圍更廣。在引導學生思考和自我探究時,對所學習的文本進行解釋便會不知不覺浮現鏈文本,鏈文本出現的范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生思維的活躍性和開闊性,以及學生已有的經驗和認識水平。
鏈文本看似沒有秩序但在教學活動中卻不能忽視。伽達默爾的理解過程的立足點——視域,說明解釋者在對文本作出解釋時首先是從自己的視域(也就是個人所處的現實情境和自身經驗的結合)出發,那些企圖讓解釋者跨越歷史并消除解釋者自身歷史性的顯然要慎重思考一下;如果解釋者消除了自身歷史性而在某一藝術作品的解釋上達到歷史的統一就缺少了解釋的多樣性,特別是對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來說,美育課程不僅是為了學生的全面發展,還得提倡學生的獨特性。學生對作品的解釋顯然很大部分來自于自身的現存經驗,鏈文本的產生也就有了其原由。
在音樂課堂上問題是開放性的,學生的回答也是多樣性的。作為一種描述性不確指的藝術,音樂語言是非推論性的,對音樂作品本身的解釋也存在模糊性,這就更加能夠說明學生對音樂作品的解釋很寬泛。鏈文本經常出現并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同樣以小學音樂教材上的《紅旗頌(片段)》為例,教師設置問題“同學們在聆聽《紅旗頌(片段)》時,動動腦筋看你能想到什么”。學生在聽音樂時可能會想起中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與此同時因為我們是音樂課,會想起中國的國歌,又或者想到偉大領袖毛澤東等等,這一系列信息所構成的集合便是鏈文本集群;而一道數學題讓學生去解答可能就是幾種可預測的解答過程和固定的答案,特別是對于小學生來說對數學題解答過程是十分固定的,因此這種問題的解釋就更加不可變了;我們常常發現“即便有時教師會向學生提出問題,表面看這是一種對話的形式,但這種對話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有教科書預先設定好的邊界,有‘經驗’的教師始終是小心翼翼地引導學生游走在這個邊界之內”(鄧友超,2009)。身為一名音樂教師就應該利用藝術解釋的不確定性來激發學生的想象力,關注學生自身視域,重視因人而異的鏈文本,即使是游離在學習材料之外符合情形的回答也要納入認同之內。
在音樂課堂教學中,學生在聽音樂《紅旗頌》時可能會想起的系列信息所構成的集合是鏈文本集群;鏈文本集群關系到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同時也體現出學生自身的經驗。對于一些特殊的作品來說來自學生的鏈文本可能會出現較大的差異,在一些少數民族音樂作品上,可能某位學生了解或是接觸過相關文化,那產自于他的鏈文本必然比較獨特。
(二)自主與創新
先文本/后文本,是一個文本承接另一個文本,兩個文本之間內容有明確的聯系。許多歌曲出自特定的文本,并被改編或選用不同的樂器演奏傳遞下去,這樣前后相連的文本便是先/后文本。而隨著現代教學理論和教學實踐的發展,在課堂上已經由單一的語言模式跨向多模態話語的組合傳遞信息,比如音樂繪本故事通過文字、美術和音樂等的結合讓學生能有更好地體會。
在音樂課堂上先/后文本這對組合文本概念的形成一般出現在創編擴展之后的展示環節。音樂課堂上最常見的先/后文本是對于音樂作品再演唱或者再演奏,對于一首女孩歌唱的兒歌我們可以在課堂上進行男女分開演唱形成男女兩個版本,同樣對于一首歌曲的旋律,教師和學生合作采用鋼琴或者竹笛對其進行演奏也會與之前的文本形成先/后文本,在這里最常見的后文本與原文本之間顯然還未跨入不同的感覺形式。
為了兒童在音樂課堂上能有更全面的體驗,教師在這樣的環節中要引導學生跨越話語模態,利用不同的感官感受來對所學內容進行自己的解釋。例如將兒童舞蹈引入音樂課堂,讓學生們用自己的肢體語言來表現自己所聽見的音樂,亦可以讓學生通過簡單的繪畫來描述自己聽到的音樂的視覺形象,這樣可以使得學生自己的經驗世界和音樂產生聯系。同樣的,在許多課堂中一些老師也會創造圖形符號或者肢體語言來幫助學生理解所學內容;學生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音樂而形成文本都是自己對音樂的解釋和體會,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可能在語言上缺乏對音樂的表達能力。某些時候學生沒有表達出來并不是他對這個作品沒有自己的體驗而是缺少他能表現的方式。這樣讓學生用自己能表現的方式來表現他們的想法,也可以看到一個作品的不同效果以及學生們自己的優勢;自主性的表現不局限于以音樂為唯一的表現方式,我們可以在音樂的環境中采用各種表現形式,突破單一的音樂課堂反饋,以實現多樣化的音樂學習評價方式。
值得教師重視的是,對于所學習的作品和知識的檢驗可以通過學生演奏/演唱或綜合表現以及學生自己的創編形成的后文本來實現。在課堂的綜合表演環節,學生們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展現自己對作品的理解,老師同時也要跨越不同的話語模態來分析和評價學生的反饋。在課堂的擴展創編環節,學生的創編文本來自于對先前接受的文本的理解。先/后文本是課堂文本延續豐富不可缺少的伴隨文本,通過話語模態的擴充更是讓先/后文本變得豐富和形象。
四、結語
在教學中通過顯性伴隨文本使得課堂材料豐富,并擴展文本的范圍,告別材料的單一性。特別對于低年級學生而言,課程材料的多樣性才會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作品。對于解釋性伴隨文本意義的正確認識可以幫助教師引導啟發學生,開拓學生的想象力,并檢驗學生的學習和擴展水平。正確認識音樂課堂上這些伴隨文本的功能,重視文本攜帶的信息并加以利用可以幫助分析音樂教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