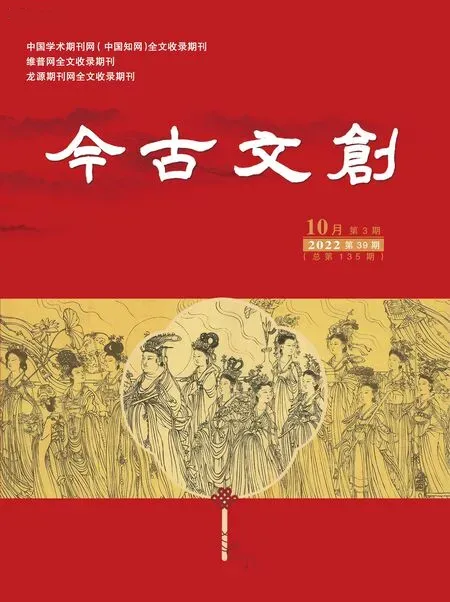創傷理論視角下的《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解讀
◎李雪松
(哈爾濱師范大學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卡佛是美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著名小說家和小說界簡約主義的大師,是繼海明威之后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作家,被譽為美國的契訶夫。卡佛擅長以凝練簡約的寫作風格展現生活背后的深淵和隱秘的情感。”《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是美國短篇小說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說。小說透過啞巴的故事, 清晰地再現了啞巴作為社會底層人民飽受來自愛情、生理及社會各方面的折磨。本文試圖從創傷理論角度入手,解讀小說中啞巴心理創傷的來源及其對生存處境的反抗卻最終走向毀滅的人生悲劇。
一、創傷因素
“創傷” 最初應用于病理學,后來發展到精神分析學以及精神病學領域。“心理創傷”是創傷理論中一個基本概念,它指某一事件或者災難給受害者心靈留下難以彌合的傷害。弗洛伊德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 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 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創傷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在美國,它尋求詳細闡述創傷的文化和倫理內涵。”創傷理論可以更好地解讀《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中啞巴的命運。啞巴面臨著愛情、生理和社會帶來的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最終采取極端化的方式去找尋終極的自我逃脫。
二、創傷成因
(一)愛情因素
愛情是廣為探討經久不衰的文學話題,正如有人把愛情視為“生活中的詩歌和太陽”,有人則視之為“甜蜜的苦酒”。這兩句似乎傳達給我們這樣的信息:愛情是幸福的然而又是痛苦的。對于啞巴而言,痛苦的愛情生活在一定程度對其造成傷害。啞巴的創傷來源于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就是妻子的不忠和背叛。“她是個比他年輕很多的女人,據說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從鬼混一詞可以推斷,妻子并不忠實于自己的家庭,追求生活的刺激和享樂。墨西哥人在下文再次被提及,“啞巴的老婆和一個大塊頭的墨西哥人坐在運動愛好者俱樂部里”,文中對于超出普通友誼界限的行為并沒有過多提及與定義,然而這看似無心的提及可以讓人發現妻子出軌并不是一個偶發性事件,而是一個經常上演的行為。愛情尤其是家庭的基本要素是雙方相互信任,妻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無疑讓啞巴內心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啞巴對于妻子愛而不得,只得把自身那種近乎本能對于妻子的關心和愛護轉移到鱸魚身上。這樣妻子和鱸魚之間就產生某種勾連與延續。鱸魚對于啞巴而言是難以言說的精神慰藉與寄托,是一種近乎變態的愛情指向對象。這近乎變態的愛情體現在對鱸魚“囚禁式”的保護與私有。“囚禁讓受害者與加害者長時間的接觸,產生一種屬于威權統治的特殊形態的關系。”保護似乎是出于男性對于女性天然的保護欲望,在此刻,鱸魚即為女性形象的化身。私有似乎指向作為丈夫的啞巴對于妻子的排他性與獨一性所屬權的愛情。啞巴擔心鱸魚跑掉,便“用柵欄把草場圍了起來,然后用帶倒刺的鐵絲電網把水塘圍住”。他不惜為此花掉所有的積蓄。啞巴對鱸魚如此偏執的看管與束縛,實際上是妻子遠離自己所造成的創傷的后遺癥——啞巴想竭盡所能困住他們,既指鱸魚,又指妻子。妻子已然遠離,那不如竭盡所能讓已在掌控的鱸魚留下來。啞巴對鱸魚的囚困為常人所不解,人們評論道“看他那樣,你會以為這個傻子是和那群魚結婚了呢”。結婚一詞含有明顯的暗示性意味,人們對于啞巴行為的評論恰恰說明,啞巴已經把鱸魚視為精神上的妻子——占有性和排他性。當洪水迅速蔓延過魚塘,大量鱸魚或是被水流沖走,或是游至他處時,啞巴“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見到的最悲傷的人”。啞巴失去鱸魚,不由得讓大家聯想到啞巴失去妻子的愛這件事。一個是實實在在的妻子,一個是精心培育并視為精神妻子的鱸魚。啞巴都曾為二者真真切切付出過,結果卻是無論是人還是魚,都最終出于種種原因沒能留下來。啞巴為此受到雙重打擊,心理創傷最大限度地凸顯出來,如同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讓啞巴徹底喪失理智和清醒,以至于“用一把錘子干掉了老婆,然后把自己淹死了”。大家可以這樣理解,啞巴把鱸魚視為自己的妻子,鱸魚逃離自己的控制,激發起啞巴被妻子背叛的創傷進而對其形成二次傷害。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啞巴因為先后兩次失去愛情而形成愛情創傷。
(二)生理因素
文學人物的生理缺陷如丑陋的面孔、聾啞都可能是一種象征,代表對世界的扭曲感知與投射。“生理缺陷自卑感可能縈繞著一個生理有殘障的小孩”,對于啞巴而言生理缺陷造成難以彌合的傷痛。啞巴渴望像正常人一樣與人交流溝通來表達自己的情感,然而遺憾的是他并沒有被賦予這可貴的能力。這樣來看,啞巴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失語他者。失語者往往無從發聲而不為人覺察和發現。我們可以大膽推斷啞巴并不是一開始就不能與人交流,至少在他童年的早期是可以的,后來不知何種原因造成現在這個狀態。啞巴意味著有口不能言,無法準確地向人傳遞思想動向,別人也就無從確切感知啞巴的所思所想。單單是失語已經足夠把人置于邊緣化,更何況啞巴還有一點聾。“我不覺得他是真聾,至少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么聾。”從這里可以發現,啞巴不是完完全全的失聰,還可以接收到些許的聲音,而這聲音來源或許是啞巴為數不多的接收信息渠道之一。大家試想一個生活在罩子中的人,眼睛被動隔絕光線,耳朵被動切斷聲源,這就是啞巴的真實生活困境,因而在很多時候啞巴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某種程度來說,啞巴是一個與外界環境進行單向互動的被動接受者。毫無疑問這一身份使他接收到的往往是嘲諷和愚弄。有一些人總是取笑啞巴,嘲笑他的做派。面對最為惡劣的挖苦,“啞巴總是不聲不響地忍著”。試問啞巴不想反駁無情的言辭嗎?答案顯而易見,因為幾乎沒有人愿意忍受來自他人的生理性侮辱和歧視。啞巴只是做不到用語言去反擊而已。畢竟想到和做到可以被視作一個理想和現實的相互關系問題。同時,我們可以觀察到作品對于啞巴外貌的描述,“一個長著皺紋的矮個男人,禿頭,四肢短而粗壯”“他的牙齒向內包住棕黃色的爛牙,這讓他看上去十分狡詐”。外貌是帶有直接的視覺感官與效果,往往影響對某個人的初步印象與判斷。尤其注意到的是“狡詐”一詞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這種情緒不僅是作者帶給讀者的直觀態度,更是周圍人對于啞巴的直觀判斷。啞巴因為丑陋粗鄙的外觀受到冷落和疏離,因為口不能言的缺陷受到排擠和譏諷。每多一次對啞巴的生理缺陷的玩笑性愚弄,啞巴就更進一步走向創傷。
(三)社會因素
社會是由一個個人組成的系統性整體,每個人都是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個人是社會中一分子,個人幸福感與獲得感很大程度來源于社會認可與需要。可悲的是啞巴所處的社會對他并不足夠寬厚與包容。啞巴所處的社會環境是造成其心理創傷不可忽視的因素。啞巴在社會中的身份是一家鋸木廠的清潔工。啞巴“永遠是一頂氈帽,一件卡其色工作衫,一件牛仔外套罩在連體工裝褲外面”。可見啞巴處在社會底層,從事著工資微薄且又臟又累的工作。啞巴的生活圈子似乎只有家庭、工作地兩點一線。文中提到啞巴唯一的朋友就是“我父親”。“我父親從來不取笑啞巴,至少我沒見到過”,這說明在我見不到的時候父親或許像其他人一樣對啞巴進行戲弄,又或許父親只是在我出現的時候,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啞巴。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個人真正走近啞巴的內心世界,傾聽其內心的真實感受。父親并不是啞巴真正意義上合格的朋友,這一點在文中鱸魚事件中得以窺探。父親并不尊重啞巴的真正意圖與個人尊嚴。“父親終于迫使啞巴去做那件事。父親說,就這樣了,他明天會過來做這件事,因為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這里的事情指的是啞巴需要去掉那些弱小的魚來保證其他魚的成長空間。對此啞巴的回應是一邊拽著自己的耳朵,一邊盯著地面。透過種種動作描寫,可以發現事實上啞巴對于此事的態度是深深的排斥和拒絕。正如文中提到的“啞巴從來就沒有說可以,他只是從沒說不可以罷了”。由此可以印證父親并不是啞巴真正意義上的好友,哪里會有一味施加自己想法給別人而毫不顧及其真正的所思所想的朋友呢?回到文章本身,啞巴為什么會拒絕清理出弱小的魚苗呢?啞巴似乎是把弱小的魚和自身處境聯系在一起。二者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是社會大環境中的弱勢部分,面臨著被驅逐的尷尬境遇。弱小的魚被清理出魚塘勾連著啞巴的潛在憐憫與同情。當然,這一暗含“叢林法則”的驅逐行為隱喻同樣弱小的啞巴被清理出社會,不免惹人深思。同時,大家通讀全文,沒有發現全文任何一處提到啞巴的名字,反復出現的只有“啞巴”二字來指代活生生的人。通常之下,人用名字來區別自己和他人,具有鮮明指代性。而啞巴這一代號毫無疑問是根據其顯著生理特征得名的,這就說明啞巴在人們心中與常人有別,長久的忽略與漠視以至于讓啞巴周圍的人忘記啞巴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停留在人們心中的反而是“啞巴”二字。用特征來指向具體的某個人,尤其是別人痛苦的短板,是多么諷刺和挖苦的事情。由此可見啞巴作為社會中失語的邊緣人群受到社會帶來的深痛創傷與打擊。
三、啞巴的反抗與影射意義
啞巴受到來自愛情、生理和社會的打擊形成創傷性記憶,表面上看起來啞巴并未及時做出反擊,但他時時刻刻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回應。“創傷患者大多是在個人的生活領域內來尋求從創傷解脫的方法”,啞巴也不例外。啞巴的愛情指向對象包括妻子和鱸魚。面對妻子的出軌行為,啞巴最終采取激進且極端的方式,“用一把錘子干掉了他老婆”。而面對來釣鱸魚的父親,啞巴“發出氣急敗壞的咕噥聲,搖著頭,揮舞著手臂”,因為鱸魚是啞巴精神上的伴侶。面對所愛之人和所愛之物先后的遠離,啞巴的反抗包含血腥和暴力。血腥在于用錘子殺死出軌的妻子,暴力在于搖頭揮手臂的襲擊性指向。當洪水沖走鱸魚——啞巴最后的精神寄托,啞巴的心血付諸東流,自此啞巴性格大變,不愿意與人交流共處。文中從客觀視角對啞巴的外貌進行描寫,似乎是啞巴周圍的人達成的認知共識,即在人們的眼里啞巴一直以來就是這個樣子。啞巴不在意人們對自己的看法嗎?顯然不是。很多時候啞巴反抗的方式是強有力的,常常會通過情緒傳達出來,正如父親說的“這人動不動就發怒”。在工作崗位上,卡爾碰掉啞巴的帽子,啞巴拿根粗棒釘對其進行追趕。在大家看來碰掉帽子或許只是一個玩笑或許是無心之舉。然而啞巴心中積郁已久的壓抑與克制爆發出來,拿起粗棒釘這一舉動恰恰說明啞巴的反擊是真真實實存在的。“啞巴現在每周曠工平均一到兩天”,面臨著被解雇的風險。這說明在之前啞巴是很少或者幾乎不曠工的,現在頻繁曠工就證實啞巴對工作本身和工作中的人產生厭倦,而厭倦是對事物反抗的表現之一。啞巴承受著愛情、生理和社會方面的鉗制,遭受著三重折磨與創傷。遺憾的是,啞巴在創傷之下無從建立安全感,喪失理性意識,最終沉沒于深暗的水塘,留下悲劇性的人生。表面上看來,雷蒙德·卡佛好似在書寫啞巴飽受折磨的人生,實際上是在讓大家從啞巴的悲慘境遇中,窺視到后工業時代大背景下底層民眾生活的真相。“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是非人道的、不道德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是異化的人。”男主人公啞巴的不幸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射現代大機器社會下人們生活的散亂與迷惘,勾連美國眾多生命的悲慘結局。啞巴的經歷不是偶然性案例,而是成千上萬的“啞巴”深受大機器時代人性喪失與錯亂而遺留下來的深深創傷的具象化縮影。
四、結語
通過對啞巴一系列的描寫,《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將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痛苦與掙扎呈現出來。啞巴深受愛情、生理、社會帶來的創傷,陷入無盡的絕望與迷茫,最后溺于魚塘。啞巴是社會失語形象的典型代表,經歷過不幸和反抗,卻仍然以悲劇收場。雷蒙德·卡佛用悲涼細膩的筆觸展現給人們后工業時代下的美國下層階級的庸碌生活及其悲劇性主人公啞巴,從啞巴的人生經歷勾連出美國后工業時代普遍存在的創傷問題,隱喻性地再現了民眾深受創傷破壞性的影響。同時,《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試圖告訴人們,要勇敢地直面過去、走出創傷經歷,踏上充滿希望與可能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