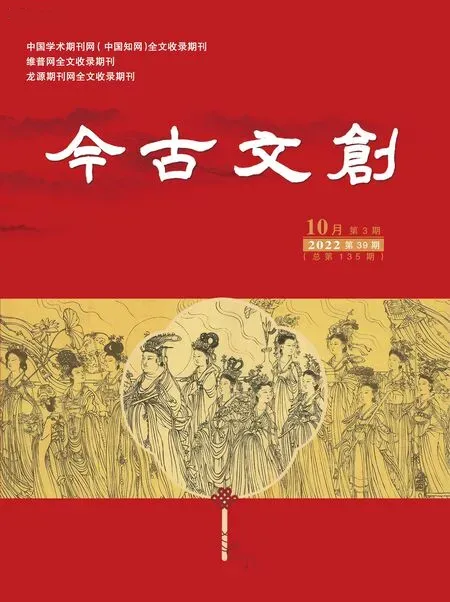本真性時代的兩條退路 : 《莊子》哲學研究
◎施浩東
(上海大學 上海 200444)
世界赤裸地橫亙在眼前,事物亦坦然地展示著自己,人居其中,卻不免茫然——存在無言,人當如何處之?不知道正確答案,不知道游戲規則,更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迎來終點,但哪怕如此,當人第一次發出此問,第一次試圖為世界尋求解讀之時,世界已為人而變。價值的齒輪轟然旋轉,將整體的世界分割為人文的世界,樸素的生存轉化為多彩的生活,寂靜的時間流轉為屬人的歷史——自然變成了一場找不到規則和盡頭的人生游戲。
有人試圖為自然、為社會建立絕對律令,他們相信自己知道規律是什么,相信自己的理論是人與世界關系的最優解,并開始為自己的學說公然辯護,要求他人服從于既定的規則。不同的人建立了不同的價值與規則,于是產生對抗與爭端,是非與真偽。又有后來者,由此是非對抗代代無窮,周而復始。
對于這一類玩家,我們不妨將他們歸納為對永恒與必然性的追求者。但此外,還存在另一類玩家,他們堅持一種“零視角”,反對這樣或那樣的律令,拒絕忠于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認為矛盾與偶然是這場“人生游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又以莊子哲學尤為典型。
長期以來,前者都在我們的歷史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我們都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解釋世界的一切,相信世界確實存有一種真實。但時至今日,科學與社會的發展正讓這個觀念似乎變得越來越可疑了。量子力學的發展動搖了傳統的物理學大廈,基于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我們永遠無法同時測量到電子的動量和位置,甚至能量E和時間T也是此起彼伏對我們永遠呈現出一種模糊的狀態。也就是說,在事物的深層狀態,如量子層面的微觀狀態,總是呈現出一種不符合邏輯的不確定狀態——對于必然的追尋似乎只是我們的一廂情愿,只存在于我們的觀念世界。更值得懷疑的是,生活世界變化萬殊,基于一定時間條件的律令永遠無法窮盡生活的變化從而暴露了其局限性所在。在智能時代的背景下,隨著信息的傳播和教育的普及,個體的話語權被前所未有的放大。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來自外界強加于人的社會模式——通過政治權威、長輩教誨、宗教等方式所強加于人——扼殺了人的獨特性、獨立性與創造性。他們要求從強加的社會角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回歸或者說創造出真實的自我意識。如查爾斯·泰勒所宣稱的,對傳統社會角色及倫理的反抗引導向了一個徹底的“本真性時代”。在本真性時代,政治和權力不再高懸于蒼穹之上主宰一切,人類對自由的向往,正是莊子哲學新的生命力所在。
因此,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重新討論莊子哲學不僅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早在兩千多年前,莊子就以其恢宏奇詭的文字深刻地批判了對絕對律令、絕對價值的一味強求所帶來的惡果,并為身處于本真時代的我們提供了兩條退路。
一、超然本性的喪失
在莊子看來,在人之初,人的本性是與道為一的,人類之初的至德之世是最理想的和平治世,此時的人類亦不必糾結于自身的意義問題。其后,隨著成心的形成,世人將完整的世界區分成了彼我、始末、是非、尊卑、勝敗等等分界,于是終日爭辯不休,鉤心斗角,勞心疲神地沉溺于無用之辯中,人也就背離了道,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淪落為有待的對象了。
對于成心,莊子說:“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這里的“成心”陳鼓應先生將之解讀為成見之心,但筆者認為韓林合先生的解釋更為恰當—— “完成了或成熟了的心,即有了完整的心里官能(認識、感受和意欲等)的心,而非特指成見之心”。韓林合先生進一步指出,“成心”正是是非之分的基礎,因此也可以稱為“是非之心”。正是在這種是非之心中,“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顯然,在這一段文字中,莊子將批判的筆鋒直指儒墨二家。正如前文所言,如果將莊子視為道家“零視角”玩家的代表,那么在這場人生游戲中,儒墨二家顯然是信奉律令并視自家之言為唯一真理的玩家代表。在莊子看來,儒門也好,墨家也罷,他們的理論都是不具有絕對性的,二家之爭辯皆不過是成心而已。換而言之,這種對人生游戲規則的尋求與辯護是無意義的,其結果只是成心四起,人淪入是非的無謂爭端中。
在《應帝王》的結尾,莊子用“倏忽鑿竅,七日渾沌死”的寓言的方式進一步揭示了這種來自成心的異化對人的本性的摧殘,莊子將這個故事放在七篇《內篇》等末尾,可見其重要性。如憨山德清所指出的:“此倏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對渾沌的解讀頗豐,一般認為渾沌指向混同、自然的原初狀態。莊子將其尊為中央之帝,亦是彰顯了莊子對這種狀態的推崇。原初的渾沌無有七竅,亦無須視聽,此時的渾沌是完滿的。但倏與忽并不這么認為,在他們看來,七竅視聽是人皆有之的,出于一種報恩的善意,倏忽為渾沌日鑿一竅,結果就是渾沌七日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殺死渾沌的過程并非是兇惡的魔鬼與刀兵,而是一種仁慈的善意。開鑿七竅的過程并非一日之短,而是用時七日,可見這是一個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簡單地說,原初的渾沌不具有七竅,因此也不具有人的種種是非區分,不具有屬文明人的社會性,而倏忽的目標就是把渾沌改造成一個社會性的成員——一如以儒墨為代表的規則尋求者將社會角色與規范強加于本真的人。當渾沌的改造被完成的那一刻起,原本的非社會性的渾沌就已經死亡了,同理,當社會改造完成之時,人也就與完滿的道相分離了。
《渾沌之死》作為一個悲劇神話,不言而喻的,莊子通過這個故事表達了對原初狀態無可避免地喪失的失落。從寓言的角度來看,這個喪失的過程正是人不可避免地走向文明的過程——對規則與智識的追尋讓人的單純被剝奪了,人的天真被扼殺了,人因規則而產生種種是非區分、步入文明社會,但代價就是完滿狀態的消失。顯然,莊子把這個過程視作是人的不斷墮落的過程,而面對這種墮落,如何消解也就成了《莊子》全書的主題之一。
在《齊物論》的一節中,莊子對這種喪失了本然之性的狀態做了更為細致的描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在莊子的視野里,喪失了本然之性而圄于成心之中的人是可悲的,他們整日鉤心斗角、形體不寧,沉溺在是非與所為所構成的牢籠之中,種種情態日夜交侵卻又不知所以。他們的生命失去了生機與意義,他們的心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更可悲的是,大多數的人津津有味地過著麻木不仁的、喪己于物的生活,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的生活狀態是缺乏意義的。
那么,既然對規則的尋求、對是非的執迷、對經驗的迷信等種種成心造就了人生的種種困境,從莊子的視角出發,我們又當如何超越成心,復歸于道而得到解脫呢?
二、退路其一:齊“物論”
如前文所言,隨著現代社會的深入發展,人類愈發感覺主流的思維模式造就了種種人生困境,以儒墨二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永恒的追求,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絕對律令的向往反而使社會危機常常發生;相反,肯定相對,以一種“零視角”游心于人世間的莊學反而在這個本真時代為人類打破主客樊籠提供了一盞明燈。在《莊子》一文中,他向我們提供了兩條退路,以使人消解成心,從而復歸于道。
莊子向我們闡釋的第一條退路就是齊“物論”。既然人心中的物我、是非、真偽、善惡、貴賤、生死等種種成心造就了人與道的分離,使人的本真被異化了,那么,要回歸于道,首先要做的就是齊“物論”,也就是放棄被社會規則所蔽的種種是非俗見,從規則的建立者給人強加的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在莊子看來,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任何形式的絕對是非區分界限可言。
在《齊物論》中,莊子對齊“物論”做了詳細的說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在莊子的論證中,人首先將彼此絕對地區分了開來,在彼此之上建立起來是非之別,并以此之是來否定彼物之非。但是,這些是非彼此都是相對的,彼此都是相對而生,彼此隨起隨滅,方可方不可。莊子得出結論,彼與此實際上是相同的,彼就是此,是就是非。為此,莊子要求從這種是非區別中超脫出去,將這些都看作是相對的甚至虛假的。若能做到這一點,也就是達到了“明”的境界。
對此,勞思光先生的闡釋頗為精彩,“一切理論系統相依相映而生,又互為消長,永遠循環;如此,則理論系統之追求,永是‘形與影競走’,自溺于概念之游戲中。倘若心靈超越此種執著、而一體平看,則一切理論系統皆為一概念下之封閉系統,彼此實無價值之分別。”
正是因為封閉系統的概念實際上沒有價值分別,因此,在莊子看來,以儒墨二家為代表的規則建立者把自己的理論視作唯一的是非標準并在此之上建立道德體系、社會規范的做法是極其危險與有害的。而如果一個人能夠忘掉是非分界,自然就會把社會名聲看作是桎梏而已,更不會陷于對其的追求而喪失本真了。也就是“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
通過齊物論,莊子成功地消解掉了規則建立者們的塑造的理論基礎,打開了種種道德規范和社會制度對人的自我的禁錮,為人的心靈找到了一個通往逍遙的避風港。
但對外部規則的禁錮下解放帶來的結果并不是唯一的,一方面,這種解放讓人的本性得以舒展,人的自我得以張揚,但另一方面,這種解放的副贈品往往是對自我的沉迷。一如德安博對反諷主義者的闡釋,當他們看透了規則、是非中的偶然性與相對性,從社會約束和道德律令中抽身而去,將自身與社會角色相分離,他們將懷疑一切的合法性,其結果就是從社會領域退回到個人領域。從正面來說,這種強烈的個體意識帶來的是強烈的自我創造的需求與實踐,這種力量對于一個現代的、成熟的民主政治團體而言,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但從負面來說,這種過度高昂的自我意識往往將他們推向社會規則的對立面。顯然,這種嘗試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對于莊子所處的年代而言,戰亂頻繁,社會體制尚未成熟,對自我意識的過度渴望并不利于個體的生存,更難以在那個艱苦的年代保持開朗與從容。
事實上,在很長的時間里,許多研究者認為莊子式的角色是作為烏托邦式的反諷主義者,如德安博語,“許多研究者認為這種道家的模范是一種‘承受外部壓力、只對自己真實、專注永久自我探索’的角色,它強大到足以在可能異化的社會中形成一種身份,從而實現‘自我創造’。”
但顯然,莊子筆下的人物并非是如此的“強者”,一如他在《德充符》中塑造的諸多形不全之人、在《人間世》中塑造的“無用之木”,恰恰相反,莊子筆下的道家圣賢往往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現的。這種矛盾形象的塑造正是莊子向我們展現的第二條退路——對自我的消解。
三、退路其二:吾“喪我”
在莊子的筆下,有許多寓言的內容都是與個體面對殘暴的、險惡的社會權力的危險性相關的。如在《人間世》中,莊子就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顏回向孔子辭行,他準備訪問衛國,以自己所學去改造衛國的殘暴君主。此時的顏回可以說代表著一種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他并非被上級指派,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力圖去改造世界。但這種嘗試是危險的,面對顏回的請行,孔子的答復是“若殆往而刑爾!”從莊子的角度來看,顏回顯然已經被儒家的規則道路所束縛,通過對“善”對追求來肯定自己的社會角色,他力圖以儒家禮義去改變衛君的做法本就已經落入了是非取舍的有待境界。但這個問題在這里并非是我們的首要關心對象,我們更關心的是,即使是那些看透了是非規則的相對性,從而從社會角色中解脫出來的人,當他們從外反內,專注于自我,以自我對抗外部壓力之時,他們面對的困境實際上和出使衛國的顏回是相似的——個體的脆弱讓他們面對社會權力處于極危險的境地。
借孔子之口,莊子給出的答案是“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首先,孔子要求放棄聽之以耳,而是聽之以氣。對于這個氣,陳鼓應先生將之解釋為“心靈活動到達極精純的境地。換而言之,‘氣’即是高度修養境界的空靈明覺之心。”通過這種境界,最終產生一種“虛”的心境。
對此,顏回問道,“未始有回也”的狀態是否就是“虛”的境界。對此,孔子予以了肯定。也就是是說,對于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而言,面對個人與社會的沖突而招致的危險境地,他們的答案是對主體自我的主動消解,可謂是自我的“虛”。
然后孔子進一步解釋了一個完成了心齋的,或者說虛己的人是如何行動的,“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在這種狀態下的人就像是一面鏡子,能夠適應任意一種社會境況,扮演任意一種社會角色,他們隨環境而采取適當的行動,而不被危險所縈繞。通過“心齋”的虛己,他們能夠從容地游心于這個世界。
在《齊物論》中,莊子將這種虛己的觀點表達得更為清晰,也就是開篇所提到的“喪我”——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對于“吾喪我”,陳鼓應先生將之概括為“摒棄我見”,也即是要通過將成心之我、偏見之我的摒棄,來達到忘我、與萬物同為一體的本真狀態。
在這里,“吾喪我”之“我”實為主體之自我,亦即自我中心的觀念,所謂“喪我”也就是要取消自我中心主義,消解掉主體之自我,從而避免以己之所是為是,以彼之所是為非,自以為是地將自己與他者隔絕開來的做法。
自我中心消解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自我與社會角色間矛盾的消解——他們不再為了自我創造而對抗社會,而是從容地悠游于社會角色、社會規則之中。我們不能因此而斥責他們虛偽,事實上,他們就像是一面鏡子,其本身可以說是空無一物,卻又真實地、不加修飾地反映出他所面對的一切。
更準確地說,通過“喪我”,莊子建立了一種頗為“空虛”的角色,他們不追求功名利祿與是非規范,忘我地如水面一般隨風而動,悠然自得在社會規范中穿行,灑脫地在各個社會角色與規則間切換。德安博將這類角色稱之為“真實假裝者”,即與真實自我無關的、完全偶然的社會角色扮演者。對這個觀點,筆者保持認同。
事實上,對于這種“喪我”者對于不同社會角色的扮演、適應能力,《莊子》書中多有暗示,如《大宗師》中,“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莊子以夸張、吊詭的手法隱喻了“喪我”者在面對環境變化而切換社會角色的能力——若化為雞,就打鳴報曉,若化為彈弓,就打鳥捕獵,若化為車馬,就乘它而去。所謂“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火不熱,沉水不溺”,正是莊子對這種境界的藝術性描述。
四、總結
總的來說,莊子通過“齊‘物論’”與“吾‘喪我’”兩條退路,幫助我們在這個本真時代保留了復歸于道的可能。兩條退路又互為遞進,從而構成了這種理想人格的多維性。可以說,莊子將人分成了三種,我們可以將之分為“成心者”“齊物者”和“喪我者”三個境界。
“成心者”,也就是常態意義上的大眾、凡人,他們被種種外界強加的是非、真偽、彼我規則所束縛,終身籍籍于成心之中,迫切地把外在社會人格內化于自身卻不知自身早已與道背離,在被異化的道路上愈行愈遠。這種人在莊子看來最為可悲。
“齊物者”,也就是能達到齊“物論”境界的人,他們以相對性消解了外界是非界限的絕對性與唯一性,往往轉而追求自我的真實性和創造性,從而從種種社會桎梏中超脫出去。其結果常常是自我意識的高揚,這種人面對強勢的社會權力是危險的。
“喪我者”,這種人建立在“齊物者”的基礎之上,或者說只有“齊物者”才能成為真正的“喪我者”。他們既憑虛己以遨游于世,從容地游走在權利的刀鋒之間,又能從成心桎梏中解脫而去,他們無為而又自然,是真正的圣人、真人與至人。
不同于我們歷史上的先輩們,身處于“本真性時代”,時人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外在強加的主流價值觀、文化環境、社會要求等所帶給人之本真的種種異化,隨著互聯網和智能設備的發展,個體的話語權在空間上被空前放大,每個人都有機會在虛擬空間里充當信息的造物主形態,其所帶來的諸如狂妄自大、執迷不悟、肆意地以一己之見對他人口誅筆伐等等不良后果更是屢見不鮮。那么,莊子通過文中的兩條退路像我展示了一種“關于如何以沒有目的的方式巧妙地漫游于世間的哲學”。
一方面,這種哲學幫助我們從狂轟濫炸的信息狂潮中暫時抽身而去,避免我們的本真被其裹挾而死亡。另一方面,這種哲學也至少告訴了我們,如何周旋于社會處境中——如同一面鏡子——從而免受傷害。
①???漢斯·格奧爾格·梅勒、德安博:《游心之路:莊子與西方現代哲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5頁,第50頁,第190頁,第193頁。
②查爾斯·泰勒:《世俗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536頁。
③⑥⑧⑨?????????郭象、成玄英:《莊子注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2頁,第34頁,第27頁,第35頁,第113頁,第73頁,第80頁,第81頁,第81頁,第24頁,第143頁,第126頁,第290頁。
④⑤翰林合:《虛己以游世——莊子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第22頁。
⑦憨山德清:《莊子內篇注》,香港佛經流通處1997年版,第299頁。
⑩勞斯光:《中國哲學史》,三民書局1981年版,第216頁。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40頁,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