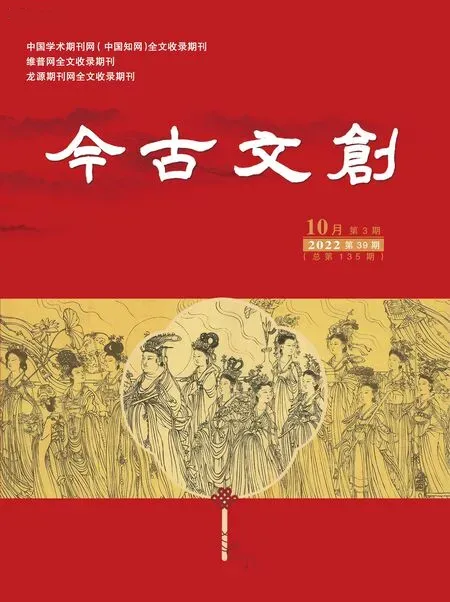論《茶花女》與《羊脂球》中女主人公悲劇命運的來源
◎樓玲妤
(浙江樹人學院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小說《茶花女》講述了巴黎上流社會一位有名的交際花瑪格麗特與貴族公子阿爾芒從相識、相戀,最后被迫分開的一段曲折凄婉的愛情故事;《羊脂球》講述了妓女羊脂球與一行與她社會地位差距懸殊的人乘坐同一輛馬車從敵占區逃亡途中發生的故事。本文將從兩位女主人公所處的父系社會、自身的性格特點以及理想追求這三個方面比較分析她們悲劇命運的來源。
一、父系社會
(一)外表出眾
在父系社會里,女性是否美麗取決于男性的審美愉悅程度,男性力圖把女性美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之中,女性之于他們,只是生理層面的物品,是性對象,因而女性的容貌與身材成了美麗的基礎條件。
《茶花女》中,以男性視角對瑪格麗特進行的外貌描述正反映了這一點,“她身材頎長,窈窕得有點過度……”“在一張艷若桃李的鵝蛋臉上,嵌著兩只黑眼睛,黛眉彎彎,活像畫就一般……由于對肉欲生活的強烈渴望,鼻翼有點向外張開……皮膚上有一層絨毛而顯出顏色,猶如未經人的手觸摸過的桃子上的絨衣一樣。”處女般純真的面孔、性感的身姿,完全符合當時男性對女性美的創造要求,也是瑪格麗特能成為巴黎名妓最基本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她悲劇的最初來源。
而《羊脂球》中也有類似對伊麗莎白的描寫,“她的臉蛋兒像一個發紅的蘋果,一朵將要開花的芍藥;臉蛋兒上半段,睜著一雙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內部映出一圈陰影;下半段,一張嫵媚的嘴,窄窄兒的和潤澤得使人想去親吻。”說明羊脂球的美麗是天然的,并不是通過精心打扮而顯示出來的,正因如此,她才被普魯士軍官看上而最后不得已委身于他。
(二)特殊職業
父系社會幾乎將女性極端地劃分成了“貞女”和“蕩婦”兩種類型。
《茶花女》中,阿爾芒的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無法自拔地愛上了瑪格麗特,轉而帶著對妓女的固有偏見,要求瑪格麗特為了阿爾芒的前途以及他們整個家族的聲譽著想而主動離開阿爾芒,“您愛阿爾芒,您就只能用這種方式向他證明您的愛情,即犧牲您的愛情,成全他的前途”,并且以重操舊業為借口讓阿爾芒誤以為她是由于放不下錢財,貪戀原先巴黎紙醉金迷、尋歡作樂的生活才離開的,最終導致瑪格麗特在阿爾芒不明原因的謾罵和詆毀聲中含淚而死。這體現了在父系社會下男性對女性的壓制,是阿爾芒父親的出現打破了瑪格麗特因被阿爾芒打動而想要重新開始平凡生活的夢;男性還以自己的偏好衡量女性的貴賤,而劃分的標準往往依賴于表面現象而不是女性身上更加深刻的品質,阿爾芒父親否定的不單是瑪格麗特個人,而是妓女這一群體,他固執地認為,“上等人和情婦之間只能是買賣關系,絕不能產生真正的感情,不然就會玷辱門楣,斷送前程。”
《羊脂球》中對當時社會看不起妓女的現象更是通過幾位貴族太太的言行舉止表現得淋漓盡致,“好像她們覺得,在這個不知羞恥的賣淫婦面前,她們必須團結一致,把她們做妻子的尊嚴顯示出來才行,因為合法的愛情總是高于放縱的私情的”,她們不但看低羊脂球,還聯合起來在私下里辱罵她,認為她是婊子,是社會恥辱。如果說前面《茶花女》的部分展現的是父系社會下男性對女性意志和行為的絕對操控,那么從這里人們看到了那些依附于男性存在的上流女性身上的自私和冷漠,她們用“男性的語言、觀點和思想概念、評判標準來攻擊或詆毀女性。”
(三)抗爭的不徹底性
起初的瑪格麗特由于長期在公爵的包養下生活,聽慣了花言巧語、看盡了人間冷暖,潛意識里早已默認自己是男性隨時可以拋棄的玩物,本身放棄了自己作為女性在男權控制下的抵抗。而阿爾芒深情地告白和無微不至地照顧喚醒了她心中對真愛的憧憬和向往,她為了愛情背上沉重的債務,不惜變賣貴重物品離開巴黎跟隨阿爾芒到鄉下重新開始生活,勇敢追求生活與愛情自由的行為,體現出瑪格麗特身上的抗爭性。但在后來面對阿爾芒父親無理的要求時,她并沒有顯示出頑強的抵抗,而是以舍棄自己的幸福為唯一選擇,最終維護了阿爾芒的前途及其家族的聲譽。這些情節反映出在父系社會下“母系氏族因沒有形成女性可以傳承的文化系統,沒有形成完整的意識形態,即使有部分象征性標記存在,也只能以零星的或者是隱形的方式散落在父權文化系統中的邊角,被后來者忽視。”瑪格麗特不但肉體不受自己掌控,在精神上也顯示出了屈從于男性意識的傾向,可以說她忍辱負重的犧牲精神有余,但堅決抗爭的戰斗信念不足,因此,在阿爾芒父親的威權話語面前,只表現出了短暫的、不徹底的抗爭。
與茶花女相比,羊脂球的抗爭精神則多了些堅決性,不僅體現在她偉大的愛國情懷與高貴的民族氣節上,也表露于她面對他人辱罵以及拒絕男性時的態度。羊脂球的反抗在文中第一次出現于聽到貴族太太對她的謾罵后,“她以大膽而極富挑釁的目光掃視了她的這些鄰座”,她的行為隨即就取得了效果,“于是車廂內馬上肅靜下來”。
與馬車上的其他人不同,她是由于反抗普魯士士兵的蹂躪,幾乎掐斷了那人的脖子,為了避免被捕才選擇逃亡,而當民主黨人高尼岱之后的痛罵傷及了她崇拜的拿破侖皇帝時,她“面色變得比野櫻桃還紅,氣得說話也結巴了”,毫無畏懼地予以了反擊。
當高尼岱趁著夜色想要猥褻羊脂球時,他被她結結實實地打了一拳;當得知普魯士軍官想要占有她后,她堅決地拒絕了,回到車上“臉漲得通紅,氣得說不出話來”。然而作為本身就缺乏話語權的女性,加上妓女的身份,在面對男性的絕對權威與眾人的壓迫時,羊脂球的反抗又顯得單薄無力,最終還是走向了妥協。
二、性格
(一)善良
瑪格麗特雖然因現實所迫從一個美麗純真的農村少女淪為了權貴們的玩物,但她身上“來自下層人民的純樸善良的精神光輝始終未被泯滅。”瑪格麗特看著阿爾芒為了報復自己故意牽起另一個漂亮妓女的手而感到傷心欲絕,但卻始終都沒有告知阿爾芒實情,任由他誤會。瑪格麗特不愿知道實情的阿爾芒會又一次不顧一切地要和她在一起而誤了自己的前途,也不愿讓他記恨于父親。病痛的折磨,相思的苦楚,難言的委屈,她把一切難熬的苦難都留給了自己。
瑪格麗特的善良還體現在她典當首飾支付她和阿爾芒的生活費卻不準別人告訴他;又像文本最后寫到,“看見哥哥回來,她笑容滿面,這個純潔的姑娘一點也不知道,僅僅為了維護她的姓氏,一個遠方的妓女就犧牲了自己的幸福。”瑪格麗特在自己和阿爾芒妹妹的幸福之間,成全了后者。
與羊脂球坐在一輛車里的都是體面的上層人士,相比之下她只是一個身處底層、受人歧視的妓女。途中馬車因風雪耽誤了行程,附近又沒有飯館和小店,沒有事先準備食物的人那時都已饑腸轆轆,開始惺惺作態搭訕和暗示羊脂球。羊脂球面對一車看不起她的人依然表現出了她善良的本性,慷慨地拿出了自己本來預備用作三天旅途中吃的食物和大家分享,以德報怨。然而這只換取了其他人短暫的和善,隨著食物逐漸被瓜分殆盡,很快人們對她又恢復了之前的冷淡。
當普魯士軍官以過境為要挾提出要羊脂球陪自己過夜的條件時,她成了所有人平安離開的關鍵,但她毫不猶豫地拒絕讓馬車上的人憤憤不已,因為大家都很自私,害怕她這種行為會引起災難,并利用她單純赤忱的愛國之心以種種偉大的理由規勸她前去。然而眾多女英雄的感人事跡都沒能使羊脂球動搖,直到修女以著急前去救助生天花的法國士兵為理由打動了善良的她,最終應了普魯士軍官的要求。此外,過程中車上的其他婦女在心里暗自嫉妒和較量為什么被叫的人不是自己的心理,體現出她們“披在身上的那層薄薄的羞恥布只能掩蓋她們的外表”,在身份地位和現場表現的反差對比下,更凸顯出羊脂球的坦蕩和上流人士的虛假。
善良的羊脂球不愿一行人遭難,更不忍心讓眾多的法國士兵得不到救治,強壓著自尊把自己獻給了普魯士軍官,可當她第二天回來時,那些說過不會忘記她的人們全然換了一副模樣,所有人都裝作不認識她,就算是她主動打招呼也無人回應,甚至像躲避災禍似的避開她。到中午大家都拿出了從旅館中帶出來的食物開始享用,根本沒人顧及由于匆忙上車什么都沒有準備而餓著肚子的羊脂球。
羊脂球的兩次犧牲并沒有得到上流人士的感謝,也沒能喚醒他們泯滅的良知或拯救他們自私的本性。羊脂球最動人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并沒有因為自己被傷害而反過去傷害別人,她一次又一次地被犧牲,一次又一次地怪自己傻而感到氣憤和羞愧,她并不是不知道與自己同車的是怎樣一群丑陋、虛假的人,但當選擇再次來臨之時,依然堅定地選擇站在良善與奉獻的那一方。
(二)軟弱
瑪格麗特的軟弱在“抗爭的不徹底性”的部分中已經可見一斑,至于羊脂球,她此前已經慷慨地與大家分享過食物,但當自己饑腸轆轆卻沒有人理睬她時,她理應可以要求其他人和她分享食物,但是她并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在車廂中悲憤地哭泣,從這點上看,羊脂球的性格中也存在著軟弱的一面。
(三)自卑
瑪格麗特是由于出身貧苦,流落巴黎而被逼為娼,并非真的喜歡性帶來的熱烈與快感,但在小說里她的話語卻處處透露出她對自己身份低賤、只能任人擺布的觀點的認同,“我們不再屬于自己,我們不再是人,而是物。他們講自尊心的時候,我們排在前面;要他們尊敬的時候,我們卻降到末座。”所以在選擇面前,瑪格麗特自動放棄了她作為女性天然擁有的選擇愛、追求愛和享受愛的權利而成全了別人。另外,也正是自卑導致了她的軟弱,也許從根本上瑪格麗特就不認為她與其他所謂的正常女性一樣可以去競爭以守護自己想要的東西。
羊脂球愿意相信“只要動機純潔,行為總是可以被原諒的”這一說法,根本原因是她內心有因妓女這一職業形成的罪惡感,她認為自己是有罪的,渴望通過善舉使上帝寬恕她的過錯,進行自我救贖,這點從她在旅途被困時還要去參觀嬰兒洗禮的行為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三、理想追求
茶花女追求兩性關系的自由與平等,這是她對于真正美好愛情的基本訴求。長期依靠出賣肉體獲得公爵的錢財來維持生活的瑪格麗特清醒地認識到了男女地位的懸殊差距,她把男性當作自己躋身于上流社會的提款機,而她也只是男性釋放性欲、滿足虛榮心的工具,知道自己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被無盡物化卻無力改變。因此在過去的時間里,瑪格麗特認為“如果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我反而會死去,現在支撐著我的,就是我現在過的這種充滿狂熱的生活”,所以她肆意揮霍著法郎,用各種名貴物品來逃避和填補自己精神世界的空虛。
而阿爾芒的出現——一個會真心愛護她的人,他善良體貼,會悄悄打探她的病情;看到咳嗽不止的她會用乞求的語氣希望她保重身體;甚至會因為她的病痛落淚。這讓瑪格麗特擁有了拋棄過去,走到物質生活的對立面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勇氣,并向阿爾芒提出要“信任我,聽我的話,而且不多嘴”這樣的要求,說明她認為雙方地位平等、互相尊重是開展一段健康的戀愛關系的基礎。
羊脂球則有著與茶花女全然不同的理想追求,愛國主義情懷是她行動的底色。小說的創作背景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法國軍隊在遭到普魯士士兵的強力打擊后,不久便宣布投降,很多人由于看不到希望而選擇棄城逃跑。羊脂球因為無法忍受侵略者的野蠻行徑及此帶來的恥辱,差點掐死了一個進駐她家的士兵,無法在當地繼續生活而被迫逃走,相反,與她同行的九個人則都是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離開。為世俗社會所不堪的妓女,卻是馬車上唯一一個因為與侵略者抗爭而不得不離開敵占區的人,這使那些表面上風光無限的上流人士黯然失色。
此外,羊脂球認為自己多少代表著祖國而在普魯士人面前顯露出嚴肅高傲的氣概,也顯示出她強烈、自覺的愛國意識。她拒絕民主黨人高尼岱的求歡,氣憤于普魯士軍官的無理要求,體現了一個普通的法國人真摯的愛國情懷和高尚的民族氣節。
茶花女與羊脂球都生活在畸形的環境里,由于妓女身份而不受人尊重,不同的是前者在絕望中追求愛情自由,后者則在毀滅中堅守民族大義。
四、結語
正如《茶花女》里所說:“人世間的這些悲劇,卻往往又是在維護某種道德規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茶花女和羊脂球都生活在男性具有絕對權威的社會下,在那個物欲橫流的年代里,因為身份的特殊性而處處受人歧視,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又由于她們內心始終堅守著美好的人生理想,表現出的善良、軟弱、自卑的性格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產生。
朱立元先生曾這樣評價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他不僅指出了悲劇對于人的靈魂的凈化作用,而且抓住了人們在欣賞悲劇時所經歷的由消極情感(憐憫與恐懼)到積極情感的轉化過程。”茶花女和羊脂球所遭受的痛苦的根源并非她們的罪惡,而主要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身份,這兩部作品在創作時間上雖然相隔了32年,卻同樣展現了在父系社會下性格相似的兩個妓女心中的理想被殘酷現實反復打磨以致破滅的悲劇性遭遇,不僅使人產生了對她們命運的深切同情以及對黑暗現實的痛恨之情,與此同時,更激發起了與邪惡勢力抗爭的勇氣,因此它們才能在時間的長河里顯示出經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