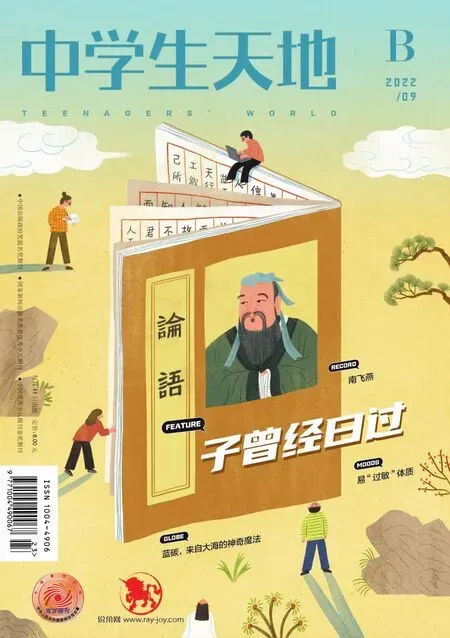孔子的財富觀
文/劉正平(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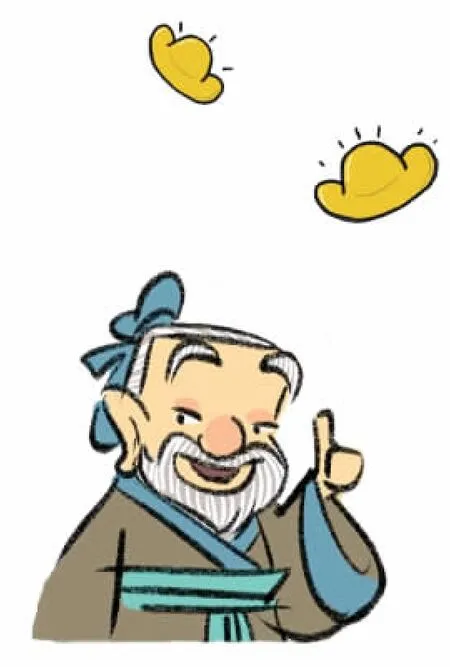
在我們的印象中,儒家諱言“富貴”。《孟子·滕文公下》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似乎受孟子這一論述的影響過深,古代的讀書人很少公開談及對財貨的追求,那些視富貴如浮云、輕財富如糞土、樂善好施的精神往往受到追捧和贊美,就像杜甫所說:“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元末明初施耐庵的《水滸傳》里,宋江之所以能夠籠絡人心,就在于其慷慨好義、仗義疏財。清代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里,鮑文卿的一句“須是骨頭里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也令人贊嘆其有骨鯁之氣,對不義之財嗤之以鼻。與此相應的是,古人形成了一種扭曲的財富觀,那些主動追求財富或者熱衷于談論財富的人和事往往受到輕視。士農工商,商居末位,整個古代社會形成了賤商的觀念。
《論語·里仁》記載,“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述而》也記載,“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些材料都是強有力的佐證,表明孔子正面肯定富貴是“人欲”,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作為孔子財富觀的又一佐證,《史記·孔子世家》有明確的記載:魯定公五年,季孫氏家臣陽虎囚禁了季桓子。孔子認為,魯國的國政完全處于混亂狀態,臣子以下犯上,秩序顛倒,所以拒絕做官,退而專心治學。這就是當時孔子所說的“富貴不可求”的狀況。
關于如何對待財富的問題,孔門弟子子貢最有代表性。現有的研究成果認為,子貢在孔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他解決了孔子學說傳播過程中的資金問題。“在孔子時代,確實是作為富商的子貢‘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他不僅資助孔子及弟子周游列國,竭力捍衛和傳播孔子學說,維護孔子形象,而且因為他的入門,那時有許多向學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圍。”(楊朝陽《子貢在孔門弟子中的特殊地位》)孔子是反對子貢做生意的,他贊賞顏回安貧樂道的生活,但現實畢竟是殘酷的,所以顏回和子貢的最終命運也大相徑庭。孔子曾感嘆:“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不聽話而熱衷于做生意的子貢,最后不但生活無憂,還是孔門弟子中對孔子感情最深的一個,多次幫助孔子和同門解困。他為孔子守墓六年,是孔子所主張的“富而好禮”的典范。
子貢曾經和孔子討論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由此可見,孔子主張正大光明地追求正義之財,但在財富不可求的情況下,也要能夠安貧樂道。子貢曾啟發孔子:“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心領神會:“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可見,孔子也想將自己“賣”個好身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