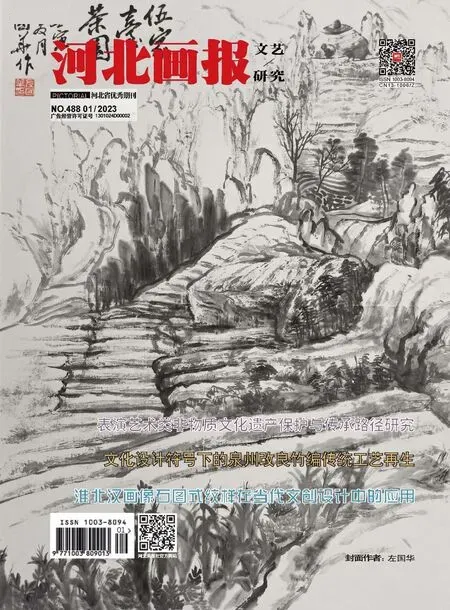文化設計符號下的泉州改良竹編傳統工藝再生
莫芷姍 許瀚櫻 鄭黎
(華僑大學美術學院)
一、泉州改良竹編發展演變
(一)傳統竹編的歷史淵源
據考證,距今兩萬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先民以竹為材編織器物。而后,貴重金屬的少量出現和竹子量大價廉,導致器物使用出現階級分層。竹編工藝制品則作為一種民間工藝品存活下來,且被廣泛應用于生產、生活等方面。
唐宋時期,泉州竹編工藝盛極一時。隨著商品經濟逐步發展,從事竹業生產的手藝人日益增多。據史料《福建通志》寧國府記載:“竹,有數十種郡邑資之為利。”直至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泉州竹編工藝品為當時的一種重要出口貿易商品之一,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現今作為閩派竹編的代表,泉州瓶罐、永春漆籃的竹編器物最為經典,其造型古樸,色調濃重,編織紋樣粗獷典雅,功能上以實用為主。
(二)改良竹編的發展與困境
改革開放后,李碩卿先生汲取傳統國畫中的藝術風格以及出土文物器皿的造型特點,增強了其藝術性和表現力,獨創出“泉州改良竹編”。不同于傳統竹編的編織形式,泉州改良竹編是在竹編胚體的基礎上融合了多種編織技法,運用鑲與編、插在竹編胚體上綜合表現出了多種立體編織紋樣。竹編藝品在上色及磨光后,紅與黑雙層顏色的竹篾編織突顯出有層次與明暗分化的紋樣。泉州改良竹編技法形式逐漸發展并綜合多變,制作出的竹編品類也逐步豐富。
九十年代后期,泉州改良竹編步入了又一創新的階段。筆者曾走訪非遺傳承大師凌文彬,其改良竹編藝品《花木蘭》的創作是改良竹編發展歷程上的跨越式邁進。在改良竹編藝品《花木蘭》中,凌文彬大師運用竹皮和竹簧兩種材料來交叉編織,一黃一白的顏色交織更加突出面部立體感。作品中為更加立體呈現花木蘭面部細節所運用的編織技法也各有不同,凌文彬大師運用了8種改良竹編的編織技法,如鼻梁運用“小人字花”編織;眼珠運用“一起一落”編織;眼簾是由“十字花”和“三條盤”組成;頭發運用“大人字花”編織;領子運用“三葉旋花”編織,領邊是“鰻魚骨”;臉則是“六角旋紋隆點花”編織而成,粗中有細的編織技法立體呈現出人的臉部特征。凌文彬大師自述:“頭部的制作歷時7年才完成,但創作過程中最大的阻礙還是資金的緊缺,竹編編織后輩人才的流失。”凌文彬大師曾嘗試將已被市場淘汰了的“竹編搖籃”由大改小,使其從日用品的體量轉為工藝品的體量。作為改良后的工藝品“小搖籃”,被賦予了新一層的精神文化含義。但在現今文化消費市場中仍處于“小眾”地位。
綜上所述,筆者在走訪與調研中總結出以下幾點泉州改良竹編的發展困境:其一,資金鏈斷裂,無法形成一個閉合的循環發展路徑。第二,工藝品的創作生產脫軌于當下消費市場的發展趨勢,對于當下文化消費市場認知相對不足。第三,因儲備人才的不足,改良竹編工藝品的完成時間成為最大的不穩定變量。
二、泉州改良竹編的符號價值
(一)改良竹編中的文化符號
符號學家查爾斯·莫里斯認為:藝術品是一種類象征符號,其獨特性在于符號載體本身就傳達出價值。某些類象符號載體直接蘊含著價值特征,符號功能和價值功能這兩種價值特征是一致的。價值特征以直接與間接兩種方式被感知,間接感知即為符號功能所意指的價值特征,而直接感知是符號自載體所蘊含的價值特征。
泉州改良竹編多以獸類和人物作為創作主體。例如改良竹編藝品《花木蘭》的創作是泉州竹編從傳統日用品類轉化為工藝品類創作的一次跨越,象征泉州改良竹編中日用符號至藝術符號的轉化,突出改良竹編藝品的符號功能被直接感知特征。竹編小搖籃的改良創作凌文彬大師曾敘述到:“傳統的竹編搖籃代表的不僅在結構上是閩南竹編手藝人的智慧產物,傳統的竹編搖籃對于老一輩人在情感上更多的是一種思念父母以及家鄉情懷的歸屬寄托。”因此決定將傳統的竹編搖籃的體量由大改小,將原本為嬰兒用品的實用性價值轉化成具有意指符號價值的竹編工藝品。而其中的意指符號價值,蘊含著改良竹編小搖籃被創作者重新賦予不同的情感語言,如作為新婚賀禮則祝福著新人早生貴子,作為新居喬遷之禮則寓意著家業興旺,作為送別親友的海外僑居之禮則寓意著順風順水、不忘家國的情懷。
雖然改良竹編小搖籃作品的創作已局部脫離了其日常用具的象征性特征,即作為嬰兒用品的日用符號,僅是保留外觀上的一些特有的符號特征。但僅僅改良竹編小搖籃的體量,想要達到提升消費者對其文化符號產生認同還效果甚微。改良的竹編小搖籃缺乏清晰的功能定位,使其對于消費者的直接感知價值過于單薄,且在文化消費市場中竹編工藝品定位相對模糊,缺乏清晰鮮明的設計符號特征,是其難以拓寬其在消費市場中發展的客觀因素之一。

圖1 凌文彬作品·花木蘭(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2 凌文彬作品·小搖籃(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二)改良竹編的設計符號植入
傳統的泉州改良竹編通常的創作多以“符號載體”形式表達,作品自身具有獨特的審美性和獨立性,同時改良竹編作品中藝術符號所表達的情感語言一般以間接或直接的表現形式使觀者感知。改良竹編小搖籃是創作者將日常符號元素轉化為藝術符號載體的一種嘗試,改良竹編小搖籃作為文化商品在市場上銷售,目的是為了引起消費者情感共鳴和情懷認同進而產生消費行為;但僅從體量的變化以及創作者賦予作品的情感語言,難以適應現下的文化消費市場。
學者吳佳醍提出:“設計符號學是基于符號學與設計學所衍生與發展出的交叉性學科,設計符號學是由具體的物質材料構成的相對穩定、多義以及抽象的符號,具備表達綜合性、交叉性的藝術文化形式特征。”當代社會人們對商品的消費已不局限于使用價值,更多的是消費附著在商品上的某種象征符號。
設計符號價值既可以是基于概念創作吸引消費者,也可以是以消費者需求為目的營造。筆者認為泉州改良竹編以其綜合性的鑲與編、插在竹編胚體中展現其編織技法的創新特點,在編織紋樣中所呈現的綜合性紋樣:如雀目編織法、旋花編織法和辮形、平順編織法等,這些具有特征性的改良竹編編織紋樣,是作為符號化元素再設計的重要突破口。提煉泉州改良竹編中編織紋樣以及編織技法為設計符號元素,結合設計創新突破原本傳統、單一的符號載體類型,可使泉州改良竹編的設計衍生工藝品更好適應當下的文化消費市場。同時,通過設計衍生下的泉州改良竹編作為符號載體所蘊含的情感語言,會使消費者更加直觀。以下兩個方向可作為改良竹編設計符號創造價值的出發點:其一,泉州改良竹編作為設計符號元素。因泉州改良竹編的編織紋樣有其獨特性,設計中可充分發揮其紋樣獨特性的藝術特征,突破其具象的編織呈現。其二,泉州改良竹編融合設計后成為一種符號載體。改良竹編工藝品在創作體量與類型上可嘗試跨品類融合,不局限于單一種類材質作為表現藝術形式的載體。
泉州改良竹編可以通過符號元素提取的方式,結合改良編織技法與設計理念融合出一個新的富有情感和情懷輸出的“符號載體”。突破泉州改良竹編藝術品限于博物館展示,可使泉州改良竹編藝術化被動為主動,融入現下的文化消費市場。例如2019年某法國奢侈品牌推出了皮革與竹編結合的竹編包,以及2021年西班牙品牌羅意威建立了工藝基金會與我國部分傳統工藝達成合作,其中最為典型的四川竹編與其他物料相結合,通過設計四川竹編家具再一次進入輕奢家具的消費市場中。案例中四川竹編工藝自身作為符號載體表現設計,不僅以消費者的需求為目的營造價值,也達到了令消費者更直觀感知其竹編藝品背后淡雅的符號語意。
泉州改良竹編融合設計后成為新的“符號載體”。基于設計符號學理論,符號語意構成一般分為藝術符號和情感符號,泉州改良竹編的情感符號語意恰需要通過設計去傳達。傳統泉州改良竹編作品中的藝術符號主要體現在編織紋樣和竹篾色彩的編織構成,為保留泉州改良竹編獨特的在地性文化,在改良竹編紋樣通過設計可“化繁為簡”,例如,常見的有提煉并簡化構成泉州特有的城市元素圖樣,在編織技法運用不變的情況下,將相對復雜的編織紋樣做減法創作出既能保留改良竹編的藝術性也能突出其情感符號的文化商品。同理,設計相關的顏色主題都可令人關聯想象,選擇代表泉州以至于閩南的顏色記憶,有石雕的灰、古厝的磚紅、古寺櫻樹的粉、島嶼海灣的藍以及惠安女的色彩繽紛等。回歸上文中,改良竹編小搖籃目的是為了觸發老一輩人孩童時情感記憶。但作為文化商品,對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情感記憶是具有一定年代時效性,把文化商品中情感符號價值營造落點于城市、地域特色上,使改良竹編自身成為一種符號現象,其中的符號語意能使消費者從一件文化商品觸發對這座城市的記憶與情感,強調出改良竹編源于泉州古城的文化意義。
(三)品牌推動符號具象
現今,文化消費市場中品牌是大眾消費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品牌需要文化商品傳遞其個性符號意義,品牌與文化商品二者關系相輔相成。例如,致力于研創有溫度的手作產品,介入傳統民藝復興務實的品牌慢物質,其品牌核心是通過設計將傳統手藝作品轉譯成現代語言并留存下去。其中作品《勝利在望》誕生于“年畫復活計劃”,運用木板年畫傳統技藝結合設計后的年畫進行創作,年畫表達“百業隆勝,萬事通利”的寓意,印制技藝上著重保留手工痕跡,畫面中的虛實、濃淡變化,向消費者傳達年畫的質感與情緒。打破了傳統當做門神年畫的用途,延展出一套具有收藏價值的年畫文創禮盒。
無獨有偶,不同于慢物質的另一品牌自然造物,則以“再造”為核心。通過各大社交媒體平臺“再傳播”非遺手藝文化,再設計后的一系列非遺文創商品能契合當下消費者在精神文化與實用功能上的需求。自然造物的設計再造并不拋離非遺手藝自身作為“符號載體”的傳統,例如,“鐵藝新生”企劃誕生于手打鐵器行業沒落的現象,隨著工業化的批量生產沖擊使得打鐵匠人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困境。自然造物團隊通過對鐵器制造的體驗調研,基于文化消費市場上推崇具匠人精神的個性化商品的需求,設計并創作出符合現代茶道的鐵藝器皿。這種方式使得鐵藝“活化”轉型為手藝者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并讓消費者感受到了其中的人文溫度。
上述案例中,民藝的情感符號通過設計得到了新的詮釋,借助品牌將設計后的民藝文創商品所蘊含的藝術符號與情感符號更好的轉譯給了消費者。目的上是將步入博物館中的非遺手工藝,通過設計讓非遺手工藝品更好地回到文化消費市場,而品牌則是作為其中的助力的客觀推動因素之一。泉州改良竹編在文化消費市場中仍舊處于探索階段,為解決資金鏈的斷層,除了政府給予的資金扶持,亦可以嘗試與品牌合作;不僅打開了在文化消費市場中的知名度,也可了解當下文化消費市場中貼近時勢的消費需求,從而更好地更新泉州改良竹編的創作載體或符號特征。
三、結語
竹編作為民間工藝的瑰寶,提升其文化消費傳播、打開新的生存路徑對提高地方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傳承傳播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改良竹編的現狀分析,加入品牌概念結合新時代下的審美和設計創新,對文化符號的提煉和融合從而賦予其新的傳承意義,融入改良竹編本身獨特的情感化傳承,對打開文化市場,提升竹編可持續發展打開了新角度,讓竹編工藝重新回歸生活,迎來新的符合當下的生存路徑。在時代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非遺文化的流逝亟需擴展產業鏈、和文化市場相接軌,使消費者能更直觀、更多方面地感受到手藝人所賦予的情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