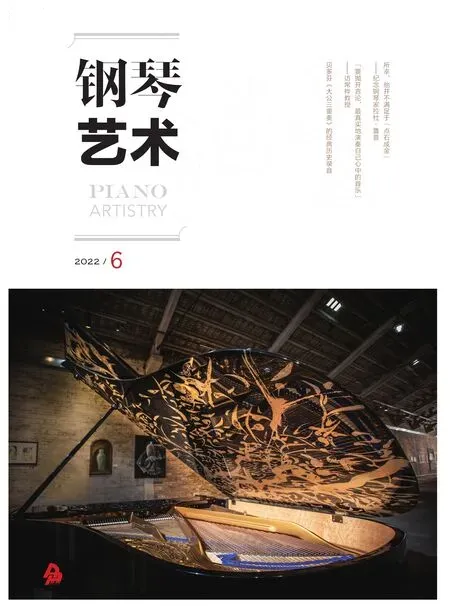模仿而來的演奏永遠是不真實的
——訪帕斯卡·內米諾夫斯基教授(上)
訪談者/仲 一
訪者按:施坦威藝術家帕斯卡·內米諾夫斯基(Pascal Nemirovski)作為當代最受青睞的鋼琴家與教育家之一,活躍于全世界范圍內五十多個國家與地區。他于2016年被英國皇家伯明翰音樂學院(Royal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任命為鋼琴教授并擔任鋼琴部負責人一職。在此之前,他曾任教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和普賽爾音樂學校(The Purcell School)。
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任教的十年間,在負責學院“鋼琴教學法”課程設計的同時,他編訂出版了多本鋼琴教材。因在音樂教育上的杰出貢獻,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授予了他“榮譽研究員”(Hon ARAM)的頭銜。
內米諾夫斯基曾獲施坦威與弗萊德里希基金會(Steinway &Freundlich Fund)所提供的全額獎學金就讀于茱莉亞音樂學院,師從于娜迪雅·瑞森伯格(Nadia Reisenberg)、阿黛爾·馬庫斯(Adele Marcus)。之后回到巴黎跟隨弗朗斯·科里黛特(France Clidat)和阿列克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學習。
其學生曾摘得眾多國際大賽的重要獎項,其中不乏“利茲國際鋼琴比賽”“布佐尼國際鋼琴比賽”“埃特林根國際鋼琴比賽”“青年音樂會藝術家大賽”,等等。

Q(仲一):感謝您在繁忙的行程中,特意留出時間接受此次訪談。聽說您剛剛結束了一系列的音樂活動,昨天才返回巴塞羅那的家中。
A(帕斯卡·內米諾夫斯基):首先,很感謝能有這次被采訪的機會,真的十分榮幸。我昨天剛回到巴塞羅那,前段時間真的是太忙了。接下來,我將會在下周四(2022年2月25日)飛往維也納教授一場大師班,緊接著是三月份在伯明翰音樂學院的大師課。當然,最忙碌的時間其實是在六月與七月。
Q:六月和七月的活動很密集嗎?之后的日程安排是怎么樣的呢?
A:沒錯。6月4日,我將在伯明翰音樂學院的音樂廳錄制一些斯克里亞賓作品的演奏視頻。緊接著6月5日會在倫敦錄制一場音樂講座,這場講座的主題是“要相信你的耳朵,而不是你的手指”。6月16至18日,我會前往馬德里開展一系列以“音樂藝術”為主題的大師班,主要針對的是西班牙本土的鋼琴家。6月21日,我將飛往美國的富特旺斯,在得克薩斯國際鋼琴音樂學院與音樂節(PianoTexas International Academy & Festival )教學授課,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音樂節。在那里我將會和許多我尊敬的同事、朋友們一起共事,比如諾曼·克里格(Norman Krieger)、斯蒂芬·霍夫(Stephen Hough)、讓—埃夫蘭·巴福杰(Jean-Efflam Bavouzet),等等。其中幾位也將會在最著名的賽事之一——“范·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中擔任評審,這也使得這個音樂節變得更有意義。因為受邀的參與者將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甚至參與到此次的“范·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中,有機會與大賽相同的職業樂團進行同臺合作,這對這些青年音樂家來說將會是一次很好的經歷。再之后的7月3至9日,我會出席一個在以色列新舉辦的國際音樂節。值得一提的是,“阿瑟·魯賓斯坦國際鋼琴比賽”也將是其贊助單位之一,它將會是個競爭十分激烈的音樂活動。我目前安排在夏季的最后一場活動將會是在意大利的“布雷西亞國際音樂節及夏季學院”(Bresci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 Summer Academy),然后我需要一個假期來休息,或許將會是一場旅行。

Q:聽起來真的是一系列很密集的行程,真的需要一個假期來休息一下。
A:與一群有才華的音樂家朋友和優秀的青年音樂家一起工作,我樂在其中。但是我也的確需要一個假期!
Q:聽說在您十分年輕時就已經將大部分的生活投身于鋼琴教育事業,是什么讓您做出了如此決定?您的音樂啟蒙經歷又是什么樣的呢?
A:這其實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首先,我的父親是位法俄混血的音樂家。在我剛出生不久時,伴隨我的就是普羅科菲耶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了,因為我父親當時正在練習這首作品。這或許算是我接受音樂教育的開始。父親很熱愛音樂,所以,我曾“被迫”在家中聆聽了許許多多的音樂作品,因為他一直在練習。換句話說,從出生的那一刻起,音樂就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地我就開始了鋼琴學習,準確地說,我應該沒有其他的選擇。
之后,我遇到了一位來自蘇聯的鋼琴老師,那時她正在法國參加比賽,并在著名的“瑪格麗特·隆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順便提一下,你要知道,俄羅斯的鋼琴學派,尤其是在那個年代,享有著極高的聲譽。他們訓練出了一大批擁有高超技巧的杰出鋼琴家,活躍在各大國際鋼琴比賽中。她在我面前輕松地展示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魯什卡》、肖邦的練習曲等十分艱難的作品。那時我大概13歲,還在練習諸如舒伯特即興曲這樣的作品。我第一次和她上課時,她轉身用俄語對我說道:“帕斯卡,你需要開始練習普羅科菲耶夫了。”于是,她給了我普羅科菲耶夫的《d小調托卡塔》。很難想象,我從舒伯特的即興曲一下跳躍到了普羅科菲耶夫的托卡塔。與此同時,她還讓我練習了肖邦的敘事曲、第一首練習曲等有難度的作品。
現在我們回到你的那個問題。當她教授我作品的時候,不僅僅告訴我如何做并且可以輕松地為我示范演奏,這對一個學琴的孩子來說是十分重要且具有影響力的。當孩子看到老師的一舉一動時,會耳濡目染地被其影響。觀看她上課的方式、移動的手指,聆聽她的演奏都能給我帶來不一樣的畫面感,我被這樣的教學震撼到了。或許,這就是我會想要成為一名鋼琴教育者的原因吧。另一方面,就是所謂的“分享”。我就是這樣的性格,我想向我的學生分享我的所學,分享任何我了解到的新的知識與內容,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Q: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了解到您有許多學生已經活躍在國際舞臺,其中更是有許多人曾摘得眾多國際大賽的桂冠,您是否對他們有一套獨特的訓練方法?
A:我有許多很優秀的學生,他們天賦異稟、認真好學。比如伊曼紐爾·伊萬諾夫(Emanuil Ivanov)、丹尼爾·勒布哈特(Daniel Lebhardt)、路易斯·史威茨貝爾(Louis Schwizgebel)、里瑟·德拉塞爾(Lise de la Salle)等。有些人已經在重要的國際比賽中嶄露頭角,我很為他們感到驕傲。
我其實沒有所謂的獨特訓練方法。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老師,要十分了解自己的學生,要了解學生身上的可能性、天賦和潛力。對于參加比賽的學生,我必須要對他們進行極度專注的教導,要確定他們做了關于譜面上的一切標記,攻克了所有的技術難點,把握了準確的風格。當然,也絕不僅僅是這些,最重要的是賽前的舞臺實踐,他們要帶著這些作品數次登臺。使他們充分獲得對演繹作品的自信,也是教學的一部分。在技術層面,你要坐下來陪他們逐句鉆研雕琢,直到他們可以很好地把握和學會聆聽自己的演奏。但是,如果學生一直在模仿老師的處理與演奏方式,按部就班地使用老師的知識與邏輯,最終也只是一個很好的模仿者,沒有自己的靈魂與特色。
經過多年的教學經驗,我發現應該去嘗試支持并相信學生自己的練習方式,運用他們獨有的想象力來完成新作品的學習。對作品演繹的根源要來源于自己的大腦,模仿而來的演奏永遠是不真實的。我的好友斯蒂芬·霍夫(Stephen Hough)曾對他的老師講“我上過最棒的課就是當你什么也沒跟我講的時候”。再好比大鋼琴家霍洛維茲,他有過非常嚴格的訓練,但當他前進至一定階段后,就會擁有屬于自己的特色。嚴格的訓練固然重要,但是使他變得出眾的是他的個人魅力。因此,在教導學生時我格外注意他們的潛力在哪些方面。同時,我也會去了解他們所受過的教育和文化來源。

帕斯卡與他的學生伊萬諾夫(左)和勒布哈特(右)
Q:在您的悉心指導下,您的學生伊曼紐爾·伊萬諾夫一舉摘得了被譽為國際最重要的音樂賽事之一——“第62屆布佐尼國際鋼琴比賽”的冠軍。能講述一下你們是如何備賽的嗎?
A:其實備賽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要豐富他自己的舞臺經驗與自信。因此,曲目的選擇是十分重要的。對曲目的設計安排會直接影響評委與聽眾的感受。另外,正如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參加比賽的學生都會選擇那些自己有著充分演奏經驗或是十分自信的曲目,這同樣特別重要。你的參賽作品一定要有大約三到五次的舞臺經歷。我曾聽我的老師說過蘇聯時期的一些訓練方式——晚上把已經入睡的學生叫醒,在沒有任何熱身和準備的狀態下要求他們直接開始演奏參賽曲目,以此來檢驗對作品的熟知程度,訓練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進行演奏的能力。
除此之外,要適當推薦他們去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比如,在伊萬諾夫準備圣-桑《第二鋼琴協奏曲》的時候我曾告訴他“一定要去讀法國文獻,要了解當時的巴黎,清楚法國音樂作品的風格”。在演繹不同的作品時,一定要去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去結交一些具有那些文化的外國人,與他們交換意見,這會對作品的演繹起到質的飛躍。我有一個10歲的中國學生,他非常有天賦,可以演奏很多作品。但我一直叮囑他要去聽一些錄音,要讓他擁有很豐富的知識背景。否則,對于許多作品風格的把握很容易出錯,尤其是在他這樣小的年紀。我記得小時候,老師聽到我在練習斯克里亞賓的《第四鋼琴奏鳴曲》,她非常“粗魯”地對我說“你在彈什么?我甚至無法分辨出這是什么樂曲”。這樣說很苛刻,但是真的幫助很大。當你的學生達到一定水平時,苛刻是絕對需要的。他們一定要明白虛心才能使人進步,絕對不可以自負。
Q:您曾擔任過許多重要國際音樂大賽的評委,甚至是藝術總監。站在職業評審的角度,您認為什么樣的演奏才能給評委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A:不同文化背景的職業演奏者對作品都有著不同風格的詮釋。比如,你會發現德國、法國,或是俄羅斯的參賽選手即使演奏同一首作品的方式也有可能會非常不一樣。這個很難斷定他們之中誰好誰壞。但是,一個很出眾的個人風格,會直接吸引評委們的注意力。從他上臺、走路鞠躬、向大家展現自己的方式,到演奏時對音樂的專注方式,都會使其與眾不同。有時候出于音樂的美學理念,評委們會不太認同演奏者的某些音樂處理方式。但是,如果他的個人風格十分出彩,就有能力讓聽眾跟隨他獨特的步伐來嘗試接受他對音樂的獨特詮釋。這讓我回憶起我曾經的一個朋友,很不幸的是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他曾是梅西安的學生之一,有著高超的記憶力,能夠背譜演奏很多艱難且復雜的現代作品。有一次他演奏梅西安的作品給作曲家本人聽,梅西安說“盡管你好像沒有按照我譜子上的音樂標記來演奏。但是,我覺得聽起來更好”。其實,我們也不得而知其他那些偉大的音樂作品背后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對話。所以,當我們聽到一些極度有天賦的演奏家來進行與眾不同的演奏時,我們或許會被他們吸引。當然,我說的是那些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優秀職業選手,他們在演奏時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力,但會讓你覺得他的音樂很有說服力。霍洛維茲是我最喜愛的藝術家之一,我十分敬重他的演奏,也會經常聽他演奏的斯克里亞賓練習曲,絕不會感到厭倦,這才是我們一直提到的“天才”的含義。相反的,在有些比賽中,一些選手演奏十分精準,沒有任何錯誤,但聽眾卻不會在其演奏結束后有很多的留戀。這或許就是個人風格特色有所欠缺的一種體現吧!
Q:您經常鼓勵自己的學生參加比賽嗎?
A:不是的,其實恰恰相反,很多學生會告訴我他們想要參加比賽。但是,絕大多數時候我給他們的答復都是“不行”。我會問他們為什么想要參加比賽,參賽的目的和期待又是什么?他們總是跟我說他們想要參加比賽,卻又說不出參賽的緣由。因為我想要知道他們僅僅是為了要一些比賽經歷,還是想要贏得比賽?如果僅僅是為了追求后者,那學生很容易在比賽中得到消極的結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備賽過程是十分苛刻的。對參賽者的要求不僅僅是演奏得多么精準,當然這也很重要,但是能讓參賽選手出彩的是他獨特的個人風格。除此之外,他們對參賽曲目一定要有充足的舞臺經驗和自信心,這些都是必要條件。不僅是比賽,那些經紀公司的面試,或是那些坐在各大比賽觀眾席的經紀人,都只會物色符合這些條件的鋼琴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