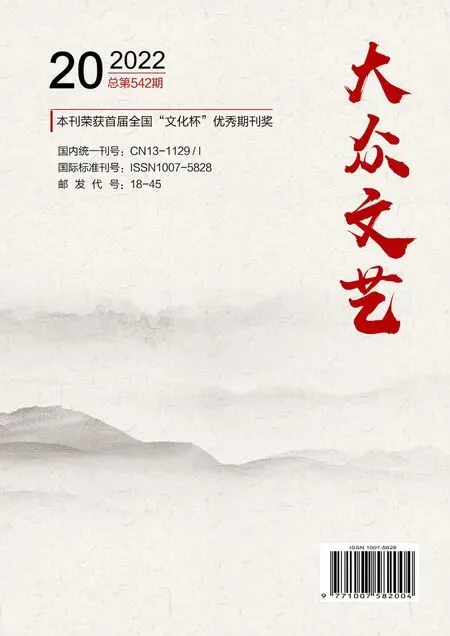一部將文學作品搬上舞臺的舞劇
——舞劇《塵埃落定》之我見
王 飛
(淮陰師范學院,江蘇淮安 223200)

(一瞬攝影IF)
“舞劇《塵埃落定》從藏族作家阿來《塵埃落定》的小說中抽取‘典型’人物與情境完成‘周莊夢蝶’式的主體演繹。通過那個每天清晨不斷拷問著‘我是誰’的傻子二少爺的眼睛,看看這世間,如吾父吾兄般的‘聰明人’,在真實與虛妄間何其癲狂,直到覆滅的‘塵埃’將人性的貪婪與愚蠢暫且掩埋……”
——張萍
一、舞劇《塵埃落定》的創作與選材
舞劇《塵埃落定》的創作改編自與其同名的文學作品《塵埃落定》,這部小說以其、它獨特的敘述方式及其富含魅力的語言表現了康巴藏族的歷史。“蘊藏著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和神秘的魔幻色彩,對普遍意義上的民族文化、歷史、自然、人性進行著完美的呈現。”這部小說作為藏族作家阿來老師的巔峰之作,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
截至《塵埃落定》首演之際,細數在它之前創作的舞劇。他們的選材有的來源于話劇,如《雷雨》;有的來源于重大歷史事件,例如:《八女投江》《浮生》等;也有通過地域的文化名人來創作的,像《李白》《杜甫》《昭君出塞》等;還有直面當代題材和時代問題的,例如:《戈壁青春》《青衣》等等。我們不難看出,在《塵埃落定》登上舞臺之前,在舞劇創作題材的選擇上,其實大部分還是一以貫之的以古代名人,名事抑或是話劇作為選擇來源。那么《塵埃落定》的選材在當時無疑是一個“新事物”的嘗試或延續,它基本脫離了原有的選材方式,選擇以民族題材的文學作品進行民族舞劇的創作,這無疑給人一種歷久彌新之感。
舞劇《塵埃落定》追隨文學作品,把文學作品搬上舞臺,同時將小說中蘊含的經典價值結合時代、結合當下進行舞蹈的演繹,演活了故事,演活了“一代人”,更演活了這部劇。但編導并不是完全照搬原著,而是在尊重原著,基于文學作品的基礎上,用舞蹈的形態和語言來“演故事”,“但由于舞蹈‘長于抒情拙于敘事’的藝術特性,雖然文學作品作為舞劇的題材為觀眾帶來了前理解”但拜讀過原著的觀眾數有限,仍有不少觀眾表示,沒有看得太明白,這也對舞劇自身的繼續推廣增加了難度。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對觀眾在審美的層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塵埃落定》的定位是‘民族舞劇’,也是擔得起‘民族’二字的民族舞劇。”田露老師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阿來老師的作品本身就極具民族性,在很多的敘述中也都是寫意的,這給了觀眾很大的思考和感悟的空間。創作初期,我們大家也一致認為要保留文學作品素材中的民族性,保留‘根’但不做成藏族舞”。在此理念的影響下,無疑給民族舞劇創作時保留最原汁原味的東西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也給舞劇的創作增加了不小的難度。在多次的采風與團隊研討后,田露老師將民族舞蹈中具體的元素等進行保留,在保留民族血脈的同時又將民族語言進行轉換,最終以意象性的方式,運用“藏族人和藏族舞蹈語匯,跳藏族舞,來講述藏族事”的思路,打造了這部獨具藏族文化意蘊的民族舞劇《塵埃落定》。
二、舞劇《塵埃落定》創作的隱喻性與象征性
整部民族舞劇的創作中并沒有喧賓奪主式的為了體現其民族性或故事情節而刻意的采用靚麗服裝,或添加繁多的舞美設計,但為數不多的設計中,卻處處透露著創作團隊的“小心機”。
1.“道具”使用的“小心機”——“有生命的‘轉經筒’”
“有生命的‘轉經筒’”是指舞劇“序”部分設計的隱喻與象征性。
提到“轉經筒”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作為文化的符號,是藏族同胞獨特的祈福方式,多常見于寺廟中。在布達拉宮的西墻外,就有一排轉經筒,藏民們需要順時針用右手轉動它們以此祈福。而在舞劇中,田露老師也將轉經筒搬上了舞臺,放在了舞劇開頭,“序”的部分。但不一樣的是,臺上的轉經筒并不是寺廟里傳統意義上的轉經筒,而是“有生命的‘轉經筒’”。它的組成是由不同身份的演員構成,包括吐司、吐司夫人、大少爺、女仆卓瑪及奴隸等,只見他們圍繞圓心順時針轉動的同時,還伴隨著自轉,與站在2點方向的“傻子”二少爺一一“碰面”,在獨特的藏族音樂的映襯下,向觀眾闡釋故事背景的同時,也向觀眾一一闡述劇中人物及其與“傻子”二少爺的關系。細心的觀眾一定也會發現,起初“轉經筒”是相對聚集的“圓”,演員們的動作也相對統一,而后在公轉與自轉的過程中,“圓”逐步變大,演員們的動作也漸漸轉化為符合各自人物形象特點的姿態,隊形也在“圓”的基礎上,逐漸渙散,在二少爺進入“轉經筒”又沖出“轉經筒”后,演員們又逐漸向“轉經筒”靠攏收縮,最終回到最初的模樣繼續轉動。這里“帶有生命的轉經筒”仿佛預示著故事的點點滴滴:“人們在利益的驅使下,出現了不同的選擇,然而正義和正確的選擇只有一個,作為‘轉經筒’局外人的二少爺終究沖破‘禁錮’帶領著大家尋找到正確的方向”。這好似為后來“在利益的驅使下,在本應該種植青稞的土地上,一部分人選擇種罌粟,一部分人繼續種植青稞,而后又統一種回青稞”的故事情節埋下了伏筆。

2.道具使用中的“小心機”——“躲藏起來的丑陋”
這里道具使用中的“小心機”,筆者以舞劇中第三幕的舞蹈片段為例。
在舞劇的第三幕,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舞蹈,那就是面具舞。藏戲面具舞蹈的出現,是當傻子二少爺選擇青稞之時,原本的至親,紛紛藏在了面具之后,露出丑惡的嘴臉,圍著他起舞。從前和睦友愛的親人在這一刻也變得陌生,有了距離感。此時,殷紅的大面具不僅僅是簡單的道具,更多代表和象征的是人性的另一面,代表著即使是至親,在利益驅動下也會變成露出猙獰、丑陋面目的“陌生人”。創作團隊在面具的運用上和面具顏色的選擇上可謂是恰到好處,在此情節之下道具的使用超出了面具本身的含義,隱喻和象征性也不言而喻。
3.服裝使用中的“小心機”——“落下的塵埃”
不僅是道具使用上體現隱喻和象征性,在服裝的使用上也大有意蘊。以第四幕的舞蹈片段為例。
“落下的塵埃”出現在第四幕“塵埃”的舞蹈片段中,一提到“塵埃”大家會想到些什么呢?會不會聯想到“塵土”?聯想到“塵土的顏色”?抑或是“縹緲的感覺”?沒錯,編導團隊正是把握了“塵埃”的這些特性,并予以舞蹈表達,在服裝的顏色上采用土色或接近于大地的顏色,并配以長袖拍打地面的“碎屑”,以意象的表達方式,將演員們化作喧喧鬧鬧的塵埃,來營造“喧鬧”塵埃的視覺效果。直到舞段結束,演員們吐氣放松身體逐漸下落直至落地,預示著人們化作塵埃落定,往事落定也會成為塵埃。這一處的隱喻性與象征性也猶如是點題的畫龍點睛之筆。
4.道具與燈光結合的“小心機”——“風雨輪回,時間推移”
時間的推移在舞劇中的表現形式很多,在舞劇《塵埃落定》中,編導運用道具和燈光,就上演了一出“風雨輪回,時間推移”的“大戲”。這一“小心機”在整個舞劇的第三幕——“選擇”中,也就是面具舞,長子取得階段性勝利狂舞之后的那一段。只見舞臺中區原是土司府結構元素結合瑪尼石堆形象組成的石堆,在土司及長子等人極力要種植罌粟之后,也是在餓殍遍野之前的一幕,藍白色相間的燈光在石堆上輪回掃射中,給人以風云輪換之感,賦予了舞臺場景新的定義:時間的推移。主創團隊的這一“小心機”把燈光,道具,舞臺的運用又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給予舞美以新的寓意和象征。
其實整部劇類似的體現和安排還有很多,這樣的“小心機”也體現出主創團隊的用心。
三、創作中舞臺空間的延伸
本劇區別于傳統舞劇的舞美,是在舞臺的構造之上,由傳統平面的舞臺設計增加了中后區可升降、可傾斜的陡峭平臺。它時而如山坡,時而變換為青稞田,給舞劇提供了更多的調度空間。這一平臺的運用很廣泛,在不同的情節中它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舞劇第一幕,它猶如黑褐色的土地翻滾開來,是收獲金黃的青稞田;第二幕又變成了滿山殷紅的罌粟花,在漸漸地蘇醒;在第四幕中它又變成了土司、土司太太及長子被迫“逃離”時的“通道”,隨著平臺的漸漸斜起,大兒子的滾落,也預示著他們的無處可逃。另外創作團隊為了使演員們在傾斜的平臺上自如舞蹈,將平臺的表面處理為凹凸不平的大地肌理質地以形成阻力給演員們進行表演帶來一定幫助的同時,也在視覺上給觀眾呈現了如厚重土地般粗糲的質感。再結合舞臺后區的操控平臺和燈光架的起落,將祥和的草原山坡而后在欲望的“掌控下”被慢慢吞噬形成層層變化的舞臺場景營造得淋漓盡致。
在本劇中,創作團隊加入了升降板來擴大自己的舞臺空間,以達到舞劇的效果,而還有一些導演,沒有增加任何其他的道具,只是調動起整個劇場的空間,就無形中達到了舞臺空間延伸的效果。這部民族舞劇叫《坪上花開》,是一部講述彝族故事的民族舞劇。其導演在尾聲謝幕之時,為了達到烘托全劇的效果,欲呈現彝族少男少女手舉火把,蜿蜒在韭菜坪上,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場景,導演選擇在觀眾席的位置出發,演員們手舉火把,順著觀眾席天然的“蜿蜒”而后徑直地走向舞臺,此時,由臺下到臺上的過程仿佛是山下到山上的過程,無形中延伸了整個舞臺的空間,還使得觀眾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這一創意在后來的演出中也成了讓觀眾難以忘懷的情景之一,也是整部劇的亮點之一。
對于舞臺空間的延展,《塵埃落定》《坪上花開》的創作團隊無疑是動了腦筋,也收獲頗豐。在這個迅速發展的時代,人民審美要求的日益提高,我們的舞劇能否給予觀眾不一樣的舞臺視覺效果,舞臺空間的延伸無疑也是重要的一點。
四、創作中舞劇創作體現的價值與局限性
1.價值——給觀眾以啟迪
正如第四幕解說詞說的那樣:“我們,往往會親手打碎那些好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恍然發現,失去的才是最好的。我們往往執拗于那些沒有得到的事物,而失去了對所擁有的珍惜。”這也是整部舞劇演出結束給筆者最大的感受。其實不同的觀眾對于舞劇的觀感是不同的,成千上萬名觀眾對“塵埃落定”的理解也有成千上萬種,但無論如何這部舞劇留給大眾的啟迪,是無可置疑的。與傳統舞劇不同的是,這部舞劇從傳統舞劇英雄主義的啟示轉換到了人性的思考,上升到了對人這個本體的思考。而這部舞劇所體現的就是現代社會人們的心理狀況或價值觀。
正如編導田露老師說的那樣:“創作是給接受者們以啟迪,笑罷,哭罷噘出苦澀,而不是廉價無思想的空洞;創作的悲壯,帶來的淚水是為了洗凈心靈上的塵垢,而不是模糊了前路。”是的,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斷豐富,物質的膨脹使得人們的價值觀也變得扭曲,不健康的思想也愈來愈多,就像劇中的“聰明人”不知足的心態,以及“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等這些不良思想,帶給社會的負面影響也不言而喻,而就在此時,這部舞劇的出現,就像一股清流涌出,“激濁揚清”引發人們思考,給予人們以啟迪,從另一個側面來講,也是舞蹈功能和價值的體現。
2.局限性——“范圍”的限制
在這里的“范圍”是指受眾群體的范圍,是基于其舞劇創作團隊的初衷:“在看得懂、記得住的情況下能若有所思就是它的價值所在”所提出的。但是,由于舞蹈的局限性和觀舞者自身修養的局限性等等,真的每一個走進劇場的人都可以完全看懂嗎?答案當然是不一定。那我們怎么能夠看得懂記得住并有所思呢?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也是今后舞劇創作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總結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舞劇《塵埃落定》創作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整部劇的價值也值得肯定,但是否真的達到了預期呢?我們應該怎樣使得實際距離與預期距離愈來愈近呢?這值得我們的深思。但即便如此,這些都泯滅不掉舞劇《塵埃落定》的成功,將文學作品搬上舞臺的成功,以及它給予我們的震撼,它所體現的繼承性、獨創性等都將為今后舞劇的發展趨勢給予借鑒,我相信我們高質量舞劇將不斷層出,所有的問題也都將一一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