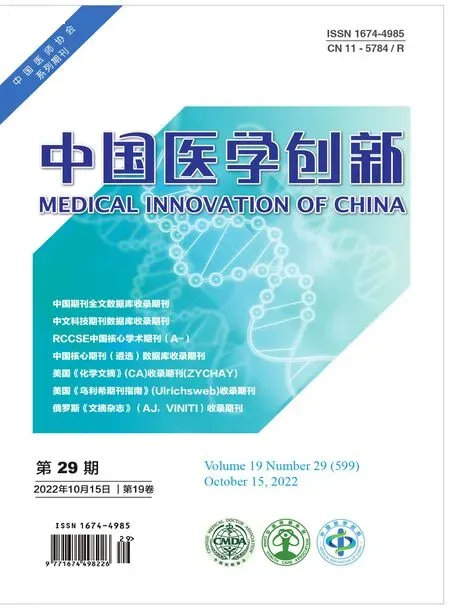國際標準化比值/血小板比值在評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肝纖維化中的效能*
楊璐璇 張文勇 劉美琴 沈秀娟
盡早明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程度,有助于早期篩查需要進行抗病毒治療的人群,減少肝硬化、肝癌及其他肝臟相關事件的發生[1]。肝臟組織活檢作為肝纖維化診斷的金標準,存在風險大、費用貴、可重復性差等缺點,目前常見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又存在局限性,如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和血小板比率指數(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ratio index,APRI)評估HBV 感染相關肝纖維化程度的準確性較低,肝纖維化4 因子指數(fibrosis-4 index,FIB-4)在診斷晚期肝纖維化及肝硬化方面效果更好,瞬時彈性成像技術受操作者及患者狀態影響較大,部分無創模型是基于慢性丙型肝炎感染而建立的,易受肝功能干擾,故如何對慢性HBV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進行高效能的無創性診斷仍屬于臨床一大挑戰[1-4]。
目前一項研究發現國際標準化比值/血小板比 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to-platelet ratio,INPR)在預測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慢性HBV 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時有較好的效能[5],但缺乏廣泛的臨床驗證,故本研究將這一新型指標與其他常見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進行比較,驗證其診斷肝纖維化的效能,為慢性HBV 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診斷提供幫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 年10 月-2021 年9 月在蘇州大學附屬傳染病醫院進行肝臟病理檢查的187 例慢型HBV 感染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符合文獻[1]《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中慢性HBV 感染的診斷標準;(2)接受肝臟組織活檢。排除標準:(1)合并甲肝、丙肝等其他肝炎病毒感染;(2)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酒精性肝病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3)合并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腎炎、血液系統疾病等慢性疾病;(4)合并惡性腫瘤;(5)合并急性感染;(6)近半年曾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等可能影響血常規及肝功能的藥物。本研究已經醫院倫理學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1.2.1 肝臟病理學檢查 在排除肝臟穿刺禁忌證后,在彩色多普勒超聲引導下行經皮肝穿刺活檢術,標本用福爾馬林固定,經石蠟包埋,連續切片,經HE、網狀纖維和Masson 染色等處理,由兩位經驗豐富的病理醫師閱片,并依據Scheuer 評分系統進行肝纖維化分級,分為S0~S4 期,S0、S1 為無顯著纖維化,S≥2 為顯著纖維化,S≥3 為進展期肝纖維化,S4 為肝硬化。
1.2.2 臨床指標 收集患者的性別、年齡、肝臟穿刺前一周內的血小板計數(platelet,PLT)、紅細胞體積分布寬度(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γ-谷氨酰轉移酶(γ-glutamyltransferase,γ-GT)、國際標準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及瞬時彈性成像技術所測量的肝臟硬度(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
1.2.3 計算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 APRI 計算方法為:[AST/正常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ULN)×100]/PLT。FIB-4 計算方法為:(年 齡×AST)/(PLT×ALT 的平方根)。γ-GT-PLT 比值(GPR)計算方法為:γ-GT/ULN/PLT×100;RDWPLT 比值(RPR)計算方法為:RDW/PLT;INPR 計算方法為:INR/PLT×100。
1.3 統計學處理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4.0 軟件,正態性計量資料采用()表示,比較采用t 或t′檢驗,非正態性定量資料采用M(P25,P75)表示,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H 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Spearman系數進行相關性分析;采用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評價INPR 及各肝纖維化無創模型的診斷價值。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的一般情況 187 例慢性HBV 感染患者中男122 例(65.24%),女65 例(34.76%);平均年 齡(40.89±10.25)歲;S0 期2 例(1.07%),S1期46 例(24.60%),S2 期87 例(46.52%),S3 期31 例(16.58%),S4 期21 例(11.23%),其中139例(74.33%)進展至顯著肝纖維化。不同肝纖維化分期患者的性別和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肝纖維化分期患者的ALT、AST、γ-GT、PLT、RDW 及INR 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ALT 在S≤3 時隨著肝纖維化的加劇而上升,在S4 期明顯下降,AST、γ-GT、RDW及INR 隨著肝纖維化的加劇而上升,見表1。

表1 不同肝纖維化病理分期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表1 (續)
2.2 INPR 及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在不同肝纖維化中的比較 不同肝硬化分期患者INPR、APRI、FIB-4、GPR、RPR 及LSM 比 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INPR、APRI、FIB-4、GPR、RPR、LSM 與肝纖維化分期均呈正相關(P<0.05),以INPR 與肝纖維化的相關程度最高,見表3。

表2 INPR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在不同肝纖維化中的比較

表3 INPR及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與肝纖維化的相關性分析
2.3 INPR 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診斷模型的診斷效能比較 在診斷顯著肝纖維化、進展期肝纖維化及肝硬化時,INPR 的AUC 分別為0.699、0.834 和0.896,均高于其他常用無創診斷模型。見表4、5、6 和圖1。

圖1 INPR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診斷模型在各肝纖維化階段的診斷效能比較

表4 INPR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診斷模型的診斷S≥2的效能比較
3 討論
肝纖維化是慢性HBV 感染患者向肝硬化發展的關鍵步驟,早期發現后可通過抗病毒治療達到逆轉[4],故盡早診斷慢性HBV 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程度具有重要臨床價值。但在臨床工作中很多患者進展至肝硬化階段時仍無明顯臨床癥狀,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在排除肝硬化或診斷重度肝纖維化效能較好,常規影像學檢測對于早期肝纖維化診斷意義不大[4],加之其中40%~70%的患者持續ALT 正常[6],難以通過常規監測早期診斷肝纖維化,故尋找一個精準度較高且簡便的肝纖維化診斷方式勢在必行,本研究結合臨床經驗及最新研究發現INPR 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肝纖維化診斷指標,具有簡便、廉價、可重復性高的優點,有待于推廣至臨床應用。

表5 INPR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診斷模型的診斷S≥3的效能比較

表6 INPR與常用的無創肝纖維診斷模型的診斷S4的效能比較
目前國內外關于無創肝纖維化針對方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新型血清學指標,例如微RNA 作為一種功能性RNA 參與了肝纖維化的進程,能夠區分顯著肝纖維化和非顯著性肝纖維化并優于其他診斷指標[7-8],白細胞衍生趨化因子2 的表達水平與肝纖維化進展呈正相關,診斷效能優于APRI 及FIB-4[9-10]。二是影像學無創診斷技術,如磁共振彈性成像、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磁共振紋理分析等基于磁共振的診斷方式均體現了良好的診斷效能[11-13]。三是根據現有指標構建各種模型[14-17],或在既往認為與肝纖維化無關的因素里尋找和肝纖維化相關的指標,如血小板壓積、鐵調素與類風濕因子[18-20]。但上述方式在診斷肝纖維化方面存在不足,故在不斷完善相關研究的同時,仍應圍繞肝臟相關指標尋找簡便且高效能的肝纖維化診斷方式。
INR 作為終末期肝病模型的參數之一,可獨立預測肝衰竭患者的預后[21-24]。現有研究發現在不同病因所致的肝硬化中,乙肝肝硬化人群的INR 最高[25],可見INR 和慢性HBV 感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凝血酶原時間是慢性HBV感染患者肝纖維化的獨立危險因素[26],本研究亦發現隨著肝纖維化的進展,INR 顯著升高,故可考慮基于INR 建立慢性HBV 感染患者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
在PLT 方面,既往認為肝硬化通過門靜脈高壓引起脾功能亢進,從而引起PLT 減少,但目前發現在慢性肝病的進展過程中,已出現了PLT 下降,肝炎病毒感染可造成骨髓抑制,肝纖維化的進展可導致血小板生成素下降,同時自身免疫紊亂可導致PLT 破壞增加[27],結合目前已有研究發現PLT 是預測慢性HBV 感染患者顯著肝纖維化的獨立因素[26,28],故將INR 與PLT 結合作為慢性HBV 感染患者的肝纖維化的診斷模型,可有效提升診斷效能。
本研究發現與其他常用的無創肝纖維化診斷模型類似,INPR 會隨著肝纖維化的加劇而上升,但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無論是與肝纖維化的相關系數,還是診斷各肝纖維化期的AUC,INPR 均高于其他模型,具有良好的診斷效能,結合現有的無創診斷方式模型的缺陷[4],INPR 在診斷顯著肝纖維化時效能更好,有利于臨床工作,有助于盡早啟動抗病毒治療,改善慢性HBV 感染人群的預后,有效減少肝硬化和肝癌的發生。
目前基于凝血指標的肝纖維化診斷模型尚未成熟,本研究雖然填補了這方面空白,但由于本研究樣本量較少,尚不能明確其最佳診斷閾值,在后續的研究中將進一步明確,并研究其內在機制,研究是否能作為治療效果的評估指標及肝纖維化治療的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