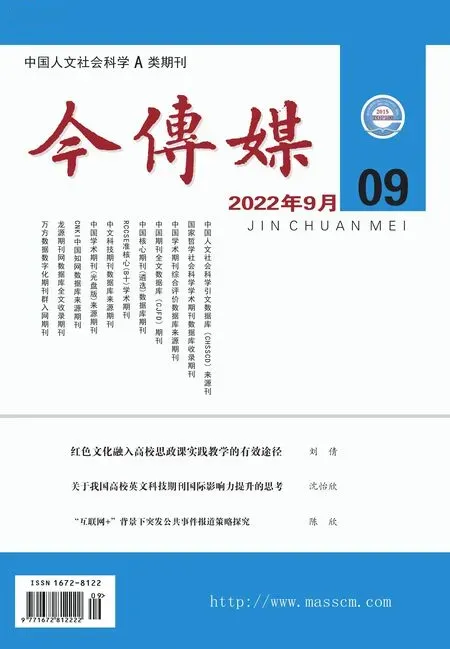探索國產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創新路徑
商慶琪
(曲阜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山東 日照 276800)
新媒體的不斷發展為紀錄片帶來了空前的發展前景,紀錄片創作者的思維方式不斷發生轉變,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的本體也開始發生轉變,互聯網思維開始融入紀錄片的創作過程,新媒體視頻平臺成為紀錄片傳播的重要陣地。新媒體環境拓展了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空間,客觀、中立、旁觀不再是建構紀錄片真實感的主要手法,創作過程、敘事角度以及技術融合等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創新,開創了人文歷史紀錄片新的美學形態。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的發展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態,拉近了紀錄片和觀眾之間的距離,也縮短了創作主體和接收主體之間的距離感。
一、敘事的“沉浸式”探索
紀錄片作為一種以真實感為美學基礎的藝術創作,真實是紀錄片的靈魂,是紀錄片賴以生存的根基。無論是美國的“直接電影”、法國的“真實電影”、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理論,還是格里爾遜的“畫面+解說”創作方式,都是創作者對紀錄片真實感的追求。21世紀以后,新媒體的快速生長使紀錄片的受眾群體呈現出年輕化的態勢。比如,人文歷史紀錄片 《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以“90后”“00后”為主體的新媒體視頻平臺嗶哩嗶哩 (以下簡稱B站)投放后一路躥紅,并且在新媒體社交領域掀起了故宮文物熱的國風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年輕受眾群體中的關注度不斷飆升,這讓創作者意識到只有提升紀錄片的有效傳播,才能將其價值最大化地發揮出來。新媒體環境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加開放、多元且更具有包容性的創作環境,為紀錄片的創作以及有效傳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至此,“以觀眾為中心”的互聯網思維逐漸開始融入到紀錄片創作主體的思維模式中,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中國紀錄片打破了以往的單向傳播模式,轉而開始注重觀眾的觀影體驗,通過加強觀眾的參與感和沉浸感來提升紀錄片的真實感,這逐漸成為新媒體視域下國產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新的創作趨勢。
2020年,優酷視頻推出了中國第一部互動紀錄片 《古墓派:地下驚情》,率先在新媒體視頻平臺上打開了國產互動紀錄片的大門,為紀錄片的創新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古墓派:地下驚情》依托互聯網技術通過設置游戲來提升觀眾的參與感和沉浸感,故事講述的先后順序以觀眾的選擇為主,不同的選擇會帶來不同的觀影內容。主線也會根據觀眾的不同選擇而有所不同,這對歷史知識愛好者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雖然這種游戲式的互動紀錄片增加了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的參與感,但是其傳統線性的敘事方式與游戲式的互動卻是自相矛盾的,這種游戲式的互動節點的設置極易打斷觀眾觀影的連貫性和沉浸感。《2020網絡原創節目發展分析報告》中提到:“在‘國產互動紀錄片的看法’的受訪者中,有37.32%的人認為互動模式會影響觀影的連貫性,進而會影響自己的觀感體驗。”因此,如何依托互聯網技術做好互動紀錄片,找到紀錄片在傳統的線性敘事與參與感和沉浸感之間的平衡點,成為當下互動紀錄片創作者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除了依托互聯網技術觀眾的觀影體驗,還可以通過敘事視角的創新探索,來增加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的沉浸感。2021年11月28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日本放送協會 (NHK)聯合制作的紀錄片 《世界遺產漫步》,將紀錄片與Vlog相結合,通過虛擬人物來塑造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帶領觀眾對中國的云南、廈門和杭州等城市進行了“云端漫游”。Vlog是采用第一人稱來記錄生活的一種視頻形式。隨著新媒體和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利用微單、手機等便攜攝影器材對自己的日常生活進行記錄,形成了一種符合年輕觀眾觀看和傳播習慣的視頻形態。《世界遺產漫步》在Vlog式紀錄片的創作形式架構下,整體的節奏較為緩慢,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化身“游客”慢“游玩”,實現了“沉浸式”云游中國,感受世界文化遺產的魅力,引發觀眾思考并找回自我。這種創作方式是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創作者的創新性實踐,為觀眾帶來了較好的觀影體驗。不論是國產互動紀錄片的開創,還是 《世界遺產漫步》這種Vlog敘事視角的運用,都是紀錄片創作者基于新媒體環境視域下,互聯網思維在紀錄片創作中的創新實踐,對國產紀錄片的長足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二、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
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展,紀錄片年輕的觀眾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大。2019年,我國推出了第一部歷史題材的劇情紀錄片 《風云戰國之列國》,它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歷史紀錄片的敘事方式,開創了紀錄片新的敘事方式,促進了我國紀錄片多元化的發展。如何在保證“真實”的基礎上,利用好“情景再現”的拍攝手法對紀錄片進行劇情化的敘事,成為劇情紀錄片需要突破的困境。“情景再現”主要是通過真人扮演的方式來彌補歷史影像匱乏的缺陷,其影像的本質是電影化的攝制方式在紀錄片上的體現。比如,紀錄片之父弗拉哈迪的 《北方的納努克》,就是最早采用這種方式來還原歷史的紀錄片。
2009年,中國就提出了“劇情紀錄片”的概念,直到2019年,才推出國內首部歷史題材的劇情紀錄片 《風云戰國之列國》。在傳統紀錄片的表現手法上,“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的學術爭論一直存在,前者強調內容的真實性介入式記錄,并且承認藝術的假定性;后者則強調創作者應該做窗戶上的蒼蠅,不干預拍攝對象的觀察式記錄。紀錄片的真實性包括空間的真實、時間的真實、人物的真實、事件的真實,以及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獲得的真實感。如今,我們所追求的紀錄片的真實是基于創作者所傳達的信息的真實性,以及觀眾在影片獲得的真實感。采用了“情景再現”創作手法的歷史題材的劇情紀錄片 《風云戰國之列國》,其真實性不僅體現在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上,也體現在服化道上,真實的細節帶給觀眾更加真實的觀影體驗和更好的代入感。該紀錄片中故事性、戲劇性的內容,是從 《史記》《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正史資料中提取的,“情景再現”的創造手法既保證了內容的真實性,又增加了可觀性。此外,該紀錄片邀請了王勁松、于榮光、李立群、喻恩泰、林永健、鄭則仕、海一天七位老戲骨,來演繹戰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七位歷史人物,他們用演技將觀眾帶入到了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大大增強了觀眾的沉浸感。
2020年,湖南衛視和芒果TV推出的紀錄片 《中國》,采用了“戲劇化”的處理方式,在史實的基礎上加入了合理的想象和推演,將歷史事件與戲曲舞臺的假定性相融合,實現了紀錄片作為一種影視創作的寫意性表達。比如,第一季第十二集 《盛世》中,高墻象征著城池,屏風象征著屋舍,壁畫象征著敦煌石窟。紀錄片 《中國》通過對色彩濃厚的布景以及道具的假定性演繹表達,來構筑觀眾心理層面的“真實感”。此外,《中國》借助戲劇舞臺的假定性,以“虛、簡、神”的“物、態、形”,通過演員豐富的神態表情和肢體動作以及觀眾的聯想,使紀錄片勾勒出寫意性情境。《中國》中具有象征意味的場景,拓展了該紀錄片的敘事空間,提升了觀眾的觀感體驗和想象空間,其簡潔的構圖和歷史事件的凝結,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敘事結構,引導觀眾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參與影片中留白的想象,從而提升了紀錄片的詩意性美感。早在1926年,格里爾遜就提出了“紀錄片是對真實場景的創意性處理”的定義。紀錄片的“真實性”并不僅僅依靠事實本身,因為虛構電影與非虛構電影的差別從來不會依靠這種形式或方法的不同而形成。紀錄片 《風云戰國之列國》和 《中國》對歷史事實的“戲劇化”講述,在傳播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顯著成效,并且開創了紀錄片新的藝術樣式和美學形態。但是,如何更好地處理“戲劇化”和“真實感”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創作者和學者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三、美學形態的多元化
新媒體時代,紀錄片不再是院線和電視的專屬,新媒體平臺逐漸成為紀錄片重要的傳播平臺,微博、抖音等新媒體社交平臺也成為紀錄片傳播的重要陣地。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8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8.88億人看短視頻、6.38億人在看直播,短視頻、直播正在成為全民新的生活方式。隨著新媒體視頻和社交平臺的不斷發展,紀錄片的觀眾群體不斷趨向年輕化,為了迎合年輕觀眾的觀看習慣和審美趣味,紀錄片的美學形態也趨于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比如,《中國》《如果國寶會說話》 《此畫怎講》 《大唐帝陵》等人文歷史紀錄片就受到了年輕觀眾的熱烈追捧,這也意味著超高清紀錄片、微紀錄片、動畫紀錄片等形態逐漸成為紀錄片新的美學形態。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制作的人文歷史紀錄片 《如果國寶會說話》,于2018年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首發,隨后在“央視頻”、B站等新媒體視頻平臺進行傳播。該紀錄片以一集五分鐘的微體量形態進行傳播,在表達上趨向個性化、年輕化,以旁白“叮、叮,您有一條來自國寶的留言,請注意查收”開篇,通過擬人化的講述將文物活化,成功縮短了當下年輕觀眾群體與千年歷史文化長河之間的時空距離感。這種感性的情緒表達對年輕觀眾群體提升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信心,具有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同時,這種消解的宏大敘事以個性化、情感化為主的表達方式,構成了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微”型美學形態。
除此之外,當下的人文歷史紀錄片開始注重畫面的美感和層次感,形成了具有儀式感的觀影模式,在制作體系和敘事語言上,開始趨于電影化的創作標準,給予受眾極致的視聽享受。在人文歷史紀錄片《中國》中,創作團隊采用了50格的拍攝手法、電影語言、寫意性表達以及舞臺化設計,為觀眾帶來了一場極致的視聽盛宴。比如第12集 《盛世》,講述的是大唐盛世下的繁榮景象,屏風、單桌、飾品盒建構成了長安西市粟特人的店鋪,在講述過程中,其采用戲劇舞臺的假定性進行了留白,還放慢了剪輯速度,在慢鏡頭下,平民貴族共處一室、歡聲笑語,一番熱鬧的市集景象浮現在觀眾的腦海中,將大唐的繁榮盛世展現得淋漓盡致。
對國內紀錄片的創作來講,動畫的加入開創了一種新的美學形態。動畫與紀錄片相結合不僅彌補了紀錄片歷史資料的匱乏,也為史實的講述提供了更多可視化的張力,提升了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在年輕觀眾群體中的關注度。比如,動畫紀錄片 《此畫怎講》將情景劇的創作方式融入到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使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更年輕態,更個性化。此外,紀錄片 《但是還有書籍》在第二季的創作過程中,歷史資料的板塊采用了動畫的形式,為該紀錄片增添了許多活力,吸引了更多的年輕觀眾。超高清鏡頭、微紀錄和動畫,同紀錄片的真實美學雜糅融合,開創了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新的美學形態,不僅對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在年輕觀眾群體中的有效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還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大眾化傳播,以及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結 語
近幾年,我國新媒體平臺和傳統媒體的深度融合發展,不僅增強了我國紀錄片的傳播效果,也提升了紀錄片和觀眾之間的互動性,促使國產紀錄片躋身于電影、劇集和綜藝的行列之中,不再是小眾文化。同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也促使國產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創作進入多元化時代,拓展了紀錄片創新發展的空間。在此背景下,紀錄片創作者要搶抓機遇,對紀錄片進行不斷的創新探索,從而創作出更多具有新意且不失偏頗的藝術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