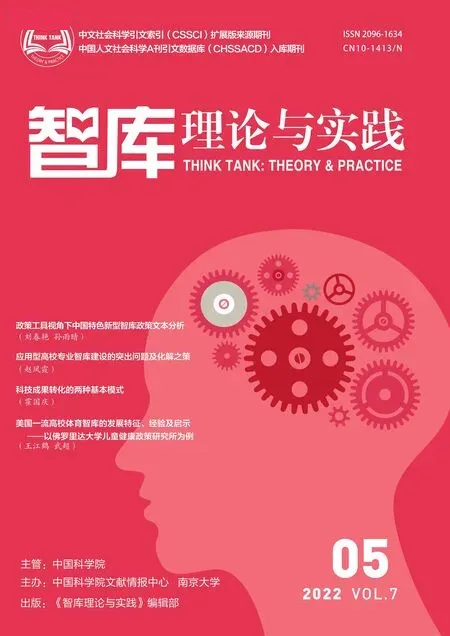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的作用探究*
■ 王蓉 陳菲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武漢 430079
1 引言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顧清揚副教授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要想在波詭云譎的國際社會中尋求生存之道就必須重視治理人才的培養,新加坡十分重視依靠智庫吸引與培養國內外人才,并力圖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1]。由此可見,新加坡早已認識到智庫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并將其視為重要“幫手”。作為“東盟十國”之一,新加坡素有東盟“大腦”之稱,其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通過整理新加坡各智庫基本信息及其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的典型事跡,分析和總結了其發展現狀、特點及其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
2 新加坡智庫發展歷程
自1965 年新加坡獨立后,建設高質量的政策研究機構成為新加坡各界的共識,智庫的研究成果也逐漸受到新加坡各界的重視。新加坡智庫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3 個階段:初步發展階段、持續發展階段以及蓬勃發展階段。
2.1 初步發展階段
20 世紀60 年代至70 年代可視作新加坡智庫的初步發展階段,在此階段發展起來的智庫只有兩所: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IIA)和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成立于1962 年,是一家非營利性的獨立智庫,也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智庫。該研究所由基金會、會員訂閱和企業贊助提供資金,不接受新加坡政府的定期資助。其致力于政策分析,促進政策制定者、私營部門決策者和專家之間的深入對話,以塑造公共政策與社會反應。該研究所以東盟作為研究重點,旨在就地區和國際事務進行研究、分析與討論以及為推動環境可持續性問題提供政策建議[2]。
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的前身是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東南亞研究所是在1968 年根據議會法案成立的一個自治組織,致力于研究東南亞地區的社會政治、安全、經濟趨勢與發展以及該地區廣泛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問題,旨在激發學術界的研究和辯論,提高公眾對該地區的認識,為促進解決該地區面臨的各種問題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該研究所下設3 個研究中心:東盟研究中心、新加坡亞太經合組織研究中心以及淡馬錫歷史研究中心。為紀念新加坡第一任總統尤索夫·賓·伊薩克(Yusof Bin Ishak),2015 年8 月,該研究所正式更名為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3]。
2.2 持續發展階段
20 世紀80 年代至90 年代被視為新加坡智庫的持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智庫類型主要是高校型智庫,是依托于各大高校建立發展起來的,其研究涵蓋的內容及地域范圍也變得更加廣泛。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智庫主要有新加坡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IPS)、新加坡國際基金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SIF)、國防與戰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IDSS)和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EAI)。
1988 年,新加坡政策研究院以獨立型智庫初創,專門研究和產出新加坡公共政策理念。2008 年,該研究院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一個研究中心,繼續致力于公共政策分析。該研究院對影響新加坡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戰略研究,并通過社會調查洞悉民眾的態度和愿望[4]。新加坡國際基金會成立于1991 年8 月,該基金會擁有一支來自不同信仰、背景和文化的多元化團隊,其目標是“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和平、包容并為所有人提供機會的世界”,鼓勵新加坡人采用國際視野,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幫助海外新加坡人與新加坡保持聯系[5]。1996年7 月30 日,國防與戰略研究所在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內成立,由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陳慶炎揭幕。該研究所的成立是為了對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安全、外交關系的發展進行研究,并促進對新加坡和該地區的戰略和國防問題的理解。2007 年1 月1 日,南洋理工大學成立了由5 個研究中心及其他研究項目組成的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以滿足新的研究需求,國防與戰略研究所成為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旗下5 個研究中心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一個①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其余四個研究中心分別為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研究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ICPVTR)、國家安全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National Security,CENS)、多邊主義研究中心(Centre for Multilateralism Studies,CMS)、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NTS)。[6]。東亞研究所由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博士1983 年所建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發展而來。后幾經易名,定名為“東亞研究所”,此名沿用至今[7]。顧名思義,東亞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范疇與東亞地區有關,該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是當代中國(包括港臺地區)。隨著研究的深入與資源的積累,該研究所已從最初的研究重點——當代中國,擴展至包括日、韓在內的東亞國家[8]。
2.3 蓬勃發展階段
21 世紀以來,新加坡智庫進入蓬勃發展時期,在這一階段涌現出了大批智庫機構,且高校型智庫仍占據優勢地位。由于此階段發展起來的智庫數量較多,本文不一一列舉,僅選擇幾所影響力相對較大的智庫進行介紹,分別為新加坡南亞研究 所(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ISAS)、亞洲與全球化中心(Centre on Asia and Globalisation,CAG)和水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Water Policy,IWP)。
作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個自主研究機構,南亞研究所于2004 年成立。其成立源于南亞日益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以及南亞和東南亞之間緊密的歷史聯系。南亞研究所聚焦當代南亞研究,致力于向新加坡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界、商界、學術界和民間社會傳達有關該地區的知識和見解。該研究所主要聚焦6 大核心研究主題:南亞國家間關系及多邊主義、南亞政治與社會治理、經濟與貿易、新技術、南亞僑民以及環境與可持續發展[9]。2006 年,亞洲與全球化中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成立。該中心致力于對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為學術界、決策者、評論員和公眾就具有區域和全球意義的問題提供準確、獨到和高質量的分析。該中心的研究議程集中在兩大領域:區域和全球秩序的前景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未來。該中心自成立以來已與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韓國、英國、美國以及歐洲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網絡。亞洲與全球化中心旨在提供機會,促進專家之間就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進行建設性和實質性的交流[10]。2008 年,水政策研究所由李顯龍在新加坡國際水周期間發起,并得到新加坡國家水務機構(Public Utilities Board,PUB)的支持。其主要任務是幫助改善亞洲的水政策和治理[11]。新加坡其他智庫信息參見表1。

表1 新加坡智庫一覽表Table1 List of Singapore think tanks

續表1
3 新加坡智庫的特點
雖然進入21 世紀后,新加坡智庫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現象,許多新智庫相繼建立,但新加坡智庫數量在世界智庫排行榜中仍處于低位水平。這并未阻礙新加坡智庫躋身世界知名智庫排行榜,反而賦予新加坡智庫一定的發展特色。本文將新加坡智庫的特點主要概括為4 點:量少質優,以質取勝;政府布局,分工協作;官學融合,教研相長;管理科學,高效運轉。
3.1 量少質優,以質取勝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研究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于2021 年1 月發布的《2020 全球智庫指數報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可知,截至2020 年,新加坡共有21家智庫。盡管新加坡智庫數量較少且大多數智庫建立僅十幾年時間,但質量普遍較高,獲得了全球認可的綜合實力和較大的地區乃至國際影響力。在《2020 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的排行榜中,排名前100 名的智庫(不包括美國)中新加坡有5 家,分別是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第26 名)、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第68 名)、亞洲與全球化中心(第69 名)、亞洲競爭力研究所(第73 名)以及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第97 名)。除印度以外的南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智庫榜單中,排名前5 位中有2 家屬于新加坡智庫,分別是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第1 名)和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第3名);而在排名前60 位中有9 家是新加坡智庫機構。由此可見,新加坡智庫具備“少而精”的特點,堅持以質取勝,尤其是以國際事務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為主的“老牌”智庫一直擁有良好的世界級專業排名[12]。
3.2 政府布局,分工協作
新加坡智庫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獲得較高質量的發展與新加坡政府的布局和大力支持緊密相關。一方面,新加坡大多數智庫建立的初衷是幫助政府應對各類國際問題。作為東南亞的一個小國,新加坡一直致力于探尋在波詭云譎的國際社會中的生存之道。大國靠實力,小國則需要靠“智慧”。因此,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依靠智庫引進人才,對國際國內相關問題進行專業分析,從而為新加坡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指導。據了解,東南亞研究所、東亞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國防與戰略研究所以及政策研究所均由新加坡政府部門根據當時的實際需求而設立,且隨著國內、地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使得這些智庫日益發展成為較為知名的智庫[13]。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大多數智庫均接受了政府的支持。正如顧清揚所說,新加坡政府歷來善于發揮智庫的溝通與橋梁作用,不僅直接出資贊助智庫發展,還鼓勵帶動其他形式的經費投入,并給予智庫充分的自主研究空間[1]。在政府總體布局與大力支持下,新加坡相繼建立起側重各個不同研究領域的智庫體系。
為了避免智庫功能重疊,新加坡智庫或是關注區域有所差別,或是研究內容有所不同,各智庫機構具有較為明確的分工。例如,國際事務研究所重點關注東盟、歐盟以及美國等區域的國際事務發展;東亞研究所特別關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研究;國防與戰略研究所則重點關注亞太地區的軍事、地緣安全;政策研究院側重于新加坡國內的公共政策和國家治理研究。這一特點對于那些與政府部門有直接聯系的智庫尤其明顯。對于全國22 所智庫來說,要想完全避免功能重疊也并非易事,加之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的,因此,智庫間以及智庫跨國合作也是極其常見的現象,這大大提升了智庫研究的效率、深度和廣度。
3.3 官學融合,教研相長
新加坡較為著名的智庫主要坐落于高等學府,尤其是依托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而設立的智庫機構。盡管這些智庫隸屬于大學,但其也會受到政府的資助與支持,各大智庫的核心工作人員通常是在高校任教的知名學者,且享有較高的獨立自主性。由于政府較為重視,不同政府部門的官員也會和智庫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系。例如,拉惹勒南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防和戰略研究所與新加坡國防部,東亞研究所與新加坡貿工部、國家發展部、外交部,均有較為密切的合作,開展咨政研究時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一手資料和數據,以確保咨政服務質量[14]。此外,“旋轉門”(Revolving Door)機制在新加坡智庫發展中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進一步強化了新加坡智庫發展“官學融合”的特點。例如,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駐巴基斯坦非駐地高級專員、駐伊朗非駐地大使王景榮(Ong Keng Yong)現擔任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執行副主席兼國防與戰略研究所所長[15];南亞研究所管理委員會成員艾伯特·蔡(Albert Chua)、李全德(Lee Chuan Teck)、吳德軒(Ng Teck Hean)分別擔任新加坡共和國外交部常務秘書、貿工部常務秘書、外交部副秘書長(亞太/東南亞)[16];中東研究所現任董事會主席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曾在新加坡外交部任職37 年[17];2020 年,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戴尚志(Simon Tay)被任命為新加坡駐希臘大使[18]。時至今日,新加坡政府要員到智庫任職似乎已成行業慣例,盡管由智庫進入政府部門任職的現象不如前者普遍,但目前該趨勢也已有所顯現。
3.4 管理科學,高效運轉
智庫最大效能的發揮有賴于智庫的專業化管理。雖然研究人員才是智庫的靈魂,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組織管理,就算是頂尖的專家也難以發揮出應有的水平,智庫的功效也有可能大打折扣。新加坡智庫大多數雖隸屬于大學或政府部門,但智庫管理一直享有較高的獨立性,并非按照高校管理制度對其進行管理。一般來說,智庫實行的是董事會或理事會負責制。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設立董事會負責研究所重大事項決策,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由國內外知名人士構成的理事會指導管理,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由新加坡政府高級官員、跨國公司董事和學術機構的精英組成董事會負責管理[7]。包括南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國際基金會等在內的智庫機構均實行董事會制或者成立專門的管理委員會。這種較為專業和科學化的管理模式進一步增強了新加坡智庫的運作效率,為智庫的高品質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4 新加坡智庫對東南亞區域治理的貢獻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東盟在調整鞏固的過程中產生了政策分析需求,同時隨著地區局勢的新變化,東盟各國開始尋求建立政策咨詢機制以協助治理,并建立起東盟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SEAN ISIS)。新加坡智庫在其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下,立足于自身特點與優勢,積極參與東南亞及東盟的治理工作,并承擔東南亞區域治理的獻策者、政策解讀者、區域治理合作的參與者以及人才的培育者的責任,為東南亞的區域治理做出了突出貢獻。
4.1 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現實可能性
4.1.1 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現實可能性 東南亞區域治理的現實需要。一方面,二戰結束后,東南亞國家紛紛獲得獨立,如何擺脫殖民時代的政治運作模式,處理好宗教民族矛盾,以避免東南亞地區陷入混亂局面,成為東南亞區域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為解決上述問題,1967 年東盟成立,至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東盟進入調整和鞏固階段,隨著冷戰的緩和,美、蘇在該地區力量的收縮與調整,使得地區局勢發生變化,東盟成員國逐漸意識到需要做出更多的外交努力以適應新的地區安全格局。囿于各國政府人力、物力、財力的有限性及東盟秘書處政策研究、咨詢服務能力的不足,東南亞區域治理的正式結構中產生了政策分析“真空”,這一“真空”恰好為智庫介入區域治理提供了契機[19]。另一方面,東盟不似歐盟一樣具有超國家性質,不具備權威的決策機制。但東盟各國發展水平各異,矛盾紛爭頻發,特別是在涉及主權、領土、安全等較為敏感的話題時。這使得決議、政策等的出臺更加困難,因此,急需一個非官方的磋商平臺促進各方溝通,更好地凝聚共識。智庫依托知識、社會、媒體、專家和政治領域的豐富資源塑造了一個獨立的運作空間,可較為靈活地避免因敏感問題引發的爭端,成為重要的“二軌外交”行為體,這較好地滿足了上述需求。在此背景下,1988 年東盟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這一半官方智庫網絡創始成員包括5 個東南亞國家智庫機構,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基于東南亞區域治理的現實需求,智庫成為彌補東南亞區域治理政策“真空”的重要角色,智庫網絡也逐漸發展成為該區域的“二軌外交”機制,為該地區的治理發展提供了智慧與動力。
4.1.2 新加坡政府的推動與支持 新加坡地緣環境和資源稟賦特殊,自建國以來,其政府始終懷有強烈的小國危機意識,為突破小國“脆弱性”局限,在國內層面、地區層面乃至全球層面,新加坡均力求找準身份定位,以發揮“小國大外交”作用。就地區層面而言,參與東南亞區域秩序的構建對新加坡具有重大意義,即使作為一個小國,新加坡也從來不甘于僅僅是一個“被領導者”。正如隆德新所言,新加坡尋求樹立一種“軟領導者”或是“低姿態領導者”的身份角色。“軟領導”的實現方式主要包括說服、議程設置、吸引與交流。“說服”立足于根據不斷變化的局勢而制定與之相適應的說理方式與戰略;“議程設置”則與說服緊密聯系,在合理預測、分析和說服的基礎上,制定符合共同利益的路線圖,從而影響甚至決定議程設置;“吸引”則需要靠本國的成就與示范作用;“交流”效果的最優化則需要超越僅依靠官方渠道的傳統模式,進行多渠道交流[20]。就此而言,無論是實現“軟領導”的4種方式中的哪一種,智庫均能夠在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新加坡智庫發展中的政府布局特色以及政府對部分智庫的大力贊助中不難看出,新加坡政府早已將智庫作為其實現地區“軟領導”以及推動國內發展的重要幫手。
4.1.3 新加坡智庫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如前文所述,新加坡智庫具備了“量少質優,以質取勝;政府布局,分工協作;官學融合,教研相長;管理科學,高效運轉”等特點,這為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條件。除此之外,新加坡智庫發展歷史悠久,最早的智庫成立于1962 年。可以說,新加坡智庫與國家同時發展壯大,為國內治理獻計獻策的同時,致力于幫助開拓新加坡的對外發展空間,其取得的良好績效使其在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是新加坡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意見領袖作用”的主要抓手。
4.2 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具體表現
在東南亞的區域治理中,新加坡智庫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力地推動了區域一體化進程,尤其是對東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主要作用與貢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4 個方面。
4.2.1 東南亞區域治理戰略的獻策者 新加坡素有東盟的“大腦”與“軍師”之稱,東盟許多的政策和規劃雛形均來自新加坡智庫[15]。作為東盟與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創始成員之一,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始終聚焦于東盟發展的相關問題,著力推進區域合作進程。其官網公布的2017—2021 年的年度報告中均設有“東盟專欄”,此部分內容主要總結分析年度內有關東盟的重大問題和主要議題。從報告內容可以看出,雖然每年的研究重點有所不同,但綜合來看其研究涵蓋的范圍廣泛而全面,且主要是地區熱度較高或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2020 年,該研究所帶頭開展了“東盟合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并向東盟外長和東盟秘書長提交了重要建議,這些建議為2020 年4 月14 日召開的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東盟特別峰會提供了重要參考[21]。在另外一些有關東盟地區機制建設與發展戰略制定過程中,同樣有新加坡智庫的身影。例如,在《東盟憲章》(ASEAN Charter)制定、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下文簡稱ARF)預防性外交議程設置與有關2015 年后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下文簡稱AEC)未來的政策辯論中,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東盟的奠基性文件是一份僅僅兩頁的《東盟宣言》(ASEAN Declaration),直至2008 年《東盟憲章》正式生效前,東盟并沒有一份完整、系統且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文件,亦不具備國際法要求的法人資格。2005 年12 月,起草憲章的動議在第11 屆東盟峰會上被正式提出,成員國隨即組建了東盟知名人士小組(ASEAN Eminent Persons Group,EPG)負責對憲章的起草提供建議。新加坡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較早洞見了這一需求,邀請來自國防與戰略研究所、菲律賓戰略與發展研究所等智庫研究員及其他領域的知名人士進行研討,并于2005 年出版了一部名為《制定東盟憲章: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的觀點》(Framing the ASEAN Charter: An ISEAS Perspective)的手冊,為可能參與憲章制定工作的人提供建議。該手冊內容涵蓋了對東盟旗幟、標識、成立日、目標、原則、組織架構等方面的建議,可以說是一部初具雛形的《東盟憲章》,為《東盟憲章》的制定工作提供了借鑒[22]。ARF 作為一個地區安全機制,是東南亞地區維護自身安全的主要平臺之一,預防性外交是其發展進程中的三大目標之一,不僅體現出鮮明的“東盟方式”特點,還關乎ARF 的自身發展[23]。在邁向預防性外交制度化的努力中,ARF 委托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及另一所研究機構進行了一項研究,旨在吸取其他多邊組織在預防性外交制度化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基于這兩所研究機構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提出了具體建議,成為審議“預防性外交工作計劃要點草案”的討論基礎,并最終使得《東盟地區論壇預防性外交工作計劃》于2011 年7 月獲得通過。在AEC 的建設過程中,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及東南亞研究所同樣扮演了獻策者角色。2013 年7 月,東盟經濟一體化高級別工作組委托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和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編寫了一份“關于2015 年后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愿景文件”,旨在評估2015 年東盟經濟共同體的進展,確定并分析該地區面臨的地區和全球挑戰,以及為AEC提出2015 年以后的政策建議。2014 年2 月,在仰光舉行的第25 次東盟經濟一體化高級別工作組會議上,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和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向工作組提交了最終文件,并獲得了工作組高度肯定[24]。在東南亞區域治理戰略制定中,不止新加坡智庫,各東盟國家智庫均是獻策者,借助智庫網絡的力量,東南亞的區域治理戰略制定更具科學性與合理性,較好地彌補了東盟的“政策真空”。
4.2.2 東南亞區域治理政策的解讀者 智庫的作用與功能之一是通過其研究成果,如出版的書籍、發表的論文、創辦的學術期刊、雜志訪談、政策簡報以及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與多方人員建立有效聯系、進行有效溝通[25],從而引發對有關政策的討論,促進對政策的深入理解,以求政策的順利實施或是改進。新加坡智庫同樣憑借其出版的期刊及發布的各種評論文章,擔任了東南亞區域治理政策的解讀者角色。
以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為例,為了增進對東盟的了解,并為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做出貢獻,該研究所專門成立了東盟研究中心(The ASEAN Studies Centre,下文簡稱ASC)。ASC研究人員在主要的新聞媒體和在線平臺上積極發聲,分享其對東盟發展有關問題和政策的解讀與建議。ASC 通過組織各種活動,如東盟圓桌會議和東盟系列講座,邀請高層政策制定者、知名學者和商界領袖共同探討有關東盟發展的政策理念,以更好地了解東盟。由該中心編寫的《東盟焦點》(ASEAN Focus)季刊通過文章分析將廣大受眾與東南亞的重要發展聯系起來,以增強各界人士對東盟的理解和認知[26]。《東南亞事務》(Southeast Asian Affairs)是該研究所出版發行的另一部影響力較大的旗艦出版物,其宗旨是提供對東南亞地區主要政治、戰略、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和動向的易讀、易懂的分析。自1974 年出版發行以來,《東南亞事務》的研究重點聚焦在東盟國家,同時兼顧亞太地區發展問題[27]。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名譽教授哈爾·希爾(Hal Hill)曾評價《東南亞事務》為了解這一迷人的區域(指東南亞地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南[28]。ASC 榮獲了2020 年度“東盟獎”(ASEAN Prize)[29],此獎項用于獎勵對東盟共同體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個人或組織。ASC 因其促進對東盟的更多了解和認識,以及為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杰出貢獻而成為斬獲此獎項的第一個組織[30]。除ASC外,包括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等在內的多家新加坡智庫的研究領域均涉及了東南亞區域治理政策的分析解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各界人士對東南亞區域發展與治理的認知。
4.2.3 東南亞區域治理合作的參與者 智庫不僅可以為學者、政客、官員、媒體人和商人之間的互動和討論提供機會與場所,還可以通過舉辦各種論壇、學術會議、非正式外交活動等不同方式參與國內外治理工作[31],成為區域治理合作的參與者。
一方面,新加坡智庫通過舉辦論壇活動、研討會、座談會作為其為區域治理發聲的平臺,成為區域治理的“主動參與者”。例如,為了應對緬甸局勢,維持東南亞地區穩定,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于2021 年8 月舉辦了兩次對話活動,分別邀請了東盟十國的22 名主要專家、多名緬甸專家和智庫代表,對話活動強調了東盟對緬甸政變反應的重要性,探討了東盟及緬甸問題特使應采取何種顯示行動和緬甸政變的優先事項問題。該研究所組織了以“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縮小東盟的數字鴻溝”為主題的公共網絡研討會,研討了疫情之下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以及影響東盟數字化發展的長期因素等問題[32]。除此類形式的研討會外,國際事務研究所定期開展代表性活動——“東盟與亞洲論壇”(ASEAN and Asia Forum),從2007 年至2022 年,該論壇已舉辦了13 次,論壇主題主要圍繞東盟與地區發展問題。例如,2021 年該論壇的主題為“從2019 新冠肺炎疫情中復蘇:區域戰略和數字未來”,2019 年的主題為“中美沖突與東盟:生存、轉型、成功”[33]。類似的還包括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東盟圓桌會議”(ASEAN Roundtable)和區域展望論壇(Regional Outlook Forum)。通過舉辦各類活動,新加坡智庫不僅為政界、學術界等各界人士提供了交流研討平臺,實際上還充當起了與區域治理密切相關的研討會的議程發起者,以其敏銳的感知與專業的知識推進了區域治理進程。
另一方面,新加坡智庫也會受邀參與部分有關區域治理的會議或活動,成為區域治理的“被動參與者”。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參與,智庫研究人員的觀點都被輸出到更大地區范圍,影響到不同層次的決策者,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區域治理的方方面面。
4.2.4 東南亞區域治理人才的培育者 由于依托大學建設,新加坡部分智庫同樣提供人才培訓服務,開設有研究生課程。例如,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的使命便包括成為亞太地區戰略和國際事務中領先的研究和研究生教學機構。該研究院聘請國際知名專家和學者教授課程,開設有戰略研究、國際關系、亞洲研究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多樣化的碩士課程。迄今為止,該研究院已為來自66 個國家的學生提供了課程培訓[34],還推出了亞太高級軍官計劃(Asia-Pacific Programme for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APPSMO)、亞太地區高級國家安全官員計劃(Asia-Pacific Programme for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rs,APPSNO)以及恐怖主義分析員培訓課程(Terrorism Analyst Training Course,TATC)。亞太高級軍官計劃由該研究院下轄的國防與戰略研究所主辦,旨在提供交流平臺以供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高級軍官能互相分享軍事和安全發展的專業知識[35]。亞太地區高級國家安全官員計劃由該研究院下轄的國家安全卓越中心主辦,活動面向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級政府官員,成為提供國家安全治理分析框架、治理技能的重要工具[36]。恐怖主義分析員培訓課程則由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研究國際中心定期舉辦,一般邀請專家、反恐學者、分析師和有關從業者交流想法或是實踐經驗[37]。除高校型智庫外,新加坡的部分獨立智庫也為區域治理人才培訓做出了一定貢獻。例如,2022 年3 月26 日,新加坡國際基金會啟動了一項名為數字實驗室(DigiLABS)的志愿服務計劃,在東南亞迎來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時期之際,該計劃將通過其強大的志愿者網絡和行業合作伙伴支持該地區青少年的數字能力建設[38]。2020 年,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成為新加坡國家青年理事會的合作伙伴,為其亞洲就緒青年計劃(Asia-Ready Exposure Programme,AEP)提供專業講座和相關培訓,僅當年舉辦的3 場會議就吸引了800 名年輕人參與[35]。
5 結語
智庫首先在美、英等發達國家發展起來,因此,智庫曾一度被認為是“英美現象”。縱觀學術界現有關于智庫的研究成果,大多數仍聚焦于英、美等發達國家智庫。但在當今世界,智庫不再是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專屬,其正在以更為靈活、廣泛的方式影響著國家治理乃至區域或全球治理,發揮著官方渠道難以發揮的作用。新加坡的治理成就曾令世人驚嘆。作為東盟的“大腦”,同時也作為小型國家成功轉型的“智慧之國”,其成功、有效的治理經驗值得探索與借鑒。“智”離不開智庫,對智庫建設和人才引進的重視是其取得突出治理成效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通過資料整理、梳理出新加坡智庫的發展脈絡,并從中總結其特點。事實證明,盡管數量不多,但新加坡智庫的作用與影響力不容小覷,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新加坡智庫為東南亞區域治理獻計獻策,特別是在東盟發展和東南亞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本文列舉了新加坡智庫在《東盟憲章》制定、ARF 預防型外交議程設置與AEC 2015 年后政策辯論中所起的獻策作用。此外,新加坡智庫時刻關注東盟、區域發展的最新動態,在緬甸局勢問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諸多棘手且嚴峻的問題上,貢獻了獨到的見解與智慧,為應對區域發展與治理中的新老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其次,新加坡智庫借助出版的書籍、刊物、簡報等渠道進行政策解讀與宣傳,發揮了政策解讀者的作用。專注研究東南亞區域的智庫這一點尤為明顯,如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發行的《東盟焦點》《東南亞事務》均是各界人士了解有關區域治理政策的重要窗口。再次,新加坡智庫積極參與區域治理活動,主要包括兩種途徑:其一,主動舉辦或承辦有關活動,包括學術會議、論壇及非正式外交活動等,較為典型的是由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定期舉辦的“東盟與亞洲論壇”和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舉辦的“東盟圓桌會議”;其二,智庫專家與研究人員受邀參與區域治理工作,成為區域治理的“被動參與者”。最后,新加坡智庫為區域治理培育治理人才,例如,新加坡國際基金會的數字實驗室志愿服務計劃,國防與戰略研究所主辦的亞太高級軍官計劃等。
由此可見,新加坡智庫一直致力于發揮智庫典型功能,積極為區域治理獻計獻策,提供咨政議政服務,積極參與治理工作,并為區域治理培養人才。在將來,新加坡智庫仍將緊跟時代潮流,繼續為東南亞區域發展與治理貢獻智慧與力量,在更多方面或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是否具有更為科學的方法來系統衡量這種作用與貢獻?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如何?這將是未來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