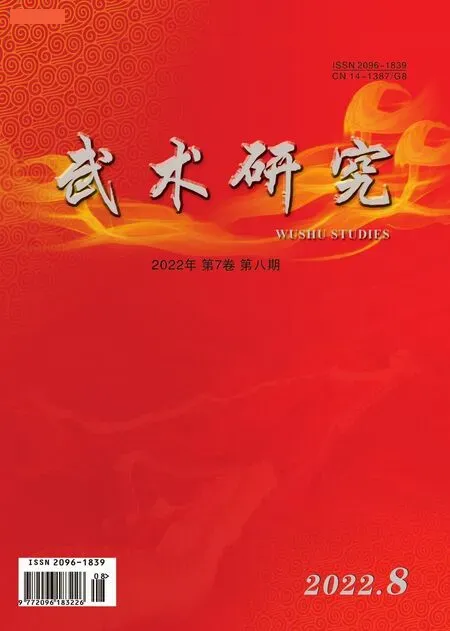武術視角的老子“利物”思想研究
朱安洲 喬鳳杰
1.上海交通大學,上海 200240;
2.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
“利物”是指老子思想中取法于道生之化育,并實踐于治世的思想內容。在老子看來,萬物依“道”而生,“道”養育萬物而成。根據“依道治世”的邏輯線索,老子希望統治者能夠善待百姓,輔助百姓。老子有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第八章》)“利物”的字面意思是指滋潤萬物,而作用到治世當中則是一種利民之德。老子“利物”的思想可以分為以下三層來理解:第一,老子認為自然的規律是利物而不害物,即“利而不害”;第二,老子認為圣人在治世時常常輔助萬民的自然本性而不加以干預,即“輔而不為”;第三,老子認為圣人施與而不求回報,給予而不圖索取的做法可以消解君民之大怨,即“執契不責”。“利物”思想的這三重含義主要代表了圣人治國愛民的方法與理念,而武術作為一項社會文化活動,其中存在的教育和管理等現實問題,都能夠從老子的“利物”思想中得到啟示。
1 武術視角的“利而不害”
老子認為統治者要多幫助而不要傷害百姓。老子有云:“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八十一章》)“利而不害”是老子“利物”思想的首要內容也是基本要求。老子把“利而不害”看成是自然規律,即自然的做法就是“利物”而不害物。老子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第八章》)老子發現“水”具有“柔弱、處下、利物和不爭”的特性與作用,而“道”也這樣,所以他認為“水”接近于“道”。人們要取法于“道”,自然就要做到“利而不害”。“利”在這里就是指“不積”“為人”和“與人”。老子認為越是幫助別人自己越富有,越是為他人做奉獻自己越有所收獲。“不害”的字面意思就是指不傷害,在其他章節中意義也是如此:“往而不害,安平太。”(《老子·第三十五章》)“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老子·第八十章》)然而“不害”具體所指乃是不要逼迫和壓榨百姓,即老子所講的“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老子·第七十二章》)。
“利而不害”應該作為武術教育的基本精神。武術教育者要盡可能地幫助學生而不要去傷害學生。武術是中國最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這項運動已經從未中斷地傳承了上千年。之所以能傳承發展這么久,除了武術自身的魅力之外,武術教育在其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武術教育最被人稱道的地方就是武術中親密的師徒關系。中國傳統武術的師徒關系和現在學校教育中的師生關系存在巨大差異。現在的師生關系更像西方教育理念下的契約關系,因為“契約”存在所以才建立起師生關系,當契約不存在了師生關系也就淡漠了。而傳統武術中的師徒關系是終身制的,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即使師徒不在一起,但是他們還能保持緊密的聯系和親近的關系。之所以能夠這樣,乃是因為中國武術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老子講“利而不害”,而武術中的師傅就很好地踐行了這一點。傳統武術中的師傅將徒弟視如己出,總是想方設法幫助自己的徒弟,而且不去傷害他們。當徒弟的利益受到傷害時,師傅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打罵體罰學生是現代教育所禁止的教育方式,但在武術訓練中這反而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然而奇怪的是徒弟卻好像根本不會記仇,隨著時間的增加,徒弟對師傅的感情反而會與日遞增,甚至會產生一種依依不舍的感情。從筆者多年的習武經歷來看,徒弟和師傅不記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師傅做到了“利而不害”。師傅會真正幫助徒弟,而不會去做傷害徒弟利益的事。至于那點皮肉之苦對于武者來說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更談不上是什么傷害。什么時候徒弟去找師傅,師傅都會有求必應,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于這樣的師傅,武者如何能夠不愛戴?“利而不害”也應當作為武術管理的基本原則,武術管理者要盡量幫助而不要傷害習武者。何為不要傷害?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武術管理者不要做壓榨和強迫習武者的事。例如,在某些少體校,校方會強迫學生購買器械和定制隊服而趁機斂財,器械要求每半年必須更換一批,隊服一年會要求定制春夏秋冬款,這無疑給學生父母增添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少體校習武的學生不比現在參加興趣班或聘請私人教練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家庭條件一般,而且他們的父母在支持孩子習武這件事上已經比其他普通在校學生的家庭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如此只會有損學生習武的積極性,長此以往必將影響武術的傳承與發展。筆者主要是想以此來強調武術管理者在管理武術時不要強迫和壓榨習武者,否則這些行為會嚴重傷害到武術愛好者的武術參與行為。
2 武術視角的“輔而不為”
老子認為統治者應該遵循萬民的自然本性,給予輔助和引導,而不應該橫加干涉、胡作非為。老子有云:“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這是“無為”思想的表述也是“利物”思想的代表,代表了“利物”的作用方式。“輔”就是輔助、協助的意思(任繼愈,2006:143)。“輔”是老子“利物”思想的一個主要“動作”。在圣人與百姓的關系中,老子希望百姓為主,圣人為輔。百姓處于首位,圣人居于次位。圣人給予百姓的幫助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而是潤物無聲的輔助。老子有云:“太上,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他認為君民最好的關系就是百姓只知道有君主而已。也有版本寫作為“不知有之”,那這種說法就更加意味深長了,就是說君民最好的關系就是百姓都感覺不到君主的存在。事情辦成了,百姓都認為他們本來就是如此。可見,圣人的這種“輔”已經達到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境界。
“萬物”既可以指廣義的自然界萬物,也可以理解為狹義的萬民,在此主要是指萬民(董京泉,2008:458-459)。“萬物之自然”也就是指萬民的自然本性與訴求。萬民的自然本性與訴求具體是指什么?在筆者看來,老子認為萬民的自然本性是“化、正、富、樸”,也就是他所講到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五十七章》)。萬民的自然訴求是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子·第八十章》)。“不敢為”也就是不敢妄為、不敢胡作非為的意思。君主違逆百姓的自然本性與訴求就會遭到百姓的唾棄與反抗,君主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古之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其實民心的得失主要就在于統治者是否尊重百姓的本性和能否滿足百姓的訴求。“輔而不為”可以作為武術教育的作用方式。武術教育工作者在面向學生開展武術教育時應該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借鑒“輔而不為”的思想就是要求老師在教育學生時要盡量多引導輔助,少干預限制。實際上最關鍵的就是做到兩點:“輔”和“不為”。“輔”意味著老師和學生在教育關系中,老師是輔助者,學生是被輔助者。老師要以學生為中心,針對學生的自身情況和個人需求來實施教育行為。一方面,“輔”的前提條件是老師需要了解學生的自然本性和個人訴求。每個學生都有自身特點,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如果老師對此做不到清楚明白,也沒有辦法很好地引導輔助學生。一些老師也做了很多自己認為對學生好的事情,但這些并不一定符合學生的客觀情況,其結果就是既得不到學生的認可,也起不到實際上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這種教育行為從外表上看是一種隱性或柔弱的方式。對于學生來說,最好的感受就是自始至終都感覺不到老師的存在,而實際上老師卻給予了學生很多幫助與關懷。特別是對于武術學生而言,這點尤為重要。練武的學生一般性子都比較火爆,如果老師的教育方式太生硬,練武的學生就會產生強烈的抵觸心理。哪怕是對學生再好,學生也不領情。武諺有云:“師徒之間心不齊,手里黃金要變泥。”師徒之間貌合神離,教育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不敢為”就是要求老師在實施教育時不能妄為。所謂不能妄為就是指老師不應該違背學生的自然本性而單憑個人的意志來開展教育的行為。在武術教育里,“不敢”顯得尤為精妙和藝術。武術老師教學生哪有什么可不敢的?但作為一個“輔而不為”的老師就真的會有所不敢,他所不敢的是誤人子弟。這個“不敢”既體現了武術老師對教育的謙遜和敬畏,也彰顯了老師個人修養的武德。莊子有云:“災人者,人必反災之”(《莊子·人間世》)。武諺亦有云:“誤人子弟者,必被子弟誤。”能夠以此為戒的老師才是好老師。
“輔而不為”可以作為武術管理的作用方式。武術管理者在開展武術管理時也要注意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應該強行妄為,要遵照武術發展的自然規律和武術人的自然本性來開展引導輔助性工作。依老子的邏輯來看,武術人的自然訴求至少應該包括生存、富足、練武和成就這幾個方面。生存和富足是大部分人的共同訴求,練武的權利和取得武藝成就是習武之人的專屬需求。假如有一天剝奪了武術愛好者練武的權利,可想而知是什么后果。習武者或多或少都會想在武術方面有所成就,這個成就不一定非要是打比賽奪金牌,得到其他形式的認可也算是武者的一種成就。如果管理者不能滿足武者的基本需求,甚至違逆廣大武術愛好者的意愿,那恐怕武術管理將無從談起。同時,在滿足武者的基本需求和遵循發展的自然規律之外,武術管理者還應該注意管理方式。較為理想的管理方式也是采用一種柔化的管理手段,最好是能做到治理于無形,不要以管理者為主,而要以廣大武術愛好者為主。管理者做好輔助和引導工作就足夠了,切莫做沒有建設意義的強行干預。武術管理者要多做調研并且深入調研,切實了解武術愛好者的自然情況和真實需求,然后針對性地開展管理工作。
3 武術視角的“執契不責”
老子認為統治者應該施與而不求回報,給予而不索取。《老子》第七十九章中有云:“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簡而言之就是“執契不責”。“執契不責”是老子“利物”思想的又一層涵義,主要體現了“利物”而不求回報的境界。所謂“左契”,古時候人們刻木為契,剖分左右,各執一半,以求日后相合符信,左契是負債人訂立的,交給債權人收執,就像今天所說的借據存根。“不責于人”也就是不向人索取償還。“司契”意為掌管借據存根,“司徹”意為掌管稅收(陳鼓應,2003:342-343)。老子認為即便大的怨恨得以調和也必然還有余怨,就算以德報怨也還是不能妥善處理。老子認為妥善的處理方式是給而不要,就好比手執借據卻不向人索取一樣,這樣也就沒有怨恨可生。有德的人就像手拿借據而不索取的人,無德的人就像掌管稅收而逼人交稅的人。老子所講的“執契不責”也是一種“利物”之德,他旨在強調施政者要多給予而不求回報,少索取而不傾軋于民。給而不索取,施而不求報,老百姓就會感恩戴德,不與為政者積怨。反之,為政者如果非但不幫助百姓,還要用賦稅來榨取百姓,就會使百姓心生怨恨。怨恨一旦形成再想要化解就沒那么容易了。
“執契不責”的思想可以指導武術教育者建構良好的師徒關系。在武術中,人們對師徒關系看得特別重要,對師德和師恩推崇備至。武諺有云:“師徒如父子,情親似海深。”父子關系幾乎是這個世界上再親密不過的人際關系之一,而將師徒關系比作父子關系,這充分體現了武者對師傅的尊敬。父親對孩子具有生養之恩,總是想方設法地幫助和照顧孩子,什么都想給他最好的,而且從來不圖回報,甚至甘愿為其犧牲性命。而武術中的師恩也毫不遜色,師傅將徒弟視如己出,竭盡全力將平生所學傳授給他,還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除了沒有生育之恩兩者沒有多大差別。所以,在武術中才會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武諺有云:“尊師要像長流流水,愛徒要像鳥哺雛。”無論是“如父子”還是“像鳥哺雛”都體現了老子“執契不責”的“利物”思想。
“執契不責”思想有助于糾正和打擊武術界的“拜師”亂象。拜師儀式本是產生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在武術中傳承至今的一種確認師徒關系的儀式化方式,但卻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其變成借機斂財的工具、各取所需的伎倆和沽名釣譽的手段。徒弟故意大擺陣仗,以表示對師傅的尊重,以期討得師傅的歡心,借師傅之名聲獲得自身之江湖地位;師傅也樂意徒弟這樣鋪張浪費,以獲得經濟上的利益,以期獲得對徒弟索取的權利,借拜師形式沽名釣譽一回。老子有云“絕偽棄詐,民復孝慈”,棄絕偽詐,人們可以恢復孝慈的天性。師慈徒孝絕不靠一次隆重的拜師儀式就能表現出來,有些人無非是想利用拜師這種形式表示自身的與眾不同,借機享有一些特權。我們應當適時撕去有些拜師儀式的偽詐面具,還武林以風清氣正。正如老子所講的“六親不和,有孝慈”一般,當師傅做不到“執契不責”時,才會通過拜師這種形式來約束徒弟。其實如果師徒二人都很有武德,何需用一個拜師儀式來增進感情。一個愿學,一個愿教,教的人傾囊相授,學的人虛心求教。如果有一天,師無所可教,徒無心而學,那就換師易徒。有些人會認為這樣就是不尊師重道,不利于武術的傳承。筆者則認為不然,尊師重道不應該流于形式,傳承發展也不是靠一次虛榮浮夸的拜師儀式就能夠完成,這樣的儀式其實也不能說明徒弟對師傅有多尊敬,師傅對徒弟有多愛惜。但是,筆者并不是反對所有的拜師行為,那些不以名利為目的且有利于增進師徒感情的行為還是值得提倡的。
“執契不責”思想有助于調和武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關系。武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相互依存的共同體,兩者不能完全脫離彼此而獨立存在,但處理不好二者關系也會導致矛盾沖突。特別在出現權力失衡和供需錯位的情況下,兩者的關系更容易破裂。作為擁有權力的一方,武術管理者應該具有“執契不責”的精神和智慧。“執契不責”的思想啟發武術管理者在管理武術時要盡可能地多給予被管理者幫助與支持,并且做到給予而不索取,幫助而不求回報。武術運動的有序開展和進步發展離不開管理者的統籌管理和幫助扶持。而要完成幫助和扶持,就離不開財力物力的供給。武術管理者就如同手持借據的被借貸方,處于主動分配資源的地位,而被管理者就像借貸方一樣需要得到資助。作為被借貸方,既可以選擇給予也可以選擇不給予,既可以要求回報也可以不要求回報。而老子給出的建議是要給予但不圖回報。因為這樣做有利于得到被管理者的好評,而且不易導致積怨產生。就好比人們求神拜佛一樣,因為有求必應還不圖回報,才會有那么多的人頂禮膜拜。如果神佛不給予幫助,或者幫完了非要得到人們的好處,人們也就不會那么虔誠了。武術管理者不是神佛,沒有無所不能的神通,可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圍之內盡量幫助需要者也會得到人們的感激。如果還能做到不圖回報,那么就會有更多的人愿意服從管理。反過來,武術管理者如果非但不幫助習武者,還總想從武者身上索取些利益,那么就勢必會與武者積怨。當怨恨達到一定程度,再想亡羊補牢就為時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