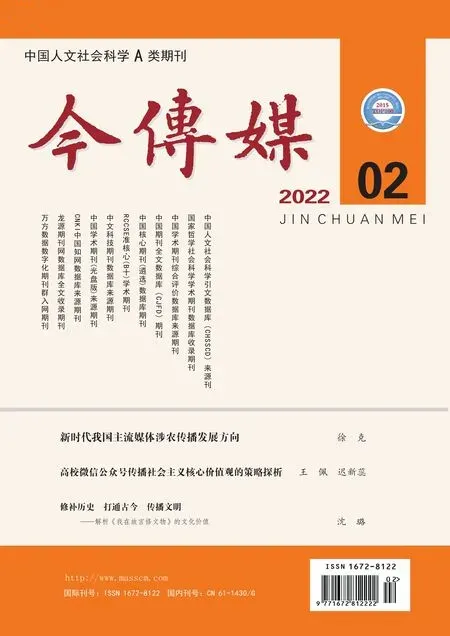文化傳播的多維敘事圖景
——以 《覺醒年代》為例
宣振宇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文化傳播的策略需要應時而變。《覺醒年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之作,以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 《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時間線,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與其他歷史劇一樣,《覺醒年代》的主題依舊是革命、救國、傳承,但其新穎之處在于以民國時期的思想爭鳴作為出發點,從封建王朝走向民國的意氣風發,展示了有識之士的思想覺醒。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志士之間的交流、討論,推動著中華民族走向新時代,再現了百年前每位革命先烈的鮮活形象。《覺醒年代》不同于其他歷史劇,其以多維度視角展開文化傳播,形成了生活化、儀式感、符號化、身體嵌入等多角度的文化敘事圖景,打破了過去影視作品單一的敘事模式。
一、敘事基調生活化
影視作品的情感表達與傳遞一直是受眾關注的焦點。多數情況下,受眾不僅關注影視作品所表現的情感維度、情感關系,更關注情感的修辭效果。歷史劇的敘事通常通過英雄式的主角光環來刻畫。《覺醒年代》側重敘說了陳獨秀的家庭生活,其與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之間的矛盾在劇中著墨較多,刻畫了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旗手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陳獨秀在決意喚醒民族與國家的心聲吐露于廣大民眾之后,受到了陳延年、陳喬年的認可,從而豐滿了其個人形象,打破了過去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新青年》雜志的創辦者的單薄形象,體現了其作為父親的不易。在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職前,校長蔡元培“三顧茅廬”,親自登門拜訪,從側面反映了陳獨秀超凡的個人魅力。
此外,還有李大釗回家鄉時的情節:妻子在家中捉雞做飯,孩子們在院中玩耍,一句“憨坨回來了”讓李大釗的個人形象從嚴肅轉換到了質樸的丈夫和父親角色。李大釗炕上教孩子下棋的畫面、生活窘迫時對孩子說“吃羊肉塞牙”的善意謊言、與工友們共同過年的生活場景等等,這些生活化的敘事,在影視場景的視覺沖擊下得以呈現。
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敘事的生活化更能貼近觀眾。過度渲染人物本身的歷史光輝形象會拉遠觀眾與歷史人物的距離,而個性化與生活化的敘事基調在《覺醒年代》中得以施展,歷史英雄人物不再是遙不可及,進而提高了觀眾對歷史劇文化傳播的接受度。
真實人物自然是原型敘事,虛構人物往往是聚集眾多人物原型的經歷與特點創造而形成的。如劇中虛構角色張豐載的設定,就是結合了眾多歷史反面人物的性格去進行刻畫的,屬于劇作方的有意搭建,在重要事件中擔任著破壞者與阻撓者的角色,是一種逆向傳播。對反面角色進行敘事是歷史劇創作下的一種反向傳播,生活中存在兩面性,一味地正向傳播容易導致人物性格與形象失真,也容易使歷史劇的文化傳播產生斷裂風險。在主流人物及話語外反向呈現主題,增強了正面敘事的力量,生活化敘事的基調得以鋪陳開來。
劇中的“覺醒”,更多的是從文化思想層面展開敘事,文化傳播中人的因素尤為顯著。陳獨秀的激昂,不是單獨的一份力量,是在有著共同思想信仰的同志的擁護下持續傳播的,革命過程中遇到了來自以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保守組織的圍追堵截,烘托出思想覺醒之路走得異常艱難,是配合生活化敘事之外的人物個性化嘗試。
二、敘事空間場景化
“傳播儀式觀”創始者詹姆斯·凱瑞指出,“儀式”包括上至宇宙觀的認知,下至具體的實踐行為,具有多維解讀的可能性。傳播與儀式在形成團體、分享意義方面具有一致性,傳播是歷史與傳統的共享,即共享文化的過程。通過傳播,社會成員彼此互動產生情感共鳴與身份認同,世代相傳的文化價值觀得到傳承,形成一個有秩序、有意義的“文化世界”。
在場景的安排下,儀式感得以搭建,其中的文化與思想也在共鳴中得以傳承。《覺醒年代》中多次出現演講的場景:從陳獨秀的日本初談國事開始,到回國后在朋友間的志向表述,再到上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后力推 《新青年》的發言;還有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的就職演說等等,都是創作者建構的一種具有儀式感的場景規訓,觀眾在不自覺間就陷入具有龐大吸引力的儀式框架,即在選定的固定場景中感受到了一種儀式的嵌入,從而獲得高度的被互動性。
在演講之外,場景的建構從個體開始擴展到雙人乃至多人,互動性逐漸顯現。如胡適與黃侃之間關于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唇槍舌戰,以白話文獲得滿堂彩為結局,引發文言文擁護派的強烈不滿,文化傳播從自發階段走向自覺階段。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他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及群體意識需要提取該記憶的延續性……盡管集體記憶是在一個由人們構成的集合體中存續著,并且從其基礎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才進行記憶”。
集體的聚攏始終是 《覺醒年代》嘗試呈現的一種文化傳播圖景,“覺醒”不是個人的事情,需要依賴多人的共同協作。陳獨秀的交際圈都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忘我奉獻的愛國志士,他們為國家考慮諸多,歷史上的集體吸附著后來的觀眾集體。
電視劇 《覺醒年代》的畫質類似電影,在敘事時注重質感的把控。劇中,魯迅出場時,搭建了一個對比強烈的環境,圍觀行刑場面看熱鬧的民眾、需要血饅頭救命的民眾,與以魯迅為代表的冷靜洞察者融為一體,通過鏡頭的蒙太奇效果完成魯迅人物出場的渲染作用。再如毛澤東的出場,是一段在雨中過街市的場景,在并不漫長的時間里,將社會百態一一展現開來,過路的富商大賈,鬧市里的販夫走卒,在鏡頭里得到充分的展示,把社會的階層分化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人物出場的特定場景里,對比儀式得以建構,產生了高度的情感共鳴,繼而把年代的集體記憶嵌入觀眾的意識之中。
三、敘事視角全知化
敘事視角是敘事作品中觀察和講述故事的角度,可分為全知視角和有限視角。其中全知視角是自由度最大的敘事視角,能夠對敘事對象進行全面的觀察甚至深入人物內心,但同時也拉開了敘事者與敘事對象間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文本的真實性。
《覺醒年代》中的全知視角頻繁出現,如在毛澤東的出場畫面中,配合出現的牛耳向觀眾傳遞了一個重要訊息:毛澤東將是引領中國革命的關鍵人物,即“執牛耳者”。敘事人以第三人稱提前展現出仍未發生的事情,超越了時間的規定性,樹立了全局觀,進而引發了觀眾的民族自豪感。
情節安排之外,李大釗的臺詞“我們不能總是在十字路口徘徊了,到了該決斷的時候了”同樣是全知視角敘事的延伸。盡管這句臺詞很簡短,卻飽含著對中國屈辱歷史的無盡感傷,也飽含著怒其不爭的憤懣心態。其后的決斷便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中國迎來了文化層面的大變革,十字路口的徘徊成為歷史,期待的國民性覺醒了。全知敘事視角的滲入再一次提升了文化傳播力度,烘托了敘事者與觀眾之間的共情氛圍,敘事作品本身的內容更加流暢地嵌入受傳者一方。
全知視角的敘事在 《覺醒年代》中屢見不鮮,借助視覺媒介的鏡頭語言、畫面濾鏡等形式,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對歷史情節本身存在心理預期,能夠更加深入地體會作品細節。
四、敘事手段符號化
傳播符號學奠基者皮爾斯提出了“符號三分法”,其按照符號與對象的關系,將符號分為像似符、指示符與規約符。其中規約符是依賴社會約定俗成的關系而存在的符號,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相對應的聯系,往往需要依靠解釋者的思維與指代物之間的聯系而進行解碼。
《覺醒年代》里,規約符的使用首先體現在食物上。陳獨秀在日本吃盒飯發表“片面”言論被中國留學生呵斥后,李大釗拿出自己的干糧解困,是以食物作為規約符號進行隱喻,“干糧”指代著溫飽問題未能解決。陳獨秀回國后在朋友的出版社里接受歡迎儀式時,兒子陳延年出于報復準備的荷葉黃牛蹄事件,“食物”則指代著陳獨秀作為革新者不被理解的無奈,而后陳獨秀父子和好,荷葉黃牛蹄再次作為規約符出現,隱喻著理解需要時間的淬煉。陳獨秀前往北京談雜志籌資事項時,向北京當地人學習火鍋的地道吃法,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迎接胡適回國的特色飯局,包括后來北京大學教授團請辜鴻銘參與辭退英國籍教員談判的特別宴席等諸多場合,都是以食物作為規約符,是對思想文化進行的隱喻,表達了破壞與重建的意圖,文化傳播的隱喻建構得以完善。
劇中所使用的符號還包括宴席名菜里蓄勢待發的青蛙,人物演講中不停爬行的螞蟻,街道上任勞任怨的牛等等,不勝枚舉,以動物隱喻人物,是賦予動物以人性,大千世界里的萬物皆可符號化,希冀在需要革新的年代里,作為主體的人——國民可以投入時代的潮流,大展拳腳,真正覺醒。
五、敘事意象身體化
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考出發,身體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注重身與心的合一,“蘊含了身與心、感性與靈性、自然與價值、生理和無意識,且在時空中動態生成、展現的生命整體。”
人類的身體符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此重視,身體文化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具有使用價值。《覺醒年代》中,文化人士見面時的鞠躬行為是民國時期文化圈層認同感的建構,告別了過去跪拜的傳統,映射著走向新時代的蓬勃氣息。觀眾雖在屏幕之外,也被轉向了精神層面的意識在場,從而完成文化傳播的認同建構。
視覺文化的消費在本質上是“景觀”消費,德波提出的“景觀社會”理論能夠成為解讀新媒介空間中身體景觀的社會結構背景。他認為各種堆積的景觀成為貌似真實的存在,而真實的生活世界卻被影像所遮蔽。身體在各種符號化塑造和幻化下,以虛擬方式替代了肉身存在,成為新媒介空間中的網絡秩序存在和日常生活方式。
歷史劇 《覺醒年代》中利用身體的景觀來傳播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同樣是消費著媒介空間中觀眾的吸引力,從而完成對文化傳播的身體意象的使用。該劇在介紹陳延年、陳喬年兩位愛國青年的最后歲月時,也是以腳下的鎖鏈為意象,演員身上綁著真實的鎖鏈來回走動,為了演繹出真正的歷史現場感,身體的沉重行走,對屏幕外的觀眾而言是一次新型的消費,從文化傳播角度看來,是觀眾情感的螺旋上升。不同于“景觀社會”中的遮蔽與替代,《覺醒年代》嘗試從身體意象的角度來展現和表露一個年代的風貌。
六、結 語
《覺醒年代》作為獻禮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歷史劇,其承擔的文化傳播責任巨大。從劇作的敘事方式、身體意象、符號使用等多維度進行研究與分析后,觀察到該劇在文化傳播方面進行了一定的創新與發展,在符號的選擇、場景的搭建、身體的意象上挖掘出新的著力點,為之后歷史劇作品的輸出提供了一份可以借鑒的樣板。《覺醒年代》這部重大歷史題材劇,從多維度將中國故事敘述得鮮明、生動,切實講好了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