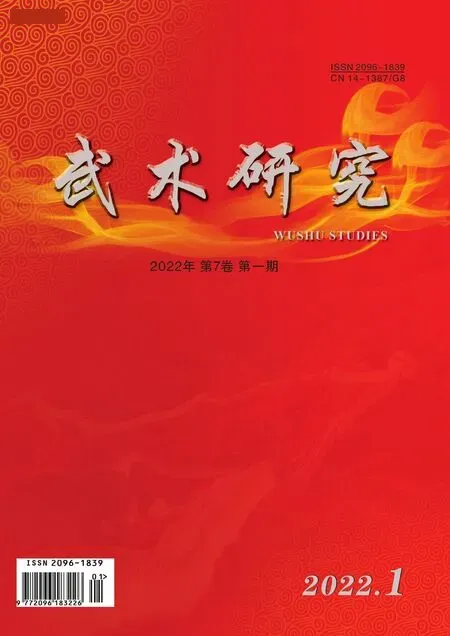中國兵器技擊的演變特征解析
李東洋 陳嘉豪
鄭州財經學院體育教學部,河南 鄭州 450044
1 中國兵器技擊的演變特征
1.1 由“繁榮”走向“落寞”
“多樣化與多元化的兵器實戰技理群的遺失”是兵器技擊變化的顯著體現,這里的“多樣化與多元化”指多樣化的同種與異種兵器之間的實戰技術對抗。冷兵器時期為了滿足戰爭多樣化的作戰需要出現劍對劍、刀對刀、刀對槍、刀對棍等短兵與短兵、長兵與長兵以及長兵與短兵之間的技理對抗,如據史料加載,漢代出現了“斗劍”“劍對戟”“劍對鉞”“戟對劍、鉤鑲”“空手入白刃”“棍對棍”“劍、盾對劍、鉤鑲”“戟對戟”“劍盾對雙戟”等多種兵器技擊的攻防格斗。因此,縱觀整個兵器發展史,正是由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戰爭的孕育,才使得兵器技擊的發展展現出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到了現代,兵器技擊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理應得到更好的繼承與弘揚,以此來使民族文化源遠流長。但現狀是自從民國時期長兵和短兵誕生以來,便一直沿著這個軌道發展,基本沒有關于其他兵器種類的技擊,其次是在“四高三低一冷”的影響下,長兵和短兵的發展如逆水行舟,基本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最后再加上短兵、長兵自身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導致其也并沒有很大程度上在社會大眾中得到普及。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是,現代兵器技擊技術群只能看到同種兵器之間的技術對抗,基本沒有異種兵器之間的技術對抗。雖然異種兵器之間的技術對抗還存在著很大的質疑,但是這并不代表著沒有可能,因為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想象力遠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動著進步。想象才是知識進化的源泉。”況且兵器技擊又有著源遠流長的發展歷史,因此加強兵器技擊的實踐才能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1.2 由“技擊”走向“審美”
據中國武術史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國家之間的利益紛爭,使得戰爭頻繁爆發,因此,參軍入伍的人數眾多。而在軍事戰爭中,由于士兵身體素質的強弱和技能水平的高低往往成為決定戰斗力的重要因素,從而推動了習武練兵活動在社會大眾中的普及,如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到的“技擊強、武卒奮、銳士強”的史話。同時,伴隨著荊楚長劍的問世,使這一時期盛行起來了論劍與佩劍之風,從而百姓多有“劍癖”的行為習慣。據《莊子》記載,昔日趙文王喜劍,養劍士、門客上千余人,日夜不停的“相擊于前”,另一方面,從“莊子說劍”“越女論劍”所闡述的劍術理論水平之高,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兵器技擊發展情況。再加上當時的社會制度,即“社會對武士有多種需求,或做談判后盾,或為謀殺刺客,或為血親復仇,或作為護衛保鏢。”更加拓展了兵器技擊的活動范圍。
到了漢代,國家的“教民以應敵”政策,使得兵民合一、同仇敵愾,共抵御外敵的入侵,如1975年成都曾家包出土的東漢一號墓東后室北壁下部記錄圖則反映了當時的訓練生活情景,還有兩晉時代的世襲兵役制也是其具體體現,從而推動了習武練兵活動在百姓中的普及。
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武舉制度的創立,同樣擴大了習武練兵的人群,如邱丕相主編的《中國武術史》介紹:“制舉武科考試是面向社會大多數人的,有庶民、衛官、現役軍官、現役文職官員、科舉落第者等多種”,在考試內容方面,包括了射長跺、騎射、馬槍、步射等項目。
到了宋元時期,則出現了專門的武學教育,使得武術訓練朝著更加科學、系統的方向發展,同時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的民間武藝結社組織,如“英略社(使棒)”,也推動了習武練兵在民間的普及。
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國家對武術的重視程度增加,出現了專門的武術管理機構,使得競技武術映入社會大眾的眼簾,競技武術通過類比模仿西方競技體操的運行、評判模式來進行文化的推廣,再加上其在學校、社區、戲劇、電影中的開展,使得兵器技術的發展由“技擊”走向了“審美”。
1.3 由“一體”走向“多元”
溫力教授在其著作《中國武術概論》中以刀、槍、劍、棍為例講解了冷兵器時代傳統武術技術圓融一體的發展走勢,其中傳統武術技術體系是包括了套路演練、格斗對抗以及圍繞兩者而產生的功法練習等內容。其中套路的作用在于銜接單個技術動作,使之訓練起來更加方便,從而提高訓練效果,其次還有便于傳授、記憶的作用。格斗對抗是直接進行攻防能力的訓練和實戰經驗的積累,以及檢驗武術套路訓練中所獲得的某些技能、體能運用于實際對抗時水平高低的手段。在內容上包括了單勢的對抗練習和自由發揮的對抗練習。例如,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詳細記載到了六合槍法的訓練方法,“長槍,單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須兩槍對較,一照批迎切磋,繃擠、著拿、大小門圈穿,按一字對戳一槍,每一字經過萬遍不失,字字對得過,乃成武藝。后方可隨意應敵,因敵制勝”。“比槍,先單槍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槍對試、真正交鋒”。這段話的意思是單人學槍,首先進行進基本的手法、步法、身法練習,然后再進行“繃擠、著拿、大小門圈穿”等內容反復雙人對練,最后再“復二槍對試、真正交鋒”。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槍法拆招、喂招、實戰的訓練過程。另外,六合槍法在《紀效新書》中是以套路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兵器技擊和套路演練是密不可分、唇齒相連的兩個部分。
而到了現代,在競技武術的影響下,兵器技擊和套路演練朝著兩個相互平行的方向發展,各自成為一個運動項目。正如周偉良而言“雖說改革開放后的散打運動是對原有單一套路比賽形式的補充,但在技術結構上套路和散打不再是有機整體的‘舞對合彀’,而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而對于兵器技擊而言也是相同的道理。由于兵器技擊和套路演變兩者之間的不同的內在作用機制,使其朝著“練為戰”和“練為看”的價值追求方向演進,進而導致了“擊舞殊途”發展境地。
2 文化主題的變遷引領著中國兵器技擊發展特征的嬗變
文化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發展趨勢。不同的時代由于政治策略、生產水平、科學技術、需求創造、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也使得其物質條件、價值觀念、精神訴求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從而造成了文化主題的變遷,而文化主題的變遷也并不是多種物質條件單向作用的結果與機制,同樣它還會對其他的方方面面造成影響與改變,而武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份子,不可避免的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相應的改變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從而使自身獲得生存的方式。本文從社會背景、精神訴求、目標導向三個方面的文化變遷對兵器技擊發展特征的嬗變緣由進行闡述。
首先是社會背景的不同決定了其由“繁榮”走向了“落寞”。而這里的社會背景包括了軍事作戰方式、社會發展進程、科學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在內。冷兵器時期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各個國家之間隨時都面臨著戰火即發的狀態,因此提高本國的軍事實力是其首要的任務,如春秋戰國時期以戰車數量的多少來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從中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為了提高其軍事戰斗力,君主、將領想方設法的從各個方面著手,從而推動了兵器的演變、技術的發展以及民間的普及。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便出現了火器,由于火器在士兵作戰過程當中的價值功效上明顯高于冷兵器,從而推動了火器在軍事戰爭中的普及,而火器在軍事戰爭中的普及和升級不僅是技術問題,同時也需要巨大的軍費,使得現代國家基本路線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進而社會各階層都有了明確的分工,生存已經不再是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問題,而當自身處境受到威脅時人們又會利用法律武器來進行自我保護,正如李印東老師所言:“兵器技擊只能在很小一部分人群中開展。”因此兵器技擊的發展由“繁榮”走向了“落寞”。
其次是精神訴求的不同決定了其由“技擊”走向了“審美”。武術的發展是走向技擊還是走向審美,不是由其自身決定的,也不是由官方主導的,最終原因還是要歸結于大眾的選擇,不管是受什么因素的影響,但最終還是大眾的選擇。冷兵器時期戰火肆起搞得民不聊生,因此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國泰民安、安居樂業、健康長壽、子孫滿堂,但是由于生長在動蕩的年代里,很多事情便身不由己,出于本能的反應,習武練兵是其最佳的選擇,不但能夠防身自衛,還能夠上陣殺敵、建功立業,享受官場所帶來的榮華富貴,在民間還能行俠仗義、交友結誼、陶冶情操、爭勝品名,贏得萬人矚目等諸多功能益處,因此兵器走向技擊為主流的發展方向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到了現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體育領域的話,娛樂、健身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訴求。在娛樂方面,武術套路以其絢麗多彩的高難度動作以及行云流水、氣吞山河、勢如破竹、逍遙灑脫、清秀典雅的技術動作吸引著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球,從而忍俊不禁的想要去體驗一把,其中青少年則偏好于練剛猛疾速的技術動作,如自選刀、槍、劍、棍等器械,而中老年人則偏好于氣定神閑的技術動作,如太極劍。在健身方面,中華武術以“天人合一、內外兼修、陰陽平衡”為指導思想,以“動靜疾徐、剛柔相濟、虛實兼備”為技術特征,以“三尖相照、內外三合、形神合一”為動作要領,從中不難發現中華武術從“器、技、道”三個層面以全息應對的方式引領者大眾的健身發展,而從現代運動員所展現的技術動作“精、氣、神”來看,明顯能夠感覺到其身體體質高于其他項目的運動員。因此大眾選擇走向審美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是目標導向的不同使傳統兵器訓練體系由“一體”走向了“多元”。冷兵器時期,從軍事斗爭角度來講,其習武練兵的直接目標是提升隊伍的戰斗力以取得戰爭的勝利,從民間競技的角度來講,其直接目標是提升自身武技水平來制人而不受制于人,但總體來說,其都是圍繞著技擊水平的提高而進行的。而套路、功法都是為了技擊水平的提高所采用的技術訓練方法,其中套路的訓練主要用來提高拳勢之間的連貫性、肢體之間的協調性以及身體總體的整合性等效果,而功法則用來提高身體某一部位的力量、速度、耐力以及抗擊打能力等身體素質,從而使得傳統武術呈現出了圓融一體的發展走勢。而到了近代,伴隨著火器的出現,冷兵器在軍事中的統治地位逐漸被取代,從而使得傳統兵器基本上成了毫無用武之地的破銅爛鐵,為了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在愛國人士張之江等人“強種救國”的呼聲中,兵器逐漸走上了復興之路,其中中央國術館舉辦的“國術國考”設定了短兵和長兵以及相應的套路作為競賽項目,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刀、槍、劍、棍走上了競技體育的發展道路。而到了現代,從國家的角度而言,其直接目標就是為了使中華武術進入奧運,以此通過這個平臺來進行中華文化的傳播,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喜愛中國,進而融入中國這個大家庭中來促進綜合國力的提升。奧運會具有嚴格的規范性、公平性、公正性,運動員在裁判員的主持下按照統一的量化規則進行技能的展示,最后根據其技能展示情況進行分數的評估,而傳統武術一直以實用性作為技擊效果好壞的評判標準,具有嚴重的模糊性,而進入奧運的目標導向作用,使其不得不對其技術規格進行嚴格的規范,因此套路在競賽規則的導向下朝著“高、難、新、美”的方向發展,而對抗項目就朝著短兵的方向發展。而從運動員的個人角度來講,其直接目標就是完美的發揮出自身競技狀態以得分、奪牌,由此可以看出目標導向的不同,從而使它們之間以一種類似與平行線的狀態發展,進而走向了多元化。
3 結論
兵器技擊經過歷史的洗禮逐漸褪去了技擊的光環,在社會大眾的精神訴求中偏向了審美,外加社會的發展進步、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等社會背景因素的影響,同時伴隨著西方體育文化的進軍,更加速了兵器技擊體系的肢解,使其由合到分,進而導致兵器技擊技術體系的體育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