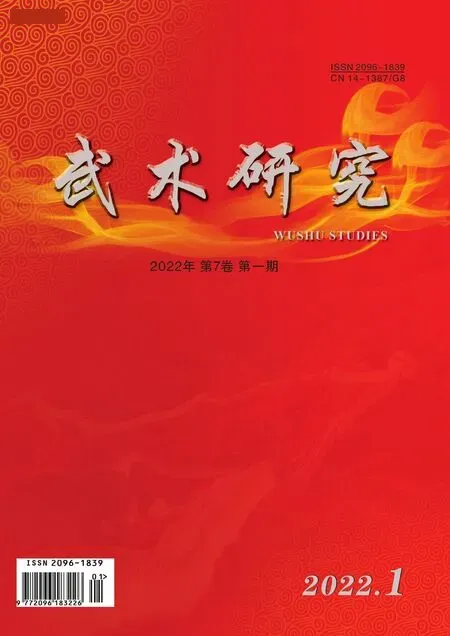秦州鞭桿舞的表演形態(tài)及特性探析
莊 園 孫 威 謝智學(xué)
西北民族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124
鞭桿舞又稱“打鞭子”,主要流傳于秦人的發(fā)源地,即天水市秦州區(qū),秦州區(qū)斜坡村一帶是中心區(qū)域,有著數(shù)千年的歷史,鞭桿舞是秦州社火活動(dòng)中的重要組成項(xiàng)目,是地方歷史文化中的一塊魁寶。社火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不同時(shí)代的人們往往結(jié)合自己的思想與生活來(lái)豐富和改造傳統(tǒng)的社火,賦予新的思想內(nèi)容和新的社火風(fēng)格。幾千年來(lái),秦州鞭桿舞是在適應(yīng)和利用生產(chǎn)勞動(dòng)環(huán)境中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風(fēng)俗習(xí)慣,涵括了漢民族文化和秦州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研究鞭桿舞的形態(tài)及其特性,對(duì)于弘揚(yáng)地方民俗文化,促進(jìn)民間體育、民間舞蹈的發(fā)展,傳承地方民間文藝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業(yè)界應(yīng)該解決的一個(gè)重要課題。
1 秦州鞭桿舞的歷史淵源
1.1 鞭桿舞起源于秦地
鞭桿舞是一種體育與舞蹈相融合的藝術(shù)形式,這一藝術(shù)形式的基本內(nèi)核和特征,無(wú)不與其淵源和最初面貌有著無(wú)法割舍的密切聯(lián)系,也與形成這藝術(shù)形式的最初環(huán)境存在千絲萬(wàn)縷多的關(guān)系。鞭桿舞的淵源要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居住在犬丘的秦人先祖非子,因擅長(zhǎng)養(yǎng)馬,于是周孝王便在汧河和渭河之間的地域讓其負(fù)責(zé)養(yǎng)馬,非子用自己獨(dú)特的養(yǎng)馬之技,使得馬群的數(shù)量疾速增長(zhǎng),成為一名畜牧業(yè)的成功者,并被周孝王賜地封贏。可以看出,“秦”是因養(yǎng)馬有功得到的封地,是鞭桿舞的起源地?zé)o疑。鞭桿舞的基本樣態(tài)更是表現(xiàn)出古老時(shí)期秦人日常與“馬”相關(guān)的生活狀態(tài)。
1.2 鞭桿舞形成于牧馬
在冷兵器時(shí)代,爭(zhēng)池略地,車兵、騎兵都離不開馬,它是軍隊(duì)必不可少的一種裝備。受戰(zhàn)事的影響,馬在軍事上的地位舉足輕重。鞭桿舞的形成是那個(gè)年代牧馬業(yè)備受重視的縮影,而鞭桿舞也就成為“馬背上的舞蹈”。秦建國(guó)后在西北游牧區(qū)設(shè)“六牧師令”,馬匹之多需要大量的人來(lái)管理,在閑暇之時(shí),人們手持牧馬的鞭桿在空地練習(xí)驅(qū)馬馴馬的動(dòng)作,后來(lái)兩人一組慢慢交流切磋鞭馬技藝動(dòng)作,在嬉戲打鬧中漸漸衍生出一套動(dòng)作,這種運(yùn)動(dòng)沒(méi)有場(chǎng)地要求,器材就是牧馬時(shí)手持的鞭桿。因此,上至高官厚祿,下至白丁俗客都可將其作為一種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休閑。
2 秦州鞭桿舞的表演形式
2.1 有相對(duì)固定的表演時(shí)間及儀式
從古至今,社火表演是秦州各地最重要的節(jié)日民俗活動(dòng)。每年的農(nóng)歷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間是社火表演的固定時(shí)間。表演內(nèi)容豐富多彩,有鞭桿舞、唱小曲、打四川、牧牛等節(jié)目,多在廟宇、家庭院落及村莊公共場(chǎng)所表演。初三的晚上必須在廟里舉行“官場(chǎng)”的敬神敬先人祭祀儀式,隆重而嚴(yán)肅的鳴炮,磕頭的交接儀式等眾多習(xí)俗都體現(xiàn)出它世代相傳的歷史性痕跡。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人本身的一套程式化動(dòng)作(或表演)成為符號(hào)載體......來(lái)表達(dá)象征性內(nèi)容”。祭祀儀式結(jié)束之后,社火活動(dòng)便正式開始,其中鞭桿舞的表演也愈演愈烈,隨著參與人數(shù)的逐步增多而推向高潮。直至正月十五的晚上,大家再統(tǒng)一去廟里進(jìn)行叩拜,社火活動(dòng)就此結(jié)束。鞭桿舞是社火表演的重頭戲和不可缺少的節(jié)目,一般是活動(dòng)中的最后一個(gè)節(jié)目,往往起著壓軸的作用。當(dāng)然,也可形成一個(gè)單獨(dú)的節(jié)目進(jìn)行表演。
2.2 有寓意吉祥的道具“鞭桿”
鞭桿舞的主要道具鞭桿,通常是用三四尺(約90厘米)長(zhǎng)的竹竿或堅(jiān)硬木棍加工而成。生(男)、旦(女)兩角的道具鞭桿長(zhǎng)短不一。生角的鞭桿稍短,打法更為復(fù)雜粗曠,有跳躍性的動(dòng)作,還有武術(shù)的仆步動(dòng)作等,給人展示的是“武”的剛勁。傳承者一般都具備良好的武術(shù)基礎(chǔ)和身體素質(zhì),這樣才能更好的展現(xiàn)西北人特有的“剽悍”和“剛烈”的舞性。旦角鞭桿稍長(zhǎng),打法柔美,給人展示的是女性“舞”的細(xì)膩。鞭桿兩個(gè)頂端用綠帶和紅帶纏繞,生角為綠,旦角為紅,下面分別扎有紅綢和綠綢的彩花,生角紅綢彩花為陽(yáng),旦角綠綢彩花為陰,象征陰陽(yáng)和合之意,彩花下面系有四個(gè)銅鈴,象征八卦,再下面兩頭鏤空分別藏有兩枚銅錢,象征兩儀和四象,又有招財(cái)吉祥的寓意。
2.3 有多種樂(lè)器伴奏的配樂(lè)及伴唱
《八度神仙》曲
一度神仙漢鐘離,頭撓抓鬢不整齊,
手里拿的八寶扇,扇搧富貴萬(wàn)萬(wàn)年。
二度神仙呂洞賓,頭頂青絲一冠巾,
身后背的二龍劍,楊柳童兒緊跟隨。
三度神仙張果老,悠哉騎驢過(guò)仙橋,
倒騎驢子仙橋過(guò),口吹云霧上九霄。
四度神仙曹國(guó)舅,身穿繡龍滾蟒袍,
當(dāng)年在朝一品官,修就一座大羅仙。
五度神仙鐵拐李,身背葫蘆騰云走,
身后背的大葫蘆,八仙過(guò)海顯神通。
六度神仙藍(lán)采和,人人都說(shuō)是妖魔,
妖妖妖來(lái)魔魔魔,少說(shuō)一句是非少。
七度神仙何仙姑,人人說(shuō)她無(wú)丈夫,
有丈夫來(lái)無(wú)丈夫,多說(shuō)一句惹禍福。
八度神仙韓湘子,人人說(shuō)他是孝子,
手里拿著竹笛桿,走著行著唱道歌。
鞭桿舞表演時(shí)所用的打擊樂(lè)器頗為多樣,有堂鼓、乳鑼、大鑼、小镲、手鑼等,拉弦樂(lè)器有二胡、板胡、三弦琴,吹奏樂(lè)器有嗩吶、笛子、管子、笙等。這些樂(lè)器視其表演的條件,無(wú)固定的規(guī)定性,可多可少。現(xiàn)存遺留下來(lái)的常用伴奏樂(lè)器共有六種,分別是有堂鼓、大鑼、小镲、二胡、板胡和笛子。在伴奏節(jié)奏上較為單純, 以平均節(jié)奏型為主, 長(zhǎng)短、短長(zhǎng)等節(jié)奏型為輔, 周圍還組織數(shù)人伴唱助興,樂(lè)隊(duì)成員都是由年長(zhǎng)的傳承人擔(dān)任,唱詞大多講述民間傳說(shuō)或神話故事,但伴奏都是統(tǒng)一的,只有歌詞不同,在比較莊重的儀式上伴唱《八度神仙》,而閑暇之時(shí)的表演會(huì)伴唱《十二月花》。這兩首曲子都已具有了上百年的歷史。
2.4 有識(shí)別角色的多種配飾
最初秦州鞭桿舞的傳承方式為傳男不傳女,以男性擔(dān)任表演角色,其分為生角和旦角,生角為主角,旦角為配角(男扮女裝)。直到2015年,取消了“男扮女裝”的這一表演形式。生角和旦角在演出時(shí)用不同的服裝和配飾來(lái)區(qū)別。生角的服裝是根據(jù)秦人服飾制作的長(zhǎng)袍,以黑色為主,頗有古樸之風(fēng),給人剛毅、忠誠(chéng)、勇敢的形象。旦角要打扮成女性的裝束,也類似于戲劇裝扮,頭戴假發(fā)麻花辮,腳踩繡花鞋。同時(shí),演出時(shí)還要對(duì)臉部進(jìn)行豐富多彩的涂抹,涂抹的樣式則類似于戲劇臉譜。通過(guò)這種涂抹,一方面,作為超脫于人的“神秘”裝扮,可達(dá)到與神靈溝通而獲得神秘力量,驅(qū)邪逐疫;另一方面,通過(guò)臉部涂抹,與神靈交流,傳達(dá)某種心理訴求,祈求神靈的庇佑。總而言之,服裝道具所流露的文化信息即包括經(jīng)驗(yàn)性的,也包括超經(jīng)驗(yàn)的,但無(wú)論是哪種信息,它都在傳播的“同構(gòu)”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3 秦州鞭桿舞的舞蹈形態(tài)
3.1 有瞬息多變的表演形式
舞蹈的基本步伐分為行進(jìn)步和固定步,行進(jìn)步整齊劃一,氣勢(shì)磅礴,震天駭?shù)兀还潭ú叫D(zhuǎn)交叉,或蹲或躍,動(dòng)人心弦。表演時(shí),有站立舞鞭桿、劈單叉、魁斗踢星、虎抱頭等動(dòng)作姿態(tài),演員按順序敲擊肩膀、前臂、膝蓋、腳尖、跳起后勾向上的鞋底等部位,靈活多變,并用鞭梢擊打地面,其氣勢(shì)雄厚,鞭隨人動(dòng),人隨鞭狂。演員根據(jù)鼓點(diǎn)、節(jié)拍變換隊(duì)形,有大擺尾、鷂子穿林、雙進(jìn)門、同心圓、八卦陣等。生角和旦角的一套動(dòng)作以八個(gè)八拍為一小節(jié),和伴奏伴唱的音樂(lè)正好匹配。如:《八度神仙》唱完一段,生角和旦角便打完了一段;第二段循序漸進(jìn),循環(huán)往復(fù),直至打完八段,基本就結(jié)束了。
3.2 有人數(shù)不一的表演陣型
鞭桿舞表演時(shí),四人為一組,生角、旦角兩兩相對(duì),形成了和諧對(duì)稱的秩序整合。根據(jù)表演場(chǎng)地的局限性,既能以組為單位進(jìn)行,也可組成八人、十二人、二十四人等長(zhǎng)陣、方陣進(jìn)行變幻豐富的表演,人數(shù)最多時(shí)可由六十四人同時(shí)演出,可謂氣勢(shì)磅礴。如在家庭庭院當(dāng)中進(jìn)行時(shí),受場(chǎng)地大小的局限,只四人一組進(jìn)行;在村廣場(chǎng)或演出表演時(shí),則二十四人進(jìn)行,靈活進(jìn)行;甚至在私下練習(xí)時(shí),隨著音樂(lè)節(jié)拍的伴奏,隨時(shí)增加或減少出場(chǎng)人數(shù),但人數(shù)都是以四人一組相加,秦州鞭桿舞對(duì)人數(shù)也有一定的寓意,在人數(shù)上,四人一組逐層疊加,在古代,四人表示祈求四季平安、太平盛世的意義,表示伏羲八卦的自然和諧與天地合一之美。
3.3 有重心低移的行進(jìn)動(dòng)態(tài)
鞭桿舞的重心低移是從動(dòng)作姿勢(shì)、節(jié)奏、力量、速度等各個(gè)層面所顯現(xiàn)出來(lái),主要表現(xiàn)在腳步、膝蓋、擺臂、下蹲的運(yùn)動(dòng)體態(tài)上。這種運(yùn)動(dòng)體態(tài)的核心為腳步,屈膝、擺臂、下蹲都是以腳步為基礎(chǔ)加以形成的,重心低移的前提條件也是腳步,因此,想把握好鞭桿舞的精髓,第一步則是學(xué)會(huì)腳步,腳步乃重中之重。任何運(yùn)動(dòng)都遵循著循序漸進(jìn)的原則,這也是科學(xué)與智慧的體現(xiàn),鞭桿舞的重心低移還表現(xiàn)在起打時(shí)的下蹲動(dòng)作和跳躍動(dòng)作,這就使運(yùn)動(dòng)軌跡做了一個(gè)U型,力學(xué)原理決定了人體只有將重心降低蓄力,才能獲得較大支撐反作用力。由此,也詮釋了鞭桿舞伴奏中“重拍”所結(jié)合“下蹲再跳躍”的連續(xù)動(dòng)作過(guò)程。
4 秦州鞭桿舞的特性
4.1 原始性與古樸性
在今天秦州鞭桿舞的表演中,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占據(jù)時(shí)間較長(zhǎng)的舞蹈圖式,即圓形。正如蘇珊·朗格所言: “那種環(huán)舞或圈舞作為舞蹈形式與本身自發(fā)的跳躍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它是在履行一種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職能,或許這是舞蹈藝術(shù)最圣潔的職能—將神圣的‘王國(guó)’與世俗的寰宇區(qū)分開來(lái)。”這個(gè)舞蹈形態(tài)是在舞者們圍圓移動(dòng)或面向圓心歌舞的過(guò)程中形成的,四人一組逆時(shí)針環(huán)繞一周移動(dòng),舞動(dòng)時(shí)兩人相對(duì)向圓心而舞等多種多樣的表現(xiàn)形式。經(jīng)過(guò)筆者走訪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首先,鞭桿舞要在各種形狀、場(chǎng)地大小不同的廟宇中、庭院里表演,這些物質(zhì)的空間普遍較小,太復(fù)雜的隊(duì)形不允許出現(xiàn),圍圓而舞時(shí)則可以隨時(shí)根據(jù)空間大小而變化,既節(jié)省空間,還能使舞蹈在視覺(jué)上具有無(wú)限循環(huán)的延續(xù)流暢效果。其次,圍圓而舞是人類流傳至今最基本的一種集體舞蹈形式,它是一種較為古老、原始的舞蹈樣貌,還映射出原始篝火舞的遺意,歷史悠久,古樸質(zhì)純。
4.2 儀式性與繼承性
著名人類學(xué)家維克多·特納指出,“儀式不應(yīng)該被看作是‘驚奇怪誕’的,因?yàn)樗南笳饕饬x并非誕妄而恍然的。文化符號(hào)的構(gòu)建并非一蹴而就,其存在都有現(xiàn)實(shí)的價(jià)值與意義。秦州鞭桿舞也不例外,一直是民俗社火活動(dòng)期間休閑娛樂(lè)活動(dòng)的主要內(nèi)容。清末民初,秦州鞭桿舞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其表演隊(duì)伍達(dá)到頂峰,當(dāng)時(shí)秦嶺鄉(xiāng)一帶的“老幼、婦孺皆會(huì)舞之”。秦嶺鄉(xiāng)人在農(nóng)閑和節(jié)日時(shí)便用鞭桿舞表達(dá)著他們最殷切的期待,以鞭桿舞迎瑞祈福,期盼來(lái)年莊稼豐收、生活平安的美好訴說(shuō)。鞭桿舞在一脈相傳的發(fā)展中,也會(huì)受到社會(huì)因子的影響,由于歷史原因,社火活動(dòng)曾被迫中斷,鞭桿舞也淡化出人們的視野,1977年春節(jié)是鞭桿舞被挖掘之后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表演。秦州社火長(zhǎng)興不衰,為鞭桿舞在秦州地域的傳承與發(fā)展提供了一片養(yǎng)分充足的廣袤沃土。
4.3 地域性與文化性
縱觀秦人全貌,先秦是在隴右天水地區(qū)逐漸繁榮而興起的。其生存環(huán)境是四面受阻,東隔隴山與周王室相鄰,西、北兩面廣布戎、狄,秦人在周人與戎狄的夾縫當(dāng)中生存。[4]在這種狀況之下,秦人因地制宜,排除萬(wàn)難發(fā)展生產(chǎn),出現(xiàn)了農(nóng)牧兩旺的景象。而源于秦人牧馬的鞭桿舞也不例外,悠久的歷史沉淀已將民族文化烙印和地域風(fēng)格特色深深打入其中,在其誕生、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了鮮明、個(gè)性的特征。鞭桿舞剽悍、剛烈、粗獷,明顯融進(jìn)了西部少數(shù)民族擅長(zhǎng)馬戰(zhàn),喜好軍功的氣質(zhì),這些也正反映了秦人入鄉(xiāng)隨俗,虛心學(xué)習(xí)吸收西戎文化,追求中興的不懈努力,充分說(shuō)明天水秦文化強(qiáng)烈的兼容性和博大的開放胸懷,傳遞出天水秦文化鮮明的功利色彩和進(jìn)取精神,贊揚(yáng)了秦人輕死重義、果斷勇敢、粗獷悍厲的民族性格,洋溢著不畏困難、跨越障礙、勇往直前的積極精神。
5 結(jié)論
鞭桿舞秦人在長(zhǎng)期牧馬、馴馬的生產(chǎn)勞動(dòng)和社會(huì)生活的過(guò)程中產(chǎn)生, 它繼承和體現(xiàn)了隴右天水秦文化的精髓。并與民俗社火祭祀活動(dòng)不斷相互促進(jìn)、融合, 一直處于錯(cuò)綜復(fù)雜的藝術(shù)交織狀態(tài)之中。
就表演機(jī)制、舞蹈形態(tài)觀之,秦州鞭桿舞集社火祭祀程序、道具、配樂(lè)、服裝、裝扮涂抹為一體,通過(guò)其服飾扮相可表達(dá)出與戲曲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其祭祀儀式體現(xiàn)著中華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浸透,表達(dá)出原始伏羲文化的遺跡。就特性而言,秦州鞭桿舞具有民間舞蹈的原始性與古樸性,儀式性與繼承性,地域性與文化性,傳達(dá)著“舞蹈是人類生命儀式”的基本人文精神,處處彰顯著秦人披荊斬棘、威猛豪放的民族性格特征。只有深刻、準(zhǔn)確的了解鞭桿舞,掌握其精髓,才能更好地把握鞭桿舞的審美特征、演繹鞭桿舞的審美風(fēng)格,使其在推廣和傳播的過(guò)程中、在繼承發(fā)展的長(zhǎng)河中始終保留秦人具有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的身體語(yǔ)言表達(dá),并在此基礎(chǔ)上使它的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一脈相承、不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