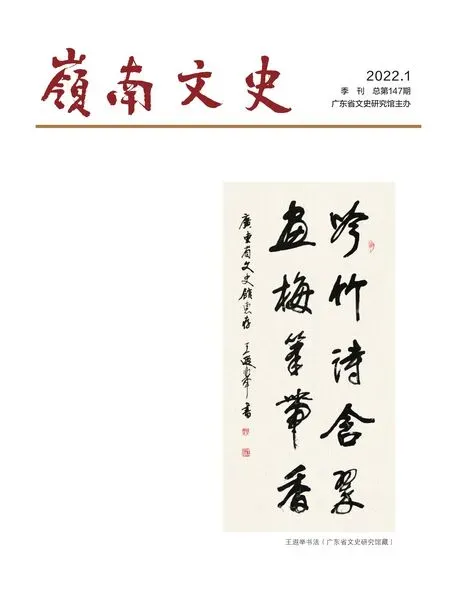陳昌齊《賜書堂集鈔》考述
廖粵 羅志歡
(作者廖粵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文化史籍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羅志歡:暨南大學)
《賜書堂集鈔》6卷為清代漢學家陳昌齊的著作。陳昌齊(1743-1820),字賓臣,號觀樓,又號啖荔居士,廣東海康(今雷州)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中允大學士……嘉慶九年(1804),出為浙江溫處道……在任五年以鞫獄遲延,部議鐫級,江南、福建大吏辟調,皆不往,歸里主雷陽、粵秀講席,修通志,考據詳核,著書終老焉”。陳昌齊精通考古、語言、文學、天文、歷算、醫學、地理等。一生著述主要有《賜書堂集鈔》《臨池瑣語》《天學脞說》《測天約術》等。勘校《永樂大典》,編校《四庫全書》,編纂清嘉慶《海康縣志》《雷州府志》、道光《廣東通志》等。王念孫譽之為“粵東碩儒”,梁啟超推之為“粵中第一學者”。
“賜書堂”為陳昌齊書齋名。是書之所以稱為“集鈔”,不稱“文集”,張舜徽在《清人文集別錄》中略有所言。張氏曰:“論學之文極少,意此編不名文集,而名集鈔,蓋乃選輯之本,而非撰述之全,未刊之篇,猶甚繁富。”可見此書為陳昌齊著述之選編,集文、序、雜記于一書,其未刊者繁富。
值得注意的是,《賜書堂集鈔》所載的序文中有些為地方志書所不載。如清嘉慶《雷州府志》不載《續修雷州府志后序》、嘉慶《海康縣志》不載《海康縣志序》等。學界關于陳昌齊的研究成果雖多,但多涉及其生平、治學成就等方面,如吳茂信的《陳昌齊》、林子雄的《陳昌齊研究》《陳昌齊及其著作》、陳海烈的《塵封二百載 秘籍顯新容——〈陳昌齊詩文集〉影印出版簡述》等學術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雖對《賜書堂集鈔》有所涉及,但暫無專文論述其中廣東地方史料以及陳昌齊方志學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試為研究清代廣東地方文化以及陳昌齊方志學思想提供一定的史料依據,并補地方史志記載之不足。
一、版本敘錄及內容
《賜書堂集鈔》凡六卷,現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流傳極少,僅見上海圖書館收藏。書前有高郵王念孫序。卷一應制文字;卷二雜記;卷三地方志序文;卷四書序;卷五書簡及雜文;卷六墓志銘。是書后由嘉應吳蘭修、南海曾釗、番禺林伯桐、海豐林光紱、電白康景平、南海陳昌運、番禺儀克中、海康官元勛、徐聞李梓瑤等九人共同校刊,收入《陳子遺書》。《陳子遺書》稿本現藏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另有清刻《賜書堂全集》,凡集鈔6卷詩鈔一卷。影印再版方面主要有二:2010年該書被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2016年該書被收入《陳昌齊詩文集》,為《嶺南文庫》系列之一。另外,民國時期編纂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收錄此書。
卷一,應制文字。應制文字是“凡被命有所述作,則謂之應制”。可見應制文即為所受皇命而作,多作歌頌升平之象。此書收錄了3篇應制文,分別是《圣駕四諧盛京恭謁祖陵禮成恭賦》《圣駕四諧盛京恭謁祖陵禮成恭頌》,《圣駕六巡江浙恭頌》,另附兩篇《緩糧謝恩折子》。此卷收錄的應制文與陳昌齊長期作為四庫館臣、翰林編修有關。陳昌齊自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翰林院散館,至乾隆五十五年出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其在翰林院、四庫館歷事凡二十年,經其校勘之書、應制之文不勝枚舉,此卷應制文即為此時所作。
卷二,包括18篇雜記,分別是《修溫州府儒學記》《修溫州府譙樓記》《修永嘉縣儒學記》《修遂溪縣儒學記》《修徐聞縣儒學記》《修粵秀書院記》《黃氏祠堂記》《蔡氏義田記》《陳雲亭公祠堂記》《鄧氏祠堂記》《官彥美公祠堂記》《王氏繼孫記》《雷州特侶塘記》《報恩精舍記擬作》《修天寧寺記》《石城惜字塚記》《守經堂記》《雷陽新館記》。以上這些雜記可歸為兩類:一是其為府學、縣學所做的雜記。主要是申明重士重教,以教化地方,“國家設官以治民也,而四民首士,則治民必先教士……知重士且欲教士以治民”。二是其為祠堂、寺廟、堂館所作的雜記,主要強調封建禮法綱常。如在《黃氏祠堂記》一文中,其強調“大宗”與“小宗”在祭祀范圍上應有所區別,可見封建綱常倫理和宗法等級較為明顯。其曰:“蓋古者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祀其始封之祖,百世不遷,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也,小宗始于繼補而漸及高曾……大宗惟祀始祖,故合一族之人以供祀事,小宗祀止四親,奉祀事者則等而下之五世孫也,以五世之孫祀其先四世于義為宜。”
卷三,地方志序文。包括3篇序文,分別是《續修雷州府志序》《續修雷州府志后序》,陳昌齊均參與編纂這兩部志書。其中后兩篇序文又附錄《輿圖志序》《地理志序》等。《續修雷州府志序》為嘉慶十六年(1811)所作,文中陳昌齊認為:“自樂史作太平寰宇廣記闌入……是古之地志特史之一門,后之地志實為府州縣之全史”。可見其認為地理志對地方志的重要性。乾隆三十七年(1772)其任散館編修,“獨任地理門,直省地志繁復,稽核詳審,故生平最精地理之學”。故其在編纂《雷州府志》時亦是親力親為考據雷州府輿地形勢。其曰:“吾嘗稽之往牒,聞之故老,參以生平閱歷用是,悉其形勢,得其土,宜知其民人所習尚。”《海康縣志序》為嘉慶十七年所作,他認為縣志的作用主要在于輔助理縣之用,對地方官理政大有裨益。“余惟縣之有志為理縣作也……下車伊始輒能辨其人民、財用,周知其利害以亟施”。經其參與編纂和校勘的這兩部志書質量皆為上乘。
卷四,書序。包括14篇書序。分別是《永嘉賓興會紀事序》《海塘攬要序》《粵秀書院課藝序》《雷祖志序》《韓節愍詩集序》《荷經堂文集序》《測天約術序》《天學脞說序》《杜陵吳氏續修族譜序》《梁氏族譜序》《黃氏族譜氏》《官氏族譜序》《丁氏族譜序》《南海陳氏續修族譜序》。以上書序包括三種,即紀事序、詩文集序、族譜序。紀事序多以勸誡士子堅守學業為主。如其以農人“荒歉不荒耕”以及商賈“折閱不廢市”之理勸誡士子堅守學業。其曰:“今夫良賈雖有折閱不廢市也,故卒獲利,今夫良農雖有荒歉不廢耕也,故卒多獲農資則不得不廢耕矣。”詩文集序是其為他人及自身的著述所作的序文,其中《測天約術序》《天學脞說序》即其為自身的著述所作的序文。《測天約術序》為其數學著述,阮元評價此書曰:“所著有《測天約術》一卷……最為簡要。”《天學脞說》為其研究天文學之著述,但已失傳,僅有《賜書堂集鈔》收錄之《天學脞說序》,殊為可惜。族譜序是其為族譜所作之序文,其在《杜陵吳氏續修族譜序》的序文中闡述了族譜的來源和作用。“禮有大宗以收族屬,宗法既廢,于是士大夫各著家譜,以時增輯,莫敢或弛,匪徒夸地望也,宗法不可復,而收族之意于是乎存焉”。陳氏認為,族譜有凝聚族力、團結鄉里之用,在宗法松弛之時,族譜可代替其作。故古人曰:“教民和親,莫先于敬宗、收族,宗法廢而譜牒始興,譜牒廢而骨肉亦薄。”故古人多修譜以彰顯本族榮耀,教化本族子弟。明清以后,修譜頗為繁盛,這既與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密切相關,更與崇文重教的社會風氣有關。
卷五,書簡及雜文。包括9篇書簡及雜文。分別是《戒雷陽書院諸生書》《與諸生講實學書》《與諸生論時藝書》《復曾勉士釗書》《再復曾勉士書》《逃虛閣詩鈔跋》《魁星考》《龍應宮天后神功頌》《座右銘》。書簡主要是陳昌齊對書院諸生訓誡教育的記述。如在《戒雷陽書院諸生書》一文中,其向諸生提出讀書要做到“四戒”:戒驕傲、戒輕薄、戒忿怒、戒強酒。雜文主要是其與友人來往之書信,如《復曾勉士釗書》即為其就學術問題給南海曾釗的書信。從雜文可見,陳昌齊在高度贊賞曾釗學術功底深厚的同時,亦就某些問題提出質疑研討。從此雜文,不僅可窺見一代乾嘉學者陳昌齊與曾釗切磋學問之旨趣,更可窺見陳昌齊治學之嚴謹謙虛,尤其是對一字一句的精詳考據,不愧為乾嘉學派大學者。
卷六,墓志銘。包括9篇墓志銘,多為故友或家人所寫。分別是《黃雨堂明府之母楊太宜人墓志銘》《臨高縣儒學教諭蔡君墓志銘》《林古風先生墓志銘》《新會縣教諭前署福建寧詳縣知縣吳君墓志銘》《灤州刺史莫君墓志銘》《陳母吳太孺人墓志銘》《潘母周太夫人墓志銘》《誥贈太宜人旌表節孝李母趙太宜人墓志銘》《亡妾曹氏暨長女佩瓊合葬墓碣》。
二、地方史料及價值
《賜書堂集鈔》中有不少序文為地方志書所不載,如清嘉慶《雷州府志》不載《續修雷州府志后序》,嘉慶《海康縣志》不載《海康縣志序》等。另據林子雄、司徒尚紀等學者統計,該書“80多篇文章中,有50多篇是關于廣東地方事務的,其中記述雷州、遂溪、徐聞文化教育事業的又占很大比例”。這些序文對于研究清代廣東地方文化以及陳昌齊學術思想均大有裨益,史料價值較高。且可補地方史志記載之不足,達到“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效果。為考察其文獻、史料價值,茲略舉數例以說明。
可為研究清代廣東粵秀書院的發展史提供原始材料。《修粵秀書院記》一文詳細記載了粵秀書院重修的細節和過程,從此可窺見昔日粵秀書院之規模,是研究粵秀書院發展史的重要史料。據其記述,嘉慶二十五年(1820)粵秀書院重修時的人員安排、重修規模、重修時間、經費支出等細節尤為詳備。粵秀書院重修一事在清道光《廣東通志》中亦有載,但只見有“粵秀書院……知府羅含章倡捐重修”等寥寥數語,對粵秀書院重修的細節不得而知。詳細記載粵秀書院重修一事的還有梁廷枏所撰的《粵秀書院志》一書。是書十六卷,《廣州大典》史部地理類有收錄,內容詳述粵秀書院的規例、考課、度之、修葺等,其中卷五《修葺》記述了嘉慶二十五年粵秀書院重修的細節與過程。經筆者核對,發現其記述與陳昌齊《續粵秀書院記》一文相同。陳氏之文成于清嘉慶年間,而梁氏之書成于清咸豐二年(1852),可證陳氏之語先于梁氏之語,且陳氏為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史料價值更高,為研究清代廣東粵秀書院的發展史提供了較為珍貴的原始材料。
可為研究清代雷州地區風俗、宗教提供史料參考。《賜書堂集鈔》收錄的序文中有不少是記述清代雷州地區歷史文化的,甚至為雷州地區志書所不詳。故深入探究這些序文對于研究清代雷州地區的風俗、宗教等大有裨益。其序文主要反映清代雷州風俗、宗教的兩個特點。一是反映了清代雷州地區祭祀過濫,巫術盛行,其民尤重巫醫的現象。“雷俗崇信巫覡,陬澨之間叢祀疊起,溯其由來,茫無援據,而泯泯者方且祈之禳之,日奔走于酒醴牲牷之供,惑滋甚矣”。雷州地區古有巫術盛行,唐宋間即見載于史書,如沈括的《夢溪筆談》載曰:“余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肉;又咒之,則熟肉復為生肉;有咒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從沈括的記載可見在唐宋時期雷州地區巫術已盛行,且千奇百怪,直至明清時期這種現象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粵俗之甚者”“粵俗尚鬼未有如雷之甚者,病不請醫而請巫,香幣牲牷焚修懴祝,竟與病人相終始”。二是反映清代雷州地區媽祖神廟系由潿洲島傳入,此為方志記載所不詳。這一記載為研究雷州地區媽祖信仰傳播路徑提供參考。其曰:“吾雷三面環海,琳宮紫宇到處有之,惟郡城南關外之龍應宮為最著,神自潿洲移入宮,入宮之時有龍見,故名龍應。”但經筆者查證發現,關于媽祖神廟從潿洲移入雷州一事,雷州地區方志并沒有較為清晰的記載,甚至連陳昌齊主持編纂的嘉慶《雷州府志》《海康縣志》均沒有詳細記載,只有“天妃于海神最靈,諸渡者必走謁祠問吉兇……以故瀕海在置祠,而潿洲孤島立起海中,沃壤而鄰于珠池”等語。可見雷州地區方志只記載民人尤其渡海者熱衷于信奉潿洲媽祖神廟之事,而不見雷州地區媽祖信仰從何處傳入之記載,足見《賜書堂集鈔》的史料價值不可低估。
三、方志學思想述論
《賜書堂集鈔》卷三著錄了《續修雷州府志序》《續修雷州府志后序》《海康縣志序》等3篇地方志序文,詳細記述了雷州地區府志、縣志的編纂過程,以及陳氏對方志學編纂中某些問題的獨特見解,尤其是在方志的文獻搜集、人物評價、材料考辨等方面,其見解與方志學家章學誠等人對方志學的見解頗有相似之處。故深入剖析這些史料,對于研究陳氏方志學思想,乃至考察其學術思想有一定的助益。
從這3篇序文分析,其方志學思想可歸為以下五點。第一,新志以舊志為基礎,并與時俱進,加以創新。編纂方志必以舊志為基礎,對其加以增訂或勘誤,故曰新志是為“踵前人之舊,門類之舛錯者厘定之,事故之后起者續增之,刪其繁冗,補其闕略”。陳昌齊在《續修雷州府志序》中亦曰:“吾嘗稽之往牒,聞之故老,參以生平閱歷用是,悉其形勢,得其土宜,知其民人所習尚。”可見其在編纂志書過程中不僅參稽舊志、譜牒等文獻,亦結合時下之變化,并通過實踐調查,補舊志記載之不足,駁舊志記載之訛誤。第二,精于考據,反復求證。這與其作為“乾嘉學派”大家者精于考據密不可分,通過幾部志書亦可見其考據學之功底。經其編纂的方志大多考據嚴密,幾易其稿,對于可疑之處,多方求證,以使無惑方付諸剞劂。故其曰:“幾經考訂,以為無可疑矣,而以疑義進者旋至也,一人也,幾經諏詢以為無遺議矣,而以異議來者旋至也,雖已付諸剞劂,氏猶必鉤稽印證,數更改以求其是焉。”又曰:“僚屬吏掾質之乎,紳庠耆老又以次核實,于躬所閱歷如是者……無惑乎。”陳昌齊編纂的方志得到較高的評價,與其精于考證有很大關系。第三,區分、厘定府志與縣志體例之別。如在清嘉慶《海康縣志》中,他認為兵防、勛烈、流寓三門應歸郡志,故對舊志的體例進行調整。“舊志分十八門,今定為八門……其兵防、勛烈、流寓三門并統之郡,非縣所得專也,故刪之”。方志學家章學誠亦有此看法,其認為通志、府志、州志乃至于縣志應各列體例,各有側重,而不是由上下行政區劃的志書簡單拆并而成。其曰:“如修統部通志必集所部府州而成,然統部自有統部志例,非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拆統部通志之文即可散為府州志也……府志自應于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第四,編纂方志要窮究一地之文獻。陳昌齊在《海康縣志序》中強調全面搜羅一地文獻的重要性:“必文獻足而后能征志,雖不足以盡一方之文獻,而文獻未始不存焉,取而征之。”又曰:“文獻足而后能征獻,不足則求之文。”一地文獻之窮究對于一地方志的編纂質量至關重要。章學誠亦認為:“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滅無聞者矣。”第五,地方志品評人物應秉持“據事直書”的原則。方志人物傳記對方志編纂尤為重要,故古今之史志多列人物傳記一目,如司馬遷的紀傳體《史記》專列《列傳》一目。而由于史料文獻的缺失,如何客觀公正地品評人物,為之立傳,是方志編纂者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著名方志學家章學誠認為方志人物傳要“據事直書,善否自見”,方足以客觀公正。在編纂志書時,陳昌齊亦秉持這一原則,尤其是在面對文獻缺失之時,采取訪之眾人、舉出于公的方式,使人物品評出自于眾人之見,此法較為公允。故其曰:“問其族屬,訪之與評,庶幾無誤虛聲,稱事錄焉,故家巨族尚有譜乘相傳,其子孫式微或竟無后者,尤未易定其品題也,則察核難,且舉出于公,人人皆得置議其間一事也。”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對于陳昌齊的研究雖多提及其編纂方志的成就,但研究其方志學思想不多不深。事實上,陳昌齊方志學思想雖未形成系統的方志學理論,但觀念、思維卻有其獨到之處,值得深入研究。
總之,陳昌齊《賜書堂集鈔》所載廣東地方史料文獻價值、史料價值頗為珍貴,對于研究清代廣東地方文化以及考察陳昌齊方志學思想,彌補地方史志記載之闕漏、訛誤均大有裨益。是書文獻價值、史料價值之高與陳昌齊在經學、訓詁學、方志學等方面造詣密切相關,且其治學之嚴謹為世所少見。桂文燦在其《經學博采錄》中曰:“粵東自國初以來,詩壇最盛。講學者承前明道學之遺,躬行實踐。自東吳惠半農來粵督學,喜以經學提倡士類……若夫博通群書,以漢儒訓詁說經者,以文燦所聞,蓋自海康陳觀樓觀察始。”桂氏之語確當。
[1][清]趙爾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二,列傳一百四十九,第3冊[M]。北京:中華書局, 第2927頁,1998。
[2][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序,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5頁,2010。
[3]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J]。《清華學報》,1924(01)2-37。
[4]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30頁,2004。
[5][16]吳茂信:《陳昌齊》[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71頁,2008。
[6]林子雄:《陳昌齊研究》[J]。《廣東史志》2003年第2期,第64-67頁。
[7]林子雄:《古版新語——廣東古籍文獻研究文集》[M]。廣州:廣州出版社, 第132-138頁,2018。
[8]陳海烈:《塵封二百載 秘籍顯新容——〈陳昌齊詩文集〉影印出版簡述》[J]。《嶺南文史》2016年第4期,第10-15頁。
[9]《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清]陳昌齊:《陳昌齊詩文集》[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11]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19[M]。濟南:齊魯書社,第779頁,1996。
[12][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頁。
[13][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二,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40頁。
[14][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二,第14-15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46-547頁。
[15][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嘉慶刻本,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59頁。
[17][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64頁。
[18][35][36][38][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第25、26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71頁。
[19][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四,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76頁。
[20][清]阮元:《疇人傳合編校注》[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675頁,2012。
[21][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四,第14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82頁。
[22][清]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六,清刻本,第63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99冊[M],第293頁。
[23]司徒尚紀:《雷州文化概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80頁,2014。
[24][清]章學誠:《修湖北通志駁陳憎議》//張樹棻纂輯:《章實齋方志論文集》[M]。濟南: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第280頁,1983。
[25][清]阮元修,陳昌齊纂:《廣東通志》第49冊[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第18-19頁,1986。
[26][清]梁廷枏:《粵秀書院志》,卷五,第15頁,咸豐二年(1852)刻本//陳建華、曹淳亮:《廣州大典》,第34輯,第21冊[M]。廣州:廣州出版社,第447頁,2008。
[27][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嘉慶刻本,卷三,第12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64頁。
[28][宋]沈括著,侯真平校點:《夢溪筆談》[M]。長沙:岳麓書社,第174-175頁,1998。
[29][31][明]歐陽保:(萬歷)《雷州府志》卷十一,秩祀志,萬歷四十二年(1614)刻本,第21、15頁//《廣東歷代方志集成》雷州府部,第1冊[M],第166-167、163頁。
[30][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五,嘉慶刻本,第16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95頁。
[32]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4冊[M]。濟南:齊魯書社,第755頁,1996。
[33][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第1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59頁。
[34][42][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第3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60頁。
[37][清]章學誠:《章氏遺書》第11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頁,1985。
[39][清]陳昌齊:《賜書堂集鈔》卷三,第34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06冊[M],第575頁。
[40][41][清]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12、292頁,2015。
[43][清]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一,民國刻敬躋堂叢書本,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