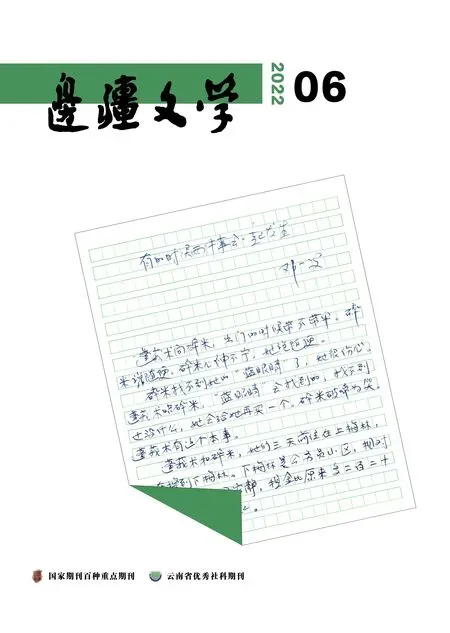底層、荒誕和寫意
—— 我讀2021 年《邊疆文學》 『邊疆開篇』中的小說
王 皓
2021年《邊疆文學》“邊疆開篇”欄目刊登了眾多優秀中短篇小說,包括呂翼《穿水靴的馬》、蔣在《等風來》、趙雨《流逝》、李浩《灶王上天見玉皇》、夏天敏《嗩吶聲近》等,它們所寫的題材和表達的主旨各不相同,觀察的視角不一,從底層農民的生存狀況到當代人的精神剖析,均各有發現。本文從底層敘事、荒誕敘事以及寫意敘事三個視角切入,試圖分析潛藏在小說背后的審美特質。
一、底層敘事
“底層”這一概念在詞典中解釋為喻指社會、組織的最低階層。關于“底層文學”的概念,學者李云雷認為它是“在內容上,它主要描寫底層生活中的人與事;在形式上,它以現實主義為主,但并不排斥藝術上的創新與探索;在寫作態度上,它是一種嚴肅認真的藝術創造,對現實持一種反思、批判的態度,對底層有著同情與悲憫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資源。”他的觀點普遍為學界所認同,可以說“底層文學”是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經驗的文學作品,聚焦底層階級的窮困和無助狀態,揭示其艱難的生活現狀以及底層人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作家主要呈現底層人民的生活日常和情感體驗,以農村或城鄉為背景,多以農民、城鎮底層為對象,關注底層生活困境,展現出平凡個體為了改變困窘的現實處境而付出的努力。底層寫作力圖將底層的真相作最原生態的展示。這種創作意圖就使得底層文學作品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寫實的敘事風格,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創作,往往采用現實時空形式和情節的緊密、場景的逼真、細節的真實、人物形象的豐滿等現實敘事方式,流露出作家較強的現實關懷和責任意識。
例如海桀的《腸香無二》(《邊疆文學》2021年第4期)從底層敘事中關注民生,從一種道德主義出發,揭露市場經濟時期新舊兩代食品經營者之間的觀念沖突,批判新一代經營者為了“金錢至上”而砸壞傳統摘牌的茍利行為;又如秦羽墨的《去明月寺練練槍法》(《邊疆文學》2021年第5期)則對小鎮里基層鄉村官場丑態進行揭露,刻畫了游手好閑的底層人物莊聰明與民警發生矛盾被扣押車具后進行暴力反抗而雙雙殞命的慘狀。
呂翼的《穿水靴的馬》(《邊疆文學》2021年第1期)更是典型的底層敘事,講述了易地搬遷背景下農民隴啟貴從農村搬進城里新房而引發一系列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隴啟貴作為新時代的農民和被脫貧對象,生活在基礎設施落后的野草坪,住在破敗不堪的茅草房,不通電,不通水,交通不便。然而政府實施易地搬遷工程,為貧困山區人民在山下修筑起幸福家園小區,這讓隴啟貴對新生活開始有了期望與向往,他牽著心愛的馬“幺哥”想要上高速去參觀新家園,經過一番周轉終于來到小區。但小區采用現代化管理方式,拒絕牲畜進入,他卻不顧阻攔暗自牽著馬進入小區,為了讓馬方便上樓,還將撕成四塊棉布褂子把幺哥的蹄子包了起來,防止馬蹄在瓷磚地面上打滑;為了躲避管理員他甚至讓馬坐電梯,結果馬卻突然在電梯里大小便,瞬時彌漫著沖鼻的腥臭,狼狽不堪。最后隴啟貴只得在物業監督下將電梯打掃干凈,并牽著馬悻悻而歸。
小說以喜劇的手法刻畫了隴啟貴這一漫畫式的農民形象,再現了農村易地搬遷過程中,農民對新管理制度的疑惑不解和新舊生活方式的矛盾沖突。農民在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同時,也面臨種種困擾和落后傳統殘留的難題,外在的局限和自身根深蒂固的愚昧落后觀點,依然頑固地潛伏在他們的意識深處,阻礙了他們擺脫物質貧困和精神愚昧的步伐,新的農村政策與過去的落后生活方式造成其認知的差異,也便由此生發出一場荒唐的鬧劇。新時代的農民依然難以跨越和繞過這種城鄉差異沖突對他們的有形和無形的鉗制,作者敏銳發現了農民遇到的新的困擾,以主動介入的姿態,并采取一種“民間立場”,在對農民書寫中實現對底層民生問題的關照與人文關懷。
不同于《穿水靴的馬》的喜劇氣氛,夏天敏的中篇小說《嗩吶聲近》(《邊疆文學》2021年第10期)卻是聚焦底層農民的苦難生活,展現了作家一以貫之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悲劇色彩。作者以悲涼的筆觸寫下烏蒙高原山區一支支哀婉深沉的歌,他的筆尖流淌的都是烏蒙高原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凄苦畫面,集中呈現了夏天敏底層寫作的“苦難”主題,揭示了鄉村農民的艱難生存狀態和畸形的生命態度。
小說描寫了貧苦山區云山老漢的悲苦人生,他的兒子順來在一次礦廠事故中導致癱瘓,喪失自主行動能力,照顧他成了云山老漢多年來的職責,父子倆在清貧中艱難維生。然而老漢一輩子省吃儉用,貧困使他遭受歧視與侮辱,生前的不幸使他只想在死后有一口好棺材,揚眉吐氣一番,“嚴酷的生活使他們對另一個世界充滿幻想,一口好的棺木幾乎就是一個人一生的念想”(《邊疆文學》10期第7頁)。但老漢的錢只夠買一副棺材,他不忍心死在兒子之前怕無人照顧,“棺材”又是他心中的一個癥結,于是便上演了“活人出大喪”“花錢雇孝子哭喪”等“可笑”又“可悲”的鬧劇。老漢對棺材的盲目欲望,致使其在生前潦倒狼狽,“這些苦難,并非僅僅來源于惡劣的自然環境或頹敗的現實秩序,而是更多地來自人性的崩落以及欲望的瘋狂增殖。也就是說,這些苦難,在很多時候是由于人們自身的某些欲望所催發出來的,并非是一種不可超越的現實不幸。”云山老漢對貧苦現實生活的無奈以及不合理的欲望觀和生活觀,致使他陷入為自尊將畢生心血投擲在“棺材”的漩渦之中。作者在正視這些底層苦難的背后,剖析了隱藏在苦難之下所蘊含的復雜人性,從而引發對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精神困境的深刻反思,并表達對鄉村社會生存環境的質疑和批判;同時也展現了作家的人道主義關懷,通過對農村貧困落后的揭露,對農民群體苦難處境的展示,旨在呼吁社會對農村、農民群體的關注與理解。
一些評論家在討論“底層寫作”時,特別強調要“重建知識分子立場、重溫人道主義價值關懷”后兩位作者都深耕于烏蒙大地,用極大的熱情關注著這片土地中的底層小人物,對他們投以人道主義的目光,描繪社會歷史浪潮中地處偏遠的鄉村底層,呈現出中國鄉村一隅的真實圖景,揭露無法逃離鄉土的小人物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生存掙扎。作家呂翼更加注重新時代的變化與落后農民之間的矛盾,而作家夏天敏筆下的農民似乎仍舊鎖閉在一個相對停滯的落后社會,少有外界力量的介入,更深究農民自身的困境。
二、荒誕敘事
文學意義上的“荒誕”最初被予正式命名是源于上世紀興起于法國的反傳統戲劇流派的概括,隨著中西方文學的交流融通,西方文藝思潮涌入中國,西方的荒誕敘事的熱潮開始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涌現,其時產生了一批“荒誕文學”它們通過荒誕性的敘事手法,虛構事物和情節,背離現實,從某種主觀感受出發來改變客觀事物的形態和屬性并深入現象的深處,揭示事物的本質。荒誕敘事技巧在文學作品中往往采取內容層面和形式層面的荒誕形式來解構真實,或以非常態的外在語言形式的敘述產生一種荒誕的效果。
例如朝潮《好像在哪見過你》(《邊疆文學》
2021年第6期),講述了“我”因夢而尋一個名叫“大唐”的地方,卻在途中認識令人可疑的樊先生,并由此生發尋找兄弟的想法,在一切謎團均為解開之時,樊先生卻消失得無影蹤,致使故事撲朔迷離,荒誕離奇。又或竇紅宇的《春聲醉》(《邊疆文學》2021年第9期)則以幽默的筆調講述了一對陌生男女頻頻相遇而發生的一些趣事,然而故事末尾卻筆鋒一轉,以女人的離奇死亡將小說引向荒誕的暗門,叩響了男主人內心的疑惑與傷痛,無從以正常的因果邏輯追尋女人為愛而死的動機,故事在男主人公混亂離奇極盡崩潰的荒誕精神世界中戛然而止。
索南才讓的短篇小說《葬身》(《邊疆文學》2021年第12期)則更是一篇運用荒誕敘事的離奇怪誕小說主人公阿音木在遭遇一次意外雷劈后,發生了一些奇怪的變化,醒來后的他目光呆滯、眼神渙散,且開始做起了連續的怪異的夢,在荒誕的夢境中他預見了他人的死亡,且一步步成為現實,“他仿佛一個高明的殺手,無聲無息置人于死地。夢就像準備過程,等夢做完了也就完成殺人任務了。”(《邊疆文學》第12期第7頁)這致使他產生了自己用夢境殺死他人的負罪感,在連續夢見好友桑德和心愛的女人死亡后,他在神經質的絕望中又夢到父親,于是在不堪精神的重負下走向崩潰。小說撇開故事的合理情節與時空的均衡性,解構了傳統小說中時間、地點、人物與環境等遵循邏輯的敘事要素,注重展示的是一種潛意識狀態下的主觀感覺、復雜情緒和抽象意念。用夢境殺人是一種打破常規的荒誕敘事手法,這往往產生一種與日常生活經驗相對立甚至偏離生活現實的“陌生化”效果,使主人公偏離傳統敘事因果邏輯而墮入混沌的夢魘之中。怪誕的情節走向致使主人公陷入非理性的混亂世界,揭露了人不可知命運的殘酷性。其次在結構和意旨上小說不具備合理的邏輯剪裁與秩序,甚至讀不出作者想要表達的主旨與中心思想,人物也沒有完整的性格指向。但這其中有關生命、死亡的思考,或許體現出一種虛空意識,一切都是夢魘無法窮盡和明確,沒有規律可循,無法言說,帶有玄妙的色彩。在充滿荒誕色彩的情節、場景和結構中傳達的人對于命運無可把握的一種無奈,從潛意識層面揭露人的生存本相,表現出作者對人存在狀態的深切質疑與關照。
李浩《灶王上天見玉皇》(《邊疆文學》2021年第6期)更是采取了一種“非常態”的荒誕視角,不同的是荒誕背后卻暗示一種現實真實。文中是以一個曹府灶王的身份進行第一人稱視角敘述,描繪了他上天宮與各神仙共赴宴的荒誕奇崛體驗。作為玉皇大帝百叟宴的觀禮群仙代表,灶王來到仙氣繚繞、威嚴莊重的天宮,然而天庭也有繁復的手續,經過重重關卡審查,終于到達仙驛館休息,在正式晚宴前各神仙需每天學習各項天庭禮儀并模擬演習。在百叟宴當日,眾仙齊聚一堂,場面盛大宏偉,但灶王謹遵天庭禮儀,不敢動幾下筷子,最后餓著肚皮而歸。荒誕的藝術實則敲開現實的大門,這種“非常態”視角的運用在審美格調上增添了感染力的同時也影射出人間的行活實況。看似荒誕的神界世界,實則卻有著凡間的影子,不同時空呈示的奇異的天庭景觀引領讀者走進了現實迷宮,思考現實世界與虛擬神界世界的聯系,在對照中喚醒其對現實的敏感。作家采取“灶王”這一非常態化身份描繪華麗莊嚴的仙界空間里的所見所聞所想,別具匠心地揭露在常態視閾中難以發現一些社會問題的“變異”和“瘋狂”,以隱喻和反諷表達對一些官場形式主義的拒斥,在荒誕敘事中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引發人們對現實問題的反思。
這幾篇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有荒誕敘事的傾向,有的是在一種草原牧歌式的語言中刻畫情節和故事的荒誕性,以揭露人的命運的虛無;有的則是采取外在荒誕的殼子,以現實為摹本建立起的卻是一個高于現實、具有魔法感的世界,具有現代哲學意義的追求,共同體現了作家們非凡的想象力與荒誕敘事能力,為《邊疆文學》增添幾分神秘色彩。
三、寫意敘事
傳統的寫實小說的中心任務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重結構的完整,強調情節的跌宕起伏,和表述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寫意小說并不以刻畫人物性格為目的,它們減弱情節,結構不緊密,著重營造一種氛圍、傳達一種心緒,有別于寫實寫作的藝術構思。因此寫意性的敘事不遵循傳統敘事原則,不以塑造人物為中心,人物往往成了一種載體;淡化小說的故事情節,注重小說意象、與意境的創造,以空間為小說的結構核心等特點。寫意敘事多借用意象、隱喻與象征等手法,“這些新的詩性方式改變了以往小說重在反映現實,再現現實的‘寫實’的美學向度,而使小說出現了重在暗示、重在象征、重在形而上理念、形而上寓意的‘寫意’的美學向度”
蔣在的中篇小說《等風來》(《邊疆文學》第2期)也有寫意敘事的傾向作者并沒有通過連續的情節來講述完整的故事,而是采用一種綴段性的情節組成,(所謂綴段性情節是指前后無因果關系而串接成的情節)插敘手法的介入使事件失去了時間的因果的鏈條。作者片段式地截取小女孩的生活場景,用插敘的方式追憶小女孩曾經與爸媽的溫馨時光,與當下令人心酸的生活經歷形成對比。其次,作者無意去塑造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而是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展現了一個處在孤獨無依寂寞狀況中的小女孩“她”的悲慘生存境況:她的父親消失,母親也在一次意外后在醫院長眠不醒最后被拔掉氧氣管,然而家里的兩個表哥卻也經常打罵她欺負她,善良的喜來幫助過她,愿意和她交流和玩耍,但命運卻將他弱小的生命吞噬,女孩和哥哥們目睹了他的溺水過程卻并未施救而是跑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似乎呈現一種以符號為意象的詩性方式,運用隱喻性的象征意象,小說圍繞“風箏”這一意象符號,以它為敘事線索,牽引制約著小說情節的發展,展現小女孩回不去的溫暖空間。每次它的出現,小女孩都置身在從前的快樂時光,它成了連接父母親的物件,風箏成了她過去美好生活的一種印記,寄托著她對父母的思念,象征著女孩的期待與希望,“她把風箏放在腿上,靜靜地等待著,她相信等風來了,她的風箏就能飛起來,她的爸爸就能回來”(《邊疆文學》第2期第19頁)。在文末,她等來了風,將風箏放飛,她自己似乎也要飄起來了,在這一隱喻建構中完成了一個孤苦無依的留守兒童的凄慘人生的關照。
趙雨的短篇小說《流逝》(《邊疆文學》第8期)則是采用一種寫意的空間敘事,文中的母親在父親去世后多年以來一直獨自生活在寂寞的屋子里,不與人來往,她將自己封閉在狹小的空間里,困囿于社會邊緣,獨自留守。期間因為修繕房子與裝修經理暗生情愫,多年未出門的她竟與男人一同前往丈夫的墓地,從“家”這一空間到“墓地”空間的置換是母親封鎖多年的一種心理突破。不料經理的妻子卻找上門來對她大打出手,在狼狽中母親又重新退守回自己灰暗的封閉空間。母親自此成了區域拆遷釘子戶,在劉主任的勸說中從那個“家”逃離多年的“我”又回去,再一次打破母親的封閉空間。其間追述了曾經的家庭狀況以及父親去世的原因:母親的尖酸刻薄和陰冷性情致使父親逃離,他成為一名海員,但在意外中卷入海底喪生。他的日記冷酷記載了他的未來規劃中并沒有母子二人。但母親并不知曉,而是一直堅守在家祭奠沉緬父親。父親本應是傳統家庭秩序的軸心,對家庭關系的建構和走向具有引領作用,但他的逝世對母親造成巨大精神打擊,使家庭不再完整。母親堅守的陰冷灰暗的家的文本空間實則影射現代都市破碎家庭的精神困境,展示了家庭的扭曲異化和家庭成員關系的失衡。家不再是親人之間心靈相互依靠和撫慰的港灣,反而成了令人心痛和焦慮的地方,致使“我”和父親的逃離,最后導致家園的失落,情感的分崩離析。
文中出現了“座鐘”這一巧妙的意象,暗含時間的流逝與停滯,開篇便出現這一意象“上足發條,幾十年來,它從未走快或走慢一次,在這么一面圓盤上,時間被不斷刻制、重復,指針劃出一塊獨立天地,和外面的世界全然無關”(《邊疆文學》第8期第4頁)。文本中時鐘里的時間不僅是一種物理時間,可以計量和劃分,是流動的,某種意義上更是一種純粹時間,它顯示出母親個體的無奈與虛空,與外在時空的疏離,永遠處于一種恒常不變的狀態。直至一天母親將其砸壞,時間的停滯使她黯然的內心支離破碎,她在時間中固守和回憶,又在時間中悄然消逝。她請求“我”將座鐘修好,是想對往日時光的一種修復和期盼,這一意象意承載了母親的創傷與期望。
兩篇小說都屬于家庭題材,并在語言和敘事上有寫意的傾向,都帶有一種悲劇色彩。“孤獨”這一主題貫穿文本。《等風來》中的小女孩有著理想世界的美好期待和對落空的殘酷現實世界的迷茫,讓小說在深沉悲涼的意蘊中追問“她”的何去何從,顯示作者對留守兒童的關愛之情。《流逝》則更側重探討當代家庭關系的建構,以詩化的語言和寫意的敘事,描述了家庭關系的裂痕化,和家庭創傷下的精神危機。
以上所選取2021年《邊疆文學》“邊疆開篇”欄目中的幾篇優秀的中短篇小說,都有各自獨特的敘事特色,作家呂翼和夏天敏的底層敘事貼近人民,語言真實洗練而富表現力和感染力,在書寫農民這一群體有他們各自獨到的見解與關懷;作家索南才讓和趙雨的小說則以荒誕敘事手法深入生活深處,揭示真實表層之下另一種生命真相,傳達對生命和社會的復雜思考;以及作家蔣在和趙雨的小說則有寫意敘事的傾向,他們用詩意的筆尖切入家庭內部,關注個體生命的孤獨與無助。縱觀以上文章,無論是現實主義傾向的底層敘事,還是現代主義的荒誕敘事,或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寫意敘事的這些小說都體現了《邊疆文學》刊物的一種開放性、兼容性和思想性。《邊疆文學》從辦刊以來就堅守著純文學刊物的神圣品位,堅持“邊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學家園”的辦刊宗旨,顯示出濃郁的地方特色,彰顯獨特地域人文精神,扎根中國大地的文化血脈,造就文學創作的千姿百態。它關注高原寫作、民族寫作、大地寫作,諸如夏天敏、呂翼、索南才讓等一批作家扎根自己腳下的土地,從高原出發,書寫大地之歌,吟誦民族之曲。但《邊疆文學》也廣納全國各地優秀作家作品,所刊文章無論是內容題材、文筆文風、敘事視角等方面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涌現許多有新意、有創見、有新格局和新視野的優秀文章。它提供給廣大人民一個廣闊的展示舞臺,無論是文壇新秀或者資深作家,都能在這里綻放文學之光,產生思想碰撞,他們敏銳的發現力將復雜世相訴諸筆端,以獨立的精神創造傾注對人類的關懷和至上的美善。作為《邊疆文學》的忠實讀者,每每翻開雜志都覺得“開卷有益”,且在“潤物細無聲”中收獲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