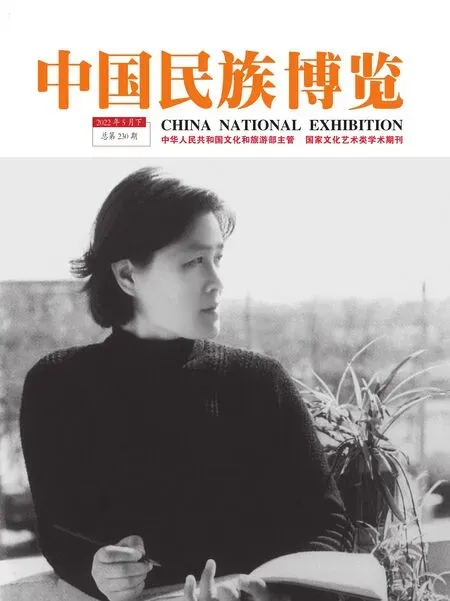彝族六祖分支史學新探
張未娜
(西安文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引言
洪水和六祖分支的記載在彝文典籍中屢見不鮮,《中國彝族通史綱要》中論述,“彝族歷史上的洪水傳說以及六祖分支是可以相信的,它已經成為了今天西南地區彝族人民所共同追認的歷史事件。而且,各地所傳洪水故事,其情節也大體相同”。學界對于彝族洪水與六祖分支的研究熱度主要集中在神話及創世史詩比較研究、祖先崇拜、遷移路線這三個方面。黃瑾、肖雪、敖行維、郭麗、楊參等用比較學的方法論證了彝族創世神話的特點,并通過創世神話佐證了彝族文化認同的歷程。對于六祖分支原因的分析,有部分學者因創世史詩中洪水和六祖分支相繼出現而將其歸結為洪水,也有學者因《西南彝志》而將其歸結為戰爭部族恩怨。基于此,通過對彝族史詩的深入比對,厘清洪水、人地關系、戰爭、六祖分支之間的因果關系是本文的寫作意義所在。
一、洪水和遷移
在《勒俄特依》《西南彝志》《梅葛》中均有對洪水和六祖分支的記載,但詳略不一,偏重各倚。在《勒俄特依》中,洪水的起因是人間勇士和天神的沖突導致天神降下洪水,結果是卻布居木的小兒子居木武吾躲避在木柜子里躲過洪水得以幸存。大水退后,武吾“智取天婚”生下漢、藏、彝三個民族的祖先,后又生下彝族六祖。在《梅葛》中,洪水起因是天神創造的第三代人人心不好,懶惰又糟蹋糧食,所以天神要求把這代人換一換并要求武姆勒娃堵水漫山川。結果是兄妹二人躲在葫蘆里逃過災難,成婚后又生葫蘆,葫蘆再生九族。在《西南彝志》《梅葛》《勒俄特依》記載中,雖然洪水的起因和結果稍有出入,但共同指出了洪水和六祖分支之間確實存在一個時間段,就是《梅葛》中記載的葫蘆生九族,或《勒俄特依》中記載的居木武吾“智取天婚”后生下的漢、藏、彝三族的時間段。至此,我們了解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洪水之后彝族并未直接遷移,從洪水至六祖分支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中間時期”。
那么為何彝族先祖在洪水后沒有遷移呢?這個問題的厘定當借助云南地區的考古資料。首先,彝族人認為人死之后,靈魂應該回到祖先的發祥地,也就是回到六祖分支的地方,而現存18部《指路經》終點大多指向了滇東北地區,故六祖分支發生地應在滇東北地區。在滇東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考古中發現,“其中石器百余件,有斧、錛、刀、網墜。陶器較完好者 20 件以上,分罐、瓶、缽、碗、壺、杯、勺等。其他尚有骨、貝、玉器,以及陶片數百”。滇東北地區出土的斧、錛、刀作為生產工具,罐、瓶、缽、碗、壺、杯、勺等則為糧食的儲存器具,為農耕文化的萌芽提供了生產資料的支撐。另外,在《勒俄特依》的流傳地四川涼山和云南小涼山普格縣內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彝族先民活動遺址,出土了大量骨器、貝器、陶器和石器。除了項飾、海貝、罐、瓦、杯、條形板斧外,還發現了石鐮和石鑿。石鐮和石鑿是典型農耕文化的產物,雖然很多學者認為彝族先祖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是從考古學資料來看,早在新石器時代,彝族便萌生了農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至洪水時期彝族社會內部已經產生奴隸和奴隸主的社會分級。土地作為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即使發生洪水,等待洪水過后,又回到原地或附近也合乎當時的社會形態。
對于洪水之后彝族先祖并未直接遷移這一論斷,從彝族先祖的“災害觀”也能得到佐證。如《梅葛》的“創世”篇中記載“試天天開裂,試地地通洞。天開裂要補起來,地通洞要補起來”,面對打雷和地震這樣的自然災害,彝族先民的做法是補天補地。同理,《雪子十二支(一)》中記載“遠古的時候,天庭祖靈掉下來,掉在額吉階勒山,變成烈火在燃燒,九天燒到晚,九夜燒到亮,白天成煙柱,晚上成巨光,天是這樣燃,地是這樣燃,為了人類起源燃,為了祖先誕生燒”。彝族是居住在半山腰上的民族,所以山火頻發,對于火災,《勒俄特依》中數次提及,但最后的結果并非遷移,而是“自適”。在文獻記載中,古彝人對洪水、地震、雷電、干旱暴曬、火災這些自然災害的處理方式并非首選“遷徙”而是“改天造地”和“自適”,所以洪水過后,彝族先祖沒有直接遷移,也是理所當然的。
二、六祖分支原因
既然洪水過后,彝族人并沒有直接遷移,那么造成六祖分支的原因更可能是隨之而來的人口小高峰。而伴隨著這次人口小高峰的是逐漸加劇的人地矛盾以及因爭奪生產資料而引發的戰爭和部族恩怨。
(一)洪水前的人地確權行為
早在大洪水之前,彝族先祖就已經確定了疆域觀的概念。在彝族文獻中,關于彝族疆域觀的最早的記載來自《封疆化域》,“有了乾天的規律,才興起了君民,有了坤地的運歷,才產生了政權,有了政權才有疆界,有了疆界才有尊卑地位,乾天君稱策舉主,封疆化地域,依山脈劃分”。“以山封域,以水劃界”的疆域觀是古彝人對土地這一“部落(族群)私產”進行確權的表現之一。到篤慕俄(《西南彝志》稱“篤慕”,《勒俄特依》稱“居木”與《華陽國志》中杜宇為同一人)時期,“以山封域,以水劃界”的疆域觀已經形成。在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年代,各部族疆域內的物產能滿足其生存需求則相安無事,一旦“人地矛盾”加劇,戰爭、遷移將變得劇烈而頻繁。
在大洪水之前,彝族社會已經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在《勒俄特依·石爾俄特》中,石爾俄特(《勒俄特依》中大洪水前標志性人物)要找到父親,需先回答約木杰列地區茲阿地都家的女兒施色幾個問題,最后一個問題是“解決祖靈又該送何方的難題”。這處情節給了我們以下信息。首先,約木杰列地區茲阿地都家的女兒知道如何實現“生子見其父”,可見約木杰列地區已經過渡到了父系社會,而石爾俄特居住的地區(部族)沒有過渡到父系社會,地區(部族)在社會形態上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發展。其次,解決祖靈送何方的問題后娶妻配偶才能實現“生子見其父”。這里的祖靈安放地不是部族的聚居地,而是自家屋壁。之后又記載了“起靈之后插在屋壁上,念經之后供在神位上,超度之后送到山巖下”的完整祭祖儀式。此處祭祀場所從“氏族”到“家族”變化是私有制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的重要表現。同時,石爾俄特找父親時帶了九個隨從者、九把銀匙子、九把金匙子、九馱銀粉末、九馱金粉末。在這段記載中,金銀湯匙和金銀粉末以及隨從都是作為石爾俄特的“私產”而帶上路去買父親。可見此時私有制已經確定,并且以“隨從”為代表的奴隸階級也已經出現。石爾俄特作為大洪水之前的標志性人物,其所處的歷史時期,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并非所有部族同時實現母系到父系的過渡,社會形態、貧富差距明顯。另外,部分地區以家族為單位的經濟積累模式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對包括土地資源、家族人口在內的私產進行“確權”的行為隨處可見。
(二)洪水后的“人口小高峰”
洪水作為自然災害,無疑對彝族先祖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一時期人口減少,生產力倒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洪水消退后,人種滅絕。洪水不僅沖走了之前已經確權的人和地,而且沖擊了原有的社會制度。在這一階段,人口減少的社會問題,甚至凌駕于階級、貧富以及道德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為了緩解這一矛盾,社會秩序發生了變化,甚至發生天地通婚、兄妹成婚這兩個有悖倫理綱常的故事。
天地通婚的故事同時記載在《西南彝志》和《勒俄特依》中。據《勒俄特依·洪水漫天地》記載,洪水后,居木武吾與天神幺女進行了天地通婚,天神恩體谷茲從開始的“主奴絕不能通婚”到后來的“苦命女兒在夫家,成天用手撕枯柴,所以我恨她”。顯而易見,作為“天”的階級十分反對“天地通婚”這樣違背原有社會階級秩序的事件。這種主奴不通婚的習俗,是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意識形態相吻合的。洪水作為自然災害,直接導致人口銳減并沖擊了原有的社會等級體系,為保證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天地通婚”才變成了可能。《勒俄特依》中天地通婚后居木武吾和妻子生下藏、彝、漢三個民族的祖先,又娶了三位天女生下彝族六祖。不管是藏、彝、漢的祖先,還是彝族六祖,都是天地通婚的結果。可見,在天地通婚后,被洪水破壞的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并產生了一個人口小高峰的時期。
兄妹成婚的故事主要記載在《梅葛》中。據《梅葛》記載,洪水淹了七十七晝夜,天神慌了神,下凡來治水。洪水消退后,人種也跟著滅絕。面對人種滅絕的困境,幸存的兄妹二人認為他們是同胞父母生,不能結合。但在天神的幫助下,“屬狗那一天,哥哥河頭洗身子,屬豬那一天,妹妹河尾捧水吃,吃水來懷孕”,懷孕之后,妹妹生下一個葫蘆,天神用金、銀錐鑿開,生出九族,彝族地區人煙才興旺起來。由于《梅葛》沒有文字記載,千百年來,它一直是靠彝族人民口耳相傳得以保存,從史詩的筆法來看,其時間跨度大、文學性強。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天神從葫蘆里能錐出九族這樣的故事情節了。《梅葛》中對九族的記載,與現代西南地區各民族的居住地、生活方式、民族特色相符,可見這一時期形成的九族對后期西南地區各民族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關于九族的傳說,亦可見西南地區白族等少數民族的歷史記載中,有學者認為這是早期西南地區各民族互相發生聯系的體現。筆者認為九族問題的探討應建立在洪水之后的時代背景下,洪水對原有社會關系的沖擊,形成了凌駕于階級、貧富以及道德之上的人口小高峰,九族的詳細描寫正是人口小高峰之后新的部族產生的體現。
對于筆者提出的人口小高峰的猜想,在《西南彝志》中也得到了印證。“天仙尼君之女,騎著神鳥飛來,與篤慕俄同住,就開辟彝族創世紀,這樣分析判斷,有了父母必有后裔,天上星星數不清,地上繁殖的人數不清。武即是慕雅枯……篤慕的六個兒子都是天星下凡,子孫多的像樹干上的枝葉,發展像海水盈溢不竭,六祖當初的繁衍,就是這樣的。”
綜上所述,洪水之前,西南地區的人民已經完成了對人口、土地的確權行為,形成了相對平衡、穩定的人地關系。洪水作為外部干預條件,打破了原先等級社會人地關系的平衡。社會各階層為了抵御洪水災害造成的生產力破壞,放松了“階層、貧富、道德”的制約,至六祖分支前期,終于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口小高峰時期,以此緩解了因洪水而引發的人口銳減、生產力破壞的社會矛盾,并形成了“九族”“藏、彝、漢”這樣新的部族。
(三)戰爭對六祖分支的催化
《西南彝志》在記載六祖分支時,對各部族遷移的路線及始末記載翔實,為后期學者研究六祖分支的原因時,形成“以爭奪土地,財產及部族恩怨為導火索,引發的戰爭直接促進了遷移”這一觀點提供了依據,對于戰爭因素在研究六祖分支原因中的重要性,因前人成果頗豐,故不在此贅述。
戰爭和遷移在彝族文獻中總是伴隨出現的。如“施阿納的子孫,聚居在東部,到朵阿武這世,舉朵婁底這地方,是武呂四子聚居,他們相延了九十世,賈喜地方十五寨,沙吐建了九個城,徹徹和魯旺,這兩座古城,被武家占據了,白天一開門,看見城里很漂亮。此時赫遮住的地方,被東部武家割據了,他只得去谷慕朵底居住”。因洪水而受到沖擊的階級、貧富、道德等秩序,使原先的社會結構變得不那么穩固,大的部族不斷分裂,新的部族產生。部族之間因搶占人口土地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再次激發,待九族分化之后,戰爭變得劇烈而頻繁。《西南彝志》在記載六祖分支的過程時隨處可見因貧富分化而導致的戰爭以及遷移。
三、結論
部分學者將洪水作為六祖分支直接原因的觀點忽視了史詩這種特殊體裁只傳唱英雄事件和重大事件的敘述特點。民族史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如果不對其進行探源,直接將六祖分支的原因簡單歸于洪水則容易以訛傳訛。洪水至六祖分支并非簡單的直接過渡,而是一個動態遞進的演變過程,首先,洪水作為外部干預條件,打破了原先社會各階層人地關系法則,社會各階層為了抵御洪水災害造成的生產力破壞,放松了階層、貧富、道德的制約,至六祖分支前期,終于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口小高峰時期。其次,伴隨著人口的恢復、生產資料的積累,又形成了新一輪的人地確權行為,許多新的部族(民族)因此產生,九族、藏漢彝這些新的部族(民族)的出現,不僅是西南地區各民族融合發展的體現,也是這一時期人口加速發展的體現。當彝族“疆域”內物資無法滿足自身發展需要時,因此而產生的部族恩怨、對外的掠奪戰爭及遷移都成為緩解人地矛盾的良策,最終形成六祖分支這次大型的人口多線遷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