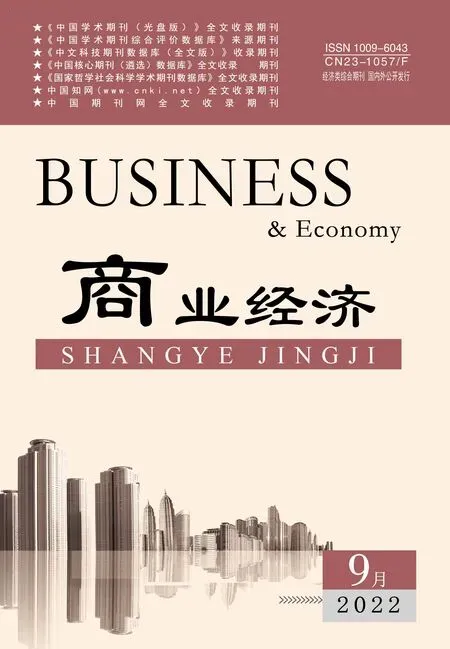多元主體共治污染的經濟機制研究
楊菁菁,鄭 晴,史 寧
(哈爾濱金融學院 金融系,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一、研究背景
自從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一方面能看到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隨之帶來的污染問題對人們的生活影響也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霧霾天氣、沙塵暴、生活用水污染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人們也越來越關注污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為回應民生關切,我國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十九大報告為未來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指明了路線圖。“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與此前“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提法相比明顯細化。基于此,本文將所研究的多元參與主體具體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然而多元主體間的經濟機制,在污染防治的過程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本文首創性分析多元參與防治污染的相互制衡經濟關系:即從政府與企業的經濟關系、到政府與社會組織和公眾的經濟關系、再到企業與社會組織和公眾的經濟關系的兩兩經濟關系著手,進而分析多元經濟關系,最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牽制格局,全面推進我國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部署。
二、多元主體共治污染的經濟機制研究文獻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生態環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導致難以完全通過純市場方式來生產和消費環保產品,因此污染問題如何通過經濟方法解決一直都是經濟學家擬求解的難題。
(一)政府與企業
在政府與企業的行為關系中,一方面,政府擔負環境規制的制定、監督和污染治理的部分投資,而企業則在環境規制約束下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另一方面,取決于企業經營情況的稅收等反過來又可能影響政府環境規制的力度和方向。對此,一部分學者認為,政府環境規制政策會降低企業生產率,減緩經濟增長速度(Jorgenson and Wilcoxen,1990) 和引起企業投資不足 (Saltari and Travaglini,2011),特別是中國地方政府在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引導下,環境規制政策執行非常有限(Lieberthal,1997)。但Porter and vander Linde(1995)提出的“波特假說”則說明,適度的環境規制反而激勵企業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生產率,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
(二)政府與社會組織和公眾
在政府與公眾的行為關系中,一方面政府通過執行并調整環境規制力度、方向與增加公共環境投資為公眾提供優良的環境質量,而公眾“用手投票”參與和評價政府的環境規制政策,并影響政府的聲譽;另一方面,公眾“用腳投票”反饋公眾對環境質量的態度并對政府施加改善環境質量的壓力。對此,Tiebout(1956)認為,公眾可以自由流動,他們可以“用腳投票”,選擇自己偏好的公共服務,給地方政府施加改善公共服務的壓力;Irwin.L.Auerbach and Kenneth Flieger(1967)也提出應重視公眾的力量,保護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Dasgupta and Wheeler(1997)使用中國1997-2003 年29 個省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公眾監督的關鍵在于污染程度,并且公眾監督的成效與公眾的受教育水平正相關。
(三)企業與社會組織和公眾
在企業與公眾的行為關系中,一方面如果企業能為公眾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和有吸引力的工資水平,不但會提升企業無形資產價值,而且擁有勞動能力的公眾(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的公眾)也愿意為企業發展貢獻其勞動力,從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如果企業不能為公眾提供良好的環境質量和工資水平,公眾對企業的負面評價會降低企業無形資產價值,同時擁有高素質勞動力的公眾也可能會放棄為該企業發展貢獻勞動力,從而制約企業長遠發展,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業改善環境質量和提高工資水平。對此,Wang(2000)通過研究中國1500 家工廠,并用小區壓力指標衡量公眾參與度,發現公眾參與度會顯著降低企業污染。Jaffeer(2011)認為,雖然地方政府對于企業污染治理的管制對改善企業治理污染的態度和行為有積極作用,但地方政府會因為考慮經濟發展而放松管制,因此公眾的參與很重要。
下文將以河北和四川大氣污染嚴重地區為例,通過主體分析法,解析多元主體相互作用與治污之間的關系。
三、多元主體共治污染的經濟機制研究案例分析
在2013 年,我國的中部和東部地區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大范圍霧霾天氣,大部分地區的空氣質量持續惡化,PM2.5 等空氣環境指標持續增高,威脅著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安全。為了更好研究多元主體對污染治理情況,本文選取了兩個地區進行調研分析,選擇了大氣污染較嚴重的地區,我國華北地區是大氣污染的重災區,其中我們選取了河北,為了研究的客觀性,選取了南方大氣污染相對較為嚴重的四川省,四川省由于四川盆地的地勢問題,冬季大氣污染不易擴散,因此,也成了大氣污染的重災區。
(一)四川德陽
四川省選取了德陽市,德陽市在四川省是大氣污染較為嚴重的城市之一,同時在多元治理大氣污染方面在全國都具有一定典型性。
1.政府主體之間構建合作機制
德陽市打造的政府合作機制主要包含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對內方面,一方面指政府內部為提高治污效率通過實時通訊技術手段及時解決各種與污染相關的突發事件,提高了對事件的反應速度,同時辦公去紙化也有利于環境保護;另一方面,強化環保執法,建立環保+警察和環保+法院的合作機制。對于過去環保部門執法能力薄弱起到了有效地加強作用,也使依法治國的理念深入人心,將環保與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僅2016 年一年德陽市共查處環境違法案件119 件,處罰金額525.7 萬元。對外方面,建立了縣域聯絡網。由于大氣污染波及范圍較廣的特殊原因,德陽市在2014 年與周邊7 個相鄰市簽訂了合作協議。主要目的就是通過信息、科研及治理方法共享方式改善大氣污染問題。
2.打造治理多元主體
德陽市的治理主體是以政府為主導、公眾社會為輔所建立的治理體系。除了上述政府之間的合作外,德陽市值得借鑒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對公眾的宣傳上,除了常見的標語、宣傳畫以及主流媒體的宣傳方法外,德陽市通過環保主題日的形式走進社區走進工廠,多角度多形式進行環保的宣傳,效果顯著,公眾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大氣污染的危害以及如何治理大氣污染,在專項治理后,德陽市的大氣污染情況得到好轉,全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270 天左右。
但是,在對德陽市的調研過程中,德陽市并沒有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參與到污染治理中,對企業的處理方式依然是簡單粗暴的關、停、罰,沒有通過污染處理提高企業的產業升級或者創新發展,因此,德陽市在專項治理后,大氣污染情況又出現的反彈,并沒有達成治理的長效機制。
(二)河北廊坊
通過我國大氣污染地圖可見,河北廊坊市是我國污染重災區,相較于同為京津冀區域的北京市與天津市,大氣污染程度更為嚴重。
1.政府主導的多元協作治理
與四川德陽的政府多元合作不同,河北廊坊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明確了不同主體責任,將治污能力與官員的獎罰相掛鉤,實現了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制定了空氣質量獎懲辦法,如果不能完成目標任務,取消官員評獎評優資格,充分激發了各部門對大氣污染治理及監管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壓政策下,廊坊市對企業大氣污染的治理做到了“一企一策”,推動了一批企業環保設施的建造或污染設備改建,間接的推動企業在環保方面的創新發展,促使企業也成了治污的主力軍。
2.社會組織參與大氣污染治理
河北廊坊的社會組織對污染治理的貢獻,除了居民更體現在科研專家的加入。政府采取政府購買的形式,通過“千人計劃”治污專家組打造了科學治污、系統治污和創新治污的新理念,其效果也尤其顯著。同時,專家小組與當地媒體共同打造了一檔討論污染內容的電視節目,通過這個方法吸進了大量市民參與到治理污染的行動中,相對于德陽市,廊坊市后續的保持情況更為顯著。
通過上述案例,不難發現單一主體在治理污染不現實,在治理過程中兩兩主體都會產生相互作用,如果忽略多元主體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割裂了這種潛在的制約關系,在大氣污染治理中,污染將會出現反復現象,不能達成大氣污染治理長效機制,這其中包含了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公眾以及企業與公眾的相互關系。
四、多元主體共治污染對策

基本思路圖
(一)二元防治:政府與企業
在防治污染的關系中,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從邏輯上分析,政府嚴格污染規制,一方面會增加企業負擔、導致企業流出和勞動力流出;另一方面企業負擔的增加和相應勞動力的流動又會反作用于政府對環境規制的強度和水平。由于政府與企業的利益是相互聯系和影響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旦政府注重經濟發展,大氣污染治理成果就會受到影響,但是反過來,大氣污染指標嚴查時期,各地方就會出現,企業被整頓、關停的問題,當地經濟受到影響。我國政府應該通過獎懲機制來促使企業主動達成環保目標,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企業升級改造設備,幫助企業自主完成節能減排的環保目標,這樣才能達到治理污染的長期效果。
(二)二元防治:政府與社會組織和公眾
環境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環境的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我國財政分權和政治集權的管理體制下,政府面對自上而下的壓力,僅將減少污染和保護環境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缺乏建立節能環保長效機制的主動性。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環保事業的最初推動力來自公眾。因為公眾是環境切身的消費者,社會組織和公眾的訴求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多元防治污染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政府與社會組織和公眾之間其實也存在相互影響關系。盡管,我國各城市在治理過程中還沒有出現公眾主導治污的現象,但是公眾對美好環境的訴求意識在覺醒,在天氣晴朗、沒有大氣污染的天氣里,公園和室外活動的人口密度是激增的,政府應該增加更多獲取公眾對生活環境需求的渠道,同時拓寬對大氣污染指標的范圍。公眾推進的大氣污染治理才能把污染治理日常化、平常化而不是政策化、項目化。
(三)二元防治:企業與社會組織和公眾
在分析政府與社會組織和公眾的相互作用關系時,我們分析了因勞動力流失所導致的財政收入減少和聲譽的降低將迫使政府采取治理環境、減少污染的機制。同時,勞動力的流失也意味著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流失,這將影響企業的長期發展。尤其,當污染企業作為污染源時,不止會導致勞動力流失,有的企業還會嚴重傷害到員工的身體健康。因此我們認為,勞動力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動是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當前制度背景下“用腳投票”的一種“退出”威脅,該威脅長期來看(由于影響人力資本在某地區的聚集)影響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企業的工資水平及優質的工作環境對勞動力的流動也會產生影響,由此形成企業與社會組織和公眾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因此,暢通員工曝光企業工作環境渠道保持勞動力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對稱性以及通過提高對因企業污染源致病的賠償額度增加企業經營成本,都是可以有效倒逼企業提高治污能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