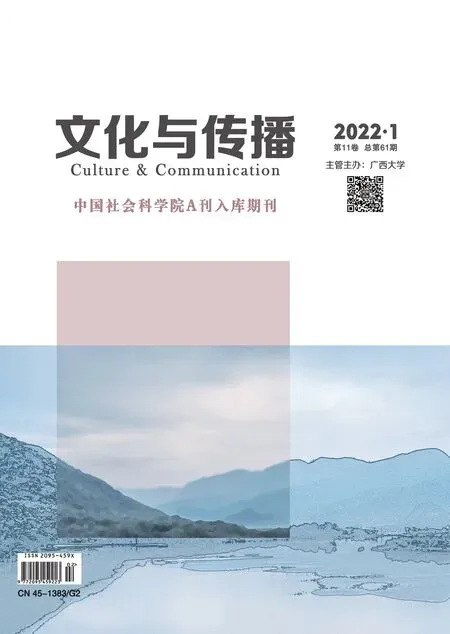“劉三姐”在新加坡的傳播與形象研究
關熔珍
形象研究屬于比較文學研究新領域,此“形象”與一般意義上的形象大不相同,往往聚焦一個國家的文學或文化現象的海外或國際化的傳播及其影響,主要關注其跨文化、跨意識形態,甚至是跨種族的海外或國際化接受或認知,也可以直接定位是該文學或文化現象的國際形象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倡議提出之后,有關中國文學或文化現象在海外的傳播情況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研究中國文學的異國形象及其所蘊涵的意義,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國家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情感和態度,更好地推進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接觸與交流。其中,在面向東南亞國家的海外文化傳播研究中,“劉三姐”的海外傳播形象研究值得關注。
“劉三姐”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沉淀下來的一張壯族經典文化名片,源自廣西壯族自治區鄉間地頭民間傳說中的山歌能手劉三姐,又稱“劉三妹”“劉三姑”“劉三媽”“劉三婆”“劉三太”等,涵蓋所有有關“劉三姐”的文化產品,包括戲劇、電影、文學、藝術等以及衍生出來的相關產品,其中電影《劉三姐》最為典型。山歌是中國民歌的基本體裁之一,主要是人們在田野勞動或休閑娛樂期間即興抒發情感的抒情歌曲。山歌內容一般較為寬泛自由,可以信手拈來,隨性而歌,往往涉及普羅大眾的生活、勞動、愛情等方面。山歌的格式結構簡潔明了,節奏自由明快。山歌情感豐沛質樸,可以嬉笑怒罵,也可以悠然空靈,充分體現了以歌言志、傳情、會友、抗爭的中國大地各民族千百年傳承下來的民歌文化傳統。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興,國內建設生機蓬勃,亟須發展適應時代的新文化。大潮之下,廣西壯族民間歌手“劉三姐”的故事被搬上舞臺,賦予“歌仙”形象,掀起了一陣席卷全國的“劉三姐”民間故事創作高潮。60年代,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同名電影《劉三姐》廣受大眾喜愛。其后,電影《劉三姐》先后多次在香港與東南亞等地區熱映,之后,在世界 50多個國家上映,創下了當時中國故事片在國外發行的最高紀錄。電影《劉三姐》引發國內外關注,從而奠定了“劉三姐”的山歌銀幕文化形象,并使這一形象突破廣西地方民族文化的界線,進入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關注領域,甚至走出國門,成為世界性的民族文化精神食糧。
“劉三姐”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大多從電影《劉三姐》的上映開始,但是在各國傳播過程中,其與不同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相遇、相融、相碰撞,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劉三姐形象國際化接受文化。其中,新加坡的“劉三姐”形象與傳播就別有特色。
因此,本文主要以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梳理 “劉三姐”在新加坡不同歷史時期的傳播和接受情況,聚焦探討“劉三姐”在新加坡傳播接受過程中所呈現的對堅強不屈、忍辱負重、追求美好生活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由此構建出文化同源、身份同構、理想同向的新加坡“劉三姐”形象,旨在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個國別的借鑒和思考,促進世界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文化。
一、邁向自治的新加坡(1945—1963):堅強不屈的“劉三姐”形象
1945年9月,英軍回到新加坡。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為英國直屬殖民地,戰后的新加坡已經與戰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當時的新加坡正處于邁向自治、努力爭取擺脫英屬殖民統治的階段。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5月30日,舉行第一次大選;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職,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1961年5月,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想把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沙撈越和北婆羅洲聯合起來組成聯邦,對此,李光耀決定舉行全民投票,最后71%的人投贊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英國的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此時,新獨立的前西方殖民地其他國家正處于國際冷戰局勢中而自顧不暇,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正面臨西方全面制裁而不得不在萬隆會議上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面對這樣嚴峻的國際國內生存環境,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新加坡華人感受到了一種無根飄零的無奈,生存和發展如履薄冰,文化上更是處于一種自我否定的邊緣空間。
此時,電影《劉三姐》在新加坡播映,帶來了同樣的黑頭發、黃皮膚、熟悉的鄉音,還有魂牽夢縈的山水。強烈的形象相似性讓當地華人紛紛前來觀影,聚焦銀幕上的劉三姐,一解鄉愁的同時,更是深入思考自己未來文化身份根源的方向問題。主角劉三姐出身草根,無權無勢,卻聰明睿智,才能出眾,不畏強權,不依附他人,不亢不卑,積極樂觀,靠唱山歌贏得了愛情。電影充分演繹出了草根階層鐵骨錚錚的氣質,把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積淀下來的奮斗不屈、生而有志的民族文化精髓匯集在劉三姐的身上。這樣的劉三姐形象讓新加坡華人觀眾的代入感極強:他們跟祖輩或者是父輩漂流而來,在新加坡落腳,無權無勢,無根無基,只能靠自己拼搏,像劉三姐一樣,活出自己的人生。
電影《劉三姐》讓新加坡華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銀幕上聽到歌聲笑語、看到智慧、看到祖國風光、看到鄉里鄉親團結友愛和希望,感悟到未來生活的方向。很快,觀看電影《劉三姐》成了當時新加坡華人的自發自覺行為,觀影的群眾越來越多。電影持續叫座,一再延長播放時間。據統計,電影《劉三姐》公映9天之后,新加坡觀眾已經達到了108295人次。公映結束時,電影在當地上映期竟然長達7個月,觀眾50萬人次,占當時新加坡人口的60%,盈利40萬新幣,創下了當時新加坡上映時間最長、最賣座的電影紀錄,甚至形成了吸引上百萬人從馬來西亞去新加坡看電影《劉三姐》的盛況。
電影在新加坡上映的時候,1978年新加坡當地報紙《南陽商報》6月14日的影訊是這樣介紹的:“劉三姐代表了不屈不撓的勞動人民之意志,她唱的每一首山歌,有真情有實意!有憤怒有控訴!有潑辣有辯駁!有正義有勇敢!有諷刺更有趣味。”而這正是當時新加坡華人的心聲。來自故土的《劉三姐》儼然成了一種表達對時局的無聲控訴、駁斥和諷刺的絕佳藝術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尋回華人堅強不屈文化基因的無聲集結令。可以說,《劉三姐》在新加坡的上映適逢其時。
因此,在當時的新加坡,電影所到之處,掌聲雷鳴。“劉三姐”形象迅速生根發芽,與當地華人觀眾形成了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上的共通共融。《劉三姐》打破了當時美國暢銷電影《亂世佳人》在新加坡的賣座紀錄,呈現一種獨特的文化氣息,展現了華人在新加坡聚集的力量。雖然當時新加坡主流媒體對《劉三姐》播放的報道不多,但是打破紀錄的票房賣座率充分說明了華人對《劉三姐》文化的剛需。很多觀眾反復觀影,甚至全家老少一起觀影,場場爆滿。可以說,銀幕上的劉三姐為當時正處在面臨新加坡自治邦努力與馬來西亞結盟構建馬來西亞聯邦之際,為即將面對異質族裔文化碰撞而深受文化身份困擾的新加坡華人指明了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方向,更充分展現了新加坡華人在飄零時局中的堅強不屈精神。
二、新馬合并期的新加坡(1964—1965):忍辱負重的“劉三姐”形象
在1962年最初的轟動之后,“劉三姐”形象沉寂了下來。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了英國殖民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新加坡的政治局勢讓華人不得不蟄伏隱忍。正是這一年,新加坡華人漫畫家馬駿幾乎傾盡家財從香港聯誼公司購買了《劉三姐》的電影并拷貝至新加坡放映,豪賭45萬元新加坡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華人遭遇嚴重排斥的馬來西亞聯邦統治之下,新加坡觀眾如潮,甚至成千上萬的馬來西亞人涌進新加坡看電影《劉三姐》,最后讓他賺了個盤滿缽滿,盈利 200多萬。
電影中的劉三姐對待生活,樂觀積極,上山可打柴,下河可捉魚,是生活小能手;對待鄉里鄉親,溫柔以待,山歌傳心,有禮有節;對待愛情,藤樹相纏,生死與共;對待酸腐秀才,毫不膽怯,斗智斗勇,以來源于現實生活的山歌對抗照本宣科,“瓷石不怕細玉”;對待敵人財主莫老爺有勇有謀,“你要殺人我會逃,你要斗智我奉陪”,甚至聰明地引導地主進入自己的擅長領域里面對歌,才智碾壓。整個電影中不見血腥、不見直接的械斗,卻又明明白白地向觀眾展現抗爭的希望和勝利的可能。顯然,對正在時局下艱難求生、忍辱負重的新加坡華人來說,電影《劉三姐》仿佛成了一劑解救苦難、指引方向的良方,能夠緩解現實生活中對時局的焦慮。
然而,這樣的忍辱負重并沒有給新加坡帶來應有的發展機遇。相反,1964年12月,馬來西亞聯邦中央政府完全無視華人遭遇不公的社會現狀,強行要求新加坡將上繳中央的稅收從原來的40%增加到60%,幾乎不給新加坡生路,甚至以此為借口,修改憲法,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的絕對優勢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這對當時的新加坡華人而言,無疑是一個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至暗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文化身份認同機會出現的絕佳時期。1965年8月9日,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在脫離馬來西亞聯邦之后,宣布成為一個有主權、民主和獨立的國家。可以說,現實社會的“劉三姐”闖出了自己的命運之道。
三、立國至1990年的新加坡:追求美好生活的“劉三姐”形象
20世紀60年代中期,獨立后的新加坡積極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可:1965年9月加入聯合國,10月加入英聯邦,1967年協助建立東盟并成為其中一員。在經濟上,新加坡充分發揮了積極能動性,大力發展經濟,逐漸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多元文化身份特色。為維系不同民族之間的情感,減少民族沖突,在文化上,新加坡實行“英語為本+母語”的雙語政策,支持各民族多元發展。
1978年,電影《劉三姐》再次在香港熱播。當時的報紙連續發表評論,認為“《劉三姐》對香港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影市場,可能是一次‘變’的轉折點”。果不其然,繼香港之后,同年,新加坡再度推出該片,同時在10家影院上映,46天盛況不衰。這是新加坡立國之后的文化盛事,可以說是盛況空前。新加坡的加龍、黃金、長江、璇宮等影院同時上映,觀眾熱情高漲,全家出動去影院觀看劉三姐唱山歌,傳說甚至是盲人也到現場聆聽。電影院幾乎場場爆滿,再創歷史之新高。新加坡“劉三姐”的迷客之一于思在1978年3月21日的《星洲日報》上發表了《可愛的〈劉三姐〉來了》的文章,圖文并茂地表達對劉三姐的喜愛之情。于思說:“《劉三姐》 這部影片為什么這么吸引人呢?依我看,該是它的歌曲優美動聽,歌詞意義深刻含蓄,景色宜人,故事又新鮮,更主要的還在于它刻畫了一個美麗生動的劉三姐形象。”在已經獲得國家獨立、正努力實現文化獨立的新加坡人看來,這個時候的劉三姐,順水而來,無依無靠,卻又活得灑脫自然,不畏強權,不求依附,以優美動聽的歌聲做自己的身份名片,以與財主秀才斗智斗勇展示自己的風姿,以來去自如、不拘一格的態度張揚自己的生活哲學,這無一不契合新加坡華人尋求文化身份的堅韌和自立精神。同年5月10日,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都對“綜藝機構在黃金戲院映《劉三姐》招待報界”的新聞做了報道,高度贊揚了《劉三姐》的人美、歌靚和山水奇秀,充分表達了對《劉三姐》的百看不厭,熱愛不已。這個時期的“劉三姐”形象無疑契合立國之后尋求文化創新的新加坡華人的需要,達到了融入認知的程度。
可以自主決定電影的放映和盡情地觀影,讓新加坡華人對《劉三姐》的喜愛從銀幕蔓延到了現實生活。“劉三姐”的形象開始呈現多元表述模式,更加滿足新加坡華人的文化需求。除了電影《劉三姐》,歌舞劇《劉三姐》以及劉三姐扮演者黃婉秋所率領的廣西民族歌舞團在新加坡也大受歡迎和熱捧。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說,在新加坡演出時,觀眾的熱情很高,里三層外三層圍滿了要簽名的人。新加坡眾多電視臺、無線電臺以及報紙媒體等,如《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等紛紛報道。《劉三姐》電影所營造的“人美、歌甜、景麗”的形象已經深入新加坡華人之心,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個華人骨子里的執著。
1979年,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開展“講華語運動”,在新加坡掀起了講統一華語的熱潮。80年代,新加坡推進了中學儒學課程的建設工作,不斷推進華語語言文化和歷史溯源建設,進一步促進了國內華人和社區之間的團結,強調了新加坡華人的中華文化身份和歷史根源。盡管此時中國與新加坡尚未正式建交,但是同宗同源的華人文化和身份認知促進了兩國漸漸接觸,相知、相交和發展。
四、中新建交以來的新加坡:中華文化符號的“劉三姐”形象
1990年10月,中國與新加坡正式建交。1991年新加坡“華族文化節”開始舉辦,其以推廣和傳播華族文化為己任,促進世界華人文化認同。“劉三姐”開始以國家級形象進入新加坡。2004年1月,中國新聞網報道“‘劉三姐’將代表中國參加新加坡‘華族文化節’”;2012年1月,新華網和網易財經報道“中國新一代‘劉三姐’亮相新加坡龍年新春舞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為活動剪彩;2013年7月,新華網熱烈報道“大型彩調歌舞劇《劉三姐》2013全球公益巡演”,其中9月巡演就在新加坡;2018年3月《南寧晚報》報道“《劉三姐》新加坡上演 廣西彩調文化展現精彩”,同年4月,新華網報道“三代‘劉三姐’放歌獅城傳承經典”、5月,新加坡Esplanade網頁上報道“Songs of Liu Sanjie-A Musical Film in Concert”,12 月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第12屆客家歌謠觀摩會上演‘客家劉三姐短歌劇’”;2019年12月,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劉三姐與小唱片賀新年”;2020年11月,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曼舞羅新娛樂戲院創本地電影放映紀錄”,其中介紹了新加坡曼舞羅新娛樂戲院和“孔子后人建金華戲院”“20世紀60年代,它獻演的中國歌唱片《劉三姐》,由黃婉秋領銜主演,連續公演186天,創下演出最長紀錄,轟動一時,至今仍然被公眾和影迷所樂道。”
這一時期的“劉三姐”傳播在中國與新加坡正常邦交之下走上了正常途徑,對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而言,“劉三姐”就是親切的鄰家姐姐,濃厚的文化認同幾乎是與一年一度的文化活動共存,開口唱山歌成了一種文化儀式,仿佛是文化活動的必要環節。其中,2012、2013、2014年的迎春活動或者是文化節都呈現出了濃厚的“劉三姐”氣息。比如,2012年新加坡“春到河畔”開幕式主賓李顯龍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說,“今年‘春到河畔’相當精彩,我每年都來,今年表演真的很不錯,尤其是剛才看了《劉三姐》的演出,勾起我的回憶”。2013年中新網報道:新加坡逾2000華人河畔“飆歌”創紀錄,“輕歌妙曲意難忘”。籌委會主席梁誠煒說,他們的靈感確實來自《劉三姐》,2012年的“對歌”吸引了1800人,人協今年把它變成“歌林大會”,人協還廣發“英雄帖”,邀請了15個集選區的歌唱好手來斗歌。人們盡情歡歌,暢所欲言,以山歌為媒介,實現新加坡華人文化圈的心心相通。新加坡華人對“劉三姐”十分喜愛,當地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曾多次邀請黃婉秋前去表演,2014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還與黃婉秋一道在旅游車上把象征廣西民俗文化的繡球一個個拋向熱情的民眾,讓新加坡民眾感受廣西的友誼。“劉三姐”這一中華文化符號在新加坡可以說是落地生根,共同構建了世界華人文化的精彩。
五、結語
《劉三姐》在新加坡的傳播,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影視文化的境外傳播現象,而是一個世界華人祖籍文化的溯源認同,是新加坡華人發自內心的、集體無意識的呈現。新加坡的華人并不是無根浮萍,他們是新加坡的最大民族,是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同樣是世界性的華人族裔。“劉三姐”的形象不僅僅是一個遠在故土的文化意象,更像是一個凝聚在華人血脈中的堅強不屈、忍辱負重、追求美好生活的基因的外在呈現,仿佛火種一粒,總能夠喚醒新加坡乃至世界華人的內在激情。這應該就是“劉三姐”在新加坡得以傳播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