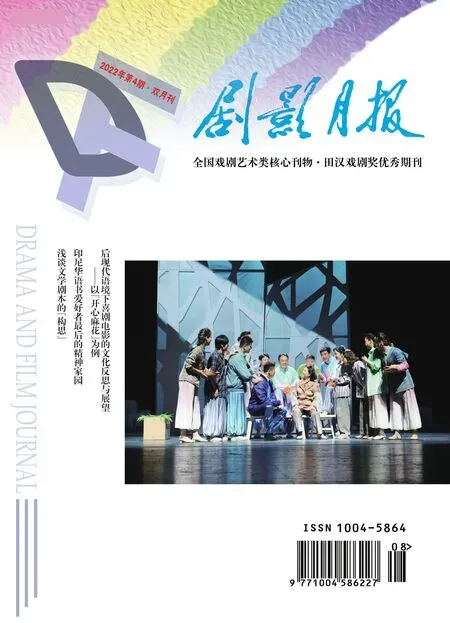論《野馬分鬃》的導演個人色彩
■黃茵 何勝
《野馬分鬃》講述了大學生左坤在畢業之際,佇立于大學和社會的十字路口,陷入了想大展拳腳闖蕩一番卻又茫然無措的境地。擁有了自己的二手吉普車之后,左坤急于逃離當前的狀態,于是一段真正的草原之行成了左坤心心念念的尋夢之旅。《野馬分鬃》是90 后導演魏書鈞的長片處女作,入圍了第7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獲得評審團特別榮譽獎。這部充斥著青春氣息、洋溢著野性氣質的影片也引得國內觀眾注目。該片是導演的第一部長片,此時導演尚未形成自己的成熟風格,但影片在制作上承載了導演雖未成熟但已具雛形的個人風格,在敘事上拒絕了傳統的以“起承轉合”為核心的敘事手段,將重點放在了對細節和狀態的展現層面,所體現出的創作初衷及命題選擇,顯得彌足珍貴。
一、光怪陸離:鏡語呈現風格化
影片中多次提及國內外的藝術片導演,在揶揄片中導演明哥的藝術理念之余,影片中同樣表明了魏書鈞“迷影青年”的身份。不難看出,《野馬分鬃》表現出了和臺灣導演楊德昌的作品的某些共同屬性,在平實的鏡頭表象之下,是對悲劇與荒涼的表述。相較楊德昌而言,魏書鈞選擇添加一些更為荒誕、迷離的影像表達自身的思考。在鏡語表現方面,影片大量運用冷靜克制的寫實鏡頭,以表現個體的經歷與客觀的現實世界,除此之外,導演也使用了非常規的敘事視角與視聽呈現方式,表現出主角細微的心理變化與迷離的生活狀態。兩種敘事方式在影片中交錯進行,而后者所呈現出的光怪陸離的景觀,更是導演初具雛形的影像風格的體現。
影片在寫實鏡頭之中傳達出對人類情感、對社會現象的深沉思考。左坤來到女友阿芝兼職的商場,兩人在電梯交談之后,阿芝搭載電梯下降,左坤上升,攝影機隨著阿芝下降,音樂出現,主持人介紹活動,阿芝隨后扮作“兔女郎”出場。鏡頭隨著左坤的再次出現上升,而此時的左坤孑然一身,與四周熱鬧的氛圍格格不入。左坤與女友阿芝所乘坐電梯的上升與下降,暗示兩人關系的疏離,同時也是對兩人不同的生活理念的展現。左坤選擇向上而去,擺脫主流的價值體系,追尋無人問津的理想。阿芝選擇向下融入人群,進入了由社會規則形成的關系網。這層關系網由兔女郎、豪車以及喧囂的音樂組成,是由消費主義元素形成的矩陣陷阱,阿芝向下愈發不可自拔。兩者愈漸疏遠,最后兩人的分離也變得理所應當。在這個兩分十五秒的鏡頭之中,導演使用單個長鏡頭進行敘事,尤其是電梯一段,采用“降—平視—升”的鏡頭表現人物關系的變化,場面調度成熟有序。在色調處理上,用冷峻的色調展現兩人的談話,在電梯向下時,則用變化的燈光與嘈雜的音樂,與前一部分形成反差對比。
導演同樣也使用非常規的、奇觀化的鏡頭表現荒涼意味。左坤與童童駕車行駛在黑夜中,開始車頭的四個燈發出強烈的光,隨后熄燈,只余方向盤上微弱的燈光,相比于視覺上極致的暗,兩人大聲交談的聲音更能吸引觀眾。而接下來的一個鏡頭,是一匹無聲的野馬奔馳在草原上。兩個鏡頭的聲畫組接,前者隱匿身軀,后者缺失聲音,讓吉普與馬形成深度互文。同時,在馬奔騰之后,左坤不得不面臨來自郭老師和畢業的壓力,前一段用曖昧的、晦暗的影像所建構的具有浪漫氣息,在課堂出現之后便被拆解。于是,左坤對于理想與自由的追尋,變得脆弱易碎了。在影片后半段出現的左坤與童童的駕車戲中,理想與自由則被徹底地否決了。劇組殺青之后,草原的現代化讓左坤說出“這也他媽太不草原了,咱們得去真正的草原”,兩人開車前往理想中的內蒙古,左坤卻因無證駕駛被警車帶回警局。警車前行,左坤坐在兩個交警中間,導演同樣用低亮的、晦暗的鏡頭表現,與此同時,車后出現遠方的焰火。左坤的草原之行終于還是沒有到達,一個烏龍事件讓這段旅行終結于將啟未啟,左坤的理想化為泡影,青春的躁動與野性在此刻也化作了黑夜中轉瞬即逝的焰火,真正的草原也成了心中有所想,但并未到達的理想之地。
二、恍兮惚兮:個體寫作與狀態呈現
從第六代開始,個體寫作便成為青年導演們常用的敘事策略,這一策略延伸到更為年輕的一代導演中,或者是畢贛對于故鄉凱里表現的執念,或者是忻鈺坤對于多線敘事的沉迷,也或者是白雪對于深港兩地尋求身份歸屬的邊緣人群的認同。不難發現,青年導演們的創作意圖,往往同他們的成長經歷、個人體驗息息相關。《野馬分鬃》并沒有脫離這種創作策略,魏書鈞用影像結合自身經歷,書寫了迷茫的年輕一代的個性,呈現了處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茫然無措的狀態。
《野馬分鬃》是一部半自傳性的影片,不論是導演的求學經歷,還是導演的畢業之后與二手吉普車的故事,都在電影中得到充分的指認,從這個角度講,影片作者性十足,導演敘事也更為個性化。影片所表現的左坤的迷惘狀態與導演畢業之時的思考相互交織。影片故事結構于導演魏書鈞的青春經歷,但在故事的具體內核中,導演對于青春的認知與體驗卻并非局限于自身一人。迷惘困惑的時期,青春獨有的旺盛的活力不知何處宣泄,化作野性和叛逆肆意張揚,對于理想的追求卻被現實的詰難所阻隔,個人與周遭社會環境的關系便開始變化,而這種變化,是年輕一代的青春的顯影。從個人經驗到一代人的認同,導演在書寫個性的同時也書寫了一個時代。
導演放棄了傳統的以“起承轉合”為核心的敘事手段,選擇用瑣碎的、無常的生活經歷成為敘事的主要部分,影片的主要目的并非單純地“講故事”,而是為了讓觀眾感受到左坤所處的狀態。電影中劇組聚餐酒醉之后,大家一同唱起了中國傳媒大學的校歌《小白楊》,這一場戲既是對青春的燥熱狀態的展現,同時也是導演對個人經驗的書寫的佐證。之后,左坤與童童在吉普車內唱起了說唱歌曲《NB克拉斯》,節奏強烈的音樂與演員夸張的肢體動作,傳達出片中人物旺盛的青春活力與野性不羈的狀態。
魏書鈞對“自我”的追問,更能以其“迷影導演”的身份進行詮釋。如上所言,影片中多次提及侯孝賢、王家衛等導演,讓導演名字所指稱的符號參與影片的敘事,同時,影片在畫框之外,更形成了與觀影觀眾的有效互動。或者是對王家衛、洪尚秀的“不用劇本”的詼諧表述,也或者是對演員豐哥“坎城膚色”的戲謔,都讓觀眾會心一笑,于是,導演的“迷影”身份與觀眾的觀影經驗便契合在一起了。
三、荒腔走板:創作者的一次叛離
影片除了對青春的迷惘狀態的展呈之外,還通過主角與身邊人物關系的變化,對左坤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有力批判。臨近畢業,左坤想大展拳腳卻陷入不斷下降的漩渦之中,這一漩渦是由社會規則和世俗觀念共同建構,影片中的左坤想要從漩渦里掙扎出來,開始選擇叛離,駕著吉普去追尋理想的內蒙古,而影片之外的創作者也選擇了叛離,通過影像表現出對于社會規則的唾棄,對周遭環境的不滿。
影片的敘事動因,很大程度上來自片中明哥所拍的電影,從而使得《野馬分鬃》成了一部“元電影”,“元電影”亦即關于電影的電影。不過本片結構“元電影”的主要目的并非探討電影本體,而是借用“元電影”巧妙表現創作者的批判性。面對童童的“給我一份劇本”的訴求,明哥以王家衛、洪尚秀為例,表示拍電影不需要劇本。在內蒙古補拍時,明哥因“民族特色”未能按時到達片場,豐哥主持了局面。明哥看過其所拍內容后,直呼“洪尚秀”,隨后兩人做出惺惺相惜的姿態,開始無腦吹捧。明哥表面對于藝術十分癡迷,崇尚電影大師,實則是借藝術之名,行不軌之事。明哥的人物形象設計,是對當前電影行業的種種亂象的揭露和諷刺。明哥與左坤不同,左坤仍保有對于藝術的追求,在拍戲時也會因補拍環境音和豐哥起沖突,但明哥卻早已將拍電影當成一種贏得自身利益的手段。
女友阿芝和左坤同時畢業,但顯然阿芝更能適應社會規則。一開始兼職做車模、前臺,又做到了領班,在規則之下游刃有余,很快便成為掌握規則的人。而左坤仍在十字路口茫然佇立,處于懵懂無知的狀態,兩人關系漸行漸遠。阿芝父親來到北京,為他提供公務員報考信息,甚至催促他在招待所報考,想將他束縛在體制之內。兩人對于左坤的訴求一致,都想讓他回歸到主流價值所認同的體系之中,表現出一種將野馬馴化為家馬而做出的努力。面臨經濟的壓力,左坤找到了明哥為他介紹的內蒙古老鄉——一個想做歌手的老板。為了迎合老板,左坤和童童開著吉普到北京各大學售賣老板的唱片,盡管無人問津,左坤在面見老板時仍然謊稱光盤已經賣完。在一段荒誕的旅行之后,回到北京的左坤發現,昔日無人問津的歌曲,已經成了流行歌曲,媒體爭相報道,網民也對其青睞有加,通過對“一百首歌,一百首詩”在不同語境中被反復提及,影片對當下病態的審美趨勢和流行文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反思。
然而左坤的叛離并未徹底,他在短暫的草原之行后回歸主流社會。愛情、學業、家庭,相繼出現了難以挽回的危機,左坤選擇背離,在奔向自由的途中,因無證駕駛被刑拘,長發被剃成平頭,正如野馬的鬃毛被剃掉,人與馬的野性象征同時被抹除。在監獄剃度之后,左坤付出了成長的代價,終于告別了過去。父親和昔日好友寒暄,左坤來到窗口,看見樓下的犯人在操練,正好是野馬分鬃的招式,隨后變陣為“感恩”兩字。同樣是平頭的左坤意識到他也歸屬這個群體,穿著制服,表示感恩,正如監獄外被社會規約所馴化的人群。回到北京之后,左坤打算賣掉吉普車,在等候中介來看車時,童童借來了學士帽給左坤戴上,童童把手機放在車內拍照。在這個鏡頭中,以吉普車的視角看左坤的“畢業儀式”,左坤和車已經不能共用同一視角,車與人通過拍照形成了對視姿態,人車已然分離。在得知這輛車會開往內蒙古時,左坤決定送出這輛車,他將希冀和自由完全寄托在吉普車身上,希望它可以到達他所不能觸及的真正的內蒙古。在影片中,吉普車和馬深度互文,但兩者畢竟還有差異,吉普車行駛在公路上,會受到交通管制,仍然處于權威的管控之下,左坤兩次受到處罰,童童甚至被一個假交警嚇到駛離了預定的軌道。而在影片最后的一個鏡頭之中,兩匹野馬則能自由地馳騁在草原上。在權威和規則之下,吉普并不能到達左坤想象中的內蒙古,而左坤也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魏書鈞導演是中傳2015級電影專業研究生,名副其實的“學院派”,《野馬分鬃》獲得的成功,對影視專業的學生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對當前我國的影視教育也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意義。總的來說,《野馬分鬃》體現出了導演強烈的個人色彩,不論是獨特的鏡語呈現,還是基于個體寫作的敘事方式,抑或是影片所展現出深刻的批判力度,都使得魏書鈞在眾多青年導演中脫穎而出,也無怪戛納電影節和First青年影展都對他青睞有加了。
[1]李少白:《中國電影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魏成穎:《〈野馬分鬃〉的反類型化敘事》,《電影文學》,2021年第8期。
[3]楊博:《元電影與迷影文化》,《傳播與版權》,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