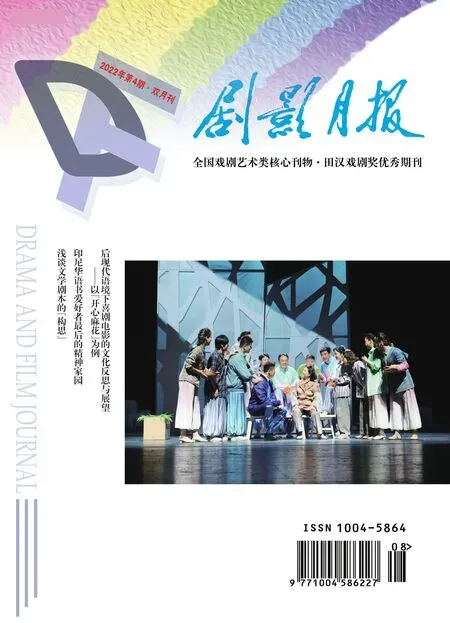昆曲在宜興的流傳考證
■殷麟揚
明代是昆曲盛行的黃金時代,昆山與宜興隔太湖相望,重文教科第的宜興子弟也會受其影響。在明代“曲圣”魏良輔改革昆山腔而為水磨調之初,即有宜興籍人士在本地傳唱昆曲,見于明代戲曲評論家潘之恒所著《鸞嘯小品》,這是目前尚能找到宜興人傳唱昆曲最早的記錄,另外明代曲家鈕少雅在其著的《南曲九宮正史》序言中寫道其來宜興傳唱過昆曲。明末清初的宜興,文風熾盛,稱冠于常州府屬八縣,更有“陽羨詞派”的領袖人物陳維崧,在其詞《蔣京少〈梧月亭詞〉序》云:“銅官崎麗,將軍射虎之鄉;玉女崢泓,才子雕龍之藪。城邊水榭,跡擅樊川;郭外釣臺,名標任昉。雖溝塍蕪沒,難詢坡老之田;而隴樹蒼茫,尚志方回之墓。一城菱舫,吹來《水調歌頭》;十里茶山,行去《祝英臺近》。鵝笙象板,戶習倚聲;苔網花箋,家精協律。居斯地也,大有人焉。”不僅證實了宜興傳唱詞曲之盛,而且包含了宜興的地理人文,一時風云際會,睥睨文壇。所謂詞為詩余,曲為詞余,詩詞曲三者雖各為分流,但實屬同源。當時宜興籍的創作文人群體有邵璨、吳炳、路迪、周濟、萬樹等,可謂群星閃耀,足稱一時之勝。自明代以來,家樂日趨盛行,宜興的望族蓄樂為樂,當時宜興蓄有昆曲家班的有:吳炳、儲懋端、徐懋曙、儲貞慶等。當時宜興望族子弟不僅創作劇本和蓄樂家班,而且還習唱昆曲。清朝光緒年間,宜興曾有過專門的昆曲社為“遏云社”,社里唱曲造詣較深有:史又浦,劉文英等,至民國“遏云社”改組為“協和公會”,有六十余人,會址在宜興瀛園,社員有周組園、賈士毅、楊蔭瀏、周策魯等。在清代至民國時期宜興歷史上還有專業昆曲團體來演出。
在宜興文化世家中有不少擅長于曲,并形成了較有規模的曲家群體。曲家們創作動機或為懷念親人,或為娛親、壽老,或為自娛自樂。在明清以來宜興籍的創作群有:邵璨創作的《香囊記》,吳炳創作的《西園記》《療妒羹》《綠牡丹》《畫中人》《情郵記》合稱《粲花齋五種》,路迪作《鴛鴦絳》、周濟作《海燕記》、詞人萬樹作《風流棒》《空青石》《念八翻》等二十余部劇作。可謂群星閃耀,足稱一時之勝。其中尤以吳炳最為突出,清初李漁曾給予吳炳劇作很高的評價:“《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才鋒筆藻,可繼《還魂》”,把吳炳與湯顯祖相提并論,足可見吳炳劇作的地位之高。民國著名學者、曲學大師吳梅則說《粲花齋五種》“以臨川派之筆協吳江之律”,贊譽它“至其詞彩艷冶,音律諧美,又為元明諸家所未逮,得玉茗之才藻而復守詞隱之矩矱,案頭場上,交相稱美,詞至粲花,則嘆觀止矣”。清初著名詞學家宜興人萬樹(吳炳的嫡親外甥),出生于宜興望族萬氏,他工詞善曲,著有《詞律》一書,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戲曲作家。萬樹精于音律,制曲嚴謹,情節曲折離奇,刻畫人物性格微妙。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在《中國近世戲曲史》中稱:“萬樹之才,足與孔尚任翱翔;其曲律可比洪,能兼二者之長者也。”文人加入昆曲的創作,一方面豐富的昆曲演出的劇目,同時也促進了昆曲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不少曲目至今仍在昆劇舞臺上演出如吳炳的《療妒羹》和《西園記》等。
耕讀并重,崇文重教的文化傳統是宜興望族的根本所在,其主體主要是官僚士大夫,他們擁有多方面的素養和才能,地位尊貴,經濟實力強。明朝中葉以來家班盛行,而望族階層就成了蓄樂家班的主力軍。家樂一方面為了滿足個人和家庭的娛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人文交際需要。
吳炳不但潛心于劇作,而且家中還蓄有昆曲家班,并親自教授。據其外甥,清代著名詞學家、劇作家萬樹回憶,吳炳在五橋莊、石亭埠所教昆曲優伶,耳提口授者前后達三百多人,由此可見吳炳昆曲家班的規模不小,也說明吳炳在昆曲上的造詣之深。明末宜興人徐懋曙曾歷吉安、黃州、寧波三任知府,為官清正,不懼豪強,杜絕請謁。明朝滅亡時堅決不仕新朝,入清后隱身于百姓之中,以蓄養昆曲家班歌姬為樂。徐懋曙在其隱居之后,以三任知府之財力和詩人士夫之修養,蓄養家庭戲班,演員眾多,技藝超群,成為清初享有較高聲譽的昆劇家庭戲班。
望族蓄樂家班主要目的為了追求娛樂,滿足精神上的追求,不為名利,而是來豐富自家生活,釋放壓力,陶冶情操,這樣有助于家庭和睦,促進家族整體與社會的聯系。通過培養高水平的家樂,從而贏得同道的肯定和贊賞,并實現其藝術價值。
昆曲誕生之日起,歷代都與文人士大夫階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文人們不但投身到戲曲創作中樂此不疲,而且還習唱昆曲以消遣自娛或借以自命風雅,客觀上也為昆曲的傳承發展起到一定作用。從晚清到民國期間,宜興人中的代表人物有徐致靖、任道镕和童斐。
徐致靖是清末維新派的人物之一,徐致靖善唱《長生殿》之《彈詞》,口齒沉著,出字收音講究,純用丹田氣,唱來音節蒼涼感嘆。閑時經常帶外孫許姬傳到嘉興等地參加曲會,演唱曲目有《伏虎》《山門》《罵曹》等。梅蘭芳秘書——許姬傳幼從外祖父徐致靖讀書、習昆曲,初唱老生外,又唱官生,得授《彈詞》《酒樓》《別母亂箭》等幾十出戲,尤以《彈詞》得徐之精髓,兼擅吹曲笛。這些經歷為他日后成為一名杰出的梨園文人打下了基礎。
任道镕是晚清能臣,而且與徐致靖有親戚關系,他歷任知府、按察使、巡撫,《清史稿》有傳。任道镕雅好昆曲,徐致靖的女兒徐仁鎰曾向兒子許姬傳回憶過:“當我十二三歲剛記事時,每年外祖要到保定去住幾天,那時,任筱老正做保定知府。據任大小姐說,府里的幕友、聽差看到徐二大人來啦,老爺就無心辦公啦,整天在上房唱曲、研究音韻、吞吐、氣口。”還說“任筱老的孫女任大小姐因為夫妻不和,常住我家,她教我《游園驚夢》《思凡》《喬醋》《刺虎》,嘴里講究極啦,真是家學淵源。”
童斐,字伯章,是曲學專家。1907 年受聘為常州府中學堂歷史和國文教員,1913年常州府中學堂改名為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任命童斐為校長。童斐在課余游藝會中教授昆曲。生、旦、凈、末、丑諸角色,都能分授演唱。劉半農、劉天華、瞿秋白、張太雷、錢穆、呂叔湘、儲師竹等都跟他學唱昆曲。
在昆曲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職業的昆曲班社和民間的業余昆曲社歷來是推動昆曲藝術的傳承和發展的兩支重要力量。他們一個在舞臺上進行藝術實踐,另一個則在臺下進行曲唱和表演藝術的研究。所謂“曲社”,是明清以來業余的昆曲演唱組織,初期稱為曲局或曲集。它是由昆曲愛好者自發組織的團體,以研究、習唱、傳承昆曲為主要宗旨。曲社成員稱作“曲友”,造詣深厚者則稱為“曲家”。曲友不是昆曲專業演員,唱演昆曲純為興趣愛好,不為演出牟利,因此更加專注于藝術的精進和提高。
清朝光緒年間,宜興曲友就組成了昆曲的研習社為“遏云社”,其中曲學造詣較深者,是史又浦、朱紹東、姚士源等人。曲社社員湯翰銘、錢庚臣等人是遏云社的領袖人物。1911 年8 月“遏云社”改組為“協和社”。協和社的曲友大部分是城內的文人雅士或有地位、有實業愛好昆曲的人士,社員有周組園、賈士毅、楊蔭瀏、周策魯等。曲友們每晚都會在瀛園的蘇亭中學習樂器演奏和昆曲演唱。盛夏酷暑之時則泛舟城外的團氿之上,舉杯邀月,引吭高歌;到寒冬臘月則舉辦“消寒會”曲友們輪流做東,圍爐聚餐淺斟低吟,其樂融融。會應時應節舉辦“蘭會”、“荷會”、“菊會”等多種活動。宜興城內每逢有重大活動,也常會邀請協和社曲友前去演奏或唱曲。
宜興是歷代蘇州昆曲班北路演出的重鎮,清光緒年間,宜興城內昆曲演出最為興盛,有昆腔鳴鳳班,該班行頭講究,演員都是蘇州昆山人,在城隍廟和果利廟演出。1930年,“協和社”曾出資邀請南方昆曲正宗昆班“仙霓社”兩次到宜興演出。一次在1932 年下半年,地點為東廟巷黃家祠堂隔壁茶館內。另一次是1935 年9 月30 日在周王廟旁南新戲院中,戲碼有《琵琶記》《孽海記》《連環記》和《玉搔頭》諸本。著名“傳字輩”藝人鄭傳鑒曾在回憶錄《昆劇傳習所紀事》中提到“仙霓社”在宜興演出的遭遇。新中國成立后江蘇省蘇昆劇團也曾多次到宜興演出,著名昆曲演員張繼青在其回憶文章和講座時,屢次提到在張渚、楊巷的演出。當時江蘇省蘇昆劇團,在宜興蘇、昆劇皆演,一般前六日演蘇劇,后一天日夜演兩場昆劇,演昆劇時上座率往往比演蘇劇還多,可見昆劇在宜興的受歡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