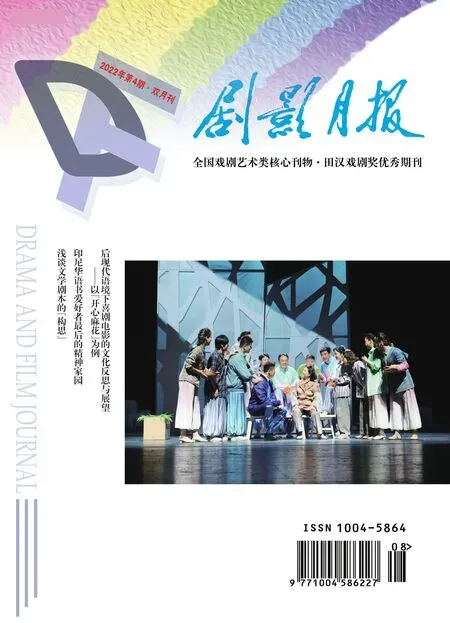向世界展現昆曲風采
■陳睿
我們要用一個國際視野去看待人類古典藝術的發展。地球村的形成,拉近了世界人民的距離,中國最古老藝術之一的昆曲必然要融入世界文化藝術之中。昆曲起源于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被稱為百戲之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珍品,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它影響了中國的多個劇種的發展,而且也影響了世界藝術的發展。
我認為昆劇藝術要走向世界傳播交流,必須要有傳承與新意,不能把幾千年留下來的東西永遠靜止不動,停止在那里,沒有創意,就沒有意義。當代優秀傳統藝術,必須要有新的模式,在不經意之間慢慢浸潤到觀眾的內心及靈魂。昆曲是可以創新的,比如,昆曲藝術可以加入鋼琴、大提琴等新的元素。2018 年我創作了《桃花扇之戀》,這也是大膽嘗試,抓住李香君、侯方域的愛情故事,以秦淮河畔風景作為紐帶,把昆曲《桃花扇》里的部分唱腔片段作為背景音樂,婉轉纏綿,余音繞梁,但是唱腔念白保持傳統不變,這就是昆曲創新。新意部分主要是在昆曲音樂方面,突破傳統音樂的實際藝術概念,把音樂藝術與夢幻世界完美融合在一起。有一場戲是李香君、侯方域在幽靜的秦淮河畔,情投意合的兩人走到了一起,即將結為夫妻又要分離,難分難舍。前奏我采用大提琴浪漫而悲傷的現代音樂,運用了昆曲《桃花扇·眠香》中【梁州序】這段著重運用琵琶主旋律彈奏的帶有傷感之情的音樂,每根琴弦都傾訴著愛情的悲傷,這種創意襯托出當時環境的凄涼感,使整個現場的觀眾進入到沉思之中。這也說明了傳承是要有創新的傳承,這樣的傳承才有價值,要是沒有創新,我看很少能有發展。
2018年受美國墨菲斯堡文化機構的邀請,我前往美國參加“中國藝術節”,演出《牡丹亭·驚夢》《掃松》。參加“國際藝術研討會”的美國公眾廣播、墨菲斯堡媒體、納什維爾公共電視臺,報道了中國演藝集團青年昆曲表演藝術家陳睿在田納西演出的盛況。在“國際藝術研討會”中,我作為江蘇省文藝界唯一代表,演講了中華文化傳統藝術傳播到世界的意義,昆曲是古典的、博大精深的高雅藝術,它的演唱是玉潤珠圓,千金念白四兩唱,至于怎樣才能影響世界文化藝術,這就需要我們有勇氣與智慧,創作又新又美的昆曲藝術體系,詮釋了昆曲藝術性——開到荼蘼花事了,荼蘼是春天的最后一種花,開完以后,花就結束了,這個在昆曲里面代表的是失落遺憾和心里的那點惆悵。把昆曲藝術之美引入世界文化藝術美學,應該有一個積極的交流。
南京創新周組委會在2019 年邀請我前往美國舊金山參加“魅力南京”文化與旅游推介會。我帶著創新版《桃花扇之戀》到舊金山市立總圖書館、斯坦福校園、舊金山市商業場館及風景地帶演出,我在不同的場地穿著中國最傳統的戲曲服裝,穿梭在舊金山室內劇場及室外實景場地,用古典俊俏的裝扮、優美身段的表演、空靈之美的聲腔,贏得了觀眾的贊美。這是專門改編的國際版《桃花扇》,以現代輕音樂彰顯秦淮河畔的風景,里面加入了現代元素的臺詞和昆曲的念白,目的就是為了能讓美國觀眾簡單快速地理解《桃花扇之戀》的故事情節。演出結束后,美國著名作曲家安·蘭姆伯格,來到后臺看望我們,連續用多個形容詞來形容她的興奮。她開心地說:“在昆曲里既有詩歌般的詩詞,又有動人的旋律。同時演員的裝扮動作令人著迷。他們如此美妙地把詩歌、歷史、人民的生活方式,用舞臺表演、詩歌、音樂精致地綜合在了一起。”
在表演演講中,國外觀眾感受到了中國昆曲是偉大的藝術。他們了解到無論是我們的傳統繼承者,還是我們向傳統學習的新一代的演員和藝術家,都能夠靜下心來細細地體味中國文化,演員、藝術家的根基就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把經典的東西原味保留,賦予它新的生命力。
昆曲也需要有一種世界潮流感,任何藝術的品種就是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的要求去發展,才能保留下來,就是大膽地、勇敢地去試驗。當然,流行音樂玩的是外音、節奏型,還有律動。昆曲又是一板一眼的,有固有的很多套路,若要再融合進流行音樂里,一定要從靈感上接近,而不是從形式接近。中國的昆曲融入現代流行音樂、西方音樂,也使得一部分國外觀眾愛上了中國的昆曲。
我用自己的方式在英國倫敦大學及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演講了《牡丹亭·驚夢》,會堂里座無虛席,來了許多國外學者、教授,有的人不懂中文,我用英語著重演講了中國最偉大的戲曲作品《牡丹亭》,它不但是一部戲曲巨著,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學作品。四百年前湯顯祖創作了《牡丹亭》,劇中描述了杜麗娘對夢中書生柳夢梅傾心相愛,杜麗娘因過度悲傷而亡,化為魂魄找尋夢中的柳夢梅,之后她又起死回生,二人結為伉儷。我說,《牡丹亭》幾乎成為中國昆曲作品的代名詞,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演出浪潮,也被越來越多的外國觀眾所熟知,介紹了昆曲還可以以折子戲形式分段表演,例如《游園》《驚夢》《尋夢》《寫真》《離魂》等,這種串折表演濃縮了原著最精華的部分。我表演了《驚夢》《拾畫》兩折,用細膩的動作指法、虛擬的形體表演、用身段展現出場景。在唱腔上,樂曲就像情感拋物線時高時低,只有這些跳動的音符才能洞悉人物心理,才能融入到表演體系。初聽不知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昆曲藝術最大的作用是撫慰人心,滋養人的靈魂。我講解、表演的《牡丹亭》深深地觸動了這些外國觀眾,有一位大學生問我昆曲美在哪里?我告訴他們昆曲之大美,就是昆曲的表演,濃情蜜意到了極致時,杜麗娘與柳夢梅連手也沒有觸碰一下,非常含蓄,但在這個含蓄里面是風情萬種,這個含蓄的表達是飽滿的。情到深處是寂寞,每一朵花、每一座小亭子、每一場落雨、每一個夜晚、每一次風吹,都是無處不在的思念……國外觀眾理解了那份內心細膩的感情,體會了這份細膩的情感在空間中的交流方式,理解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情感表現。但是中國戲曲絕對不會是六百年前的原汁原味,因為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微小的推陳出新,我們不會輕易地去顛覆它,而是對傳統藝術懷著一顆敬畏之心,一顆感恩之心。我帶著生硬英語的講述了這段劇情,臺下又一次雷鳴般的掌聲,觀眾及學者說“我懂了!我理解了!”西班牙學者Benita 女士評說:“光用很好已經不夠形容,你的昆曲演唱有一種絕世的空靈和純凈。”
有時我在想,自己創新的作品沒有方向。但是,當我的作品發表后,受到了國際名牌大學及包括一些文化機構的關注,這是我最大的欣慰。五年間我受邀前往歐美共二十四國的大學、文化機構,包括英國倫敦大學、丹麥哈勒普古典精致的音樂廳,演出演講昆曲《牡丹亭·驚夢》《掃松》《搜山·打車》《訪鼠·測字》以及創新版《一簾·驚夢》。我用自己理解的昆曲表達方式,去跟各國大學生交流,告訴他們什么是昆曲的美與雅,昆曲優雅、迷人,因景而美,因思而美,因幽而美!告訴他們昆曲表演身段模式的含義是什么。當我打動了國外觀眾的時候,我信心倍增!我發現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讓昆曲傳播到世界上,讓國外的觀眾知道昆曲的精髓在哪里。這是需要我們走向國際去講解、表演中國藝術,而且要講得生動,不僅僅是讓外國觀眾看看中國的戲曲而已,更主要的是讓他們聽懂中國的昆曲藝術,聽懂了他們就能去理解,這樣他們才會喜歡上中國的昆曲。
昆曲經常在國際上發聲,帶著中國的音符,穿梭在各個國家,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當中,我們要向這個世界表達最有力量的、最有美感的、最有精神價值的聲音。給人的感覺不僅是碰撞,好像是東方和西方的一種對話,它們融合后折射出的光芒,能讓每一個東方和西方人都能感受到。中國最傳統、最頂級的昆曲藝術形式有這樣一個結果,就是最棒的藝術,這就是藝術的力量,中國藝術是世界的,世界藝術也是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