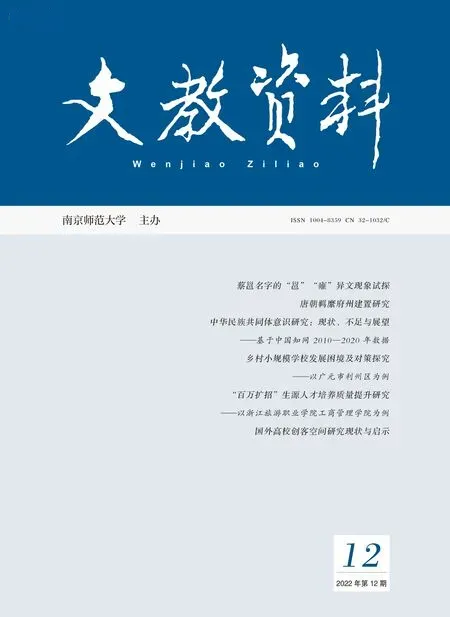論詹安泰先生的令詞格法及其詞學批評
——《無盦說詞》研究之一
王奎光
(韓山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
詹安泰(1902—1967 年),字祝南,號無盦,廣東饒平人,中國20 世紀最為杰出的詞人與詞學家之一,被學界稱為“嶺南詞派的殿軍”。《無盦說詞》撰寫于1939 與1940 年之間,旨在指導西遷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學的文學院學生學習與研究詞作。《無盦說詞·后記》云:“右居澄江時為同學講授詩詞,談鋒偶及,隨筆札出者,故意甚淺近,辭不加點。以其尚非抄襲,或于初學有裨,爰為過錄于此。”可見,《無盦說詞》雖為指導初學詞者所用,但卻頗多個人獨到之見。《無盦說詞》是詹先生民國時期詞學理論與唐宋詞研究的淵藪,具有獨立的學術價值。《無盦說詞》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即是總結與建構令詞格法。這些令詞格法雖然內容并不十分豐富,但卻頗具理論價值與詞學批評意味。本文即專門對此進行研究與評價。
一、作令詞最重情意,不可立意取巧
令詞創作的首要問題,是確立令詞的內容與形式何者為先。《無盦說詞》開頭兩則即論此問題:
令詞最重情意。情深意厚,即平淡語亦能沉至動人。否則鏤金錯采無當也。
寫令詞不可立意取巧。一經取巧,即陷尖纖,必無深長之情味。尤西堂、李笠翁輩即犯取巧之病,驟看煞有意致,按之情味索然。好逞小慧,終身無悟入處也。
“令詞最重情意”,“不可立意取巧”。“情深意厚,即平淡語亦能沉至動人”,而“一經取巧,即陷尖纖,必無深長之情味”。可見,詹先生認為作令詞自當內容第一,技巧第二,二者地位絕不可倒置。而令詞如無堅實之情意而只是玩弄技巧,則必然情淺意薄。詹先生又指出,清代尤侗、李漁等人即犯“好逞小慧”“犯取巧之病”,結果他們的詞作是“驟看煞有意致”,按之卻“情味索然”,由此可見他們于令詞“終身無悟入處”。詹先生所論語重心長,切中令詞創作肯綮,對于學詞與治詞均有積極指導意義。
詹先生的這一令詞格法是符合令詞創作實際的。其見解一方面固然是其創作與研究所得,另一方面當受到王國維“能寫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說的影響。從詹先生這一令詞格法看,詹先生并不拘泥于傳統,對于王國維的新派詞學觀,也是有所接受的。
二、令詞語言當首重精煉,而精煉須出之以自然
關于令詞語言表達,詹先生明確指出當首重精煉,再求自然,而不可立意鋪敘。《無盦說詞》論此道:
令詞非鋪敘之具。寫令詞不可立意鋪敘,須立意精煉;精煉而覺晦昧時,則當力求其自然。精煉而能出之以自然,則近乎技矣。古來令詞之精煉無過飛卿者,試讀飛卿詞,有不自然之句不?溫詞最麗密,人驚其麗密,遂目為晦昧,失之遠矣!
詹先生認為,令詞本制迥異于慢詞,故在語言表達上當“立意精煉”而非“立意鋪敘”。而當精煉過度而易失于晦澀時,則當以“自然”匡救之:“精煉而覺晦昧時,則當力求其自然。”“精煉而能出之以自然,則近乎技矣。”可見,自然之精辟不僅是革除令詞語言晦昧弊端的利器,還是令詞語言表達所能達到的最為高妙的境界。詹先生所論不僅在令詞作法理論上極具創造性,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由此可以看出詹先生令詞研究之深入與見解之精辟。
從“精煉而能出之以自然”之令詞作法批評論,詹先生推舉溫庭筠詞為最高典范。“古來令詞之精煉無過飛卿者,試讀飛卿詞,有不自然之句不?”可見,溫詞語言不但精煉而且自然。至于有“人驚其麗密,遂目為晦昧”,則是“失之遠矣”!由此可見,溫詞的麗密正是其語言自然精煉的總本表現,而他人視麗密為晦昧,顯然是沒有看到這一點。詹先生對溫詞這一令詞技法的判定與高度評價,顯然與傳統中的主流認識迥然不同,本現出其對溫詞的獨到本悟與獨到發現。當然,詹先生的這一看法也可能有所偏激,因為溫氏令詞的語言特色,以精煉雕飾為主自然流暢為輔,詹先生提出見解卻又不做任何證明,自然導致讀者理解與接受起來有些困難。不過,詹先生所論雖然可能也有待商榷,但其獨抒己見、大膽創新的精神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三、令詞寫景言情,分之為二,合之則一,景情實不可分
令詞抒情最重含蓄蘊藉,故其手段尤重借景抒情或以情寫景,但民國時期很多學詞治詞者對此認識卻不甚了了。詹先生對此頗有感觸,在《無盦說詞》中專門撰寫一則進行強調:
寫景言情,分之為二,合之則一。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善寫景者亦然,景中無情,感人必淺,其能搖蕩心魂者,即景亦情也。溫飛卿之“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孫孟文之“片帆煙際閃孤光”,馮正中之“細雨濕流光”,何嘗不是景語,而情味濃至,使人低徊不盡。作令詞固當會此,讀令詞亦當會此。唐五代人小詞之不可及多在此等處,不獨寫情之拙重而已。
詹先生認為,“寫景言情,分之為二,合之則一”,二者不可或缺且不可分離。令詞如能搖蕩心魂、感人至深,必賴景情契合無間、有機交融。而溫庭筠、孫光憲、馮延巳等“唐五代人小詞之不可及多在此等處”,“不獨寫情之拙重而已”。可見,詹先生正是從情景有機交融的角度,來高度評價唐五代詞人的,而從其表達看則又表明他對當時只重拙重言情的習氣有所不滿。
以情景交融論詩詞,前人早有論述。論詩則以清初王夫之《姜齋詩話》最為精辟:“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論詞則以清代許昂霄《詞綜偶評》評無名氏《踏莎行》語最為中肯:“融情景于一家,故是詞中三昧。”可見,無論詩詞,言情與寫景實不可分,高明者皆是以情寫景、景中寓情。其實這就是詩詞“意境”說的方法論,而令詞因本制原因尤需創造蘊藉之意境。詹先生也正是因為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就特別強調言情必須要與寫景有機結合,其實質即是要恢復令詞追求含蓄雋永富有意境的創作傳統,同時匡正當時詞壇過重拙重言情而忽視以景寫情之流弊,其針砭現實的意味非常明顯。由此也可見出詹先生不隨波逐流,敢于獨立思考、堅持己見的可貴學術品格。
四、“重、拙、大”詞法中,“拙”當為首要
清末民初,“重、拙、大”之論盛行詞壇。此論濫觴于王鵬運,而發揚于況周頤。況周頤論道:“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詹先生自然也受到較大影響,但他又不盲從所謂權威,在接受中又能有所反思。譬如詹先生就從常州詞派以“重、拙、大”評詞中發現出問題。《無盦說詞》論道:
以重、拙、大言,南唐二主及馮正中詞實過《花間》。常州詞人主重、拙、大而高抬飛卿,殆不可解。飛卿詞措語下筆,重則有之,大猶可強為傅合,將安得拙耶?而此三義中似尤以拙為首著,蓋惟拙為能得重且大,能重且大者未必能拙。
詹先生認為,若以“重、拙、大”評詞,則南唐詞在事實上要高過“花間”詞,但常州派詞評家卻因此而高抬“花間”鼻祖溫庭筠詞,實屬自相矛盾,“殆不可解”。在詹先生看來,溫詞有重,勉強有“大”,但卻絕沒有“拙”,并不符合常州詞派“重、拙、大”兼備的評詞標準。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常州詞派一直以溫庭筠為唐人最高典范的“權威”論斷。詹先生認為,常州派詞人之所以在溫詞批評中出現較大失誤,是沒有弄清“重”“拙”“大”三者之間存在極為重要的先后關系。“此三義中似尤以拙為首著,蓋惟拙為能得重且大,能重且大者未必能拙”。可見,“重”“拙”“大”三者中,“拙”當為首要,其對“重”與“大”具有關鍵性的優先地位與影響作用。換言之,“拙”可以直接決定拙“重”與“大”的存與亡。
我們知道,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大力推崇王鵬運所倡導的“重、拙、大”說,況氏也在后來對此說中“重”“拙”“大”各自作出簡要說明,但無論是王鵬運還是況周頤,均未曾對三者之間的關系作出明確規定或說明。詹先生的新見,不僅揭示出常州詞派詞論中的結構性疏漏,還在理論上補救了這一缺失,從而使“重拙大”詞論得以完善。從一定意義上講,詹先生的見解發展了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尤為難得與可貴。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詹先生這里對常州詞派詞評的批評,在表達上略顯粗疏并不嚴謹。因為,高評溫庭筠的是張惠言、周濟、陳廷焯等經典常州派詞論家,而他們評詞的標準則是比興寄托而非“重拙大”;而以“重拙大”論詞的卻是“晚清四大家”中的王鵬運與況周頤,但他們卻并未像經典常州派詞論家那樣高舉溫庭筠。不過,因為“晚清四大家”同樣重視比興寄托,因此也有人視其為正統的常派詞風,所以詹先生將他們籠統稱為常州派詞人也并不為過,但要說他們因“重拙大”而高抬溫庭筠,則顯然是一種表達上的錯位,并不嚴密準確。
五、作令詞不可局限于“重、拙、大”詞法,還應追求“輕清微妙之境界”
前文已論到晚清明國時期,詞壇多受“重拙大”詞論觀影響,往往沉湎于此言情技法,而常常忽略對其他積極方面的關注與追求,比如詞之可貴而難得之意境。《無盦說詞》論此云:
重、拙、大為作詞三要,固也;然輕清微妙之境界亦不易到,因此等境界,不容不用意,又不容大著力也。馮正中“風乍起”詞,深得此中三昧。宋詞家惟韓子耕、范石湖時有此境;淮海《浣溪沙》“漠漠輕寒”一首,亦能寫此境界,然頗著奇語,便覺矜持。
如有巧妙之意境,則貴出之以拙重之筆,庶不陷于尖纖。巧妙而不尖纖,為孟文所特擅,但或出之以奇橫,不盡拙重耳。
奇橫非險巧之謂也,令詞最忌纖巧而不妨奇橫,如張子野之“昨日亂山昏,來時衣上云”,奇橫極矣,然是何等氣象。其得謂之險巧耶!
詹先生認為,作為作詞三要的“重拙大”固然重要,但詞之“輕清微妙之境界”則同樣重要,甚至要更為重要。因為要創設此等詞境,“不容不用意,又不容大著力”。在詞史上,唐五代也只有馮延巳詞“深得此中三昧”,而宋代的韓疁、范成大尚能差強人意,至秦觀則有所遺憾了。可見,此“輕清微妙之境界”誠“不易到”。詹先生所論,意在說明作詞不能局限于“重拙大”詞法,還應或者說更應追求更高一層的“輕清微妙之境界”。這就使詞人從只單純追求作詞技法,而轉向于對詞之意境的創造。這一認識對于開拓詞作者的眼界、提升其作詞的境界,均有較大啟迪與引導作用。
然則,何以創設詞之“輕清微妙之境界”也即“巧妙之意境”呢?詹先生認為可有兩種方法:一是“貴出之以拙重之筆”;一是“或出之以奇橫,不盡拙重”。換言之,一是“拙重”之筆,一是“奇橫”之筆。細玩詹先生語意,詹先生似乎更傾向于多用“奇橫”之筆。“奇橫非險巧之謂也,令詞最忌纖巧而不妨奇橫”,似乎在避免詞之“險巧”或“尖纖”之弊上,“拙重”之筆要比“拙重”之筆更有優勢。詹先生也正因此而新“發現”了孫光憲。在詹先生看來,孫氏不僅僅是能以“奇橫”詞筆創造“巧妙之意境”的最佳典范,而且其詞法還深刻影響到北宋詞家張先的創作。總本而論,詹先生對“拙重大”詞法雖然有所認可,但又對過度講求“拙重大”有所不滿。這很有可能與當時的詞壇流弊有關,也當與詹先生自己對“拙重大”詞論的別有認識有關。
六、結語
綜上所述,詹先生對令詞格法的總結與辨析,并非機械地沿襲前賢,而是能根據自己的創作本會與研究所得,根據令詞創作的獨特性,提出諸多獨到而可貴的見解。這些見解對于令詞的理論建設、令詞的創作與鑒賞、令詞的詞史研究等,均有較大的啟迪作用與借鑒價值。此外,我們還可從中看出詹先生對于新舊詞學均能有所肯定又有所批評的詞學思想。當然,由于受到詞話本的影響,詹安泰先生的令詞理論及其批評也存有一些粗疏與籠統之處,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