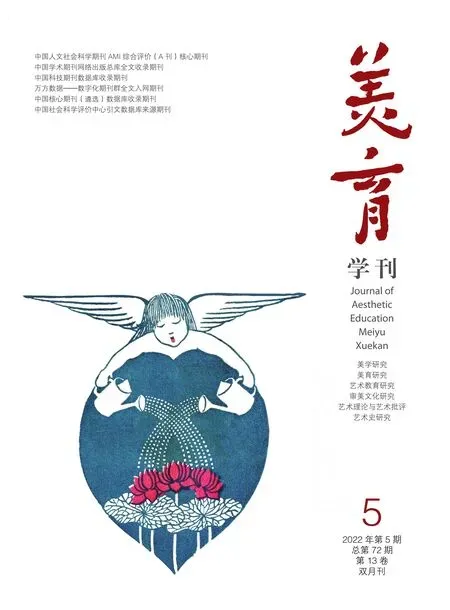資本與習性:現代漫畫藝術的心理區隔與審美選擇
——論中國連環畫與國外漫畫的歷史分野
徐秀明
(杭州師范大學 藝術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同屬對人類行為模式的敏銳洞察,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明顯優于葛蘭西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后者近乎社會結構的決定論,布爾迪厄則強調行動者主動參與、富于創造性的積極作用,認為行動者雖受制于場域,但亦可建構乃至改造場域。具體到藝術場,行動者(藝術家)爭取藝術自律、自主的努力,會對整個場域產生積極影響——場域并非不可戰勝,行動者(藝術家)只要善用自身資本、懂得斗爭策略,就可能爭取到藝術發展的自由空間。布爾迪厄關于“資本”“習性”等的重要論述,是分析研究藝術家如何在社會權力的桎梏下獲得自律性藝術場的關鍵所在。
在傳統藝術停滯、新興藝術萌芽之際,最需要行動者(藝術家)通過智慧、努力改變現存藝術場的僵化狀況。藝術史上最難能可貴的,并非傳統藝術路徑上單純技藝高超的“大師”,而是極少數既能突破前人窠臼,又為新興藝術插上堅實的經濟翅膀,使后來者能沿著自己開拓的新路繼往開來而不致憂心衣食的“宗師”。
動漫藝術尤其如此。漫畫歷史最早幾可追溯至原始洞穴巖畫,千百年來世界動漫史上藝術“大師”層出不窮,但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極少數將動漫提升到藝術層面,使其終獲社會認可的“宗師”——他們是能夠超越時代認知的領袖人物。連環畫/漫畫出現雖早,成熟卻晚,在世界各國都有被長期視為簡單粗糙的幼兒讀物的歷史遭遇。如何應對、扭轉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是橫亙于各國畫家面前的生死難題。美日等國的現代漫畫之所以如此繁盛,要么因為擁有此類高瞻遠矚,兼具智慧、資本與執行力,能夠解決社會障礙的動漫“宗師”,要么因為本國“大師”善于借鑒,能夠精準發現并成功復制別國“宗師”的經驗模式。
一、文化資本之用
“宗師”何以用一己之力扭轉乾坤?說來并不復雜,充分利用自身資本以借社會權力之勢即可。布爾迪厄藝術社會學體系中的“資本”,不是單純的經濟概念,而是至少包括“經濟資本”(貨幣財產)、“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榮譽等)與“文化資本”(教育資歷等)三種。不同形式的資本在一定情況下可以互相轉化,因此,資本與權力的聯系極為緊密。行動者擁有的資本的數量、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社會空間的位置與社會權力的大小:“資本……意味著對于某一(在某種給定契機中)場域的權力,以及,說得更確切一點,對于過去勞動積累的產物的權力(尤其是生產工具的總和),因而,也是對于旨在確保商品特殊范疇的生產手段的權力,最后,還是對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潤的權力。”藝術家常因直接占有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較少遭人輕視,其實他們擁有大量的文化資本,社會影響亦不可小覷。“藝術家和作家,或更籠統地說,知識分子其實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一部分。他們擁有權力,并且由于占有文化資本而被賦予某種特權,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資本,大到足以對文化資本施加權力。”因此,藝術家雖在直接的權力場處于從屬地位,但只要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資本,并非沒有改變尷尬處境的可能。
當然,充分運用的前提是足夠理解。“文化資本”理論包含各種資源,“比如詞語表達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識、審美喜好、學校系統的信息、教育文憑等”。為申明文化也是一種權力資源,布爾迪厄將“文化資本”細分為“具體化”“客觀化”“體制化”三種形態詳加闡述,這也是中國連環畫需要加強認知、充分利用以爭取自身發展空間的三個方面。
(一)具體化形態
指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資本。易言之,是文化通過藝術家的身體所凝聚、傳承的特殊性情傾向。行動者要成為藝術家,必須有足夠的個人性投入,除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還要有社會性建構的里比多(性欲)形式的投資,這……意味著你在開展該項工作時,可能需要忍受某種匱乏,需要克制自己,需要某種犧牲”。在艱苦漫長的藝術學習、訓練的過程中,沉淀下來的不僅是藝術知識技能,還有獨特的修養、談吐、氣質與審美趣味等個人魅力。這些個人性的修養氣質、審美趣味是藝術家超脫于世俗功利算計的文化標志,它們與實利無涉,但用于社交場合、公共媒體,卻能增加藝術家的感召力與說服力,是提升漫畫藝術、漫畫家社會形象與地位的有力武器。華特·迪士尼開創的迪士尼公司是一個百年不衰的動畫王國,人們提起他時,總將他視為一個偉大的動畫大師而非企業家。其實單論繪畫藝術成就,迪士尼不及其早期伙伴烏布·伊沃克斯。但正如恰克·瓊斯所言,烏布只是個純粹的技術天才,可以把別人的思想很好地表現出來,自身卻缺乏創意,迪士尼則是個充滿夢想而又堅忍不拔的理想主義者,極具說服感召他人的人格魅力。當時烏布有更好的工作選擇,但迪士尼以自己對動畫的深切理解與獻身熱情,成功說服烏布拒絕高薪,跟他一起為實現動畫夢想而努力,米老鼠等青史留名的天才創造才得以誕生。在他們的動畫事業起步之初,觀眾只覺新鮮好奇,根本沒人認為這種東西能有多大發展前途,是迪士尼不斷克服資金缺乏與各種社會成見,拼命尋找各方投資支持,屢次傾家蕩產般的資金投入,才使得動畫片從街頭雜耍變成搞笑短片,再由真人電影放映前幾分鐘的娛樂短片提升為與其分庭抗禮的長片藝術。單就亞洲動畫藝術而言,中國《大鬧天宮》的導演萬籟鳴、日本“漫畫之神”手冢治蟲等,都是看了迪士尼作品后,才立志從事動漫藝術的。無疑,沒有迪士尼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沒有他面對各種欺詐背叛時的忍辱負重,美國動畫不會一直走在世界動畫藝術前列。“明知不能而為之是一種樂趣”,“卡通動畫作為敘述故事和視覺娛樂的一種方式,可以為世界各地各年齡的人們帶來歡樂和信息”,“我不是主要為孩子們制作電影,而是為了我們所有人中的童真(不管他是6歲還是60歲)制作電影。這就叫童真。最糟糕的不是我們沒有童真,而是它們可能被深深地掩埋了。在我的工作中,我努力去實現和表現這種天真,讓它顯示出生活的趣味和歡樂,顯示笑聲的健康,盡管人性有時荒謬可笑,但仍要竭力追求”。這些滾燙感人的藝術思想與不畏艱難的意志交融,熔鑄成極具魅力的藝術人格,不僅感染了當時志同道合的藝術同仁,感動了一代代觀眾讀者,而且感召了世界各國年輕藝術家繼往開來,加入動漫這一嶄新而充滿夢幻色彩的藝術領域,動漫藝術才有了今天的繁榮景象。這便是具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的巨大影響力。
同樣,手冢治蟲的成功,亦與深諳“具體化”資本的運用直接相關。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同時連載好幾部熱門漫畫,還經營著一家每周都要制作一集電視動畫的“蟲制作”公司,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但仍然時刻不忘展現個人魅力以宣傳漫畫藝術。他幾乎從不推辭電視臺上節目的邀請,時刻不忘戴一頂標志性的貝雷帽,使其西裝小帽、滿面微笑的形象深入人心,極具親和力。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幾乎從不放棄到國外參加文化交流的機會,不遺余力地以個人魅力推動日本漫畫的國外傳播。1980年,作為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漫畫大使”赴美,在聯合國和美國各地大學舉行“關于現代日本漫畫文化”的演講,告訴各國聽眾:漫畫在日本如此深入人心,以致閱讀漫畫成為整個日本的普遍愛好。1986年,他受日本外務省委托擔任“第三屆日本博覽會”演講者再次赴美演講,強調“漫畫是世界共同的語言。充當全世界所有文化之間的橋梁的,那就是漫畫”;1988年病危之際還接受中國邀請,到上海參加卡通紀念活動。
相形之下,中國畫家略顯保守,不善于利用自身的社會影響力。這或許是傳統士大夫清高恬淡的超脫表現。但從當代文化產業的角度看,藝術行業需要一定的曝光率,連環畫/漫畫藝術家也是公眾人物,與讀者適當溝通是市場推廣的重要環節。只要內心清醒、不為商業炒作所惑,這與淡泊名利的傳統價值觀并不矛盾。手冢治蟲何嘗不是視繪畫為生命的藝術家,但他深知,漫畫家在公眾面前展現光彩照人的一面,有利于提高漫畫藝術的社會聲譽,吸引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投身其間。手冢治蟲過世時,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在日本,漫畫家已從以前毫不起眼的職業成為年輕人最向往的夢想職業之一!日本動漫界就連幕后配音的“聲優”都已走到臺前,成為萬人追捧的大眾偶像。中國畫家為何不可?時下中國青年漫畫家們已開始嘗試多種途徑來擴大影響力。比如漫畫家夏達常在網上“曬照片”以保持熱度,使其聲望影響擴大到了動漫讀者之外。這是合理利用個人“文化資本”的明智之舉。中國的連環畫/漫畫研究應著力加強名家名作的介紹推廣,即使不能就此推動藝術發展,至少也能普及藝術教育。
(二)客觀化形態
客觀化形態就是以文化商品的形態存在,即“在物質和媒體中被客觀化的文化資本,諸如文學、繪畫、紀念碑、工具等”。客觀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在物質性方面是可以傳遞的,但這個傳遞很可能流于一般合法的所有權轉讓或繼承。繼承或占有一套精美的連環畫,只是客觀擁有了這套連環畫的經濟意義或貨幣價值,并不意味著掌握其象征意義的解碼與欣賞能力。文化資本的客觀化形態,要求人們具備的是文化能力。
中國連環畫作者的文化能力,在自己的小圈子內絕無問題,擴大到整個漫畫藝術范疇后就明顯有所不足——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氛圍凝重激昂,多數畫家都習慣了戰爭年代文化政治的拘謹嚴肅,沿襲了居高臨下的啟蒙說教姿態。對他們來說,國外現代漫畫商業與藝術并重的藝術風格、娛樂與讀者為先的創作理念有失穩重。因此,盡管日本漫畫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進入中國市場,讀者反響熱烈,后來更是逐步取代了傳統連環畫的市場份額,但中國連環畫界依舊嗤之以鼻。1993年有研究者到連環畫出版社做社會調查,談起盛行的日式漫畫時,社長完全否定,認為后者沒有連環畫畫得好。有畫家宣稱:“日本的動漫程式化的手法太多!千篇一律的大眼睛小鼻子,只能吸引青少年觀看。中國的連環畫是深刻地反映現實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畫家的表現手法千變萬化!豐富多彩……我沒介入這個隊伍是感覺程式化!概念化的東西索然無味。”研究者問他為何不參與其中以改變中國動漫的不足,老畫家卻閉口不答。當時多數連環畫作家對強勢取代連環畫的現代漫畫,都是此種不屑置辯的傲慢態度。其實,日本漫畫固然良莠不齊,但其中新穎別致、表現力極強的圖像敘事語言早已躍然紙上。何況日本漫畫最初進入中國的作品,如車田正美《圣斗士星矢》、鳥山明《阿拉蕾》、井上雄彥《灌籃高手》等,都是20世紀日本漫畫的經典名作,不僅發行量巨大,在電視上也公開放映多次。明明看到大量日漫精品,卻無從領略其先進的藝術語言,一味情緒化地斥為低級,這不僅是泥古不化,更是文化能力不足的表現。
日本漫畫能夠后來居上、席卷全球,自有過人之處。手冢開創的“卡哇伊”(可愛)畫風,至少在把握大眾審美心理方面極其成功,全盤否定絕非理性公允的態度。當然,日本漫畫秉承“娛樂至死”的創作宗旨,與中國連環畫的“鐵肩擔道義”相去甚遠。中國畫家向以清高自許,或許不屑介入商業創作,但也不應如此剛愎傲慢。何況現代漫畫不止一種,除日本漫畫外,至少還有藝術性頗高的法國連環畫,弘揚保護弱者、維護社會正義的美國超級英雄漫畫……這些不乏積極意義的國外現代漫畫,難道也不值得借鑒嗎?尤其在法國,連環畫被尊崇為“第九藝術”。此類藝術資訊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屢屢見諸報端,當時中國為發展經濟而大開國門,絕不缺乏對外交流機會。但中國連環畫界并未因此開始向外學習尋求轉變。曾赴國外考察的賀友直坦率而無奈地說:國外連環畫的政治諷刺藝術,我們學不了……這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化管理部門對連環畫實行的形式、題材等統一規范,畫家們將其內化形成的自覺意識——“主動地接受場域的支配性價值、資本,相信游戲的爭奪對象、勝負結果,并內化為身體向度的性情傾向、感知方式和思維習慣。……當行動者認同和接受場域邏輯后,象征權力就自然而然地剝奪行動者對場域真相的反思能力。”輿論宣傳的要求和內化了的自覺意識使老一輩藝術家對題材、形式等方面的探索過于謹小慎微,即使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發展經濟的主流導向和市場的活躍實際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創作自由和寬松的可能性,但畫家們精神層面的自我束縛仍然使他們在創作上放不開手腳。
其實,國外現代漫畫不只社會諷刺漫畫一種,故事漫畫、成人繪本何嘗不是市場潛力巨大?前些年中國臺灣漫畫家幾米效仿法國畫家桑貝,創作了《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鐵》等藝術氣息濃郁的成人繪本,成功將這一現代漫畫類型引入華語世界繼而大紅大紫。朱德庸《澀女郎》《雙響炮》等四格漫畫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瑣碎情趣與荒誕心理的挖掘表現,蔡志忠《老子說》《莊子說》等將古典名著繪成通俗灑脫的漫畫,這些也都曾風靡一時。這些港臺漫畫家未必強于內地畫家,之所以能在華語世界復制國外現代漫畫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與迪士尼、手冢等“宗師”相似,都具有藝術感悟、商業敏感與文化視野等精神品質。內地畫家藝術造詣精湛的不少,可數十年來高度他律的創作情勢,使他們普遍缺乏從客觀化形態的文化資本獲益的能力。
“文化資本是作為斗爭中的一種武器或某種利害關系而受到關注或被用來投資的……行動者正是在這些斗爭中施展他們的力量,獲取他們的利潤,而行動者的力量的大小、獲取利潤的多少,是與他們所掌握的客觀化的資本,以及具體化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的。”由此言之,是否善于理解運用文化資本,乃是決定行動者成敗的關鍵。反觀國外成功的現代漫畫確實都是如此:日本漫畫起初進入中國時模仿連環畫的樣式以開拓市場;而法國連環畫在受到日本漫畫沖擊后,主動地汲取日本漫畫的表情符號、分鏡頭等獨到的繪畫技法,既取得了藝術精進,又保住了市場份額。相形之下,我們的連環畫創作沒有有意識地從競爭對手那里學習長處,最終被現代漫畫淘汰出局。
(三)體制化形態
布爾迪厄將通過體制化教育而賦魅的文憑、證書等,歸為文化資本的體制化形態。他認為,教育在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種證書賦予其擁有者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有合法保障的價值”。對缺乏專業素養的普通大眾來說,這些權威機構頒發的文憑、證書,相當于官方的一種保障,與其他簡單的文化資本具有根本性差異——相形之下,后者“不斷地去被人要求去證明自身的合法性”。由此可見體制性權力與“社會公認性”的巨大威力。
但此結論系針對藝術教育體制完善的法國藝術場而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的連環畫興起于民間,多數畫家都是草根出身,沒接受過藝術院校專業訓練。20世紀80年代連環畫鼎盛之際,中央美術學院設立了“連環畫系”,但也沒培養出“大師級”名家,對連環畫界的整體格局影響平平。故而,中國連環畫沒有教育“文憑”“證書”之類,其體制化形態的文化資本,主要體現在各級“評獎”榮譽上。
新中國成立后,每隔數年、十數年就舉行一次全國連環畫評獎活動,畫家們就此多了一種體制認可的渠道。體制化榮譽不同于民間“虛名”——它們更容易轉化為經濟資本、社會地位之類的現實利益。因此對有些藝術家來說,與其追求虛無縹緲的藝術名聲,遠不如爭取此類文化資本安穩快捷。坦率地說,新中國連環畫史上有些獲獎作者的作品未必屬于當時最佳。然而這些榮譽有時近于麻醉劑,濫用容易沉湎其中迷失自我。理想狀態或最佳方案似乎應該是:藝術家在起步階段不借助外力,依靠個人奮斗在藝術場積累名望,成名后再進入主流權力場,善加利用自身名望,為藝術爭取自主發展空間。但即便如此,這樣的路徑也會縮短自身藝術壽命。
民國時期連環畫“四大名旦”之首的趙宏本,之所以享有“連環畫祖師爺”的美譽,就是因為無意間遵循了此類藝術道路。作為中國連環畫家最具宗師氣象的人物,趙宏本的人生軌跡、藝術生涯極具研究價值。他15歲時因家貧拜師當連環畫學徒,很快展現出驚人才華,臨摹3個月后就有作品被人買去出版。全憑個人勤奮努力與繪畫天賦,在競爭激烈的連環畫壇闖出偌大名頭,結果奇貨可居,被師傅剝削了8年,好不容易擺脫師傅控制,卻發現連環畫產業全被出版商掌控,只能制造媚俗作品以換取生活保障,似乎注定了庸俗低級、備受鄙視的命運。在精神痛苦、生活貧困的雙重窘境中,受進步友人指點閱讀魯迅論連環畫的文章,1940年發起成立“連環畫人聯誼會”,創辦“連環書店”,徹底擺脫出版商限制,出版呼應革命的進步連環畫。1947年加入地下黨,新中國成立后組建“連環畫作者聯誼會”,后來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負責連環畫編輯、出版的主要領導,組織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連環畫家,編審出版連環畫數千種。在他的努力下,上海數十年來一直是連環畫“大本營”,向全國各地輸送了一大批優秀畫家。以這些貢獻來說,趙宏本“連環畫祖師爺”之稱名副其實。
新中國成立后,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連環畫管理機構,趙宏本就此進入社會權力場。只是當時風氣是藝術要單向服務于政治需要,舊連環畫得到新政權的認可支持,但要從趣味盎然的娛樂故事變成嚴肅刻板的“解放書”。這對連環畫的發展好還是不好?趙宏本長期困惑于藝術規律與文藝政策之間,以致決策者認為,趙宏本思想落伍、瞻前顧后,無力主持連環畫新舊改造的未來發展方向。黎魯當年大刀闊斧,晚年才有所悔悟:“當動漫取代連環畫的市場,我有一省悟:現實社會存有一刀切的通病。解放初把具有動漫型因素的連環畫切掉了,現在又向連環畫切去。故曰一定要尊重傳統,尊重自己的根。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沒有采取老連環畫好傳統的措施,而一味強調改造,所以趙宏本會迷惑、會抵觸,我完全不理解他們,這不是淺薄幼稚嗎?由此也種下了連環畫缺少原始草根性養料的禍根,而今為動漫打敗。”因此,即便趙宏本擁有“中國連環畫的一代宗師”的業界聲望,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都未能“復興”連環畫事業。雖然做學問應有“歷史之同情”,不應苛求他為連環畫后來的潰敗擔責。不過,既然擁有如此雄厚的“體制化”資本,而沒有據理力爭,便難辭其咎——“‘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論語·季氏篇第十六》)趙宏本錯過了力挽狂瀾、成為真正的動漫“宗師”的歷史機遇。而中國連環畫就此轉向背離現代漫畫的歧路,一去不返。
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本國動漫領域的領袖,同樣置身于被主流社會質疑,“祖師爺”趙宏本對中國連環畫藝術的作用,遠不及“漫畫之神”手冢治蟲對日本動漫的影響正面有力。手冢治蟲深諳“體制化”資本的奧秘,他早在1960年便在全日本“畫家·漫畫家”部門納稅榜上高居榜首。別人勸他效仿其他同行合理避稅,他斷然拒絕說:“不,我希望成為第一名。在畫家中,漫畫家的地位是不被人看重的。但是我成了第一名,我想這說明漫畫家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漫畫家的地位提高了。我覺得應該規規矩矩繳納稅金。”手冢治蟲甚至利用不合理的社會成見來擴大影響:他知道,社會大眾或許看不上漫畫家,但不會看不起醫學博士學位。因此,他雖在大學期間就已是著名職業漫畫家,日后絕無掛牌行醫的打算,依然在同時創作幾部連載漫畫的緊張勞作中,堅持醫學學習,直到拿到博士學位為止;他很懂得與各級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即便工作繁忙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依然幾度接受政府委托,以“漫畫大使”等身份赴各國開展文化交流;他善于利用外國政府、媒體擴大自己在國外的影響。作為劃時代的“新漫畫”的開創者,他在國外向來謙和低調,在中國坦陳自己看了萬籟鳴《鐵扇公主》后決心從事動漫創作,在美國強調迪士尼動畫對自己的深刻影響。這些長袖善舞的社會活動,使其擁有了良好的社會地位,獲得了一大串各種獎項美譽。概言之,手冢治蟲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在競爭殘酷、天才輩出的日本漫畫界始終居于領袖地位,并非全是藝術天才的原因,而是綜合實力使然。
二、習性之于心理
“大師”與“宗師”的本質區別,在于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宗師”之所以罕見,是因為身為務虛的藝術家而能逆轉現實時勢。他們通常是相當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一方面足夠天才,既能窺得自身藝術的未來趨勢,又能得到同行的認可追隨;另一方面懂得利用自身文化資本,周旋于主流社會權力場,提升自身藝術的社會地位與發展空間。
中國連環畫出現頗早,也有名家精品不斷涌現的黃金年代,何以20世紀80年代短短數年便大廈傾頹,為何數十年來整個行業未能出現一個能支撐門庭的“宗師”?這里當然有社會氛圍的原因,但絕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外在社會氛圍,因為新中國連環畫藝術的黃金時代,出現于20世紀政治氛圍日趨緊張的五六十年代,它最終沒落的80年代中期,反倒是在改革開放的寬松階段。可見事情沒那么簡單。中國連環畫藝術家自身亦有責任,必須反躬自省,否則難保未來不會重蹈覆轍。
如何公允客觀地思考行動者(藝術家)之于場域的責任問題?布爾迪厄的“習性”屬于開放性的概念,他以其分析行動者的思維模式、性情傾向等,但并未明確下定義。陸揚概括說:“‘習性’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情志雙向作用下來,集聚在個體和群體身上的總體持久性情。它是特定的階級與文化使然,涉及同一階級共享的價值觀念和生活體驗。”簡言之,行動者的習性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社會空間的主導規則內在化和具體化為性情結構;另一方面,習性作為生成性結構,能夠生成未來的生存經驗和實踐。易言之,習性是社會權力通過文化、趣味和符號交換使自身合法化的身體性機制,它內化了個人接受教育的社會化過程,濃縮了個體的外部社會地位、生存狀況、集體歷史、文化傳統,同時習性下意識地形成人的社會實踐。因此,什么樣的習性結構就代表著什么樣的思想方式、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
具體到中國連環畫,民國時期的連環畫作者在新中國成立后陸續進入各級出版社、編輯部,成為體制內拿固定工資、按政策需要創作的國家干部,社會地位、生存狀況天翻地覆。不經意間,左右連環畫藝術場走向的,由“經濟”變為“政治”;衡量行動者力量大小的標準,亦由商業收益變成政治態度。新連環畫創作模式,與舊連環畫以個人商業眼光為主而一人“圖文包辦”不同,通常是撰文、繪圖分工合作。當時文學界盛行“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術”的三結合創作模式,連環畫界大致相仿,文字腳本先由出版社的文字編輯完成,再交予畫家繪圖。理論上講,畫家也可自由選題,但創作前要正式報批,選題通常要與現實政策、路線方針配合,否則不易通過審批。一旦選題被否決,前期的辛苦努力白費。時間一長,畫家們逐漸喪失了自由創作的熱情、能力,習慣了來料加工式的創作模式。新連環畫以改編現成的文學作品為主,不為無因。1958年,顧炳鑫坦承:“以目前情況來說,自編自繪極少,編繪分工較為普遍。”可見當時的創作態勢。此種高度他律的藝術場中,畫家作為行動者最受贊賞的是循規蹈矩的忠誠度,最受壓抑的反倒是現代漫畫創作中最受重視的創新意識。
幾十年的體制內創作實踐,使連環畫界逐漸適應、習慣了嚴謹刻板的社會規則,思維模式、行為認知能力與之高度一致。習性將集體和個體的歷史內化、具體化為性情傾向,將“歷史必然性轉化為性情”。因此,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開放搞活,創作桎梏終于放開后,連環畫藝術家們的反應是茫然無措,“我們一向命題作文慣了,叫我自己編個故事實在想不出”。行動者已高度依賴于周遭環境,將不合理的生存境遇視為理所當然,喪失了基本的反思能力。
畫家們并非沒有委曲求全以保全藝術精髓的嘗試,比如努力尋找傳統題材與宣傳需求的最佳契合點,如王叔暉在傳統仕女題材不合時宜后,借宣傳1953年頒布婚姻法的機會,將反抗專制爭取自由的時代精神巧妙融入才子佳人名著《西廂記》。她以工筆重彩刻畫人物,保留了精致優雅的古典審美情趣,又運用西方繪畫透視法統攝背景,得到了輿論贊賞,被贊“閨香中近百年無此筆墨”;任率英繪反抗封建專制迫害的《白蛇傳》時,“用傳統工筆重彩勾勒渲染出符合真實比例的人物形象,顛覆了傳統人物畫不求形似但求神韻的高雅追求”;程十發善于結合時代熱點與社會背景進行藝術探索,50年代借“肅反”揭發敵特運動而繪《畫皮》,將中國傳統寫意畫的情趣與意境巧妙融入連環畫,60年代在市面只有魯迅小說有藝術趣味的情況下,采用水墨寫意技法繪《阿Q正傳一百零八圖》;等等。相形之下,立意全在政治宣傳的現實題材,雖然專意“為工農兵服務”,但因過多采用民眾陌生的西式現實主義繪畫風格,受歡迎的程度反倒稍遜一籌。丁斌曾、韓和平在程十發、顧炳鑫等人建議下,以傳統單線白描手法、借鑒京劇《三岔口》的武打表現手法繪制《鐵道游擊隊》,才成就了這本中國連環畫出版史上最受歡迎的現實題材連環畫。“文化大革命”過后,有些畫家由現實主義重返優雅精致的古典趣味,如1979年戴敦邦在《逼上梁山》中借鑒了《清明上河圖》中嚴謹寫真的方法、南宋山水畫的布局,繪畫極富歷史韻致;有些畫家從西方現代藝術對色彩的理論探索中汲取靈感,來豐富傳統工筆重彩的色彩表現力,如80年代末,戴宏海《柳毅傳書》、陳全勝《洛神賦》,或絢麗精細,或清新雅致,在色彩敷染方面超越了傳統國畫的范疇。然而這些創新終究只是技法改良,談不上開拓新道路、新格局等整體變革。
固有習性決定思維方式與行事格局,對自身文化資本了解運用有限,在與社會權力場交涉爭取自身藝術發展的社會空間時,也就難有作為。由此言之,習性可視為個體與集體歷史和未來之間的中介,它脫胎于過去,乃是一個“被建構的結構”,又使得過去積淀在人們的感知、思維和行動經驗中,形成一個“建構中的結構”,隨時可能生成未來的生存經驗和實踐。但人們往往覺察不到這一點,也就很難有意識地改變。因為日常實踐過程并不都是清晰而有意識的,藝術家的許多創作實踐并非深思熟慮后的理性選擇,而是源于近乎直覺的靈感涌動。通過習性,“行動者不是規則或規范的機械遵循者,而是‘即席演奏家’,他們對于不同的環境所提供的機會與制約傾向性地做出反應”。
“習性”這一概念,為揭示個體性情和權力運作的關系,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都提供了有效分析途徑。習性與場域之間有一種“雙向模糊的關系”:習性中滲透著場域的結構性特征,場域是習性的生存土壤。但習性絕非僅有歷史的持留、積淀,還有一種能動、形塑的反作用。“它是穩定持久的,但并不是永久不變的。”場域的形成、變革需要社會機制與個體心智之間的契合。因此,推動藝術場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在于對行動者習性的發現與修正促進。連篇累牘地分析連環畫藝術“大師”與現代漫畫“宗師”的區別,意義即在于此。手冢治蟲之所以被尊為“漫畫之神”,不是因為藝術造詣空前絕后,而是因為他在動漫尚不為日本主流社會認可之際就毅然拋棄了收入優裕、地位頗高的醫生職業,全身心地投入漫畫創作,畢生不懈地全力推動,使日本漫畫由不上臺面的少兒讀物變成了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還為其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國際市場,成為現代日本的支柱產業之一。由手冢治蟲的傳記可知,其實手冢并未經過正規美術訓練,純是幼時喜歡迪士尼動畫而自娛娛人,無意中練成了那種圓滾滾、可愛夸張而不合解剖比例的畫風,是以最初嘗試進入日本漫畫界時,屢次因缺乏素描基礎被拒之門外。但手冢治蟲并未氣餒,他絞盡腦汁,以善于故事講述的特長打動讀者,開創了“故事漫畫”的重要漫畫類型,獲得了“赤本漫畫之王”的美名;又將自己個人畫風中的可愛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居然使“大眼睛、小鼻子”的“卡哇伊”風格,成了日本漫畫在世界獨樹一幟的特點;他不辭勞苦拼命創作,每天只睡三個多小時,回家過少以致被孩子們稱為“帶很多禮物來的叔叔”;一人主管“漫畫”“動畫”兩個公司的藝術創作和商業運作,公司破產仍不放棄最初“拍出迪士尼一樣的動畫”的夢想,60歲便身心交瘁而死。如此完全、純粹的獻身精神與辛苦耕耘,終于換來了世所公認的巨大成就。美國動漫學者保羅·格拉維特在《日本漫畫60年》中,認為手冢治蟲同時扮演著華特·迪士尼(使動畫擺脫“雜耍”地位,被廣泛認可為“藝術”的第一位動畫大師)、D.W.格里菲斯(使電影從戲劇中獨立出來,與戲劇等藝術平起平坐的美國電影大師)與威爾·艾斯納(繪本小說的創始人,把漫畫從幼兒讀物提升為全新藝術形式的美國漫畫教父)的角色,稱得上是“日本動漫產業之父”。《朝日新聞》1989年2月9日紀念手冢治蟲過世時評論說:為什么世界上只有日本人那么愛看漫畫?因為“日本有個手塚治蟲,而其他國家卻沒有。如果沒有手塚治蟲博士,很難想象戰后日本漫畫會得以風行”。
為什么手冢治蟲能改變本國不利的動漫藝術場,而在中國沒有出現這樣的人物?除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之外,中國畫家過于封閉保守的習性何嘗不是原因之一?“場的自主性無論有多大,保持和顛覆策略的成功機會總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這個或那個陣營能夠在外部力量中找到的支援力量。”手冢治蟲固然驚才絕艷,但若無華特·迪士尼珠玉在前,他也未必如此堅定不移;如果沒有自幼對寶冢歌劇院、好萊塢電影的熱愛觀摩,有意識地汲取各種影像藝術的敘事技巧與視覺效果,他也未必看得清動漫藝術的發展方向。手冢治蟲從不諱言自己從迪士尼、萬籟鳴等各國動漫藝術家身上學到了很多,從不諱言自己綜合各種藝術形式豐富日漫表現手法的探索方向才有自身成就。這就是對外藝術交流的重要性。日本漫畫家代表團訪華交流時,派出了最著名的手冢治蟲和赤冢不二夫,中方則只有漫畫家接待,“連環畫界可能覺得專業不對口,退避三舍,失去了很好的交流機會”。其實,手冢治蟲等人的長篇“故事漫畫”,在中國更接近連環畫而非寥寥數格的社會諷刺漫畫。連環畫界反應如此冷淡,估計與其輕蔑嫉妒的復雜情緒有關:一方面,國內傳統連環畫慣于精雕細琢,看不上日本漫畫簡潔夸張的藝術風格,市場占有率卻相去懸殊,未免心理失衡;另一方面,連環畫一圖一文、以文為主的“圖文結合”方式由來已久,而日本漫畫一頁多格、多圖少文,形式相差太大,“非我族類”的排斥感頗強。據考察,上世紀90年代,連環畫出版人普遍不屑與現代動漫為伍,多數畫家不愿介入其中,嚴重阻礙了中國連環畫向現代動漫的轉型升級。連環畫要想繼續生存,就必須努力走出去,尋找自救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時下關于中國漫畫家努力學習國外漫畫的批評意見未必正確——手冢治蟲當年也是從模仿起步的。模仿成功典范,其實是尋求外部支持的一種策略。當然,日漫僅是其中選擇之一,法國的藝術繪本、美國的寫實漫畫,無論在藝術層次還是大眾群體上都絲毫不遜于日本漫畫。它們也曾受到日漫猛烈沖擊,但慢慢吸收消化日漫技法后,如今發展得更好。中國傳統的工筆重彩其實相當有市場,只是存在藝術斷層。如果有人能達到當年劉繼卣、王叔暉、任率英等人的水平,成功絕無問題。時下夏達《子不語》、林瑩《梅蘭芳》等都有兼學日本漫畫與中國畫傳統技法的傾向,但火候還不夠。尤其林瑩的日漫人物造型痕跡略重:《梅蘭芳》中過于追求人物相貌視覺沖擊力,除幾個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程式化嚴重。而日本漫畫固然有程式化問題,但并非不講求個性化:日本漫畫中的主角往往是理想化的俊男美女,看不出國籍種族特征,但那些“路人甲”的裝束、面容其實是非常寫實的,日本人的特征明顯。他們追求的境界乃是理想化主角、寫實化配角搭配的參差對照之美。不過只要中國連環畫/漫畫藝術家們志存高遠,此類模仿之作乃是必須付出的學費或墊腳石。只要藝術家們不斷在反省中提高自己,逐漸改變既往趨于保守的習性、改進周邊的藝術場,傳統形式的連環畫或許會消亡,但總有一天會以新的藝術形式涅槃重生。
中國傳統連環畫枝繁葉茂,百年滄桑難以一一盡數。很多表面看似純粹藝術方面的問題,都是多方面復雜因素所致。中國連環畫的興衰榮辱,說到底都是20世紀中國藝術家置身連環畫藝術場與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小場域之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中國連環畫藝術的深入研究,不僅有助于讀懂藝術、了解歷史,還可深入反省當下的藝術創作與發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