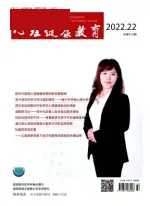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測評思路與方法
周群力 張繼明 卞冉


摘要:近年來,隨著全社會對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很多組織在選拔過程中越來越重視對心理風險狀況的考察。由于組織選拔中所關注的心理因素與一般心理測驗中關注的心理因素并不等同,故而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測量,需要有更具針對性的設計。本文提出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測量需從過往經(jīng)歷、認知偏好、行為表現(xiàn)、動機基礎四個方面尋找合適的測評形式,并且建議在實踐中選用其中2種以上的測評形式,以互為補充和校驗,降低選拔失誤的概率。
關鍵詞:組織選拔;心理風險因素;心理測驗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2684(2022)99-0009-03
近年來,很多組織和企業(yè)在選拔過程中越來越重視對候選人以心理風險狀況的考察。比如,《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2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中提到:“根據(jù)職位需要,部分招錄機關將對報考者有關心理素質進行測評,測評結果作為擇優(yōu)確定擬錄用人員的重要參考。”
在應用心理測驗對候選人進行考察時,有的組織會選用常見的經(jīng)典測驗,例如:MMPI,SCL-90,卡特爾16PF測驗等[1],也有組織會采用一些商業(yè)測評機構開發(fā)的測驗。這些測驗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組織在選拔中規(guī)避了候選人的心理風險,但如果使用不當,也可能會造成惡劣的影響。本文將就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測評展開論述。
一、什么是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
廣義上,候選人不符合工作崗位要求的心理因素都會成為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如能力不足、性格不匹配等。但在組織選拔領域,它常常是指影響候選人心理健康狀況的心理因素。
但是,很多時候心理學中所定義的心理健康,與組織選拔中所關注的心理因素并不等同。心理健康往往強調心理的各個方面及活動過程處于一種良好或正常的狀態(tài),因此心理健康量表往往是對當前或近一段時間的個體心理狀態(tài)的測量。例如SCL-90測驗,其測量內(nèi)容主要是關于當前心理狀態(tài)的[2],這與組織選拔的目標不符。
組織選拔更關注候選人在未來工作中的心理風險。有些工作崗位的工作強度高、壓力大、不確定性強,會為崗位上的員工帶來較大的心理壓力。如果候選人在心理層面上存在某些風險因素,即使其在選拔過程中心理健康狀態(tài)是良好的,未來工作中的壓力或者突發(fā)事件仍可能會“引爆”這些風險因素,使候選人心理健康狀態(tài)改變,對工作安全和個人身心健康造成影響。
因此,測量組織選拔中的心理風險因素,不能借助現(xiàn)有的臨床心理健康量表,需要有更具針對性的設計。
二、組織選拔中應當關注哪些心理風險因素?
組織若想在選拔階段對候選人的風險因素進行預測,就需要關注一些相對穩(wěn)定的個人特征。在這里,我們建議組織在選拔中關注“人格”這一概念。人格就是個體在行為上的內(nèi)部傾向,它可以表現(xiàn)為個體適應環(huán)境時在能力、情緒、需要、動機、興趣、態(tài)度、價值觀、氣質、性格和體質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動力一致性和連續(xù)性的自我,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給人以特色的心身組織 [3]。
心理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與人格相關,主要原因有:(1)人格具有獨特性,個體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多與個體的人格差異相關;(2)人格具有跨情境的穩(wěn)定性,我們可以通過人格分析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現(xiàn),同時也能預測個體在壓力狀態(tài)下的情緒和行為表現(xiàn);(3)人格具有統(tǒng)合性,它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一個健康個體的人格結構需在各方面彼此和諧統(tǒng)一;(4)人格包含個人在適應環(huán)境的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系統(tǒng)的獨特反應方式,可以預測個體應對壓力的方式;(5)人格還可以預測個體認知事物與環(huán)境的過程與方式。綜上所述,人格因素是預測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
人格所包含的內(nèi)容比較多,在進行心理風險因素測評時,要關注人格中有可能引起未來工作中風險行為或表現(xiàn)的因素。
風險性的人格因素在很多研究或理論中均有提及,如黑暗三人格理論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精神病態(tài)和自戀等。目前被廣為接受的分類模式是美國精神病學會制定的《精神疾病的診斷和統(tǒng)計手冊》,簡稱DSM,它強調癥狀模式及病理的描述,將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或人格障礙的表現(xiàn)行為進行了提煉和梳理[4]。
個體在出現(xiàn)心理健康問題時所表現(xiàn)出常見的心理狀態(tài)有焦慮、抑郁、恐懼、憤怒等,這些表現(xiàn)有一部分源自客觀環(huán)境因素,還有一部分來自個體的人格因素,通過進一步梳理國內(nèi)外關于人格相關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一些人格因素對個體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如表1所示)。
三、可以從哪些角度關注心理風險因素
從個體人格發(fā)展過程來看,個體的成長環(huán)境、家庭狀況、特殊事件等都會對個體的人格形成產(chǎn)生影響。這些成長經(jīng)歷的信息往往可以預測風險性人格因素的水平。
從個體當前的人格特征來分析,主要包含了行為、認知、動力三個方面:從行為表現(xiàn)來看,人格特征會在特定情境中表現(xiàn)出穩(wěn)定的行為傾向,這能夠解釋個體在壓力下為何會表現(xiàn)出特定的應對方式[5];從認知偏好的角度,不同的個體會將環(huán)境和刺激進行差異化認知加工,這體現(xiàn)了個體產(chǎn)生心理健康問題的認知層面的原因[6];從動力基礎角度來看,個體表現(xiàn)出的一些情緒和行為的特征與心理健康狀態(tài)高度相關(如適度焦慮能夠提高個體的效率,但過度焦慮則屬于心理健康問題),風險性人格的動力基礎會導致個體在某些方面產(chǎn)生過度的行為表現(xiàn)和情緒體驗[7]。
因此從成長經(jīng)歷、行為表現(xiàn)、認知偏好和動力基礎這4個方面,可以對個體的風險性人格進行反映,從而預測心理健康水平(如圖1所示)。
四、組織選拔中心理風險因素的測評方法
盡管很多工具可以從人格層面上對心理風險因素進行測評,例如艾森克人格問卷(EPQ)、明尼蘇達人格問卷(MMPI)、癥狀自評量表(SCL-90)、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人格障礙篩查測試(PDQ)等,但這些測驗大多都是基于候選人對自我日常行為和狀態(tài)的報告,在組織選拔環(huán)境中,往往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這些測驗有效的前提是候選人對自我有著清晰的認知。如果候選人本身對自己的行為和狀態(tài)認知不清晰或有偏差,那么測量結果會出現(xiàn)誤差,導致測評結果不準確。
其次,這些測驗在高利害環(huán)境下容易受社會贊許性影響[8]。候選人天然愿意展示自己比較好的一面,會有意無意地隱藏自己不好的一面。因此在組織選拔這種關乎個人未來發(fā)展的場合,候選人若刻意按照社會期望的方式進行反應,會影響測評的準確性,最終帶來兩種結果——有風險的候選人被錯誤選入或無風險的候選人被錯誤淘汰。
最后,這些測驗反映的往往是一種日常狀態(tài)下的心理風險。正如前面所論述的,組織選拔中關注的是高壓力和突發(fā)事件下候選人的風險,僅了解候選人在日常狀態(tài)下的心理風險情況,顯然無法滿足組織選拔的需要。
綜上,組織選拔實踐中使用的心理風險因素測評工具,需要有不依賴自我認知、抗“作假”和反映壓力下的情況幾個特點。根據(jù)我們對心理風險因素的測評思路,有幾種測評方法可供選擇。
針對個人過往經(jīng)歷進行考察,常見的方法有背景調查、面試和傳記式問卷。背景調查和面試可以設法了解候選人的過往經(jīng)歷和特殊事件,通過這些信息推斷其心理風險的情況,但對考察人和面試官的專業(yè)性要求非常高。傳記式問卷是一種標準化的測驗形式,但目前市面上尚未見到用于測評心理風險因素的此類工具[9]。
情境判斷測驗和情境模擬是用來考察候選人的壓力反應的合適測評形式。二者都可以通過收集工作中的壓力情境,編制成文字、圖片或視頻等形式,考察候選人在這些壓力情境下的反應,從而得到其心理風險的情況。不同的是情境判斷測驗會有選項,這使得這種測評方式標準化程度更高,適合大規(guī)模測試使用[10]。而情境模擬的構建相對更靈活,一些特殊行業(yè)(消防、飛行員等)還可以采用虛擬現(xiàn)實(VR)技術來構建情境,但這種形式需要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和評價者進行觀察和評價。
除了以上兩類形式外,投射測驗具有比較低的表面效度,候選人不易識別測評的目的,受社會贊許性影響較小。場景的投射測驗有主題統(tǒng)覺測驗(TAT)和羅夏墨跡測驗,這兩種測驗都有著標準化的施測流程和結果解釋,能夠反映人格的動力特征,但是在實際使用中需要有經(jīng)驗的專業(yè)人員進行操作,施測成本比較高。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標準化的認知投射測驗——條件推理測驗,該測驗通過一種看似邏輯推理的題目,從測量作答者的獨特認知模式(辯解機制)入手,獲得反映作答者人格特征的結果[11]。目前國內(nèi)已有團隊開發(fā)出適用于組織選拔用途的條件推理測驗。
綜上所述,從過往經(jīng)歷、認知偏好、行為表現(xiàn)、動機基礎四個方面都可以找到合適的測評形式。在實踐中,我們推薦組織選用其中2種以上的測評形式,因為采取多種方法可以相互補充和校驗,降低選拔失誤的概率。同時,在實踐中還應對工作內(nèi)容的壓力進行評價,并非所有的崗位在選拔時都要對所有的心理風險因素進行測評,如果崗位的工作壓力本身不大,又具備很好的支持系統(tǒng),建議可以在錄用決策時適當降低標準。
參考文獻
[1]霍團英. 中青年處級干部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調查分析[J].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4,12(4):303-306.
[2]胡燕. SCL-90用于大學新生心理健康普查的局限性研究[J]. 長春大學學報,2012,22(4):444-447.
[3]Duane P S,Sydney E S. 人格心理學(第八版)[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美國精神醫(yī)學學會.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M]. 張道龍,等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5]張繼明,卞冉,車宏生. 如何挑選"耐壓"的員工——壓力應對素質結構分析[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2006(10):47-49.
[6]Aaron T B,Arthur F,Denise D D. 人格障礙的認知治療[M]. 翟書濤,譯. 北京: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04.
[7]James L R,Mazerolle M D. Personality in work organizations[M]. Toronto:Sage Publications,2001.
[8]吳燕. 人格測驗中社會贊許性反應的測定與控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08.
[9]李英武,車宏生. Biodata——一種有效的人事選拔方法[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2006(3):74-76.
[10]劉曉梅,卞冉,車宏生,等. 情境判斷測驗的效度研究述評[J]. 心理科學進展,2011,19(5):740-748.
[11]朱鳳艷,陳海平,車宏生. 人員選拔方法:條件推理測驗的研究新進展[J]. 中國考試,2013(1):23-31.
編輯/黃偲聰 終校/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