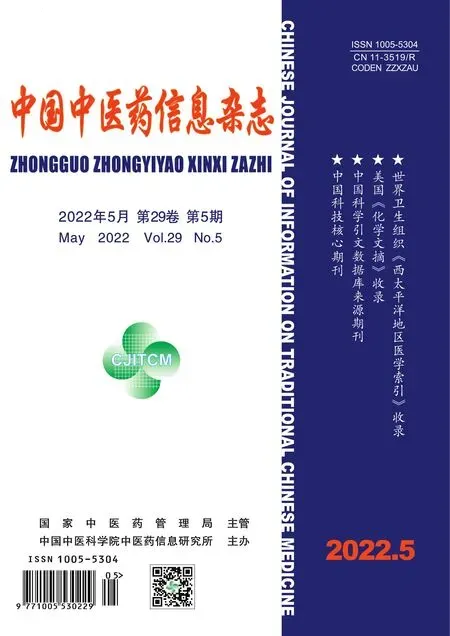基于臟腑風濕理論探討達原飲論治痹病
王愛華,呂柳,王海隆
1.甘肅省中醫院,甘肅 蘭州 730050;
2.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北京 100700
臟腑風濕指外感風寒濕邪,通過五體或官竅而內傳臟腑,留而不去,伏于臟腑,過時發病;或每于復感外邪而引動伏邪,以致疾病反復或加重。“臟腑風濕”系仝小林院士精研《黃帝內經》,在“痹病”和“伏邪”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新學說。基于“臟腑風濕”理論,筆者應用達原飲辨治痹病,臨床療效滿意,茲介紹如下。
1 關于臟腑風濕
在中醫學中,痹病是較為寬泛的概念,《素問?痹論篇》所倡“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的思想影響歷代醫家。但隨著飲食結構改變及環境變化等,“古今異軌”導致痹病之病因病機逐漸復雜化,故仝院士順應當代病因病機的發展變化,提出新的學說體系——臟腑風濕理論:臟腑功能異常是重要的病理基礎,外邪侵襲是必要的發病外因,邪氣伏留是致病的關鍵病機。
1.1 與“伏邪”密切相關
仝院士認為,臟腑風濕理論與伏邪聯系最為緊密。“伏”為潛伏、隱藏之意,“邪”為各種致病因素。《黃帝內經》雖未明確涉及“伏邪”二字,但有一些相關“伏邪”內涵的闡述,如“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冬傷于寒,春必溫病”(《素問?生氣通天論篇》)、“肌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脾”(《素問?痹論篇》)、“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此外,《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亦可見為“伏濕”“伏寒”而創的方劑,如麻黃附子細辛湯、防己地黃湯、麻杏薏甘湯、麻黃加術湯等。直至晚清,“伏邪”的概念才由劉吉人提出,“感六淫而不即病,過后方發者,總謂之曰伏邪”(《伏邪新書·伏邪病名解》)。
1.2 臟腑風濕之伏邪與痹病
痹病如大僂(強直性脊柱炎)、尪痹(類風濕關節炎)、燥痹(干燥綜合征)、肌痹(多發性肌炎/皮肌炎)、皮痹(系統性硬化癥)等,大多與伏邪的致病特點相似,通常反復發作,易過時而發,且多因外感、勞累、情志異常等因素誘發。仝院士認為,這些誘發因素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中醫之伏邪,故而痹病之病因病機可用臟腑風濕伏邪學說作較為圓滿的解釋。
所謂伏邪,廣義指感邪之后一切伏而不即發的病邪,既包括外感六淫,也涵蓋飲食失節、情志失宜、痰濁、瘀血、伏毒等內在的、伏而不發的致病因素;狹義則專指伏氣溫病,即外邪侵襲,正氣虧虛,不能祛邪于外,或邪伏于膜原,或邪伏于肌腰,或伏于肌核,或伏于脂膜,邪氣伏匿,伏而不即發,逾時而發。仝院士認為,由于伏邪或盤踞某處,或流動循行,未超過人體自身調節范圍,故具有感而不發、過時而發、復感易發等特點。
2 臨證辨治
2.1 臟腑風濕之邪多伏于膜原
臟腑風濕與伏邪聯系緊密,但邪伏于何處更是一個重要問題,《靈樞?五變》有“循毫毛而入腠理”,《靈樞?賊風》亦認為“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可見,這里所說的邪氣或入于腠理,或藏于血肉之間,與傳統意義的表里之邪有顯著差別。
臟腑風濕之邪,既非在表、亦非入里,但邪伏體內,必有其所——膜原,即《素問?舉痛論篇》“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寒氣,亦是病邪之氣,可伏于膜原之下。所謂膜原,王冰注曰:“膜,謂膈間之膜;原,謂育鬲肓之原。”(《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俞根初亦認為“膜原居于半表半里,外通肌腠,內近于中焦胃腑”(《通俗傷寒論》)。可見,膜原外不在經絡,內不在臟腑,取象比類,邪伏于膜原,既有外感性質,又有內傷因素,膜原乃表里之分界,是邪氣羈留的關鍵部位。故仝院士認為,人體正氣不足,臟腑功能低下,風寒濕等外邪皆可由外入內,不能御邪于外,邪氣則多可伏于膜原,若再經外邪引動,或循行于經絡之中,或留駐于筋骨之間,或沉積于關節,由外進至臟腑,客于臟腑經絡之間,久則影響氣血運行,故而外邪侵襲、臟腑失衡、邪氣伏留(伏邪),多種因素導致風濕痹病膠著難愈。可見,達原飲專攻膜原,引外邪從膜原而出,適用于治療痹病。
2.2 臟腑風濕與疫癘之邪
疫癘之邪多具有傳染性,而臟腑風濕之邪乃“伏匿諸病,六淫、諸郁、飲食、瘀血、結痰、積氣、蓄水、諸蟲皆有之”(《王氏醫存》)。臟腑風濕與疫癘二者病雖不同,然治則相同,所謂異病同治。故《溫疫論》宣發膜原法雖為治療疫癘伏邪所創,亦適用于臟腑風濕。祛邪外出乃治療臟腑風濕的重要原則。正邪交爭,初起正氣充足,邪不能勝正,大多正盛邪退,但風濕之邪伏于膜原,隱匿而不發,或再遇外邪侵襲,或內生邪氣引動,正不勝邪,則病情復雜,反復發作,難以痊愈,故邪氣伏留是關鍵病機,治療亦是以祛邪外出為重要治則。
2.3 達原飲的應用
達原飲出自《溫疫論》,由檳榔、厚樸、草果、白芍、黃芩、知母、甘草組成,主治溫疫初起邪伏膜原之證,方中“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疏利之藥;厚樸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吳又可認為“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此外,《溫疫論》提出:“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患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復。”早期外邪侵襲,病邪不甚,氣血未亂,津液未耗,臟腑未傷,治療相對容易,而伏邪已成,邪不去則病不瘳,傳統攻邪三法不能直達病所,延綿日久,愈沉愈伏,非達原飲不能除。達原飲立方之旨以早期祛邪為首要原則,即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治療,這與痹病的治療原則一致,臟腑風濕理論亦與其相合。
3 典型病例
患者,女,29歲,2019年4月16日初診。17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面部紅斑,雙手多個小關節腫痛,雙膝疼痛,伴雙下肢水腫,外院診斷為“系統性紅斑狼瘡”,予口服醋酸潑尼松、羥氯喹、沙利度胺片等。3周前無明顯誘因面部、雙上肢皮疹加重,間斷發熱。刻下:面部及雙上肢皮疹、輕度瘙癢、色素沉著,間斷發熱,體溫最高達39.7 ℃,脫發,口腔潰瘍,左肘、雙肩疼痛,乏力明顯,汗多,納可,寐差多夢,二便調,舌紅,苔白厚膩,脈沉細。中醫診斷:痹病,屬邪伏膜原證。治法:開達膜原、清熱祛濕。予達原飲加減:檳榔20 g,草果20 g,厚樸15 g,蒼術15 g,生地黃30 g,草豆蔻10 g,薏苡仁10 g,甘草10 g,青蒿45 g,黃芩15 g,竹葉10 g,滑石粉(包)15 g,茯苓15 g,枳殼20 g,清半夏20 g。14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溫服。西醫治療同前。
2019年4月30日二診:無新發皮疹,口干,喜飲熱水,小便可,大便溏結不調、每日2~3次,近一周內最高體溫達38 ℃,舌苔較前好轉,脈同前。守方去草豆蔻、薏苡仁,改清半夏為15 g,加陳皮10 g。繼服14劑。西醫治療同前。
2019年5月14日三診:近半月體溫維持在36.5~37.7 ℃,午后偶有低熱,面部皮疹未見明顯變化,守方去枳殼,加生石膏(先煎30 min)30 g,繼服14劑。西醫治療同前。
2019年5月28日四診:近1周無發熱,未見新發皮疹,面部皮疹減少,守方去滑石粉,繼服14劑。醋酸潑尼松減量,余同前。
其后定期規律就診,中藥仍以達原飲加減,半年后醋酸潑尼松逐漸減量維持,患者面部及雙上肢皮疹消退,無發熱及關節腫痛。
按:本案患者為青年女性,患系統性紅斑狼瘡10余年,平素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劑等,日久濕熱蘊結,經絡不通,正氣雖不充,邪氣亦不著,正邪相爭而交織于內,伏于膜原,故考慮為痹病(屬邪伏膜原證),予達原飲加減。方中檳榔能消能磨,善祛伏邪,為疏利之藥;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厚樸、蒼術除濕化熱,破膜原伏氣所結。此四味協力直達巢穴,使伏邪潰敗,速離膜原。青蒿、黃芩、竹葉、滑石粉、生地黃為佐,解毒清熱,除濕養陰,內清濕熱而不傷陰,透邪外出而不傷正,使伏邪外有出路;清半夏長于燥濕化痰,枳殼、草豆蔻助厚樸、蒼術化濕行氣,祛痰濕而逐伏邪;又因久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故加薏苡仁、茯苓顧護脾胃,脾胃運則正氣充,濕濁祛,伏邪除;甘草調和諸藥。全方共奏開達膜原、清熱祛濕之功。二診時,無新發皮疹,發熱好轉,舌苔白膩好轉,效不更方,遂守方去豆蔻、薏苡仁,清半夏減量,減輕燥濕化濁之力;大便溏結不調,加陳皮健脾理氣和胃。三診時,患者已無新發皮疹,午后偶有低熱,遂去枳殼減少理氣化濕之力,加生石膏清熱瀉火,使邪由外而出。四診時已無發熱,無新發皮疹,仍以開達膜原、清熱祛濕為法。其后病情平穩,定期規律就診,激素逐漸減量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