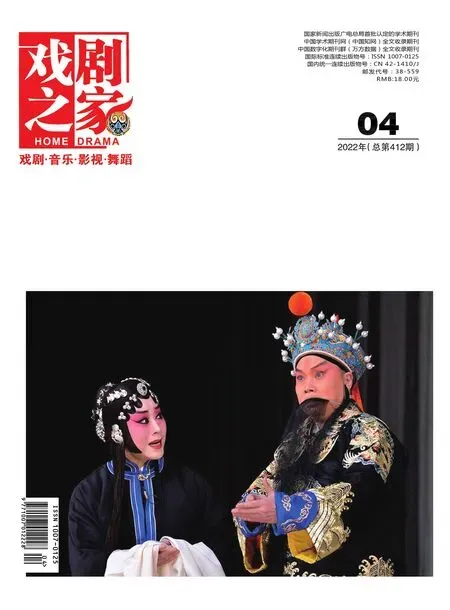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馬拉/薩德》
——不只是戲劇
趙 瑩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武漢 430074)
眾所周知,戲劇因其特征具有難以存留的特點,我們喜歡按照錄像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以便留存和研究。但很有意思的是,觀眾在觀看時,很少把這種錄像等同于電影藝術。他們會說:“我今天看了一部戲。”即便這些錄像故事有演員,有故事,有鏡頭的剪切,但我們在觀看時,仍然是沒有電影意識的。電影,作為一個復制的手段,當然可以復制著名的舞劇,歌劇和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是,即使假定這類復制力符合銀幕的特殊要求,它們至多也就是將其“儲存”起來而已,我們在這里對之是不感興趣的。而創作于1967年的《馬拉/薩德》卻是一個另類,他不僅僅是研究戲劇《馬拉/薩德》必觀摩的錄像資料,更具有電影藝術價值。
一、空間的敘事性
(一)空的空間
《馬拉/薩德》這部影片中,空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嚴格尊重布魯克的同名戲劇舞臺劇場景,完整呈現出當年演出實況。而《馬拉/薩德》這部戲劇,和一般戲劇不太一樣的是,他的影片(戲劇)的背景始終如一,故事只發生在療養院的現代浴室,整個戲劇演出過程中,沒有任何背景的改變,不會一會兒換一個幕布,也不會一會兒加一個背景,布魯克試圖用意象化的演出來營造空間的詩意。
劇場燈光的使用也極具特色,光線的存在感被降到最低,舞臺燈光的分布極為均勻且從頭至尾沒有絲毫變化,布魯克認為戲劇形式必須盡量簡單,通俗易懂又意味深刻。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布魯克導演的戲劇都像一幅中國畫一樣,舞臺上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是“空的空間”。
(二)演員的空間
演員的表演也極具意象性,道具數量被減少到最低,《皮鞭下的薩德》這一場中,本應是薩德被科黛手中的皮鞭抽打,而布魯克的處理方式非常寫意,薩德脫去上衣跪在鏡頭前,喃喃自語,而飾演科黛的女演員在其身后,低下頭彎下腰用頭發模擬鞭子,隨著薩德的臺詞,一下一下地抽打著薩德的背部,其他角色則圍在四周觀看。
電影中多增加的一層敘事:《馬拉/薩德》這部戲,采用的是劇中劇的結構敘事模式,三層時間關系,第一層即20 世紀60 年代,戲劇《馬拉/薩德》上演;第二層即本戲——1808 年,薩德侯爵指導戲劇,庫爾米和妻女現場觀看戲劇;第三層即戲中戲,1793 年,科黛刺殺馬拉事件。而在這三層時間關系中,1808 年的時間線和1793 年是不斷切換交織在一起的,加之以合唱隊時不時地進入,由此構成間離效果。布魯克除去真實呈現戲劇場景和表演外,在影片中還加入了一層觀眾,攝影機給了我們一個大全景,正在上演的戲劇《馬拉/薩德》正在由一群黑壓壓的觀眾觀看。也就是說在這部影片中,布魯克設置了四層時間關系,在前文說到的60年代前,加入了一層現在時:電影觀眾觀看60 年代的戲劇觀眾觀看上演的戲劇。但也就是這多加的一層,使得戲劇空間成功地轉化成了電影空間。
如何轉換的呢?觀眾在觀看由攝影機錄制的戲劇影像時,腦海里是有著深刻的舞臺空間的意識的,也就是說在影像中呈現給我們的空間位置,已經被預設為“舞臺上的戲劇空間”,同時,一般的記錄戲劇的影像也會有意識地如此呈現:舞臺全景,演員表演的中景,近景,特寫相互切換。所以我們看到的表演是戲劇表演,感受到的空間是舞臺空間,鏡頭的切換變更只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看到演員在演出中的狀態。
二、視角的敘事性
布魯克在他的戲劇理論書《空的空間》中,第一句話便說道:我可以選取任何一個空間,稱它為空蕩的舞臺。一個人在別人注視下走過這個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了。也就是說“別人的注視”(視角)“走”(表演)和“空間”(舞臺)構成了戲劇的最基本要素。其中“別人的注視”只是敘事接受者的基本視角,而一個文本的視角是包含了敘事視角和接受視角的綜合視角。
(一)敘事的視角
布魯克本人對觀眾的注視非常重視,《敞開的門》中他曾經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工作時,他常常會用一塊地毯作為排練區域,地毯外屬于日常生活,想做什么都可以,而當演員進入到這個地毯的時候,一定要有明確的動機,一定要積極主動。也就是說,當演員在某一特定空間中被注視的時候,他便不是他自己了,而是戲劇的一部分,凝視在布魯克的創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三重視角的構成:在戲劇《馬拉/薩德》中,薩德作為導演指導療養院病人拍戲,觀察演員演出,以便不時指導,這是第一層注視視角。其次,庫爾米和他的妻女觀看精神病療養院劇團演出的讓·保爾·馬拉的迫害與謀殺事件,這是第二層注視視角。最后的一層注視視角則是戲劇上演時,觀眾對戲劇的觀看。這三重視角使得戲劇變成了嵌套式的結構,1793 年,1808 年,以及60 年代戲劇上演三重時間三種觀看同時交織呈現在一起,構成了“此時此刻”。布魯克本人也曾說過:“戲劇指的不是劇場,也不是文本,演員,風格或形式。而是一個叫做‘此時此刻’的迷里面。”
(二)接受的視角
第四重視角的構成:在影片《馬拉/薩德》中,多添加的一層敘事,不僅僅使得戲劇空間轉化為了電影場景,更是在影片敘事中增添了一絲意味。再加上電影觀眾在銀幕前的凝視,這就構成了四重觀看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導演在影片中還增加了一層凝視,即演員看向攝影機(電影觀眾),影片中大量的這類型的特寫鏡頭,舞臺上的演員念念叨叨地說著自己的臺詞,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鏡頭。導演在這里向我們呈現了一個名叫“此時此刻”的幻覺。它把過去和將來都變成現在的一部分,它幫我們從深陷其中的地方超脫出來,又把我們和本來距離遙遠的人和事聯系到一起。
加上上文提到的四重時間的關系,形成了嵌套式的影片模式。打開一層還有一層,時空的不斷變化,戲劇時空和電影時空不斷交織,每個角色在凝視其他人的時候,同時也被凝視著,封閉式的結構把各個觀眾鎖在一部影片中。而影片添加的這層敘事關系,在這部典型的布萊希特式的敘事體戲劇中又不顯突兀,魏斯劇本中多層時空的切換敘事放到電影中來也只是多加了一層套子而已。
三、鏡頭語言的敘事性
我們一般看到的戲劇影像資料,為了最大限度地模擬觀眾觀劇時的狀態,通常是用固定的攝影機從觀眾席的角度來記錄劇情,一定程度上來說,攝影機就是觀眾。電影導演必須選定一個特定的攝影角度,他就能規定哪些東西出現在畫面上,他可以隱藏起某些他不愿意顯示或不愿意立刻顯示的東西,他可以突出表現他認為重要的東西,而同時又很可能并不直接表現他們在場面中的重要地位……一種只有把攝影機放在某一特定位置上才能為人看到的東西。讓我們繼續回顧影片《馬拉/薩德》在鏡頭上的處理方式。
(一)鏡頭語言的敘事性
《馬拉/薩德》中的鏡頭運用比一般記錄戲劇的影像豐富得多。攝影機并沒有拘泥于在觀眾席上,它在不斷地變化,時而從觀眾席拍攝,時而進入舞臺中央跟著演員的移動而變化,甚至它還出現了幾個主觀鏡頭,大量考究的構圖,小景深的運用,這都是典型的電影思維。我們來看看第一幕中,夏朗東的開場白部分,布魯克是如何用電影的手段處理的:鏡頭的起始部分是嚴格的居中構圖的電影構圖模式,緊接著鏡頭往后拉,夏朗東往前走,柵欄便顯現出來,鏡頭右移,坐定在妻女旁邊。這一個鏡頭對于銀幕前的觀眾而言,是有一個心理層次的變化的,即:布朗東在開場。到:原來布朗東是在一個被封鎖住的地方念這一段開場白。
(二)布魯克的藝術生涯
真正從事戲劇之前,布魯克學習的是電影制作,除去《馬拉/薩德》之外,布魯克的代表電影作品有《琴聲如訴》(1960),《蠅王》(1960),《告訴我的謊言》(1963),《與奇人相遇》(1968)。當然他最為人知的身份還是戲劇導演,《摩柯婆羅達》《驚奇的山谷》都為世人所稱贊,我們可以看到,創作于1967 年的影片《馬拉/薩德》,在整個創作上都與一般的戲劇影像資料有所區別,典型的電影化的處理方式,明顯的電影化的場景,景別和景深的使用,角度在舞臺上的不停切換,這些都使其成為電影《馬拉/薩德》而非記錄戲劇《馬拉/薩德》的影像。可與此同時,影片又完全符合彼得·布魯克的戲劇思想,無論是空間的處理,還是觀眾與演員之間的“凝視”,甚至是他給觀眾的關于“此時此刻”的幻覺,無一不在引導觀眾往更深的戲劇方向走去。筆者認為,能夠游刃于電影和戲劇之間的《馬拉/薩德》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布魯克的“空的空間”這一創作基礎。
四、總結
眾所周知,戲劇的表演空間雖只有一個舞臺,但如果要涉及到時間和場景的變化,就要分場或是分幕,這個時候需要有背景和道具的變化,讓觀眾的心理空間產生變化,以此來告訴觀眾:“表演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空。”可對布魯克來說這一特性顯得沒那么重要,因為他所追求的便是“空的空間”,一個沒有任何布景的空間,是真正意義上的“唯一的舞臺”。而這種“空”,能夠將觀眾們最大程度地代入戲劇,“一個赤裸裸的空間無法講述任何一個故事,這樣每個觀眾的想象,注意力和思緒都會是自由不拘的。”同樣也是這種空,讓電影所呈現出的空間也只剩下那唯一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