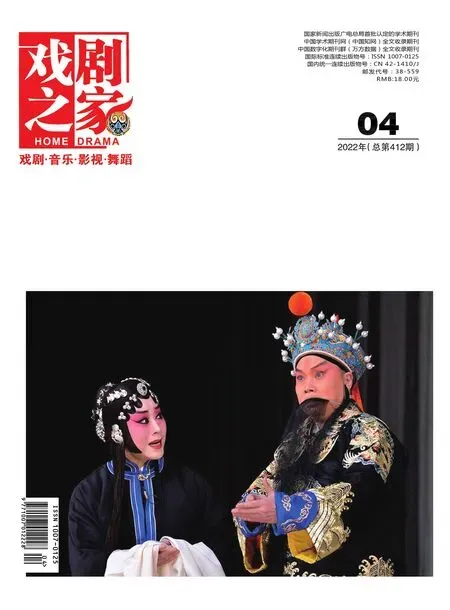從對抗到和解
——談《瑪蒂爾達》的音樂劇改編
彭應翃
(廣州大學 人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音樂劇《瑪蒂爾達》(Matilda the Musical,2010)改編自英國著名作家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1916-1990)的同名幻想小說,由丹尼斯·凱利(Dennis Kelly)編劇、蒂姆·明欽(Tim Minchin)作曲。該劇問世以來好評如潮,收獲多項戲劇大獎。此劇的矚目成就固然與原作的經典性密切相關,但是,劇本的出色改編亦是其廣受好評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達爾的原作出版之后因其對成人世界的偏激態度引起過長時間的爭議。書中“兒童與成人世界的對立和沖突構成了故事發展的重要動因”,年僅5 歲的主人公長期遭受父母——沃姆伍德夫婦(Mr and Mrs Wormwood)——的精神虐待。于是她多次施展聰明才智加以報復。入學后,她更運用超能力懲罰并驅逐了邪惡、殘暴的校長特朗齊布爾小姐(Miss Trunchbull)。故事以沃姆伍德夫婦逃離當地、瑪蒂爾達自愿離開父母、被亨尼小姐(Miss Honey)收養告終。書中主要的成人形象都屬于負面形象,瑪蒂爾達與之激烈交鋒并最終大獲全勝,這說明在敘述者看來,兒童與成人之間的矛盾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正是這種看似偏激的態度令保守主義者認為,《瑪蒂爾達》對成人形象的丑化可能會對兒童讀者的倫理意識產生負面影響。不論這種擔憂是否合理,改編后的音樂劇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令其消除。
一、和解主題與敘事形態
音樂劇《瑪蒂爾達》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情節主線,包括主人公用超能膠和染發劑戲弄沃姆伍德先生、運用超能力趕走特朗齊布爾小姐等。同時,音樂劇也通過對愚蠢暴虐的成人角色的形象化再現,表達了兒童與成人的尖銳沖突。趕走特朗齊布爾小姐之后,一曲合唱Revolting Children(《造反的孩子》)更是強化了原作的對抗主題。不過,在延續反抗意識的同時,改編劇本亦呈現了原作所沒有的和解主題,這一主題主要通過故事構架和關鍵性細節呈現出來。
和解主題首先表現在結局中,音樂劇對原作結局進行了不同的處理。原作中沃姆伍德夫婦因欺詐行為敗露倉皇逃離時,并不情愿帶上他們一向漠視的、只是個“麻煩”的女兒。同樣不愿離開的瑪蒂爾達便順理成章地要求父母放棄對她的撫養權。道別時雙方都未對骨肉分離懷有一絲不舍,沃姆伍德夫婦仍然不能理解也不愿進入女兒的內心世界,瑪蒂爾達亦不能原諒他們多年的冷漠。兒童與成人之間的沖突與隔閡在此處進一步被強化,這是達爾的原著尖銳指出卻并未解決的問題。與之相較,音樂劇的結局并非如此冷酷。同樣是沃姆伍德夫婦轉交瑪蒂爾達的撫養權,很多改編中添加的情節與細節卻暗示了主人公與父母的和解。
首先,音樂劇加入了俄國黑幫向沃姆伍德先生追討其經濟損失的情節。當一群彪形大漢打算對沃姆伍德先生的欺詐行為進行嚴懲時,瑪蒂爾達并未袖手旁觀,而是運用其語言天賦與黑幫頭目斡旋,成功令父親免遭刑罰。原作中瑪蒂爾達對父母的主要情緒是被漠視和粗暴對待后的憤怒,例如被責罵后“她感到自己怒火中燒。她雖然知道怨恨父母是不對的,但她發現很難不如此”。因此她可以快意于他們被捉弄之后的狼狽而不感到絲毫良心上的責備,也不會因他們前途未卜憂心忡忡,更不會因離別而傷心遺憾。所有孩子對父母懷有的正常感情,瑪蒂爾達是明顯缺失的。這種缺失正是兒童與成人彼此對抗這一主題的體現。音樂劇的改編凸顯了瑪蒂爾達盡管對父母有諸多不滿,但出手相救的選擇仍然說明她珍視親情這天然的紐帶。這種珍惜之情雖不能抵消她在親子關系中遭到的挫敗和傷害,卻令其形象更貼近兒童的情感世界,也極大緩解了此前劇情所著重表現的兒童與成人之間的緊張關系。
其次,改編劇本加入的重要細節還包括,得救之后,沃姆伍德先生首次用girl 指稱女兒。在此之前,令瑪蒂爾達深感惱火的是他一直用boy 稱呼她。這一稱呼的改變,是緊接著他在危急關頭被女兒運用從書本中學到的語言成功解救而發生的,意味著他終于開始正視女兒的存在,也第一次隱約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讀書正是父母與瑪蒂爾達之間隔閡與沖突的癥結所在)。所以,在最后的場景中,當沃姆伍德先生嚴肅地詢問亨尼小姐是否愿意收養瑪蒂爾達時,當沃姆伍德先生的帽子終于不再被膠水固定在頭發上時,當瑪蒂爾達主動與父親握手以示感謝時,觀眾可以斷定,雖然針鋒相對的父女倆仍不可能和平相處,但是在內心里,他們已經原諒并接受了彼此。所以,與原作相比,音樂劇更為溫暖的結局,其叛逆性有所減弱,更易于獲得成人觀眾的認可,亦能夠使兒童觀眾在接受過程中避免陷入倫理困境。
二、和解主題的敘事鋪墊
因此,可以認為,音樂劇《瑪蒂爾達》雖沿用了原作兒童與成人的對抗這一情節主線,卻蘊含了二者對抗之后的和解這一原作所沒有的潛在主題。值得注意的是,結尾的和解場景并非毫無預兆地發生,改編劇本進行了不少前情鋪墊,使和解成為順理成章的結果,觀眾欣賞時便不會感到突兀。例如,與原作中時時處在對父母的不滿、憤怒、怨恨等負面情緒中不能自拔的主人公相比,劇本用了不少細節表現瑪蒂爾達對親情的渴望。她對圖書管理員費爾普斯太太(Mrs Phelps)謊稱“我媽媽要我呆在家陪她,她不喜歡我出去,她可想念我了,我爸爸也是,他喜歡我待在身邊,但是我覺得大人還是得有點自己的空間”。對費爾普斯太太的贊揚“你父母一定為有你這樣聰明的女兒感到驕傲”,她也并未予以否認。這些都說明盡管遭到忽視和虐待,瑪蒂爾達在內心里仍然渴望擁有珍愛她、理解她、為她感到驕傲的父母。
此外,在瑪蒂爾達自編的逃生大師和雜技演員的故事里,這對夫婦出于對自己孩子的愛不惜付出生命,他們可以說是瑪蒂爾達心目中理想父母的典范。有論者指出,瑪蒂爾達講述故事時,“其想象的運作方式是將一個場景中的對話和情節在另一個場景中進行重構”。所以,其故事主人公的身份(逃生大師和雜技演員)乃是來自此前一幕中沃姆伍德夫婦的爭吵:
沃姆伍德先生:我是誰?鉆火圈的逃生大師嗎?
(Who am I?A flaming escapologist?)
沃姆伍德太太:如果你是逃生大師,我就是走平衡木的雜技演員,世界上最偉大的雜技演員。
(If you’re an escapologist,I must be an acrobat to balance that lot.The world’s greatest Acrobat.)
從敘事的建構方式看,主人公身份的設定固然與瑪蒂爾達善于利用其接受的語言信息有關,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均來自沃姆伍德夫婦自我指涉的話語,這也暗示了瑪蒂爾達心目中的理想父母是以其父母為原型的,他們在想象中的美好形象實際上寄托了她對自己父母的現實期待。正因為懷有這種期待,她才并未在父親陷入危機時袖手旁觀,也因為懷有這種期待,父親的一聲girl 才會令其摒棄前嫌、伸出和解之手。
三、從對抗到和解:敘事立場的差異
如何看待兒童與成人的關系?從和解主題可見,音樂劇編劇及詞曲作者與原著作者達爾有著不盡一致的觀點。達爾的很多作品——如《女巫》《詹姆斯和大仙桃》《查理和巧克力工廠》等——都著重描寫了自私、懶惰、貪婪的成年人。其中的兒童往往無法獲得來自成人的正面評價、教育或援助,他們只能在不被理解的世界里憑一腔孤勇只身涉險。在《瑪蒂爾達》中,達爾對成人的悲觀看法更達到新的高度。他不僅將全書幾乎所有主要的成人角色設定為反面形象,更在開篇處主人公登場前,以給平庸的孩子寫教師評語的方式挖苦那些對孩子盲目自信的父母。顯然,在敘述者看來,成人缺乏理性的溺愛,必然造成兒童的性格缺陷。這便為全書奠定了針對成人的嘲諷基調。
而音樂劇的開篇雖然在場景和人物的設計上與原作存在暗合之處(如生日會上孩子們的自夸與父母們對孩子的贊美),但是細加分析我們仍然能辨別出其針對成人的與原作截然不同的立場。原作的開篇通過嘲諷受到溺愛的平庸的孩子,強調了成人的愚蠢。而音樂劇的開場曲miracle(《奇跡》)盡管也使用了“媽媽說我是個奇跡,只要看到我,其他都不值一提”“你可以嘲笑我,但這就是事實,從來沒有像我一樣的奇跡”等歌詞表現父母對孩子的寵溺,但此處更為強調的其實是兒童與父母之間親密無間、彼此欣賞的關系,強調父母對孩子無條件的愛和贊美。在接下來的場景中,為沃姆伍德太太接生的醫生唱道:“生活中最常見的便是生命,但每一個新生命都是奇跡。”再次被吟唱的miracle 一詞更指向親子關系的理想模式:對父母來說,每一個新生命意味著新世界的開啟,是應該格外珍視的奇跡;對孩子來說,來自父母的重視與肯定可以賦予其自信、自愛以及直面世界的勇氣。正是miracle 的力量,使孩子們在第一天上學時即使倉皇失措仍然堅強應對,也是miracle 的力量,使孩子們奮起反抗特朗齊布爾小姐的虐待。而這份勇氣、自信、決心,都來自于父母的愛、鼓舞和支持。
因此,可以認為,音樂劇《瑪蒂爾達》的編劇及詞曲作者對成人、對父母、對親子關系均抱有積極的態度,這種與原作者截然不同的立場,賦予瑪蒂爾達這一形象以親情的渴望,從而促成了音樂劇結尾暗含的瑪蒂爾達與父親并未明言的和解。
綜上所述,音樂劇《瑪蒂爾達》在原作情節主線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改編。某些改編,延續了原作的觀念與風格,其目的在于使改編文本更適宜于舞臺表現。而某些改編,其落腳點卻與原作不盡相同,對結局的改動便是其中之一。針對原作中兒童與成人之間單純的對抗主題,通過更為溫馨的結尾場景及細節鋪墊,音樂劇提出了二者從對抗到和解的可能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劇的叛逆性,但是賦予其更為明確的倫理指向,從而收獲更易于被理解并喚起高度認同感的舞臺演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