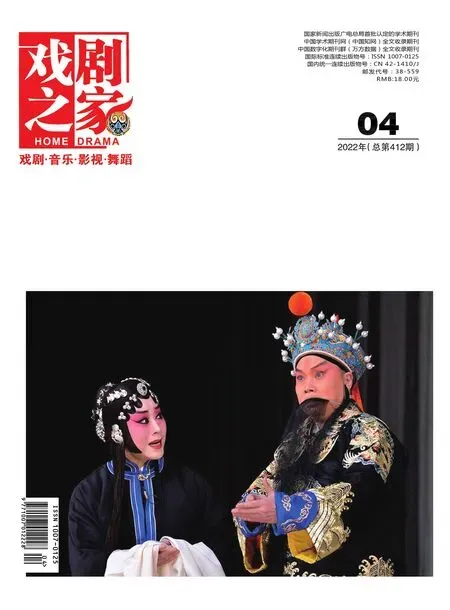文學經典與改編電影的人物塑造差異探析
——以日本經典文學《金閣寺》與電影《火燒金閣寺》為例
史心星
(中國傳媒大學 戲劇影視學院,北京 100000)
電影《火燒金閣寺》改編自三島由紀夫的著名作品《金閣寺》。小說《金閣寺》的原型取自于真實的人物——林養賢。當時他是大谷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也是京都鹿苑寺的僧徒,1950 年他放火燒掉了金閣寺。三島由紀夫將縱火案主角林養賢進行藝術加工構建了自卑敏感的溝口。人物錯綜復雜的心路歷程,寡言的外表下是仇恨與壓抑的欲望。終于,金閣寺的美付之一炬。小說《金閣寺》中多用人物心理描寫,展現溝口內心的自卑、焦慮、敏感等心境,復雜的人生觀下是溝口屈身于世俗的渺小,是對于欲望的渴盼。電影《火燒金閣寺》是否能用影像化的敘事,還原或者是超越原著中異于常人的敏感少年溝口?
一、溝口性格緣起分析:找尋內心“矛盾”的根源
(一)立足于創作背景
1.創作者情感的映射
藝術作品飽含著創作者的情感,不只是藝術作品本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創作者抒發個人情感的載體。《金閣寺》中主人公的作案動機中有對世界的反叛、對金閣之美的恨、也有壯志未酬的憤懣,種種復雜情感交織在一起締造了令世人震驚的縱火案。品讀《金閣寺》可以發現三島由紀夫以縱火案犯人為基調創造出來的溝口,似乎與三島本人有很深的淵源。書中溝口對女性角色充滿敵意,這正是三島本人情感的流露。作者兒時祖母長期臥病在床,請了多名護士和女傭服侍自己又為三島精心選擇了幾名女性玩伴。三島兒時是在女人的包圍下長大,他對女人的恐懼與否定正契合了溝口的人物個性。
比較最終溝口的縱火原因來看,三島筆下的溝口心境更為復雜,而市川昆更突出溝口的反抗精神。小說中溝口看到金閣寺燃起的大火,他終于擺脫了人生的“束縛”——金閣寺。電影中溝口縱火后被警察逮捕審訊,在押解的過程中溝口從火車上跳下。這正是導演個人情感意志的體現,相較于原著溝口更顯悲劇色彩,導演將溝口塑造成“于連式”的社會棄兒。溝口跳下火車是個人在重壓下的反抗,也是市川昆借溝口之舉所展現出的強烈社會批判意識,強化了影片的悲劇色彩。
2.日本的社會背景
武士道是“國民全體的景仰和靈感,雖然平民未能達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終于發展成為島國帝國的民族精神的表現”。武士道精神浸透在大和民族。慷慨赴死、勇敢無畏是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突出的特征,最為悲壯的死亡方式就是剖腹自殺。這是以一種最殘忍的自我“毀滅”方式來實現主體意志的升華,獲得精神上的勝利。小說《金閣寺》和電影《火燒金閣寺》中都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金閣寺為室町時代的代表建筑,周身鑲滿金箔,華麗而雅致,是足利義滿將軍政治權力擴張的標志。金閣寺被溝口所毀滅,這個事件不具有表意功能,有意義的是溝口行為的結果——“毀滅”。如同武士道精神一樣,“毀滅”蘊含著難以言狀的美,只有毀滅才能獲得意志的勝利,獲得再生的可能性。電影與小說中溝口性格的一部分是日本集體無意識的彰顯,蘊含著傳統的武士道精神。
電影《火燒金閣寺》相比小說《金閣寺》更表現日本青年戰后的迷惘,電影中弱化了溝口極度自卑下的心理活動,更多的是立足于外界壓力引起溝口縱火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戰后經濟停滯、社會不安。溝口為代表的青年對于國家、個人的發展處于極度迷茫的狀態。
(二)立足于藝術作品本身
1.生理缺陷構建起溝通屏障
小說《金閣寺》關于主人公性格緣起在開篇已經說明,其性格源于自身生理缺陷,“我(溝口)體弱,無論跑步還是練單杠都輸給人家,再加上天生結巴,我就愈加畏首畏尾。”在他看來“正常人”操縱語言就能打開外界的門,對他而言內心世界只能自己體會。舞鶴海軍機關學校的校友在同學面前暢談著自己的生活,溝口獨自坐在體育場的長凳上,校友因溝口的冷漠而發起疑問:“怎么不回話,你是啞巴嗎?”同學們哄然大笑,在溝口看來這種惡意的嘲笑是殘酷的。這一代表性情節也出現在電影中。小說點明溝口性格形成很大原因是源于身體缺陷,從而缺乏與世界溝通的工具,他人的藐視使自卑感加劇。
三島由紀夫以文字來描繪溝口的內心世界,電影《火燒金閣寺》中導演市川昆將書中情節以視聽方式呈現,電影中溝口坐在警局里將頭深深地埋下,面對警察的訊問他面無表情,仿佛隔絕于世。他的抽離與孤獨感由此顯現。三島由紀夫的語言是純粹而細膩的,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描繪心理感受,小說中除去對事件、景物或是對周圍人物的描述外,多是描寫溝口此時此景下的心理。片中對于人物心理的刻畫遠不及文字來得感同身受,但觀眾也能在導演講述的故事中給予充滿自卑感的少年憐憫。
2.原生家庭是其欲望的萌芽
溝口父親年輕時就已遁入空門,當了偏遠村莊的住持并在當地娶妻生子。小時候因當地沒有合適的學校,溝口背井離鄉被寄養在叔父家,孤獨的心境讓他變得多愁善感,心情會隨著天氣陰晴無常。關于溝口兒時的描寫,小說《金閣寺》中寥寥文字帶過。電影《火燒金閣寺》中沒有刻畫童年時期原生家庭對其敏感自卑性格生成的歷程,著重于溝口來到金閣寺后的經歷。
小說中父親對于金閣帶有一種崇拜感,溝口受父親觀念的影響頗深,只有來到鹿苑寺成為住持接班人,無限接近它參透金閣之美。《火燒金閣寺》中溝口同樣迷戀于金閣,溝口第一次見金閣寺就對它“一見鐘情”。
如果說小說中金閣是觀念美的載體,是主人公人生的羈絆。電影中的金閣則成為主人公性格走向極端化的論證,同樣影片中講述了原生家庭對他的影響,父親、母親熱切期盼他成為寺院的住持。母親變相的壓迫、目睹母親偷情后的恥辱,溝口像一個復仇者燒掉了他崇拜的對象——金閣寺,這正是他極度壓抑后的反抗。
二、溝口對人、物的界定:探尋畸形關系下的迷惘與壓抑
小說《金閣寺》運用“我”(溝口)的視角敘事,電影《火燒金閣寺》則運用全知視角,這種視角對于電影而言更易于觀眾理解。無論哪種視角都蘊含著主人公溝口對周圍人與物的感受。溝口扭曲、黑暗的異化心理下掩埋著迷茫而壓抑的真實個性。
(一)溝口對于人的界定
1.美與丑的判斷
1872年雨果在《克倫威爾序》中提出了“美丑對照原則”。在小說與電影中同樣運用到“美丑對照”,以丑來襯托美。溝口心中“美”的人物代表是:父親、鶴川。父親是溝口人生的引路人,在彌留之際帶溝口拜訪鹿苑寺住持為今后的人生鋪路,當發現母親與遠房親戚偷情時,父親用手掌捂住溝口的眼睛。電影《火燒金閣寺》中將這個場景具象化,父親為保護他的心靈不受污濁,提出帶他去京都的想法。父親的形象在溝口心中是溫暖的存在。鶴川是溝口的朋友,在《火燒金閣寺》中對于鶴川的形象較為模糊,書中溝口對于鶴川的評價帶著少有的輕快明朗之感,他認為鶴川能夠給他帶來幸福。父親、鶴川相繼離世,光明與溫暖從此離他而去,留給他的是善與惡、現實與虛幻等無解的人生命題。
在溝口的心目中“丑”人物是:母親、住持。小說中溝口對母親的情感頗為復雜,一個層面上他認為母親的心靈和外表都是丑陋的,她有著“蓬亂的頭發”“細小而狡猾的洼陷眼睛”。她那撕心裂肺的情感、急功近利的嘴臉讓溝口感到厭惡與恥辱。另一層面上溝口對母親存在某種愛欲,似乎有種“俄狄浦斯”情節的印證。母子倆在儲藏室里談話時,不斷勾起溝口對母親淺黑色乳房的回憶。當帳子下像竹葉摩擦的聲音漣漪式地擴展到整個床的震顫,溝口似乎對母親的偷情是默許的,他在驚恐中“欣賞”。電影中的母親因房屋被毀以寺院幫工的身份與溝口同住在鹿苑寺,母親對偷情的悔恨反而激起觀眾的憐憫。另一個“丑”的人物是道貌岸然的住持,他會施舍乞丐,幫助溝口進入大學。背地里收受賄賂、嫖娼。住持的世俗丑惡感為溝口所不容,他希望和住持共同毀滅來揭露他的偽善。
2.善與惡的對抗
小說中溝口對有為子和柏木的態度頗為復雜。柏木和溝口一樣喜歡離群,也一樣有著生理缺陷。柏木有一雙難看的內翻足,每走一步都像在泥濘中行走。《火燒金閣寺》中柏木的行走以仰拍的方式出現,獨特的視角凸顯艱難傴僂前進的姿態,像是跳著極度夸張的舞蹈。他的殘疾讓溝口找到了共鳴點。柏木雖有殘疾但并未像溝口一樣自卑,他擁有不拘泥于世俗的冒險精神,灑脫的人生觀撼動著畏首畏尾的溝口。但柏木同時善于偽裝又詭計多端,他所擁有的一切來源于精心布局。導演還原了書中極富有代表性的情節,柏木為得到漂亮的富家女假裝從圍欄上摔下來博取同情。柏木會慫恿溝口偷寺院里的花,偶爾的偷盜之事在柏木看來是悖德、瀆圣的快樂。
有為子是溝口年少時期愛慕的對象,在《金閣寺》是第一個出現的女性角色,也是溝口對男女之情認知的源頭。《火燒金閣寺》中缺少有為子這一重要角色。電影中溝口與鶴川在金閣寺一隅看到相鄰寺院里如木偶般精致的女子,在電影里或許女子僅僅只是美的符號。小說中有為子有一張極為標致的臉蛋,她那如鮮花般柔美的身體是溝口夏夜里幻想的對象。當有為子羞辱溝口時,情竇初開的少年感到被世界拋棄。有為子的行為是溝口病態思維的惡化。電影中少了有為子這位善惡并存的少女,也就無法對溝口心中充滿惡意的幻想世界深入刻畫,對于主人公那可憐又可悲的性格塑造也只能流于表面。
(二)溝口對物的態度
唐月梅在《怪異鬼才三島由紀夫傳》中寫道:“三島由紀夫與日本著名的評論家小林秀雄對談時談及自己創作《金閣寺》的動機是:作為藝術家的象征來描寫這個被美的觀念逼得走投無路的男子。”在《金閣寺》中隨著溝口閱歷的增長,他對金閣之美進行著新的闡釋。電影《火燒金閣寺》中,溝口對金閣之美的探索并未上升到哲理意味,對于金閣的情感更接近于人物原型鹿苑寺僧徒林養賢:“我嫉妒金閣寺的美麗。”從影片來看溝口燒毀金閣寺只是在母親偷情、父親去世、住持腐敗、戰后迷茫等重壓下惱羞成怒時所做出的應激反應。或許在溝口心中金閣是世間珍寶,有著無與倫比的貌美,是神圣般的存在。但溝口厭惡金閣之美給“丑陋”的自己造成的壓迫。
小說《金閣寺》中溝口與金閣的關系由和諧統一走向沖突對立。在父親對金閣寺的描述中,溝口開始幻想金閣,并以他希望的樣子出現在腦海。這是主人公移情的過程,將主觀情思寄托于外物“金閣”,想要達到一種“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境地。當溝口見到真正的金閣寺時,金閣寺并不“美”。在溝口心中戰亂會增加金閣寺的悲劇之美,正如王國維所言:“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日本文化里欣賞“物哀”之美,“中世時期的‘物哀’,代表武士階級的審美趣味,集中體現了他們面對戰爭與死亡時勇武悲愴、視死如歸的精神。”《金閣寺》中溝口的求“美”方式與武士相似,采取的都是毀滅。美與悲是相通的,金閣被毀會增加它的悲劇之美。在這一時期兩者的關系處于和諧統一的狀態。但戰爭并未使其毀滅,溝口認為“金閣和我斷絕關系了”“這樣一來,我和金閣共存同一世界的夢想崩潰了”。金閣寺與溝口之間和諧的狀態在不斷瓦解。
三、總結
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金閣寺》是一部晦澀難懂的作品,傳達著三島本人略帶畸形的獨特美學觀。主人公溝口寡言的外表下是陰郁而廣闊的幻想世界,總的來說溝口的人物性格并不討喜。電影《火燒金閣寺》中導演將小說中的經典場景搬上銀幕,配合視聽、演員表演等元素讓溝口這一人物更為生動,塑造了對世界充滿敵意的人物溝口。但對比小說原作,電影《火燒金閣寺》在人物塑造上仍有不足,存在著人物關系松散、主要人物出場過簡等諸多問題。
注釋:
①新渡戶韜造.武士道[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91.
②唐月梅.怪異鬼才三島由紀夫傳[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134.
③王國維.王國維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④雷芳.論《平家物語》中的“物哀”觀[J].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9):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