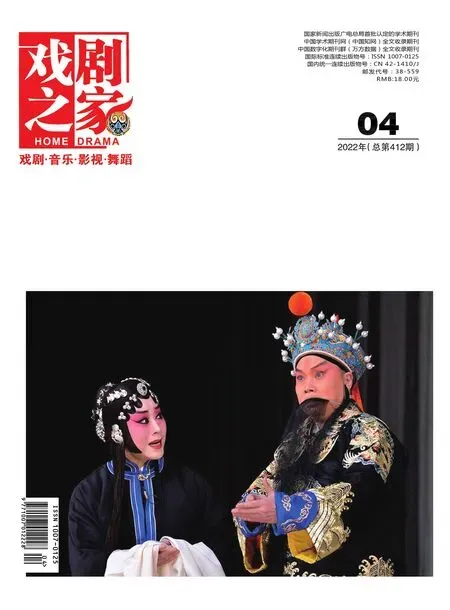倫理學批評視閾下女性形象的對比分析
——以《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一位女士的畫像》為例
董文琪
(吉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隨著女性逐漸進入寫作行列,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女性作家逐漸出現。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喬治·艾略特1860 年出版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形象尚有值得探討之處。通過其筆下的女性形象,我們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覺醒以及自我奉獻。另外,美國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畫像》中的女主人公具有鮮明的特征。本文以《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一位女士的畫像》兩篇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為切入點,以倫理學為依據,探討女性筆下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性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差異,分析女性的主體意識。
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聶珍釗認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價值就在于借助自己的批評術語研究文學。文學倫理學批評有明確的、以倫理選擇為核心的理論體系。這也是它同女性主義批評、生態批評、文化批評等文學思潮和觀念的不同之處。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一種從倫理的立場解讀、分析和闡釋文學作品、研究作家以及與文學有關問題的研究方法,它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倫理的藝術。所以,筆者借用聶珍釗教授的文學倫理學理論,分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一位女士的畫像》中的主人公的不同形象。
一、倫理困境與倫理選擇的定義
(一)倫理困境
在哲學中,倫理困境也被稱為倫理悖論或道德困境,即一個人處于兩種相互沖突的道德要求下,沒有一種要求能壓倒另一種要求。也有人將道德困境定義為,面對某種情況時,每一個可用選擇都是錯誤的。這個詞在日常用語中有更廣泛的意義,用來指心理上的困難選擇或其他類型的困難的道德問題。
(二)倫理選擇
倫理選擇是人類通過自然選擇獲得人的形式之后所要經歷的獲取人的本質的過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人類在完成第一次生物性選擇即自然選擇,獲得人的形式之后,還要經歷第二次選擇即倫理選擇。自然選擇只是從形式上把人同獸區別開來,倫理選擇才真正從本質上把人同獸區別開來。
二、麥琪與伊莎貝爾在不同倫理困境下的不同倫理選擇
在艾略特看來,婦女仍然屬于服從地位。這意味著她們應該把男性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放在首位,甚至不惜壓抑她們自己正常的欲望。她認為女性的要求,無論是心理上的還是生理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認為女性的性格特征是“那種溫柔的、母性的愛”。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我們可以看到,麥琪由于家庭觀念和傳統思想意識的束縛,一直處于愛情上的倫理困境,在這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她無法得到渴望的愛情。麥琪作為一位有智慧的善良女性,她在與菲利普相處時,受到了哥哥湯姆和其他家人的強烈反對。兩個家庭的矛盾使麥琪的感情遭受了挫折。后來,史蒂芬闖入了她的世界,再一次引起了情感上的糾葛。麥琪在這兩段感情中,面對家庭的尊嚴,不得不妥協。當時的女性沒有自由戀愛的權利,不得不向世俗觀念和家庭尊嚴低頭。在一次次的倫理困境中,麥琪都屈從于自己的家庭和傳統并且一味妥協。
反觀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畫像》,涉世未深的美國姑娘伊莎貝爾一心想去古老的歐洲,見識大千世界。伊莎貝爾是一個渴望自由的女性。她不顧周圍親戚和朋友的一再警告和反對,嫁給了奧斯蒙德。由此可見,伊莎貝爾是一個我行我素的女性,她不愿蝸居在狹小的空間,她為了自己的愛情勇于反抗。她是自由的。
在小說《一位女士的畫像》中,伊莎貝爾崇尚美國的自由和獨立,她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長見識。從她先后拒絕了沃伯頓勛爵和格特伍德的求婚這一倫理選擇可以看出,伊莎貝爾既熱愛美國的自由又醉心于歐洲的魅力。她不顧反對嫁給了奧斯蒙德,她認為和一個沒有社會身份的人結合可以保持自身的獨立。從伊莎貝爾的種種選擇可以看出,她是充滿激情,渴望自由和獨立的女性。伊莎貝爾具有女性主體意識,勇于追求自己所愛,不會被教條和傳統束縛。
三、艾略特和詹姆斯筆下女性形象不同的原因
(一)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
喬治·艾略特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其筆下的女性形象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大機器生產開始取代工場手工業,英國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社會關系層面來說,此時英國社會階級出現分化。艾略特筆下的麥琪的家族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犧牲品,而女性也是階級分化的犧牲品。喬治·艾略特筆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傳統性。有學者曾經這樣評價維多利亞時代,“比起不結婚,嫁給一個魔鬼丈夫是個更好的選擇。”女性一直被家庭尊嚴所束縛,一直遵守著家庭的各種陳規陋習。另外,她們大多是壓抑并具有激情的,艾略特主要以性別方式來展現這種壓抑和激情的矛盾性。
亨利·詹姆斯出身于美國紐約一個富裕的家庭。詹姆斯的父親讓孩子們從小就接觸不同的思想并且鼓勵他們對任何事物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童年時期,亨利·詹姆斯多次同家人去歐洲旅行,歐洲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給詹姆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亨利·詹姆斯成人后,除了偶爾回美國探親以外,一直漂泊在歐洲,他在歐洲的親身經歷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同時也為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歐美社會、歐美人,為他反映社會現實的國際主題小說創作奠定了基礎。在《一位女士的畫像中》,其筆下的伊莎貝爾便是一個喜歡見識大千世界的女孩,她一心想要到古老而神秘的歐洲,這反映了兩個大陸之間的文化碰撞。
(二)主人公的成長背景
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的不同組合使文學作品中人物的行為、思想、情感和倫理觀念復雜化、多樣化,從而塑造出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同時也引發不同的倫理沖突,體現不同的倫理價值以及做出不同的倫理選擇。
喬治·艾略特筆下的麥琪處于自我犧牲的狀態下。在書中的那個時代,由于家庭傳統的原因,她不能去上學,也就是說,麥琪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在男權社會下,女性受教育是非常不容易的,這體現了艾略特的女性觀。在感情方面,麥琪淪為兩家恩怨的犧牲品,她沒有選擇愛情的權利。最后,在去救哥哥的這一場景中,麥琪展現了自己的英雄主義色彩,她為了自己的家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人必須經歷通過具體的自我倫理選擇活動獲取人的道德本質的過程。麥琪的倫理選擇是其人性因子的體現。
亨利·詹姆斯描繪了一個鮮明的美國女性形象。伊莎貝爾從小在美國長大,是一個有自信、有激情、浪漫灑脫的女孩。她崇尚美國式的自由與獨立,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體驗生活,增長見識;同時,她又醉心于古老歐洲文化的魅力。她追求更廣闊的天地,充滿了對大千世界的美好幻想。
伊莎貝爾是獨立的,有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能夠承擔自己的選擇的后果。在美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相互碰撞下,這種文化差異使她拒絕了沃伯頓勛爵和格特伍德的求婚。在這種倫理困境下,伊莎貝爾做出了屬于自己的倫理選擇。在別人的反對下,獨立的個性使她堅持己見。她認為,只有嫁給不屬于任何階層的人,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獨立。在處于人生低谷時,伊莎貝爾勇往直前,充滿自信,將美國文化的獨立自由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亨利·詹姆斯筆下的女性更加純真善良,追求獨立,但是最終也會遭人哄騙。其對美麗獨立女性的悲劇報以同情。亨利·詹姆斯筆下的女性形象深深植根于時代背景,也反映了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被鎮壓的狀態。
四、結論
喬治·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均受到女性思潮的影響,其筆下的女性形象各不相同。艾略特筆下的女性是傳統淑女,她們可以做出自我犧牲。其筆下的女性被家庭尊嚴束縛,沒辦法掙脫。這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艾略特的女性觀,體現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反觀亨利·詹姆斯筆下的女性,從她們的倫理困境和倫理選擇中可以看出,她們是自由獨立,堅持自己想法的美國女性形象。這與喬治·艾略特筆下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其處于倫理困境下的倫理選擇自然也不同。然而,兩位作家筆下的女性的結局卻都是悲劇,這體現了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的不易以及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反抗必會遭受壓迫的現實。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也不乏像伊莎貝爾一樣獨立自由,富有主見的女性,她們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這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今女性的生存狀況以及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