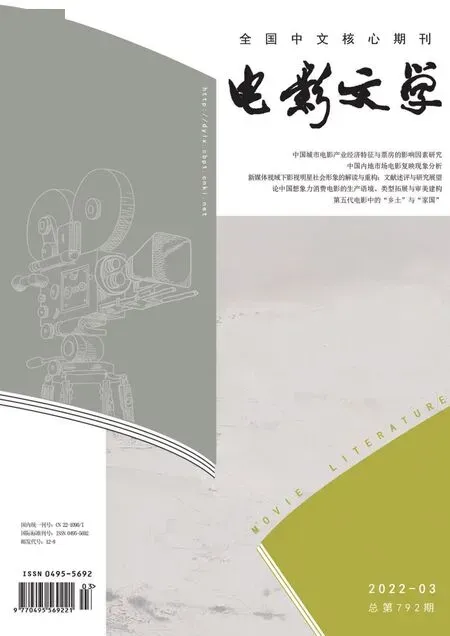詩意與紀實:藝術電影的回歸(1979—1984)
任泓璇
(忻州師范學院,山西 忻州 034000)
一、什么是藝術電影
藝術電影的歷史幾乎和電影史一樣久遠,它作為術語出現是在1908年。“藝術電影”原本是法國一家制片公司的名字,由法國銀行家皮埃爾和保羅·拉斐特兄弟創辦,初衷是為了給當時制作粗糙、“內容低俗”的電影提升品質,也是試圖給電影這門新興娛樂業一個藝術的身份。兩位制片人特意聘請著名戲劇家亨利·拉夫寫作劇本,雇用法蘭西喜劇院的著名演員擔任主要角色,聘請一流作曲家為電影放映時演奏音樂。這樣專門為上流社會制作的具有藝術趣味的影片《吉斯公爵的被刺》在1908年與法國上流人士見面。但影片并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公司也在虧損的情況下黯然破產。于是藝術電影就與“不賣座”“非主流”“高雅”“非商業性”掛鉤。雖然藝術電影在當時還未成氣候,但電影是一門藝術的事實在后來被印證,藝術電影身上的標簽也在時代的推進中越來越深刻。20世紀20年代是世界電影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電影界的先鋒潮流席卷世界,法國的印象派電影、德國的表現主義電影、蘇聯的蒙太奇學派,還有未來主義電影、達達主義電影、超現實主義電影、純電影、抽象電影等不同流派的電影百花齊放。這是藝術電影與好萊塢影片的抗爭,是試圖擺脫文學、戲劇的影響,充分探索電影形式的實驗,是充分表現導演個人理想和主觀感受的表現,是電影充分發揮藝術特性的盛宴。這一時代的藝術電影專指那些形式新穎、觀念超前、技巧豐富、理想主義的影片,當然一些商業影片也在形式上吸收藝術電影的特性,使視聽更加豐富。二戰之后,在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藝術電影回歸,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美國獨立電影、法國電影新浪潮,還包括一些紀錄電影成為主流形式。這一時期的藝術電影通常指嚴肅、非商業性、觀念突破、制作簡單的影片。時至今日,藝術電影這一名稱的應用非常廣泛,在美國,該詞匯包括外語(非英語)作者電影、獨立電影、實驗電影、紀錄片和短片。“藝術電影占據著不同于一般商業片的經濟和文化空間,這種觀念幾乎跟電影本身的歷史一樣久遠。制作出藝術質量超群(或者具有一定獨特性)的影片,這既是制片人和企業家的商業策略,也是導演的美學追求——盡管他們雙方常常在付出一定代價后發現,這兩個目標并非總能一致。”藝術電影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接受各自文化和實踐的重塑,帶有一種民族和本土的特征。我們總將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進行對立批評,但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二者并非對立關系,實則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如果沒有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先鋒派的探索,就不會有美國好萊塢有聲電影初期(1930—1945年)的黃金時代。甚至此后的好萊塢也與法國以及歐洲電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中國藝術電影歷史
20世紀80年代早期關于電影理論的大討論推動了電影觀念的轉變,以《丟掉戲劇的拐棍》以及《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兩篇文章為濫觴之作。中國電影從“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邁向了現實主義道路,從傳統電影走到現代電影,與世界電影觀念“合流”。創作領域方面,代表影片有《小花》《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歸心似箭》《巴山夜雨》《天云山傳奇》《春雨瀟瀟》等。形式上,長鏡頭、變焦鏡頭,自然光線,實景拍攝。內容上,這些形式手段都旨在傳達一種生活詩意,時間就是在散漫的生活中流逝。
1985年開始,中國民族電影時代到來,同時也是中國藝術電影的時代,更是中國現代電影的時代。藝術電影是這一時期的主流,雖然在市場上這種類型的電影并未獲得認可,但是他們的探索,為中國電影的道路提供了可行的選擇。《黃土地》《獵場扎撒》《盜馬賊》《孩子王》《紅高粱》等影片是影像美學表達潮流的代表作。比上個時期,第五代導演的思考深度更廣闊。紀實是表達的基礎手段,其目的是為了關照民族文化、人性的復雜、社會的哲學深度。形式上,長鏡頭、變焦鏡頭、實景拍攝等是影片的基本要素,畫面成為主人公。內容上,關注文化反思和哲理思考是這一時期電影的明顯特征。
1993年電影市場化改革后,一批新生代導演的大多數作品雖然在國外獲獎無數,但在國內卻被稱為“小眾”,不被主流認可。比如,張元的《媽媽》《北京雜種》《過年回家》,賈樟柯的《小武》等。似乎藝術電影從關照民族和反思重新回到了關照個人和社會方面,這些導演關注現代工業社會中,人的焦慮、局促、難以融入環境的狀態。他們通常與社會格格不入,有些是不屑與社會合流,有些是試圖進入社會,但結果總是被排斥。
千禧年后,“后五代”導演,包括霍建起、顧長衛、侯詠、呂樂等,原本是第五代導演的攝影師或者美工師,紛紛轉行當起了導演。比如,《那山 那人 那狗》《立春》,表現導演對故鄉的懷念,對往昔歲月的感傷,對人生際遇的淡淡憂愁,體現了淡淡的抒情化表達。第六代導演的極端個人化表達開始有所收縮。關注現實與社會對個人的沖擊,關注情感和情緒依舊是他們不變的追求。《世界》《二十四城記》《天注定》《三峽好人》《十七歲的單車》《卡拉是條狗》《可可西里》《尋槍》等。姜文導演的作品在個人化表達上與其他創作者截然不同。《太陽照常升起》《一步之遙》。在商業化模式與藝術追求上試圖探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少數民族題材的藝術電影嶄露頭角。萬瑪才旦《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氣球》,李睿珺《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或是展現當代生活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沖擊,或是深入少數民族腹地探索民族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南方車站的聚會》,畢贛導演的《路邊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胡波導演的《大象席地而坐》,楊超導演的《長江圖》,邢健導演的《冬》,程耳導演的《羅曼蒂克消亡史》《邊境風云》都極具個人化的姿態,展現的是導演自身的經歷或是對人生、社會的思考。形式上各有特色,形成獨具個人化的表達。藝術電影開始表現“作者”的意味。
三、中國藝術電影的復蘇
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意義非凡的一年,這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年。中國電影的新篇章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觀念和意識形態下推動開來。彼時的電影界出現兩種理論方向,一是對過往傳統電影理論的豐富補充和完善,另一種是學習西方的現代電影理論,并引入中國,與中國本土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電影理論。李佗、張暖忻為代表的電影學家引領了中國電影語言現代化討論,二人合作發表在《電影藝術》上的文章《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是中國電影觀念轉變的理論依據。彼時,“電影語言”并非電影符號學的概念,因為當時還未引進符號學學說理論,這里的“電影語言”是指電影創作技巧,與當時電影界長期信奉的傳統電影觀念相悖,傳統電影觀念認為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不可分割,脫離嚴肅的內容而談形式是錯誤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能夠提出對電影形式的探索,無疑是一種進步,也是填補多年來中國電影對電影本體探索的空白。除了提出要積極探索電影形式的要求外,中國電影理論界還提出“丟掉戲劇的拐棍”以及“電影與戲劇離婚”的要求。這是從內容上要求中國電影減少對文學和戲劇的依賴,本質上也是對電影形式加強探索的表現。關于電影形式的探索,從1979年持續到1985年。這6年間,中國電影呈現出與前人不同的姿態,“紀實美學”是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的概括性思想特征,也是中國藝術電影的代名詞。代表性影片有:張錚導演的《小花》,滕文驥、吳天明導演的《生活的顫音》《苦惱人的笑》,丁蔭楠、胡柄榴導演的《春雨瀟瀟》,王炎導演的《從奴隸到將軍》,李俊導演的《歸心似箭》,吳永剛總導演、吳貽弓導演的《巴山夜雨》,謝鐵驪導演的《今夜星光燦爛》,謝晉導演的《天云山傳奇》,張暖忻導演的《沙鷗》《青春祭》,鄭洞天導演的《鄰居》,吳貽弓導演的《城南舊事》,胡柄榴導演的《鄉音》,凌子風導演的《邊城》,郭寶昌導演的《霧界》,等等。
以影片《沙鷗》為例,探討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中國藝術電影的特征。張暖忻導演的《沙鷗》講述一個女排運動員經歷了事業失利,愛人犧牲后逐步走出陰霾,重新奮發的精神歷程。從影片的內容和主題來看,導演張暖忻在闡述中已經說明“我們通過運動員的競賽生涯寫人生,寫時代,寫我們對于生命意義的思索和對當代中國青年精神風貌的探求”。中國人被封建禮教的自謙、溫良謙恭的道德觀念束縛已久,競爭精神、拼搏精神、民族斗志被禮教消磨已久,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抱有奮斗精神的人們被斗爭打擊甚至迫害。十年動亂后,這批人被解救出來,國家也重新煥發新的生機,影片就是要為奮斗精神大唱贊歌,讓中國在新時代重煥生機,讓每一個人都能在自己的事業中取得成就。這是影片最核心的理念,有那個時代獨特的反思文化和反思歷史的精神。選取女排作為重點表現對象,能在最大限度上凸顯導演創作思想,女排姑娘們在奮斗拼搏的精神上最為大眾熟知和敬佩。
從形式上來看,秉承著“紀實美學”的理念。中國“紀實美學”受到了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和德國理論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的影響。它的基本追求是“真實”,也就是再現物質世界時間和空間的真實,手段是長鏡頭或者景深鏡頭,以單個鏡頭的空間真實構成整部影片的真實。巴贊的攝影影像本體論和克拉考爾的電影與攝影的近親性兩方面為理論基礎。《沙鷗》為了實現紀實風格,在攝影方面采取了幾項措施,包括實景拍攝,甚至有些場景需要偷拍和搶拍。多用移動攝影,讓人物和攝影機動起來,擺脫傳統的固定不動的形式,打破舞臺感。運動加入構圖,在運動中形成動態構圖,電影不是繪畫,電影是動的藝術,在動態中尋找角度,瞬間完成美感的構圖。采用自然光拍攝。影片色調力求自然、樸素、深沉。主角由非職業演員扮演,突出體現演員的本色,做到真實自然不做作。以影片中女主角在圓明園回憶的那場戲為例,共有26個鏡頭,近6分鐘時間,導演安排沙鷗從失去男友后的悲痛心情,到思考生命的意義,再到重拾對排球的信心。按照內容看,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沙鷗回憶曾經和男友觀看圓明園石頭的經歷,第二部分是重拾信心。攝影機多是跟拍,且全部是運動鏡頭。沙鷗來到破敗的圓明園石頭前,鏡頭影像出現沙鷗和男友曾經甜蜜約會的記憶,同時頻繁傳來男友的聲音,“能燒的都燒了,就剩下這些石頭”。男友雖然永遠離開了她,但是曾經的聲音還保留在記憶中,圓明園的石頭經歷了亂世后,以破碎的姿態依然存在,留給世人警醒。這一蒙太奇場景,讓沙鷗從雙重失意中開始認清現實,自己失去了愛人,也暫時失去了對排球的熱情,自己最在意的東西都失去了,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再擊垮她,為什么不試圖振奮自己,把握自己現存的最熱愛的東西。從圓明園碎石到出園的路上,兩旁楓葉正紅,陽光正好,行人匆匆,一切如舊,同期聲響起沙鷗曾經打排球時的快樂和心酸,她不再流淚了,她終于醒悟,自己當下最要緊的事是振作起來,練好排球,為打贏比賽而奮斗拼搏,為自己的人生勇攀高峰。